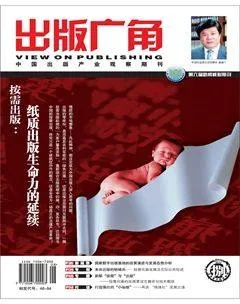论中国图画书的前身后世
2012-12-29 00:00:00沈利娜
出版广角 2012年8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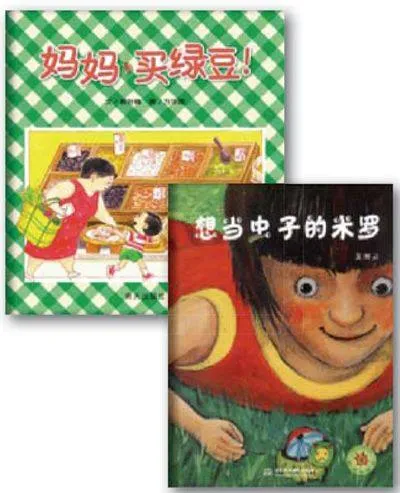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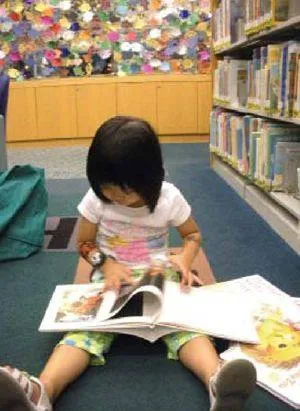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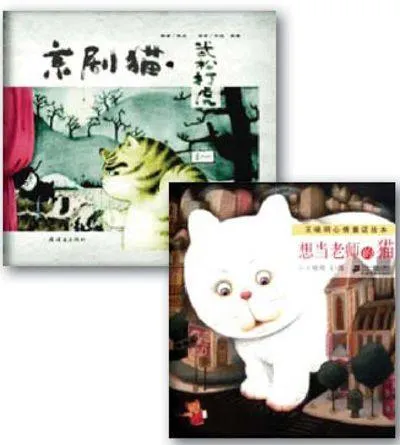
儿童插画的优秀并不代表图画书的繁荣,中国原创图画书并未因插画的优秀而渐入佳境,中国图画书仍然处于启蒙阶段,其“走出去”缺少特色和力量。
2012年4月英国伦敦书展,中国是市场焦点主宾国,据说影响不亚于2009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书展期间,中国当代儿童插画展和中国绘本图书展在大英博物馆举行,引起了英国读者和同行的特别关注。英国插画界的朋友说,中国当代绘画能够在大英博物馆展出,非常不容易,他们自己根本想都不敢想。英国老牌的《卫报》以整版篇幅介绍了来自中国的儿童插画,中央电视台《朝闻天下》节目则专题报道了这次展览。一场由中英双方插画家参加的中国儿童插画论坛在伦敦书展举行,只有50多个座位的会议室挤进了100多人,成为中国主宾国活动中最热闹的一场论坛。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主席,英国最著名的插画家安东尼·布郎和中国插画家在大英博物馆会聚一堂,英国插画同行对中国的儿童插画赞美有加。但儿童插画的优秀并不代表图画书的繁荣,中国原创图画书并未因插画的优秀而渐入佳境,中国图画书仍然处于启蒙阶段。日本人说,中国动漫绘画水平已经不逊于日本,动漫未来一定在中国,可是中国动漫仍也和中国图画书一样,看似热闹,却始终不见未来。
是绘本还是图画书
我们知道“绘本”是图画书的时尚说法,也被认为是未来最有市场潜力的图书,但很少有人知道“绘本”是日语借词。也许我们从骨子里对日语词有某种成见,但是根据汉语的用词习惯,在表意功能相近的情况下,三音节词往往争不过双音节词。效率优先是词汇学的一条重要法则。查一下各大图书网站,除了当当网、亚马逊、京东商城、博库书城、淘宝网,无一不称儿童图画书为绘本。不过,现代意义的图画书毕竟最早产生于欧美,也不管未来“绘本”的用法最后可能在市场中胜出,本文还是坚持把“绘本”称作图画书。
20世纪连环画风行中国大陆,那个年代的连环画热比现在的日本漫画有过之而无不及,印数动辄几十上百万册。20世纪80年代末,以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为代表的名著连环画热则被认为是连环画的回光返照。连环画时代已过去,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图画书持续升温,新华书店的图画书柜台数量成倍增加。
连环画与图画书并没有血缘关系。图画书由英语词汇“picture books”翻译而来,最早出现在欧美,1902年英国的比阿特丽克斯·波特(Beatrix Potter)的《兔子彼得的故事》(The Tale of Peter Rabbit)被视为现代图画书的开山之作。图画书区别于连环画、漫画主要有两点:一是以手绘为主,一般不用电脑制作,插画本身就是精美的艺术品,在画家身家以百万、千万计的年代,愿意创作几百元图画书插画的名家凤毛麟角;二是重在以图说话,文字较少,或干脆不配文字。日本现代绘本之父松居直先生在《我的图画书论》中指出,图画书中图画与文字的关系并非是简单相加的关系,而是相乘的关系,图文的融合是图画书的灵魂。一直以来,关于图画书的图文关系有多种观点,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图画在图画书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图画甚至起着讲故事的最主要作用。图画书最大的特点是画面是重要的叙事元素,是另一种文字。
目前,国际上有许多专业的图画书奖,如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奖、美国的凯迪克图画书奖(The Caldecott Medal)、英语的凯特·格林纳威大奖(Kate Greenaway Medal)等图画书奖,这些都是国际图画书市场的指向标,也标志着欧美的图画书已经非常成熟与完善。可以相信,欧美图画书阅读传统会更快速地传递给正在启蒙的中国图画书市场。
图画书承载民族未来
图画书是童书市场皇冠上的明珠,这是因为图画书对低幼儿童启蒙教育的不可取代。萝西·怀特在《关于孩子们的书》一书中说,图画书是孩子在人生道路上最初见到的书,是人在漫长的读书生涯中所读到的最重要的书。一个孩子从图画书中体会到多少快乐,将决定他一生是否喜欢读书。
图画书是儿童文学和儿童绘画艺术的结合体。有人说中国历史上没有儿童文学,也有人说中国儿童文学古已有之,古代的歌谣、传说、神话就是儿童文学。但此论偏偏就不懂事物的质和量的辩证关系,没有量,也就无所谓质。现代图书市场,儿童读物占13%~15%的份额,各国大同小异。神话、传说与成千上万的古代戏曲、话本、小说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即便像《聊斋志异》等儿童勉强能够接受的故事,严格来说也应该界定为成人文学。中国古代几乎没有儿童文学作家,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中国儿童文学先天不足,也是中国图画书的先天不足。
中国历史上没有儿童文学,是因为历史上从来都把孩子当成大人教育,孩子刚识字就读四书五经。周作人最早“发现”儿童,肯定儿童作为个体的独立性,并实践自己关于儿童文学的理念,进行儿童文学创作。他在1913年发表的《儿童研究导言》中说:“盖儿童者,大人之胚体,而非大人之缩形……世俗不察,对于儿童久多误解,以为小儿者大人之具体而微者也……”
中国历史上更没有儿童美育。中国的儿童美育由蔡元培最早提出。他所说的美育“不仅包括音乐、文学等,而且自然现象、名人名言、都市建设、社会文化,凡合于美学的条件而足以感人的,都包括在内……”图画,特别是优美的图画,对于儿童不但是认识物质世界的第一个窗口,更是最有效的美育启蒙。当越来越多的家长认识到屏幕对儿童身体和视力的不良影响,纸质的图画书也由此会日益受到重视。没有文字阅读能力,又不让看电视的儿童,图画书就是他们唯一的智育、德育和美育的源泉。有文章说,在发达国家,图画书就是低幼读物的代名词,图书馆少儿书架上摆放的大多数都是图画书。出于健康的原因,几乎所有的家长都在阻止儿童看电视,包括各种阅读器,所以,纸质图书唯独儿童图书顶住了数字化的洪流。2011年,英国纸质图书下跌6%,但儿童图书只下跌了0.7%。
对于不识字的低幼儿童,图画是他们阅读的“文字”,而图画相对文字更具体形象,更具有艺术的灵动,也更具有想象的空间。质量上乘的儿童图画书不仅有精美的图画,也有有趣的故事,在趣味性阅读的引导下也能从小培养孩子对阅读的爱好,更为重要的是让他们从小获得审美体验,培养独立的审美判断能力,能够发现美、创造美。美国彼得·史比尔的《下雨天》是一本无字图画书,但却深深唤起了笔者这个成年人对儿童时代雨天的记忆——快乐的记忆。作者用儿童的眼睛非常细腻地发现雨天的种种乐趣,蜘蛛网上晶莹的小水珠、雨水顺势而下流入下水道、故意用力踩踏溅起水坑里的积水、下水管里喷涌而出的雨水、反过雨伞来积蓄雨水……整本图画书洋溢着一种发现雨中嬉戏的快乐,甚至具有一种召唤的力量,使你想去体验这种乐趣。这样的图画书将直接唤起儿童对于生活的热情体验,引导他们去发现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成为一个独具性灵的、充满生气的人。
鉴于图画书无可替代的智、美、德育功能,中国的图画书热首先从都市小资父母开始。在当当网和亚马逊上,定价二三十元的精装欧美、日韩图画书一直热销,网购几乎成了精装图画书的唯一销售平台。当然,收入的提高和物价的上涨也在推动奢侈的精装图画书步入寻常百姓家庭。因此,我们更多的是从儿童美育的视角来确定图画书可以和一个民族的未来相关联。我们可以说,图画书和中国每年占城市垃圾总量30%~40%的建筑垃圾有关。外国人评论中国只有建筑,而没有艺术。中国建筑平均寿命只有35年,而英国的建筑平均寿命是132年。中国瓷器的价格不及日韩的几分之一,服装、家具、诸多日用品在国际市场上沦为地摊货,很大的原因都是设计上艺术性的缺失。有一位伟人说过,只有对美有着敏感体认的人才能成为情感丰富,富有同情心、创造力的人。因而,对于儿童的教育回到周作人的理念上,从小培养其对美的感知能力,图画书责无旁贷。
童年时代的中国图画书
从连环画到图画书,中国图画书才走过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相对于西方图画书的百年历史,中国图画书还在童年。
图画书是从书籍的插图发展而来的,早在公元9世纪,中国的印刷书籍中就已经有了插图,而西方要到15世纪才有这种形式的书籍。黄可先生在《中国儿童美术史摭拾》中提出:“不敢断言《日记故事》(明代嘉靖二十一年)就是世界上最早有插图的儿童书籍,但可以说明我们民族在古代对儿童读物的插图已甚为重视。”这也足以见证图画作为儿童早期阅读的一种形式在中西方的认知中是同样重要的。可惜的是中国始终没有形成图画书这一类型的图书,直到20世纪20年代周作人“发现儿童”观点的提出,中国知识界才开始对儿童文学的关注。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西方的图画书概念开始影响中国儿童文学。中国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引进图画书,陈伯吹先生于1928年就翻译了美国第一本现代意义的图画书——温达·盖格的《百万只猫》。这本图画书在美国1928年出版发行,我国于同年就翻译出版了。但是,我国对图画书的概念定位却始终没有清晰,对图画书中的图文关系认识也比较模糊。
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已经有了原创的图画书。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是当时唯一的两家专业少儿出版社之一,在五六十年代基本上每年都有图画书出版,但是年出版的量非常小。以1950年到1966年为例,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年出书量最高只有34种,始终没有形成规模。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出版界始终没有形成图画书这一类型的图书。20世纪80年代后期,连环画式微,并逐渐退出图书市场,而图画书在20世纪末却得到了发展。21世纪初,大量外版图画书被引进,同时原创图画书的声音也不断高涨。2006 年开始刊行的《超级宝宝》作为中国第一本原创图画书杂志,就是以挖掘和介绍中国文化为宗旨的图画书期刊。近几年来原创图画书不断增加,形成了一批优秀的图画书画家,同时也创立了自己的图画书大奖——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信宜图画书奖,这些奖项对于推动中国原创图画书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不仅对图画书作者进行肯定与表彰,而且也有效刺激了图画书概念的推广与传播。就出版社角度而言,明天出版社、中国少年新闻出版总社、湖北少儿出版社、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等出版社暂时成为图画书的主力军,在业内和读者中有一定的影响。在民营工作室和出版公司中,也出现了信谊图画书、蒲蒲兰绘本、聪明豆系列、蒲公英绘本馆等品牌。
不过,总体来看,童年时代的中国图画书市场仍然格局混沌,群龙无首,专业特色尚不清晰。由于图画书大部分在网上销售,因此,一般大书店都难以看到中国原创图画书的总体阵容。因4月份在大英博物馆举办中国儿童插画展和中国绘本图书展之需,笔者在当当网、亚马逊和博库书城三家网上书店进行了拉网式的搜寻,历经千辛万苦,笔者才选购到国内40余家出版社的300多种中国原创图画书(包含台湾地区)。之所以只有300多种,是因为我们在网上订购了近千种图画书后,最后只能勉强选出300多种我们认为还可以拿到英国去展览。从这300多种图画书中也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原创绘本图书的基本格局。其中,中国少年新闻出版总社40种,量大但品质并不都上乘;明天出版社30种,以精装为主,《团圆》等图画书都获得过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信谊图画书奖,质量相对较高;湖北少儿出版社25种,以杨红樱作品改编为主;新蕾出版社33种,以神话、民间故事为主;二十一世纪出版社8种,周翔的《荷花镇的早市》是代表作;海燕出版社28种,《蔷薇别墅的小老鼠》等非常优质;贵州人民出版社虽然只有7种,但均为台湾插画家童嘉及熊亮的作品;江西科技出版社的9种图画书主要改编鲁迅、朱自清、丰子恺等名家作品;新时代出版社的10种图画书以熊亮的绘本为主;中国福利出版社10种,《逃跑的铁桶》等图画书故事相对新颖。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内绘本图书基本上群龙无首,良莠不齐,总体品位与欧美相去甚远。
和韩国图画书的发展过程相似,中国目前的图画书引进和原创数量悬殊。据2012年2月16日当当网的数据统计,当当网可供精装图画书中国原创87种,欧美800种,日韩228种,原创与引进版的比例是1︰14;平装图画书中国原创1574种,欧美1785种,日韩338种,原创与引进版的比例是7︰10;可供的精装本与平装本图画书的比例为1︰4。精装本图画书一般定价在20元~30元人民币之间,相对于平装本图画书,无论是绘画还是故事都更上乘一些,而且国产原创图画书大部分以平装本出版,可见原创图画书的“低人一等”。由于购买力的原因,精装图画书市场显然还处于培育阶段。几十万字的图书在中国定价也不过二三十元,而薄薄几十页、几百字的一本图画书却也要这个价格,实在让一些家长无法接受。也许我们可以原谅这些家长们本末倒置,不理解图画书之所以是图画书,其核心价值就是图画,而不是文字,但这需要一个过程。
在韩国,图画书的童年时代也大多以引进欧美图画书为主。2004年前后,韩国市场上流通的图画书翻译作品的比重达95%。安东尼·布朗、约翰·伯林罕、可劳德、雷蒙德·布里格斯等知名度高的外国作家的图画书一出版就跟着翻译。90年代,韩国出版界多数人认为图画书并不好卖,但现在,韩国已经进入了图画书100万时代。《再见,月亮》《狗狗的屎》《是谁嗯嗯在我的头上?》《首先有一个苹果》《我们要去猎熊》等一批图画书的销量都达到50万~100万册。可以预见,中国图画书也会从今天的童年进入明天的成年。
中国图画书的明天
那么,中国原创图画书发展的症结何在?中国原创图画书的明天又在哪里?
首先是故事上的差距。图画书虽然重在图画,但故事也是关键。特别是中国的图画书,可能最主要的还是故事不行。中国的作者往往站在高处俯视孩子,没有把自己当作孩子来思考问题、发现世界,说教意味浓重。英国知名的图画书创作者、两次凯特·格林纳威奖的获得者约翰·柏林罕的图画书《和甘伯伯去兜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甘伯伯带领着一群“孩子”乘车去兜风,突然大雨倾盆,车子在泥地上快跑不动了,甘伯伯建议谁下车推一把,车上的鸡、猪、男孩、女孩都不愿意下去推车,但甘伯伯不动声色,不批评也不指令。终于车子再也跑不动了,这群“孩子”都乖乖下去推车子了。中国的成人总是不忘教导的责任,永远俯视着孩子,而柏林罕的图画书则是站在孩子的立场告诉大人们,孩子们在面对真正的困难时是会自觉地团结起来,家长们有时候不需要那么心急地去批评孩子。
低劣的改编是另一个通病。中国图画书的文字作者往往随手拿来一个传统故事或者名家作品进行改编,改编占了中国原创图画书的很大比例,这些改编图画书往往缺少童趣、缺少生气,“老气横秋”者居多。而这些传统故事注重的是知识性、道德教育,绝非周作人所谓的真正的“儿童文学”。例如把元杂剧《窦娥冤》改编成图画书,对于低幼儿童是不是一个过于沉重的故事呢?只要从孩子的视角出发,讲出充满童趣的故事,我们就能创作出优秀的图画书来。中国原创图画书真正缺少的是好的故事,缺少的是充分尊重儿童自由价值的故事。中国插画家江健文认为,在绘制技术及用材上,中英儿童插画家并没有什么区别。但在插画创作和题材上,英国画家往往更关注生活中的小事,将个人和家庭的生活状态作为题材写入绘本,注重个性的表达和人性的张扬。比如这次中西儿童插画论坛上,约翰·伯林罕的一个图画书就是描写自己的妻子生产宝宝数小时间发生的故事。这样的题材对于中国儿童插画家来说可能是难以想象的。相对于英国插画家对插画题材的主导性,中国画家目前还是以出版社已拟就的文字脚本定单绘制图画的形式较普遍,题材以经典性文学为主,过分注重教育功能。
其次是图文一体问题。欧美的优秀图画书很多都是图文出自一人之手,以英国图画书为例,安东尼·布朗、约翰·柏林罕、埃米莉·格雷维特等人的作品均是出自一人之手,他们有非常明确的图画书创作理念,因而图文往往相得益彰,故事也贴近儿童的心理。我们这次赴英参展选取的300多种画书中只有20种图书是作者图文一体的,它们是:陈致远的《小鱼散步》《阿迪和朱莉》、周翔的《荷花镇的早市》、陈菊香的《门》、吴湘云的《想当虫子的米罗》、童嘉的《图书馆的秘密》《我怎么没看见》《想要不一样》、熊亮的《小石狮》《好玩的汉子》《京剧猫》《金刚师》《梅雨怪》《泥将军》《看不见的马》《丘比特访谈录》、邓正祺的《葡萄》、吕江的《爸爸去上班》、钱茵的《芽芽搬新家》、王晓明的《爱忘事的熊爷爷》《想当老师的猫》《吓人的抢》《大梦先生》、姚红的《迷戏》。这些图文一体的作品大部分成为中国原创图画书中的佳作,甚至是最高水平。
在伦敦书展的中西儿童插画论坛上,英国著名插画家约翰·柏林罕的一席话特别引人深思。他说儿童插画创作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没有文字增加了图画表现的难度,创作中最不好把握的是文字和画面之间的关系,他最不喜欢在插画中重复文字里已有的东西。目前我国许多原创图画书存在文字过多的现象,原因在于我们的图画没有很好地起到叙事的功能。欧美图画书的一大特点是非常精细,非常注重对细节的描绘,以细节代替情节,犹如早先的默片。所以,他们能够创作出很多有趣的无字图画书,而目前国内几乎很难找到原创无字图画书。相对于欧美图画书的精细,国内原创图画书的创作者似乎没有清醒地认识到图画的真正意义,图画更多地成了文字的附庸,这对图画书的概念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理解。虽然图画可以承载很多信息,但是对于对话、心理活动等来说,图画却显得有点无力,这时文字就要承担起这部分叙事的功能,如此图文才能达到最为有效的融合。伯林罕的话道出了图画书创作中最为关键的一点,这也是为什么图文均出自一人之手的作品往往能够成为佳作的一大原因。
再次是绘画艺术上的差距。中国儿童插画作为中国当代绘画艺术的一个分支,与中国传统绘画有着明显的区别。中国当代儿童插画呈现出具象派艺术与抽象派艺术的结合,水墨与水彩的共用,真实与虚构的结合等特征,插图画家们将各种艺术元素进行融合,呈现出丰富多样的绘画技巧。近年来,中国当代儿童插画展曾在德国、希腊、西班牙等国展出,受到各国艺术家和读者的热烈欢迎和普遍关注,许多人都说中国动画和插画在绘画技术上不逊于欧美。但从我们所见的现有作品上看,能够符合以上说法的图画书还是太少。我们不知道是画家不够用心,还是优秀的画家仍然太少。
从一个艺术外行的读者眼光来看,中国儿童插画主要有两个缺点:一是粗放而不注意细节。儿童插画既是美育的教材,也是知识读物。不识字的儿童要从插画中了解世界,就需要这些插画足够精细,如同一座房子,要精细到每一块砖和每一个门环,甚至门上的每颗钉子。这也是中国动画的通病,或者说是中国制造的通病。在德国,做一分钟动画的报价是1万欧元,我们则通常只有两三千元人民币,所花的功夫不言而喻。二是形式上一味模仿欧美风格而不注重挖掘民族特色。中国的水墨画、民族纹饰图案以及色彩的应用在现代中国图画书中并不突出,使中国图画书“走出去”缺少特色和力量。熊亮的绘本是输出海外版权最多的,他的作品符合我们主张的三个要点:一是反映中国民俗传统,二是精于工笔和细节,三是图文作者合一。
最后是编辑和出版理念的缺失。从出版角度上分析就是眼光短浅。出版社的急功近利和短期行为是目前出版体制下的通病。市场需要培育,出版社就要放长线钓大鱼。有一种说法是怎么苦也不能苦了儿童。在国外,一个镇最好的房子是学校,中国图画书要尽早地进入精装时代。国家的政策扶持要更多地向未成年人图书倾斜,国家出版基金的成人化、古人化需要改变,应该更注重当代未来和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