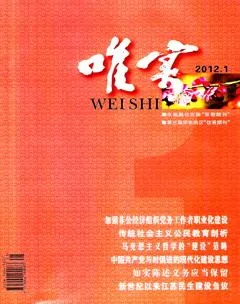执政转型背景下中央常委会体制改革及评析
作者简介:戴辉礼(1975- ),男,湖南炎陵人,中共湖南省委党校科社教研部讲师,政治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政治。
摘 要: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作为事实上的中共最高权力机构,其具体运作机制的改革与完善备受关注。在执政转型背景下,2002年以来,中央层面对常委会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具体体现在最高权力交接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工作的制度化、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的健全以及民主推荐中央政治局成员预备人选这四个方面。总体来看,中央层面的常委会体制改革显现出实现最高领导体制模式的稳定化和规范化、渐进性推进党内民主和提高执政能力、坚持常委会体制三个趋向。
关键词:常委会体制;改革;执政转型;权力交接;党内民主
中图分类号:D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2)01-0020-05
自中共十六大召开至今近十年来,随着党内民主和执政转型的步伐逐步加快,在中央层面针对常委会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与完善。在执政转型的背景和视角下,实事求是地对这些改革的现状进行分析与评估,对于明确进一步改革的根本目标和现实路径选择非常必要。
一、十六大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
及其常委会的改革
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作为事实上的中共最高权力机构,是当代中国政治权力运行的“神经中枢”。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其具体运作机制的改革与完善都是备受关注的。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改革主要体现在最高权力交接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工作的制度化、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的健全以及民主推荐中央政治局成员预备人选这四个方面。
1.最高权力交接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稳定的政治秩序是任何政治体系的基本价值目标。按照亨廷顿的基本观点,政治稳定与政治制度化之间构成正比例关系,在既定的政治参与的前提下,政治稳定取决于政治制度化水平。[1]42、60权力交接特别是最高权力交接的制度化是政治制度化的根本体现,对于保持政治稳定具有极其关键的作用。西方国家的最高权力交接是通过一套比较完善的竞争性选举制度、任期制以及退休制等制度安排来体现,因而从根本上保证了政局的稳定,故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意义上的接班问题。在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中,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事实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终身制,没有建立规范化的最高权力交接制度,因而接班问题成为困扰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在这方面的教训不可谓不沉重。在毛泽东时代,由于没有建立任期制、退休制等制度,因而无论党与国家的高层还是地方各级领导层,都是实行事实上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在最高权力交接方面,不仅没有建立稳固的集体接班制度,更是通过由最高领袖个人选定接班人的形式来进行。正如邓小平所说的:“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2]邓小平成为中共领导核心后,特别强调要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力主建立干部任期制、退休制、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对于最高领导层的权力交接,邓小平主张通过集体接班来解决。但是,最高权力层必须要有一个领导核心,而在领导核心的权力交接上,在邓小平时代实际上也没有形成制度化。邓小平并没有担任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职务,他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凭借个人的政治素质和公认的政治威望。作为最高领导核心,邓小平的退休是自己强烈要求的,不存在刚性的制度约束。因而对于他来说,事实上同样存在安排接班人的问题。在邓小平之后,形成了比较稳固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但是高层权力集体中谁也不具备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绝对权威,因而通过钦定接班人的模式来实行权力交接已经失去了可能。在第三代领导集体执政时期,虽然对包括总书记在内的政治局常委没有具体的任期限制,但是由于实行了政治局常委同时兼任国家领导人的党政合一体制,国家领导人的任期制在客观上决定了包括总书记在内的政治局常委的任期制,加上年龄限制的因素,就在实际上为最高权力交接的制度化奠定了基础。在中共十六大上,除胡锦涛外,包括总书记江泽民在内的其他政治局常委全部退出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不再担任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这就意味着他们实际上退出了最高权力层。而后在2003年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和政协会议上,不再担任政治局常委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成员也相应地不再担任国家领导职务。当江泽民同志在2004年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后,最终完成了最高权力的完全交接和平稳过渡。2007年中共十七大上,根据十六大后党内实际上存在的政治局委员及常委的候选人提名年龄不超过68岁(包括68岁)的不成文规定,到达限制年龄的常委都退出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新的最高领导层。而新产生的政治局常委会实际上又在党内外多方协商以及预选的基础上确定了下一届的核心领导人选,从而为最高权力的代际更换和集体交接做好准备。从十六大上的最高权力交接到十七大的最高权力层的人事调整可以看出,最高的权力交接通过客观形成的任期制、由年龄限制所形成的退休制以及协商产生下一代领导核心成员预备人选的制度等实现了规范化、制度化,确保了最高权力交接的平稳化和可预期性。“制度就是稳定的、受珍重的和周期性发生的行为模式”[1]10。制度的重要功能就是通过其稳定性和周期性来增强可预见性。尽管在最高权力的交接上没有形成成文的正式制度,但是上述不成文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却能发挥稳定性和可预期性的作用,因而在中共执政转型过程中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
2.中央政治局报告工作的制度化
从理论上讲,报告工作制度是体现权力授受关系的基本形式,是权力监督的重要环节。马克思和列宁的建党理论都强调了在党的权力运行中授权客体要向授权主体定期报告工作的重要性。授权客体向授权主体汇报已经完成工作的情况以及提出具体的工作设想和计划,带有述职和接受询问以及监督的性质。从现在已经公开的信息来看,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向政治局报告工作实际上始于2000年1月20日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报中央政治局常委“三讲”情况的讲话。这个讲话回顾和总结了十年来常委会的工作,提出要进一步研究和抓紧解决的几个重大问题和进一步加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工作,并且报告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三讲”的体会和收获。[3]4显然这在中共推进党内民主的进程中具有较重要的意义。从正式制度安排上来看,从中共第一个党章到十六大上通过的党章,都没有要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工作的规定。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第一次提出要建立中央政治局常委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会定期报告工作的制度。根据这一要求,报告工作制度写进了《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工作规则(试行)》、《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工作规则(试行)》两个规范性文件上。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报告工作制度并没有坚持下来。2004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正式规定了中央政治局要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工作。在中共十七大上通过的党章中再一次明确规定:“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工作,接受监督。”[4]这样一来,中央政治局的报告工作制度就有了党章层面上的正式依据。从具体实践来看,从十六届三中全会开始,在每一次中央全会上,都把由总书记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工作作为会议的主要议程,由此基本实现了中央政治局报告工作的定期化和制度化。正式规定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工作及其制度化实践,不仅体现了中央最高领导层通过这种形式强化权力来源意识、理顺党内权力结构关系以及强化权力监督的取向,而且也对地方各级常委会向全委会报告工作起到了示范和推动作用,其在执政转型上的制度意义无疑是积极的。
3.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的健全与完善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学习意识和学习能力都很强的组织。从某种意义讲,中共的建立就是源于学习。从历史上看,全党范围内的学习无疑是源于抗战时期的整风运动,毛泽东无疑是学习的爱好者和党内学习的倡导者。正是由于毛泽东的倡导,党内学习特别是高级干部的学习成为中共的传统。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全党范围内的学习依旧遵循了运动式学习模式,中央领导高层的学习也主要只是采取个人化的学习方式,在中央政治局没有形成集体学习的制度。中央领导人的集体学习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主要以法制讲座为学习形式,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法制讲座并没有持续下去。从1996年开始,在中央最高领导层又重新开始以法制讲座的形式开展集体学习,至此,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初步形成。但是,学习内容更为广泛、集体学习次数更多以及学习机制更为完善的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始于十六届中央政治局。胡锦涛在主持十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明确强调要把政治局集体学习作为一项制度长期坚持。自此以后至今,两届政治局先后组织了60多次集体学习,学习内容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历史、国防、社会以及党建等各个领域。[5]同时,集体学习的组织机制也逐渐完善,已经基本形成了制度化。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从根本上说为了提高中央最高权力层的领导与决策能力的需要,其对于减少决策失误、增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适应能力以及强化中央的示范作用等方面都具有积极意义。政治学者王绍光教授通过研究认为,中国的体制属于高适应性体制,这源于中国决策者的学习机制和学习能力,如果存在一个“中国模式”的话,中国政治体制的适应能力肯定是其中最关键的环节。[6]与王绍光的观点相似,海外华裔学者薄智跃也把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与“中国模式”联系起来。显然,这样的认识把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的意义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4.民主推荐中央政治局成员预备人选
由于中央政治局特别是其常委会在中国政治权力运行中的枢纽地位,其组成人员的产生的极端重要性可想而知。邓小平在政治权力交接的时候曾经说:“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只要它是团结的,努力工作的,能够成为榜样的,就是在艰苦创业反对腐败方面成为榜样的,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7]310正由于事涉最高决策层的权力交接,因而建国后历来政治局成员的选择与产生都充满了神秘性,政治透明性较低,外界根本无法获知相关信息。党章规定,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都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但是,在党章和党规中都没有对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候选人预备人选的产生程序和过程作出明确规定。由于没有明确的规范性制度规定,因此,在中央政治局成员预备人选的产生过程中是否能体现党内民主显然不得而知。在十七届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产生上,开启了中共历史上第一次用民主推荐的形式产生中央政治局成员预备人选。在中共十七大闭会后不久,新华社通过长篇通讯的形式正式公布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的产生经过。通过新华社这篇通讯披露的信息可知,2007年6月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由胡锦涛总书记亲自主持的党员领导干部会议,对可新提名为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进行民主推荐。参加推荐会的有中共十六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共400多人,每人都发一张上面列有近200人名单的可新提名为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的民主推荐票,然后由参加推荐会的人员进行投票。[8]在民主推荐投票的基础上,中央最高领导层综合民主推荐结果、组织考察情况、本人廉洁自律情况和班子结构需要,正式提出了十七届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建议名单,然后在十七届一中全会上进行正式的选举。民主推荐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的形式,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次预选过程,民主推荐的结果对于中央政治局的产生以及党内最高权力接班人的产生都具有实质性影响。如此一来,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了中央最高决策层的产生机制,其对于干部择优以及增强中共最高决策层的权力合法性都具有重要意义。民主推荐中央政治局成员预备人选,显然是一次比较关键的党内民主制度创新,在中共历史上具有标杆意义,一旦形成制度化以后,能发挥进一步推进党内最高权力交接的规范化和制度化的作用。
二、中央常委会体制改革现状评析
中央层面上的常委会体制改革,从根本上关系到执政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体制的调整,因而审慎地实行渐进性的改革策略是必要的。从最高权力交接的逐步规范化和制度化、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工作的制度化、健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以及民主推荐中央政治局成员预备人选等方面来看,中央层面的常委会体制改革主要体现出实现最高领导体制模式的稳定化和规范化、渐进性推进党内民主以及提高执政能力、坚持常委会体制三个趋向:
1.实现最高领导体制模式的稳定化和规范化,是中央层面的常委会体制改革的重心
从西方国家的情况来看,无论是总统制、议会制还是君主立宪制国家,都实行竞争性政党体制,国家最高领导体制模式都是一种宪政性制度安排,因而国家领导体制和执政党的领导体制之间几乎没有重要的制度性关联。在政党-国家体制下,执政党的领导体制和国家领导体制是密切相关的,两者之间的不同结合与匹配就形成了不同的领导体制模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作为常设性的中共最高权力机构,如何与通过宪法确立的国家公共权力体制进行结合,在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都没有形成固定化模式。在1982年,中共十二大和新宪法的颁布,分别确立新的中共中央领导体制和国家领导体制后,中央政治局实行“六常委制”。六位常委分别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国家主席、中纪委书记的职务。由此可见,除政协主席外,其余国家领导人(国家级正职)都是政治局常委,在最高权力层中形成了“六架马车”式的格局。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实行“五常委制”,五位常委除了一名常委主管党务和意识形态外,其余四位分别担任总书记、国务院总理、中纪委书记、国务院常务副总理职务,而国家主席、全国人大委员长和全国政协主席都没有进入政治局常委会。1989年十三届四中全会上,中央最高领导层实行了调整,常委人数由5人改为6人。十三届式的“五常委制”显然不太适合以党领政的政治体制,不仅容易造成权力的制度性冲突,而且客观上不利于最高权力层交接形成制度化。从中共十四大开始,中央政治局开始实行“七常委制”,并实行总书记兼任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体制,全国人大委员长、国务院总理以及政协主席全部都由政治局常委担任。“七常委制”的实行,不仅仅是常委人数的简单增加,而是在根本上确立了一种新的最高权力领导体制模式。这种模式的特征在于:第一,党的最高领导职务与国家主席职务实行了结合,形成了新的国家元首体制;第二,国家领导机构正职全部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形成了事实上的“党政合一”领导体制,实现了党政最高领导体制的统一。从中共十六大开始,中央政治局在“七常委制”框架的基础上实行“九常委制”,最终形成了一种稳定化的最高领导体制模式。最高领导体制模式的形成,在客观上促进了最高权力交接的规范化和制度化,与以往的政治局结构模式相比,显然更适合常委会体制下的政治权力运行。
2.中央层面的常委会体制改革体现出渐进性推进党内民主和提高执政能力的趋向
正如前面所述,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工作的制度化、民主推荐中央政治局成员预备人选等,都是推进党内民主的举措。除此以外,从十六大到十七大,在“两委”人选的推荐、考察、提名以及预选过程中体现出比以往更多的民主性特征,主要体现在扩大民主推荐的人员范围、扩大差额考察的比例、增加民意调查和考察对象公示等制度措施、扩大差额预选举比例等方面。中共十七大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以及中纪委委员的差额比例分别达到8.3%、9.6%和8.7%。[9]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显然主要是为提高最高领导层的执政能力而实行的。渐进性地推进党内民主和提高执政能力的举措,不仅对于完善中央层面的常委会体制有实质性意义,而且能给地方改革提供示范和表率作用。总的来看,通过发展党内民主来增强中央委员会特别是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权力合法性,从而使中共作为执政党具有“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10]。通过提高最高执政集体的执政能力来提高执政有效性,是中央层面的常委会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
3.总体而言,中央层面的领导体制改革体现出一种坚持常委会体制的基本理念
在坚持常委会体制的前提下,党内最高权力结构需要进一步理顺与完善,即需要进一步完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作为党章法理上的最高权力机关在闭会期间的功能与作用,需要进一步体现中央委员会的决策作用,改变其依旧是一个功能性会议形式而非一个制度化的实体组织的状态。由于中央层面没有实行党代会常任制,中央委员会每年只召开一次会议,因而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作为常设性权力机构享有事实上的最高权力是很难改变的。就中央政治局的改革与完善来说,第一,在权力产生的环节上,虽然已经实行民主推荐中央政治局成员预备人选,但是在正式选举上还没有实行政治局委员的差额选举;第二,鉴于政治局常委会在中国政治权力运行的核心地位,邓小平又多次提及其重要性,“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7]365。所以,在政治局内部依然没有改变常委和委员两个权力层次的格局。两个权力层次的存在,不仅使得中央政治局的权力更加集中在常委会中,而且导致政治局内部的分工体系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重合,即在常委分口管理的基础上,很多政治局委员实际上处于协管的地位,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现行制度所强调的真正的分工负责制的实行。以组织、宣传的分工为例,组织和宣传工作分别由两名中央政治局常委分管,但同时又有两名政治局委员分别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长,这两名政治局委员实际上在组织和宣传工作领域处于协助常委分管的地位;第三,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与全国人大、国务院等其他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来看,基本上还是一种决策与执行的关系,权力关系需要进一步理顺。邓小平的一番话可谓道破了中央权力结构关系的本质:“属于政策、方针的重大问题,国务院也好,全国人大也好,其他方面也好,都要由党员负责干部提到党中央常委会讨论,讨论决定之后再去多方商量,贯彻执行。”[7]319总之,中央层面上的常委会体制改革需要在更周密的制度设计的基础上,围绕增强权力合法性和执政有效性的原则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47.
[3]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19.
[4]本书编写组.十七大党章学习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8.
[5]薄智跃.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与“中国模式”[J].南风窗,2010(3).
[6]王绍光.学习机制、适应能力与中国模式[J].开放时代,2009(7).
[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为了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纪实.新华社通讯,2007-10-23.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0/24/content_6931498.htm.
[9]肩负起党和人民的重托——新一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诞生记.新华社通讯,2007-10-21.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0/24/content_6931498.htm.
[10]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55.
责任编辑:张功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