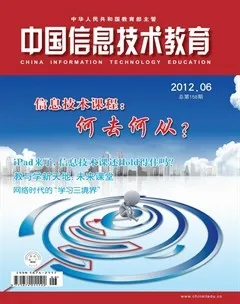山的那边是什么?
义务教育阶段的信息技术学科,过了九年没有课标的童年生活,苦乐自知。新一轮课标发布,依然难觅信息技术的芳踪。虽然近来有“民间”课标问世,仍抵不过众多担忧信息技术学科前途和命运的教师发出一声声地诘问:信息技术课程的走向是什么?仿佛千百年来中国民间那个古老的童问:山的那边是什么?
● 山那边住着老神仙——回归程序设计语言课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应用型软件的普及已不再是个问题,所以信息技术学科不要在文字处理、图像处理和动画编辑等方面花费时间,应回归到计算机课原本的特色之路——程序设计,就是山那边的老神仙。我们只要把老神仙请回来,从此就会过上幸福的生活。
其实,在基础教育阶段,信息技术课(前身是计算机课)是以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为主,还是以学生掌握编程语言为主,是一个老问题了,这甚至要追溯到20年前,当信息技术学科还没有诞生,当计算机机房还是神秘到需要换上拖鞋,穿白大褂才能进入的高档场所的年代。1995年上半年,联合国开发署(UNDP)首席技术顾问Dwight W.Allen博士到我国部分地区进行了中小学计算机教育情况的短期考察。不久,他写出了两篇题目分别为《重新考察中国中小学的计算机课程——警告》和《中国中小学计算机教育的未来》的考察报告。文中指出,当时我国不少地区的中小学计算机课程都着重讲授程序设计语言,这实际上是把培养和掌握计算机的程序设计能力作为课程的主要教育目标,而不是通过课程使每一位学生都能掌握计算机这种先进的现代化的工具。他极力反对这种做法,认为要求全体学生掌握程序设计语言,就好像在允许学生使用圆珠笔之前要求他们必须先理解圆珠笔的构造、必须先搞清楚圆珠笔内的墨水是如何转移到纸上的科学原理一样走偏了路。
当年,我国教育技术领军人物、北京师范大学的何克抗教授撰文回应Allen的评价,并专门再写一篇文章《论计算机教育发展的新阶段》,指明计算机教育的发展之路。他认为严格意义上的文化(literacy,或素养)具有广泛性、传递性、教育性和深刻性。即在广泛性上要涉及全社会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全社会的每一个行业、每一个应用领域,在深刻性上能带来整个社会从生产方式、工作方式、学习方式到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变革。显然信息素养符合这样的判定标准,而程序设计就称不上是一种文化和素养,它无法在广泛性和深刻性上达到与信息素养同等的高度,因此,用它来作信息技术学科的课程目标是不当的,自然也就被人们认为无法承担起信息技术学科未来的重任。
● 不慕他山仙,但求我山宽——不被排挤在升学大考之外,寻求深度以获新生
持这类观点的人认为:当前个别省市取消信息技术会考甚至高考,照此下去,信息技术学科必亡。或者依然对学科心存热爱和信心,但是对现状堪忧,唯求挖掘学科深度以获新生。
这个问题的答案好像狄更斯《双城记》中的传奇一笔: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不参加考试的学科是不幸的,因为一旦确定为非考试科目,那么学校、家长、学生对该科的重视程度会大大下降,被同行看轻,甚至自己的教学岗位是否还能存在,都成了问题。但同时,不参加升学大考的学科也是幸运的,因为少了很多题海战术,少了很多剑指应考的耳提面命。教师还可以在自己的课堂带领着孩子徜徉于学科的兴趣之岸,让他们从学科的本源上去经历、体验、品味学习过程和学科思维方式带来的快乐和成就。
从应试角度看待学科的重要性,只能代表升学选拔机构的人才遴选重心,却无法回答学科核心价值的走向。最能体现学科魅力、代表学科生命力的理智与情感,从来不在考试中。在应试体系下,语文可谓“享负盛名”的必考科目,那么语文学科在学校教学和考试体系中的重要程度能回答语文学科走向的问题吗?1997年,《北京文学》展开了一次“忧思中国语文教育”的专题讨论,围绕著名编剧邹静之《女儿的作业》等多篇文章,掀起一场关于语文课程走向的全国大讨论。教科书的标准答案是“惟妙惟肖”,学生就不能答成“栩栩如生”,老师手里的答案印着“齐心协力”,那么学生写出“同心协力”就被判错。捧着课文讲语文,照着答案学语文,是语文课程的走向吗?
诚然,语文不是我们要探讨的话题,众多的信息技术教师是以爱之深、恨之切的心态,关注信息技术学科的走向,但是答案不在是否被纳入或排斥于考试体系,有生命力的学科,即使今天不在体系之内,它自有生存和发展空间,而自己把课讲“死”,那么即使现在还在体系之内,总有被时代淘汰的一天。所以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怎么上好信息技术的每一节课,让学生能够带着兴趣来,带着成就感走,这才是信息技术课程走向要探讨的核心。
●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信息技术课程的走向在每一节课中
关于信息技术课程的走向,我在《信息技术课堂教学的“浅薄”之路》这篇文章(刊发于本刊2012年4月刊——编者注)中,已经表达清楚,即信息技术的课程走向,就是建立“创意、个性与自由”的课堂。我赞同“寻求学科的深度,以明确学科走向”的观点,但是学科深度,不等于知识深度,更不等于教科书的编写深度。最近,我到一所小学听老师讲《如何使用画笔工具》一课。我设想着学生运用大胆的想象和美丽的色彩描绘自己心中的图画,因为我年仅5岁的小侄子也能无师自通地用画图软件涂鸦,并乐此不疲。可是从上课起,教师就开始讲两个不同版本画图工具的界面差异,再讲工具栏的位置变化、“主页功能区”、“悬停功能”。15分钟后,孩子们终于可以自己画了,教师却给出了学习任务:给一幅小猫钓鱼的黑白图补上一根鱼线。而这样讲的原因,是因为要把教材中涉及的铅笔、橡皮擦等知识点都讲到。那么如此下去,课程即使有考试保驾护航,有教科书上达到了深度的知识点,可孩子还会对信息技术保持长久的兴趣、灵动的创意和不断地自我挑战吗?
我经常浏览一个教师专业发展的视频网站(http://teachingchannel.org)。近期,该网站少有地连续推出了九节来自美国和加拿大初中的信息技术课,其中有八节涉及信息伦理、道德与规范,主题有网络暴力、网络隐私、用批判性思维判断网站的可信任程度等,只有一节课与数字化媒体有关,看后才发现,该课不介绍媒体的定义、种类、特征,而是让学生分小组画出自己在生活中使用的数字化媒体的时间分布图,然后反思时间分配是否合理,数字化媒体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改变与益处。
孔子说“绘事后素”,有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描绘出最美的图画。基础教育阶段的所有课程,都是在帮学生培育一片肥沃的土壤,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为学生以后的人生提供厚积薄发的可能。所以,对于课程走向而言,最重要的部分还是由教师所把握,它就在我们一节一节的课堂时光里。山的那边有什么,答案就在你带着学生登山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