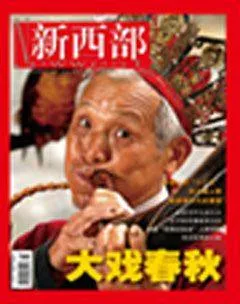杨显惠:挤开历史的门缝
上世纪70年代,还是知青的杨显惠在与人闲谈中零零星星听说,位于玉门镇饮马农场的甘肃农建十一师四团有一个来自定西专区的孤儿组成的连队。这是他第一次听说这件事情,也从此记住了“定西孤儿”这几个字。
不过,直到30年之后,杨显惠才真正开始寻访这些孤儿,并试图记录他们的故事,
只写甘肃的天津作家
杨显惠祖籍甘肃东乡县,在兰州长大。1975年,在甘肃师范大学念书期间,杨显惠曾和同学到定西做过一次基层调查。他的同学是通渭县人,他们在县城做完工作,同学对他说:你跟我回趟家吧。
他们沿着山路,往离县城很远的村里走。到了同学家,杨显惠心里暗暗吃惊:怎么连一间房都没有,一家人只有一床被子,住在拿土块垒的拱形窑洞里。
当天晚上,杨显惠和同学还有同学的弟弟三个人挤在一个炕上,合盖那一床被子。同学的母亲和衣睡在厨房里,父亲吃过晚饭就出了门,杨显惠想可能是去亲戚家借住了。第二天早上,他们在村里转悠,走到生产队的麦场上,同学指着一堆麦秸说,父亲昨晚就睡在这里。
这位同学告诉杨显惠,他家在1960年闹饥荒的时候拆掉了房子,木头都换了粮食吃。他的亲生母亲和一个妹妹都饿死了,现在的母亲是继母。饥荒过去10多年了,虽然粮食不再那么紧张,但是他家还是盖不起房子,只能住在窑洞里。
那两天的经历,给杨显惠印象太深了。1979年,他在创作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陇上七月》中,就写上了这段见闻。小说发表的时候,编辑将名字改成了《七月里》。
1988年以后,杨显惠定居天津,并加入天津作家协会,从事专职写作。虽然远离西北来到天津,但他每年都有四、五个月时间在甘肃采风写作。
1990年,杨显惠重返河西走廊,在饮马农场深入生活,挂职副场长。利用这个机会,他终于弄清了一个事实:1960年闹饥荒时,定西专区紧急成立了一个专区儿童福利院,接纳过上千名孤儿。同期,定西专区的各县、镇以及重灾区的各人民公社都成立了儿童福利院或幼儿园,共接纳孤儿超过5000人。孤儿们长大后,甘肃生产建设兵团招工,有一部分孤儿就来到了饮马农场。
从那时起,杨显惠就有了写这个孤儿群体的想法。
困难重重的寻访之路
2003年,杨显惠找到了当年定西孤儿院的一个孤儿为自己带路,从定西到通渭,再到会宁、靖远(1958年亦属e0f49fa475552d42163ba95bf20b04c632461ce473ada6e3c7b893ee45b6b2d8定西专区)和临洮,花了7个多月时间,走遍了整个定西地区,采访了150多位孤儿。
在初步采访了一些孤儿的故事后,杨显惠开始着手写作《定西孤儿院纪事》。《上海文学》杂志同步连载的许诺,给了他更大的写作信心和动力。
但是,寻访的过程困难重重。“有时候你追踪一个人或者一件事,弄了半个月,最后发现你的篮子是空的。从这个县跑到那个县,从这个村跑到那个村,好不容易找到这个人,可人家要么闭口不谈,要么几句话就把你打发了。”杨显惠说。
杨显惠发现,这些孤儿拒绝他的原因,除了不愿回首痛苦的往事,也有种种顾虑,担心领导批评他们乱说话,思想落后。有的孤儿虽然已经下岗或者退休,但对当年的“运动”还是心有余悸,害怕自己的“多嘴”会给子女造成麻烦。杨显惠给他们做工作说:“要抓也先抓我呀,要枪毙也首先是我,不会轮到你。另外我是写小说,不写真人真事。”
慢慢的,有人开始不那么抗拒了。可是,要让幸存的孤儿们说出心里话,也同样不容易。杨显惠往往通过熟人找到孤儿家里,或者把他们请到饭馆里面,有时边喝酒边采访。他还对孤儿们说,“我1965年上山下乡到了兵团,每天就是在这里挖渠种田。”一些老人才开始把他当作自己人。
幸存者们一个个开口了。有些人很冷静,一边琢磨一边说,有些人说着说着大哭起来,有些人则一直默默掉泪。
“对于那段历史,我总觉得我们的文学没有多少表达,历史学家也没能很好地总结,觉得自己应该去写。”杨显惠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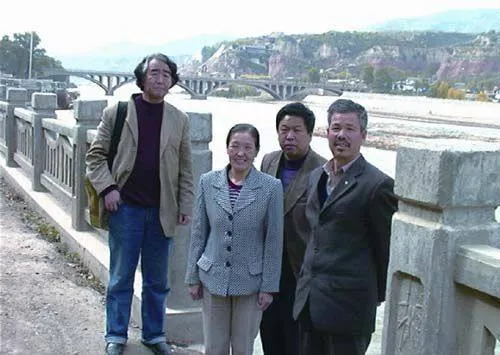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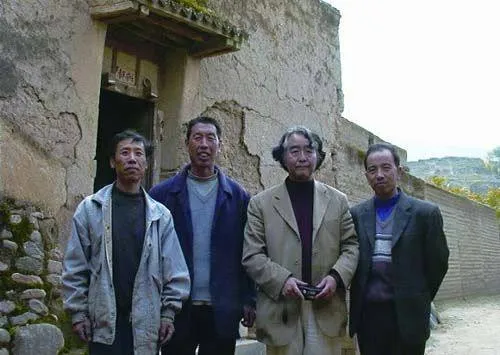
我们不该忘记他们
从2004年初开始,《定西孤儿院纪事》系列相继在《上海文艺》上发表。一个读者给编辑打电话反复问:“小说里写的都是真的吗?”这位编辑给杨显惠打电话,向他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这些故事是真的吗?”杨显惠说:“这种可怕的事情是不能虚构的。”
杨显惠不会打字,收集来的素材都写在本子上,交给女儿打,女儿打累了,妻子再帮着打。看到素材里的描写,女儿经常流着眼泪打不下去,妻子接过来,也流着眼泪打不下去。
“我的眼睛充满了泪水,抑制不住心灵的震撼,我把收集来的大量素材进行加工、提炼和剪裁,写成这部小说。我想告诉那些不了解历史或者忘掉了这段历史的读者:我们的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和进步,我们过上了前所未有的温饱生活,为了这温饱的生活,我们的前辈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无数人的生命和眼泪。我们不该忘记他们!”在《定西孤儿院纪事》的《后记》中,杨显惠表达了自己的写作初衷。
1998年,曾经亲身经历了1943年印度孟加拉大饥荒的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次年9月,他出版了《以自由看待发展》。在饥荒分析领域,他向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大饥荒不会饿死人,只有人祸才会饿死人。”
杨显惠少年时代学过绘画,他一直记得,俄国画家苏里科夫画了相当于一个小城镇人口的素描,才创作了《给沙皇写信》中的哥萨克群像,所以那幅画惊心动魄。杨显惠说,他访问了100多个右派,写了一部《夹边沟纪事》;访问了150名孤儿,写了一部《定西孤儿院纪事》。他为自己作品的真实做了这样的解释:“我的作品是用诚实的态度讲述一个个真实的故事,但‘真实的故事’是除了个别的故事写真人真事之外,十之八九都是虚构;这十之八九又都隐约晃动着真人真事的影子,虚构的故事全都使用了真实的细节。”
杨显惠自嘲“是个笨人”,也没有多么伟大的理想,但就想做一件事:“用我的笔记录自己视野中的那个时代,给未来的历史研究者留下几页并非无用的资料。这也是我从事写作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