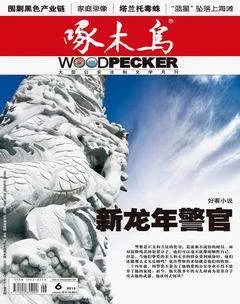太阳晃了谁的眼
一
太阳明晃晃地挂在上面。一切都是那么明亮,亮得什么东西都无所遁形。王晓阳懒洋洋地侧躺在枯草地上,厚厚的枯草暖暖的。忽地,干草的香味不知怎么就钻进鼻孔里。闻着这香味,他突然心一皱,鼻子就酸了。用手遮住眼睛,把明晃晃的太阳挡在外面,透过指缝看着牛子在不远处来来回回的瘦小身影,感觉那么不真实。
今天他是特意来看牛子的,说带他出去玩,问他去城里好不好。牛子使劲摇头,说就到后山打鸟。
带牛子去过一回城里。到城里,牛子对见到的新鲜事物只露出一丝惊讶,马上绷起小脸,满不在乎的样子。越是这样,王晓阳就越想带他尽可能去更多的地方,见更多的东西。领他和儿子一起吃肯德基,儿子兴奋地点这点那,看什么都好吃,还兴奋地问:“爸爸,你不是说肯德基是垃圾食品吗?为什么今天可以随便点?是牛子来的原因吗?”王晓阳没回答。肯德基对于儿子来说是垃圾食品,当然少接触为妙。可对于牛子,长这么大头一次进肯德基,垃圾就垃圾吧。
牛子安静地坐在那里,眼睛四处飞快地看一下,马上就目视桌子。吃的时候,看得出牛子很满意肯德基的口味,却不像儿子吃得飞快。儿子很快就吃完自己那份。牛子还剩个蛋挞,他把那个蛋挞小心翼翼地装进随身带的小书包里。王晓阳装作没看见。
带着两个小家伙到儿童乐园里玩了一气。临走,儿子拉着牛子的手要他再到城里玩。儿子也实在是寂寞,那些玩具也玩够了,电脑游戏王晓阳控制得厉害,所以小家伙还是挺孤单的。
牛子眼角瞅着儿子堆在地上的玩具,没回答。王晓阳给牛子也准备了两套新玩具,让他带回家里。
王晓阳没接儿子的茬儿,小东西懂什么,牛子本身就是城里人,牛子的户口现在还在城里呢,而且根据政策还吃着为数不多的低保。这里就应该是他的家,要不是……
王晓阳开车送他回家,不远,三十多里地。靠近城市的村子,但没紧要事,村里人也不到城里去。
牛子喜欢打鸟。自从王晓阳给他做了弹弓,并教会他发射这原始武器后,他就对它不离不弃了。每次王晓阳来看他,这是必玩的一个项目。
枪支管制是好事,但肆意地打猎不能了。这也是中国男人成长史上的一个悲哀,少了一项男人必修的项目。男人们越来越女气也跟这有关吧。没在林子里、草地上追逐过鹿,甚至兔子什么的,连只鸟都没打过,没尝过在野地里奔跑的感觉,无论如何对男性的养成也是种缺憾。
牛子打得很准了,臂力也越来越大。随着嗖的一声,应声而落的物事越来越多。可是牛子越来越内向,跟谁也不愿意说话。消融人和事物间的抵触相对容易,让他们多接触就好;人和人之间的抵触就没那么容易消融了。王晓阳也不知怎么办才好,实际上他自己也是个沉默至极的人。干的虽然是接触人的活儿,对人的心思看得也挺透,怎么说呢,用同事的话讲,他是个一天都冒不出两句话的主儿。
最早,他不是这样的,也是个开朗的人。师兄也就是牛子的爸爸出了事以后,他就再也不愿意说话了,仿佛语言是这个世界上多余的物事。
王晓阳毕业就和师兄做搭档。师兄的师傅是个老同志,本来也应该是王晓阳的师傅。但人老了,就不愿意说太多话,就把带徒弟的重任交给自己的徒弟了。刚开始,觉得什么都新鲜,跟在师兄屁股后问这问那,连师兄说话的语气都学。师兄领着他大街小巷走,看见各色人等,说着不一样的话,唠着不一样的家常。他们熟悉辖区中的每一张面孔,知道每一扇门背后的故事,知道脚下的青砖路下雨天哪块地方会汪水。
两人管的辖区就是普通居民区,很少见达官贵人,多是贩夫走卒。因房租便宜,交通也算便利,那些外来人口都愿意在这儿扎堆。常住人口才两万,暂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就达到三万。常住人口好管理,左邻右舍晚饭吃的什么都知道。暂住人口和流动人口才不好管理。做生意的、打工的,甚至躲债、躲祸的……隔几天他们就会看到新面孔在管区里出现。
师兄的妻子是个美人,很朴实的美。当时在当保姆,师兄下管区走访,一来二去就认识了,渐渐地两人竟成了恋人关系。当时引起的震动绝不比现在的明星造出的绯闻动静小。大家都不理解师兄,虽然家庭条件差点儿,可考上警校的男孩子都精神、帅气,为人再机灵点儿,那是没比的。局里好多小伙都钓到了金龟老丈人。用有些家伙的话说,那叫少奋斗二十年。其实,细算起来二十年都不止。结婚就有车有房,还有钱。老丈人都是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物,跟局里的头头们酒场、会场上常见。那升起官来,让你都来不及仰头瞅。昨天还是科员呢,今天就是副科级领导了,打个盹的工夫人家就是正科级领导了,再借着点儿人脉关系,干些买空卖空的事,那活得叫个滋润。
师兄的选择叫大家很是不解。不过也没挡住两人热恋的脚步。两人买了套小一居,结婚了,有孩子了。师兄没能像别人一样快速地从科员跳到副科,但他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乐在其中。
王晓阳也结婚了。两家没事的时候总在一起。
辖区里每天的吵吵闹闹是跟太阳一起冒起来的,月亮升上来还是热热闹闹。胡同里有早市,因为不用交摊位钱,卖的菜要比菜市场上水灵些、便宜些。住在附近的居民就起早来。八点钟过后,就剩下一地菜帮子、破塑料袋、烂了的瓜果梨桃。辖区里居民的日子就跟这地下剩的东西一样,无聊,不新鲜,日复一日,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
这跟王晓阳的理想差得太远。他的理想是当个福尔摩斯式的警探,现在却一直在基层派出所当社区民警,每天跟大爷、大妈们天长地短地聊。“现实总是与理想差得太远。”这话是师兄听了他几次牢骚、抱怨后,老气横秋地对他说的。那一刹那,总是笑眯眯的师兄像个历尽沧桑的老人。
他琢磨来琢磨去,好像是这样。比如他老婆玉。本来是冲着警察这个职业的神秘和英勇来的,结果嫁后才发现,警察也是一普通男人,钱挣得不多,越到该放假的时候越不着家,脏衣服、臭袜子满天飞,混到老就是一正科级,商品房和私家车离他们太遥远。比如他们所长,一心想当局长。不过,以他的水平和能力看,除非他离婚再娶,娶的是市委书记的女儿。但是这更不可能,市委书记有女儿的话,除非被天外飞仙摄了魂魄,否则是轮不到他的。还比如,辖区里二姐饭店的老板李二姐一直想当明星,打王晓阳认识她那天就没断了这美梦。在店里择菜、算账的当儿都打扮停当,随时出场的架势。实在闲的时候,还要唱上几段,什么《贵妃醉酒》之类的。那身段,那飞扬的眼神,使她的小店里总是断不了男人,也说不清是喜欢她的家常菜还是喜欢挠得人心痒痒的眼神和唱腔。他们愿意捧着这个烟火贵妃。
既然人人的理想和现实都差那么远,王晓阳也就没什么抱怨的。跟着师兄带着协勤每天走在大街小巷,遇到什么人都唠唠。
牛子打掉枝头上的一只麻雀后,坐在了他身边,低头摆弄他早已摆弄纯熟的弹弓,动作是那么老练和苍凉,眼里也没有该有的稚气。“叔叔,你是不是要出远门?”这是打鸟近一个小时以来他说的第一句话。
王晓阳一愣。
“你放心走吧,我没事的。”
妈的,这小子。自己要出远门?也不知道为啥突然想来看看牛子,经牛子这么一说,自己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要出门。每次出门也没这样啊,难道冥冥之中真的有什么东西在左右自己?这次出门真的会与以往不同?也该到了断的时候了。结果能是怎么样呢?自己发过誓,再也不会出现那样的局面,哪怕最糟糕的是玉石俱焚。太阳有些晃眼,他揉揉眼睛。师兄出事那天,太阳也这么好,晃得眼睛都睁不开。加之那道白光,眼睛更睁不开了,要不也不会……
二
这些年出门成了家常便饭。想走的时候,跟单位请假说老家有点儿急事,电话告诉老婆一声。老婆已经习惯了,也不跟他唠叨,也不磨叽,好像有他没他都行。同事们对一个什么都不争不抢的人很有宽容心。领导嘛,虽说不太高兴,可王晓阳这人还有点儿利用价值,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用同事们的话说,王晓阳那个蔫小子是有些神道的。
在一次搜查一个出租屋的时候,检查房客的身份证,人和身份证上的照片一致,同去的警察没看出什么毛病,网上比对也没毛病,但他的目光就是在房客和身份证之间来来回回,几个回合,那人就有些毛。刚想有什么动作,被他一脚踹翻在地。
回到所里,给发证当地打个电话,很快就水落石出了。这小子是冒用他人的身份,一切信息都是别人的,只有照片是他自己的。
跟他同去的警察有些后怕,无根无据的就把人踹翻在地,要是查不出什么毛病咋办?他就笑笑:“你没听出他的口音和身份证上所在地的口音不同吗?”
同事后来考证,所谓的口音不同,绝对不是东北和天津的区别,两地离得非常近,只是在尾音上稍稍不同,隔着二百里地的人绝对听不出来。王晓阳离着上千里,还能分辨得出?是不是神了?
警察巡逻,夜查,活儿琐碎,还累,但他们最不愿意干的就是到外地抓捕逃犯。有时线报准,少费些周折,也少受点儿罪。多数的时候,碰到模棱两可的线报,不信吧,不甘心;信吧,那就瞧吧,大海里捞针,人家吃饭,你在外面守着,手里有面包、饼干将就一下,没有就只好咽吐沫。有时走得急,连换洗的衣服都没带,夏天一身汗,冬天冻得脚钻心地疼,后来都没感觉了。还有所谓案子破了就是指案情明朗,知道犯罪嫌疑人就完事。大多数警察认为人迟早都会抓到的。于是就没人瞧得上外出抓捕的活儿了。
王晓阳愿意去,虽说他是社区民警,抓逃轮不到他,可碰上这事他就主动请战,而且不多言不多语,行动迅速。尤其是抓捕的时候,眼中的精光就像一道利剑把人刺在当场,动弹不得。他轻易不说话,好像全部的精力都集中到眼睛和手上,不说不动的他,动如脱兔,逃犯敢有些许动作,飞起一脚,就被踹翻在地。而且这活儿他越干越麻利,一点儿也不像他日常慢吞吞的样子。
让人不能理解的是,他抓住那些逃犯后总是一遍遍地问:“看见警察抓你时害怕不害怕?”十个有九个说,看见有人不顾一切地向他们冲来,第一感觉就是害怕,就是想逃走,跑得越快越好,压根儿就忘了手里还有武器;剩下那个说当时彻底吓呆了,根本想不起来跑的事。每得到这样的回答,他就颓丧几天,把自己喝得酩酊大醉。
别人暗地里嘀咕,难道他想听到逃犯不怕警察?摇摇头,也就各干各活儿去了。大家已经习惯了他的怪异。
在同事们眼里他是个不打折扣的怪人,另类。一天也说不上一句话,像活化石一样。他的办公室里有一张中国地图,上面密密麻麻的红色、绿色、黄色的小点子。一有时间,他就站在地图前琢磨,拿笔点点画画,要不就沉思。每次请假外出回来,他都在地图前站半天,有时兴奋,有时苦恼。大家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有促狭的家伙笑着说:“王晓阳等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准备组织百团大战和平原游击战呢!”
他有了外号,叫猎狗。能顺着味道摸着一个人。他能摸到的都是逃犯。一次,两次,别人认为他有好运气,可十次里有八次都让他赶上,光是运气就说不过去了。难道他背后有不可思议的力量?有大仙、神棍在帮忙?
有些新警察沉不住气,总在他身后讨教窍门。用他对一个新警察的话讲:“一个人最远能跑到哪儿去呢,现在整个地球就像一个小村落一样,人和人最远的距离是心。只要把人琢磨透了,他就跑不出去。”说这话的时候,在别人眼里他就像一代宗师一样充满自信。
师兄走了,师兄的妻子带着牛子回到村子里。隔上一段时间,他要去看一次。长时间不去,就觉得自己有啥事没办似的,难受得很。每次去,都带上老婆玉,每次从村子里回来,玉都说她再也不要去了。她说:“即使在经济上她一无所有,在地位上也处于社会最底层,食物链里的最低级,可在师兄媳妇面前还像个富翁。我到她跟前去就是为了炫耀:我有老公,而你没有。就是为了到她跟前去晒我的幸福。这种事我真的做不了了。”说归说,每次王晓阳要求她一起去,她都会去,她说受不了王晓阳恳求的眼神,一个心如枯木的人露出那样的眼神,让人心疼,真的是心疼。
牛子母亲户口在村子里,因为舍不得村里分的地,结婚后就没把户口迁到城里。牛子随父户口落在城里。师兄出事那年,牛子才两岁,王晓阳也是刚和玉结婚。如今,牛子十二岁了,王晓阳的儿子也九岁了,可师兄抱着儿子牛子那兴高采烈的样儿还在他眼前晃呢!师兄得意地说:“看吧,我儿子多像我,像个马驹子似的。”牛子小时候真的像师兄,尤其是性格上,调皮,好动。才两岁的他,恨不得耗子洞都掏两把,迈着两条小肥腿在院子里追着大孩子玩,看见人就笑。
王晓阳跟在师兄后面一天天在辖区里转,竟然暗暗渴望出点儿大案要案好让自己也有一显身手的机会。听师兄讲这片儿也发生过大案,不过王晓阳没赶上。那是他参加工作以前的事了,就发生在这片早市上。
早市上摆摊的和逛早市的人们大多不是有钱人。人要是没钱就容易活得急,看什么都有火。早市上有个卖肉的,人长得跟排骨似的,脾气却火暴得很。虽说生意不错,可家里接二连三地总有不顺心的事。他媳妇找个大仙算,说他家祖坟风水不好,要想了事,必须得把祖坟挪了,按大仙说的方法重新安葬。他媳妇就嘀咕他,让他快办这事。卖肉的烦透了,骂老婆败家玩意儿,挣点儿钱全送给跳大神的了。卖肉的带着一股火出的早市。偏赶上平时就矫情的一个娘们儿买肉。前槽肉,绞馅。差两毛钱到整,卖肉的就随手扔上一块。那娘们儿不干了:“添肉还不给添块好的,弄块血脖肉糊弄谁呢?你以为占这点儿便宜你就能发家致富啊?挣这点儿钱也不得好花,最多也就买点儿烧纸!”
卖肉的正憋着一股子气,上去就是一巴掌。两家人开始混战。混乱中,卖肉的抄起刀捅了出去,跑掉再也没回来。被捅的刀扎在左胸上,离心脏还有两厘米,经抢救活过来了。所里领导和局里领导都做卖肉的媳妇的工作:“想办法和老公联系上,没死罪,要是赔偿积极的话还能轻判些。”
卖肉的媳妇哭丧着脸:“他也没跟我联系呀!”
鬼才信她的话。在他能逃到的地方重点监守,还有几次都摸着他的尾巴了,结果都让他跑掉了。被窝里甚至还留有他的余温。
师兄给他说这事的时候表情淡淡的。本来嘛,刑事案子就不归社区民警管了。王晓阳有些蠢蠢欲动,幻想着自己要是跟那个卖猪肉的狭路相逢会怎么样,自己一定会很英武,想象一下就会热血沸腾。
理想和现实差得远,想象和现实差得更远。
那天,天出奇地好,一丝风都没有。太阳就明晃晃地挂在头顶,晃得人有点儿睁不开眼。天一暖,人就有些懒洋洋的。师兄带着他和几个联防队员在辖区慢悠悠地走着,走过王老三的水果店,老曲家的杂货店,李二姐的小吃店,老张家的粮油店,一切是那么熟悉,熟悉得有些视若无睹。后来到了任嫂的房屋中介所停下来。从玻璃窗望进去,任嫂坐在小桌子后悠荡着腿,嘴唇翻飞嗑着瓜子,眼睛则狠狠地盯着窗外,恨不得用眼神将外面走动的人拽进来,租她的房子。当然买她的房子更好,不过买卖房屋的业务像晴天下大雨一样稀少。
“怎么样?最近赚了多少银子啊?”师兄开着玩笑带着几个人进到小屋里。五六平米的小屋只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墙上四周贴着房屋信息。
“挣啥挣啊,架不住有搅和的。那个没爷们儿日子就过不下去的家伙,以为逮着个唐僧呢,怕我们知道给抢来炖着吃?还偷偷摸摸的,针眼大的地方,偷偷摸摸就能瞒住人了?”后一句任嫂是瞪着快要冒出来的眼珠子提高了声调冲外面的一个方向喊的。
顺着她的目光,大家找到了目标:李二姐的小吃店。
原来李二姐越过她这个中介招了个租房的,几十块的中介费没挣到恨得任嫂牙根痒痒。那人没办暂住证也没登记呢,几个人马上来到李二姐的小吃店。
用社区里老人的话讲,唱戏的李二姐也是个魔怔人。四十多岁,没老公没孩子,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她自己说是离婚了,孩子也给了男人。
从店门进去,李二姐正在厨房择菜。说明来意,李二姐合着韵的腔调就出来了:“呦,鼻子可真够灵的。”说完,打开后门的一道锁。她家有个后院,后院单独开门,平时把厨房连着后院的门一锁,就成了两个互不干扰的天地了。后院用于出租,李二姐带着服务员就住在挨着厨房的一间屋子里。
推开门,里面是个天井式的小院子。刷啦一下,正午的阳光像从一个漏斗中倾泻而下的钻石一样散发着灼人眼的光芒。据李二姐的描述,穿过院子里的天井才是两间住房。在这刺眼的光芒中,王晓阳恍惚见到一个瘦高的男人正在院里溜达。男人身上的某样东西白光一闪,也像钻石一样闪了他的眼睛。他刚揉了揉眼睛,就听到师兄大叫一声。那个瘦高的人影已经蹿到后屋去了,师兄却趴在了地上,血流了出来。王晓阳从来不知道人流血可以流得这么快这么急,汩汩的,带着声音,带着温度。太阳直直地照在那摊血上。王晓阳有些晕了,晃了几晃,没倒下。他又狠狠地揉了几下眼睛,刚才是自己看花了眼?
没错。他看过很多惨烈的现场,却从来没想过自己身边的人会这样流血,会这样匍匐在地上。
随着汩汩的血流走的还有王晓阳的心、气力和语言。他突然一下子就老了,老得走不动道了,甚至连做爱都没力气了。妻子玉总是暗暗想,幸亏自己怀孕了,否则以他的状态能不能生出孩子来还真不好说。在所里,他也变得沉默寡言了。以前跟同事总说笑话,拿这个开开玩笑,拿那个开开玩笑,现在就像个木头疙瘩。开始,所里人以为他是受了那个刺激,反应有些迟钝,过一阵子就好了。可没好起来,还越来越严重了,甚至连走路都有些老态了,低头、驼背,就瞅眼前一两米。所里人暗地里说:“哪是牺牲一个人,咱们是没了两个好兄弟呀!”
三
他还是管着那片社区。每经过李二姐的小吃店都以少有的速度快速走过,之后大口喘着气,好像跑了百米似的,然后坐在隔壁店铺门前那块大石头上,茫然四顾。领导看他这样不行,说给他调刑警队去,他以前不一直想当刑警吗?他说什么都不干,就要管这片。他要抓住那个家伙才可以走。人们都暗暗担心,以他这种状态怎么抓住那家伙?再说了,那家伙本来就是流窜在外的杀人犯,偶尔在这里落脚,现在杀了警察,难道还敢回来不成?在这地儿等,不比守株待兔的概率大。
但无论怎么说他都不为所动,每天就是在辖区里走啊走,在太阳地里眯着眼走。师兄出事以后,他落下一个毛病,惧怕天上的太阳,有太阳的天,就睁不开眼。
所领导让他带了几个新民警,也是当师傅的人了。他像师兄当年带他那样,带着几个新民警天天走在管区里。走过豆腐店、猪肉店、李二姐的小吃店、粮油店,再到那家介绍房屋出租的中介所,问一问最近有没有外地人租房子。房屋中介的主人已经换了,自打师兄出事,那个任嫂没法面对周围人的目光,尤其是王晓阳来中介所询问有没有外来人租房的时候,更让她受不了,结果转让了。
李二姐的饭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