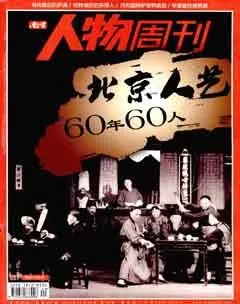吉拉的梦想
2012-12-29 00:00:00张蕾
南方人物周刊 2012年40期


曾经,德国盲女萨布瑞亚问她的藏语老师沛玛:“盲人在西藏的生活如何?”
“啊!”沛玛说,“他们的眼睛就一直闭上,整天睡觉。”
“我不相信,”萨布瑞亚说,“我也没有整天在睡觉啊!”
“是啊!”沛玛回了一句,“你就是很奇怪啊!”
西藏的民间信仰认为,盲人是前世作孽,现世遭罚,跟恶魔有关。在某些地区,人们甚至认为,碰触盲人是不洁的。盲人被认为终生废弃,无望无为,不被家人抛弃、杀死或者意外身亡,已属幸运。而学养丰富的喇嘛却说,身体残障也是一种机会——若能驾驭这种困难的处境,必能强化他们的灵魂。
在拉萨的旅馆,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去日喀则,我说,那里有所盲童学校。他们都知道:“那个德国女人吗?”
萨布瑞亚的传奇在藏人和关心藏人的群体中流传。当年,藏人传说她是能让人复明的神仙。他们带着家里的盲人,从旷野上奔来,希望得到她的加持。解释误会是让人失望的。但她骑着马上山下乡,出入盲童的家庭,带他们来到拉萨,在朗顿巷10号她建立的盲校里,对抗民间信仰,实践高僧的预言,医治更大的病症。
我对询问的旅人说:不是那个德国女人,是她的学生,也开了一所学校。
“他们是盲人,但他们有beautiful mind”
吉拉离开朗顿巷10号的生活已经有三五年的时间了。她如今生活在日喀则的一座农场,带着3位教师、4位后勤,以及21个孩子——其中17个为盲童。
确切地说,这是某部队撤离后留下的地盘儿,年岁未及花甲也至少不惑了。“军人俱乐部”残破得好像只剩下一睹门面墙,在半人高的杂草丛后故作庄严——碎掉的玻璃窗像牙齿开了豁。盲校的人在这里放鸭,打谷,牧牛羊。以吉拉为校长的琪琪幼儿园占据着靠近门口的一排平房,以前是奶牛的房子,“猪也住过”。
201yTkNSiYgqrxErDQ6IEVpIw==0年,当萨布瑞亚的丈夫、农场的掌管者、工程师荷兰人保罗指着这排房子对吉拉说,你可以把它变成梦想中的幼儿园!吉拉大叫:What(你说什么)?!
吉拉的英语说得很好,实际上,她曾是萨布瑞亚学校里,英语最好的学生之一。2005年,她跟同学尼玛一起去英国,学习了一年英语。她的口头禅是:“Why not?”和“So what?”
开园第一天,她问孩子们:谁愿意做班长?格桑尊追自告奋勇。吉拉问他为什么觉得自己行。格桑说,我会一点点汉语,我会比别人学得好。看到他自信的样子,吉拉心想:why not?
在英国的时候,怀着自卑的吉拉(负笈英伦前,这位出生在老拉孜县城旁边一座小村庄里的盲女一直羞怯地认为,英美国家的盲人的内心强大程度,一定是西藏盲人的两倍;他们也一定受过双倍于自己的良好教育)碰到一个英国盲人男孩,他每次出门都要人陪,从来不用盲杖,没法独自行走。吉拉很纳闷:“why not?”英国男孩说:“如果我带盲杖,所有人都会知道我是盲人。我会很害羞。”吉拉被震到了:“so what(那又怎么样呢)?!你不带盲杖,他们一样知道你是盲人呀——你要一直把着别人的胳膊!”
当“传统观念”袭来:“啊,你是盲人,那你也一定很蠢。”她会摆出一副骄傲、轻蔑、战斗的姿态:“嘿,的确,我是盲人,so what?我能说英语,能说汉语,我能读书能写字,我甚至可以在黑暗中读书和写字,你能吗?”
1999年,父亲带着吉拉和同是盲人的双胞胎哥哥多吉、强巴去拉萨,此后很久,三人没有再回到村庄,同村的人以为他们被扔到山沟里去了。他们寒假回家,也只低调地在自家的范围里打转——自从家里接二连三地生下盲孩子,吉拉他们家也从村子里搬了出来,在邻近村子的荒野重新盖房(因为穷,房子进度缓慢:有一点钱,就盖一点;没钱,就先搁着),为邻居省去经过他家不得不绕路的麻烦。
藏历新年后,经常去盲校拜访的摄影师车刚开车去拉孜接兄妹三人回学校。那天他建议三人晚上去村里最热闹的茶馆坐坐,把学校里学到的东西讲给村里人听。他们用英语对话,跟同乡分享他们在世界课上听说的好玩儿的事情。全村人都傻了。从此以后,乡里乡亲也对这个曾经疑似被诅咒的家庭关照起来。
留学英国后,吉拉更感到自己的独立和自信。她开设盲童幼儿园、对盲孩子进行早期教育的梦想开始实施。
保罗用3个月时间证明自己的改造宣言是靠谱的。吉拉眼前展现出一个全新的世界。
开园那天是2011年6月26日,吉拉他们一大车人唱着歌从拉萨赶到农场。她发表了一番感谢的开幕词,却让一贯外表强硬的自己哽咽哭泣。
“我有这个梦想那么多年,突然,它就在这了。”
第一堂课,她问学生(当时只有8个孩子),他们的梦想是什么。这些不满10岁的孩子不知如何回答。想了几个礼拜后,他们告诉吉拉想成为老师、翻译、作家、商人,还有司机。
当年在朗顿巷10号,吉拉的一位同学曾对萨布瑞亚说,自己将来想当出租车司机。其他的孩子都没有笑,老师也没有说什么。两天后,那个孩子又对萨布瑞亚说,我想过了,我当不了司机,但我可以开一间出租车公司。
“这些孩子,他们是盲人,但他们有beautiful mind(美妙的思想)”,“我们内心的世界是多彩的”,而这些“都来自自信”。
曾经,吉拉家的一个朋友关切她说:“你一定要施舍乞丐一大笔钱,你一定要虔诚祈祷,你一定要给寺庙多捐香火钱,你一定要点多多的酥油灯。这样,你来世就能成为明眼人了。”吉拉回答:“就算下辈子还是盲人,我也会快乐的。”
“这里像是家庭”
21个孩子在院子里跑啊,笑啊,在草坪上打滚,你看不到他们被差劲儿的视觉所禁锢。他们在教室里大声数着一周7日、一年四季、一岁12月,盲文的藏语口诀,英文26个字母,喊得直震人耳朵。
吉拉在办公室里吭哧吭哧回着邮件——有三百多封在等待。她的手机也很吵,语速极快地提示有新消息。她一天要喝三四杯咖啡,这是英伦生活的后遗症。另一个后遗症是擦防晒霜——“日喀则的紫外线实在是太强了”。
但只要一走出办公室,看到嬉闹的孩子,她就也恢复了生气。
“我真的很享受我做的事情。……因为起初我成长的方式是父母告诉我,你什么都不能做。所以我想做事情。大概就是因为这个,我希望尝试。”
琪琪幼儿园的财务完全是靠社会各界的捐款支撑,为了募捐,吉拉希望自己的汉语说得更好一些,以便跟企业家们更好地交流。从萨布瑞亚开始,募捐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管她多有名。
对于收下的孩子们,幼儿园是免费的。这对盲人家庭来说是福音,特别是,那些想尽快摆脱这个无望孩童的家庭。
次仁是去年被送来的,那时才2岁,小小的肚子总是鼓鼓的,好像营养过剩似的——父母总把他绑在床上,防止他掉下来。
这个没有运动的盲孩子,看起来更像是肢体残疾了,他不会走,也不会自己吃饭。吉拉对他的父母说,孩子还太小,幼儿园的工作人员人手也不足,能不能过一年再送来?他的父母说:不,我们照顾不了。
旺姆被送来时已经5岁了,吉拉没察觉有什么不对劲。只觉得这么大还不会说话,有点奇怪,带到医院检查,才知道旺姆不仅没视力,而且聋哑、严重贫血,并引发心脏疾病。吉拉听从医生劝说,致电旺姆的父母:孩子听不见,我们也教不了她什么,况且她情况不稳定,还是接回家吧。电话那边回答:“她的命,我们也没办法。现在秋收农忙,没时间,全部交给你们了。如果救不活也是她的命了。”
吉拉被不想负责的父母气得要死,但也只能接受。
“又不是孩子的错。”
次仁的小肚子还是有点鼓,虽然还有点踉跄,但已经能跑了。他的父母来看望他,惊讶:这是我们的孩子吗?!次仁跟同学们一起排排坐在食堂藏式的毛毯上,在等食物的时候,他们一起祈祷(吉拉说,这是一种藏人传统的祈祷方式,但今天已经不是所有的藏人都这么做了,她教给孩子们,是希望他们懂得敬畏和尊敬),像歌唱一样的祈祷诗,感谢神灵,感谢厨师,感谢所有帮助他们的人。
旺姆如今也能自己吃饭了,这个消息让吉拉兴奋得打上好几个感叹号发布在网上。别的孩子在课堂上扯着嗓子背诵的时候,她一个人在院子里游荡。当大家一起在院子一角的游乐场玩耍的时候,她也会加入,却不知为什么突然哭泣,鼻涕眼泪漫了一脸。班上学习最好的嘎玛堪珠姐姐平静地把她揽在怀里,轻声哼唱。日光城的明媚中,旺姆扬着头,表情舒展。她还是不会说话,但能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表达她的雀跃。
12岁之前的吉拉,听到的就是这样的声音。她被父母关在家里,偌大的屋子,她坐在角落里,听到墙外小朋友们的正常童年——可以出门,可以淘气;可以喜悦,可以悲伤,重要的是,可以把这些情绪都展现出来;还可以交朋友;最最重要的——
“这些就是记忆,你可以回想。但对我来说,就是一片空白。……我不后悔,但有时候我会觉得悲伤。”
吉拉的双胞胎哥哥则很听话,整日枯坐家中。吉拉总是跃跃欲试。她偷跑出去,掉到井里,磕破了头。当兄妹三人来到朗顿巷10号的时候,两个哥哥却因为手指不够灵活而不能摸盲文,吉拉觉得自己积攒12年的能量都迸发出来,她在这里找到了可以一起拥有回忆的真正的同伴。这就是为什么她延续萨布瑞亚的事业,并把孩子学习独立生活和社会交往的年龄大大提前。
“我们不希望他们把这里当成学校,我想要的是,他们觉得这里像家庭,以后他们回忆起来会觉得自己有个美好的童年。”
“这是一种美丽的相处方式”
课间,21只“愤怒的小鸟”叽叽喳喳——吉拉跑了十几家店,终于凑齐了款式和型号相近的“校服”,背后的图案是著名电子游戏“愤怒的小鸟”。
他们围着我的相机,一些孩子在取景框前探头探脑,一些孩子稀罕地摩挲着那机器的金属外壳。融洽的相处中,我时常忘了,他们或许是有眼疾的孩子。
吉拉在英国念语言学校时,同班的都是明眼人。她融入其中,老师们有时也会忽略她是个盲人。一次,一位叫玛丽的老师说:吉拉,请起立,读一下黑板上的东西。吉拉应了一声,胡乱说了一通。同学们都笑。她知道玛丽不是故意的,也怯于开开自己的小玩笑。
但有的时候,旁人的对待让她觉得莫名其妙。
比如分蛋糕的时候,有人会好心地分给她一块儿大的。
“我只是眼睛看不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比你更饿呀。”
还比如,她在机场询问路人“怎么去咖啡馆”。只听路人走上前来,冲着她的耳朵大喊:你可以从那里过去!
“我是盲人,但我不聋,我能听见。”
相比吉拉,同在幼儿园任教的哥哥强巴则要强硬一点,他认为对盲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向明眼人证明,我跟你们一样,甚至比你们做得好。当听到有人用不好的词汇称呼盲人,他会上前反驳,他操着藏语、汉语和英语给那些不明就里的人以下马威,最后鸣金收兵时收获这样的结论:“他们会觉得,虽然我们看不见,但我们有很多知识。”
有的时候人们是出于好心。强巴在路边等着朋友来陪他过街,一些行人以为他是乞丐,他们把手伸进口袋,掏出几个小钱儿,交给他。强巴说:这不错,你给我5毛,我能给你5块。行人发现冒犯,连忙道歉,并问,你需要什么?强巴回答,我需要人协助我过马路,我要去散步。行人惊讶,他就说,我们能做所有的事情,明眼人和盲人都一样的!
明眼人对盲人不够理解,包括父母不让她走出屋子,都是同样的道理——“他们不知道如何对待盲人”。
基于这样的原因,琪琪幼儿园里也收有4个视力正常的孩子。有的是玉树地震灾区的孤儿,有的是身体有小残疾,被家长托付于此。
“让盲孩子和明眼孩子一起学习一起玩很重要,他们分享,他们教给彼此东西,这些能帮到他们(将来走上社会后懂得如何互相对待)。”
美术课上,明眼孩子给盲孩子描述,颜色是什么样子。夜晚没灯的时候,盲孩子带着明眼孩子去洗手间。
“这是一种美丽的相处方式。”吉拉说。
幼儿园给每个孩子都准备了一根儿童盲杖(捐助者在美国订制的,中国买不到那么小的盲杖)。强巴说,多几个人用盲杖,就有越多的明眼人看到、意识到盲人群体的存在;盲人们也可以依靠盲杖,独立生活。
我有一个梦想
吉拉说,她的更长远的梦想是开设更多的盲童幼儿园,不仅仅在西藏。
与世界的相处,强巴的讲述没有吉拉那么清晰,但似乎包含更多。一天下午,他偷偷把我拉到一边,跟我简要地介绍了一下他的梦想。
在盲校上学的时候,他梦想做个导游。有一次听说有个外国人团队要来学校参观,他跑去跟保罗申请,由他带团介绍。保罗同意了,强巴兴奋紧张得中午饭也不吃,专注地等待客人的到来。他渴望运用那门世界语言,跟世界交流。
但导游梦不久就破灭了,因为他意识到如果他真的带着旅行团爬山拜庙,就需要给自己再雇佣一个向导。
后来他的梦想是在家乡开一个咖啡馆,给乡人和游客提供这种世界饮料。但外国游客不多,乡人也并不认同,他只能再改主意。
毕业之后他回到家乡,在一个农家乐旅馆做翻译。“我是村里第一个GvSDsV/TK5XeLuxWOq6cmQ==这样的人。”旅店的老板也很骄傲,对慕名而来的人说:是的,我们有个很好的人,他看不见,但英语很好。
但他不太喜欢这个工作,
“在旅店,我找不到意义,只是做生意,就是赚钱。在这里就很好,孩子们看不见,但我可以把自己的知识给他们,他们就能用到以后的社会生活中。”他说。
“我的终极梦想,我从没有跟别人说过,我现在告诉你:我想自己开个小小的英语学校。……如果我能开学校,明眼人也能学习,他们看到我们盲人能干这些,他们就不会浪费时间用来上网、打麻将、喝酒那些。”
其实除开这个“终极梦想”,强巴还有一个“最大最大的梦想”,就是能登上中央电视台的舞台唱歌。在拉萨时,他去电视台唱过一首歌——“我唱得最好的歌”,藏族歌手亚东的《缘》。歌里这样唱道:“阿妈曾经说,我们来到人间,是前世修来的福。如今爱人告诉我,我俩相遇,也是命中注定的缘。缘也是命,命也是缘,踏上人生的路,看到世间有太多的悲欢离合。我才知道与命搏斗,是我们编织生命的命。……阿爸曾经说,我们走过世间,是普度来生的路。如今爱人告诉我,我俩相遇也是命中注定的缘。缘也是命,命也是缘,踏上人生的路,看到世间有太多的悲欢离合。我才知道与命搏斗,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命。”
在告别西藏之前,摄影师车刚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老拉孜县城旁边的村庄里,生活着一个女孩。她眼睛看不见,只有微弱的光感。大概在10岁的时候,有医疗组织下乡来做“光明行动”,许诺她说,做了手术,安放了晶体之后,她就可以看见。手术后,她的眼睛没有任何改善,她的生活依旧是整天蜷在屋子的角落,听同龄的孩子在阳光下嬉闹。
12岁的时候,她在拉萨的表姐通知她和双胞胎哥哥去拉萨念一所由一位德国盲女创办的盲人学校。她欣喜地读书,出国,去年终于创办了自己的学校。今年6月,上海玉佛禅寺工作会邀请她和几个孩子去做检查,医生发现,当年的手术并没有为她安放晶体。上海的医院给她配了一副1500度的眼镜。8月的时候,她第一次戴上它,看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
车刚给她拍了照片,说:“吉拉,一次医疗事故,成就了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