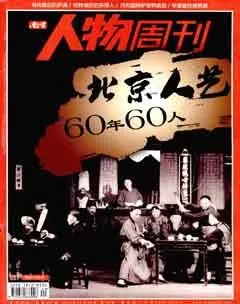觉悟不高的父亲
父亲辞世33年了。随着自己步入老年行列,对他的思念之情更甚,总想写些文字纪念他。他去世时,组织部门照例确认了一份悼词,在我看来,虚多实少,意义不大。记忆中倒有几件事情,能反映出他的性情。
父亲是陕西延川县人,地道的山沟人。1934年参加陕北红军,1955年授衔上校,1961年晋升大校。当年参加红军的陕北农民数万人,能干到父亲这个级别的是少数。
他年少时读了几年书,还在陕北最有名的榆林师范读过几个月。凭此学历,足以回乡教书谋生。当时的教书先生算是有些社会地位,衣食无忧,他为什么投奔红军?我从来没问过,他也从没谈过。抛开安稳的生活去干缺吃少穿的红军,他迈出这一步,可能就是不满现状。
1940年前后,父亲是军委总供给部粮秣处下属的科长,军委组织部长找他谈话,让他去中央机关幼儿园当院长。幼儿园是延安当时的“贵族”班,里面都是大首长的孩子,干好了自然会得到上级的赏识,但要求是:自己的孩子不能进幼儿园。父亲拒绝了:“我给别人看孩子,自己的孩子却没人管(当时我的大姐、二姐已出生)。”看来父亲的觉悟没有文学作品中塑造的党员那样高,给党做工作时还不忘自己的利益。
“文革”时父亲已经离职休养,惟一的大事是每周以党小组为单位政治学习。在讨论“毛选”中有关农村合作化的文章时,父亲兴之所至,说“合作化已经过去,这些文章现在的意义不大”。真不知他怎么想的,在那样的形势下,讲出如此胆大包天的话来。
干休所里“左”老头儿不少,抓住不放,连同他参加红军前的一些“历史问题”一并上报。省军区把父亲送进隔离审查的学习班,打算从严惩处,所幸兰州军区高维嵩副政委主持公道(父亲并不认识他),才了结此事。
1969年,林彪搞“一号命令”时,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局长权卫华(四川女红军)一家从北京疏散到临潼干休所。她得知父亲在西安,专程来看望,对父亲很是尊敬,“政委”不绝于口。我感到奇怪,父亲从“部长”岗位离休的,“政委”从何而来?父亲告诉我,解放初,权是他所在单位的政治处主任,父亲是政委,部队定职级时几个副职干部有意压权的级别,而父亲作为正职干部主持了公道。
“文革”结束前那几年,家里聊天的话题不外两个:政治,陕北老家。
谈起建国后的运动,合作化、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父亲直摇头。50年代初,农村老家没有饿肚子的(当然谈不上吃好),后来越来越差,结论自然不用说了。他还是大批彭德怀同情者中的一个。
1955年改薪金制后,父亲月薪近三百元,那时候当属高薪。可除此外没有丝毫进项,我们也绝少见到他的部下提着礼物进门。
家里孩子多,母亲虽是穷人出身却不善理财持家,还要接济亲戚。父亲不碰烟酒,基本没有个人消费,也是“月光族”。家中没有分文存款,有时还要去管理科借钱。
1965年的一天,他把我们召集在一起,用少有的正式语气讲,党决定部队系统干部减工资,他的月薪减了五十多块,以后家里的支出要更加节约。懵懂的我们当然不信,后来才明白,这是真的。直到家里的孩子都工作了,父母手头才略宽裕起来,可又开始为儿子们娶媳妇做准备,生活仍然节省。
他觉得家里厕所手纸的耗量过大,三番五次教我们怎样节约用纸,我们哈哈大笑,不当回事。那场景,如今历历在目,心中五味杂陈。
父亲对老家的感情很深,多次讲起一辈子勤俭持家的奶奶,讲起他的哥哥姐姐。我们提议回去看看,他却摇头,称回一次老家花钱太多,怕是要几千元,负担不起。
我那时还不懂人情世故,奇怪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父亲说,自己是在外做官的人,回去的消息传出,亲友必登门看望,给随行的孩子们一二十块是必须的,如此算下来,数目自然少不了,想到这些,回老家的念头只能压下,直至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