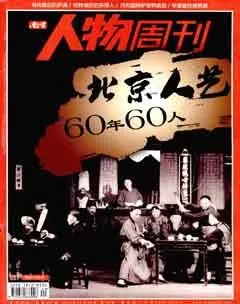寻找最后的萨满
2012-12-29 00:00:00刘洋硕
南方人物周刊 2012年40期




10月中旬的呼伦贝尔已如深秋般寒冷,78岁的老萨满关扣尼跟着村里的老人们第一次横跨了整个中国北部边疆,到海拉尔旅游。这里曾是萨满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从母系社会开始,“神灵使者”萨满们的歌声一直在这片土地响起。
老人们到来的几天前,我正开车在近半个呼伦贝尔草原寻找那些仍然在世的萨满。从海拉尔到额尔古纳、从室韦到满洲里,广阔的草原上仿佛再也找到不一位在世的萨满。市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帮忙问了几个旗,回答都是:那些萨满的传人,早已离开人世。
“在官方看来,这是一个没有萨满的时代。”长途电话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与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孟慧英说,“但在民间,萨满依然活跃。”她建议我先去找一位叫斯琴掛的达斡尔女人——如今呼伦贝尔最出名的萨满。
后来,当我见到关扣尼时。听说我找到了斯琴掛,关扣尼的侄女、曾担任呼玛县副县长的关金芬,一定要带着姑姑也去见见这位有名的萨满——从2008年开始,老人一直有一个心结:在那次失败的传承仪式过后,老人似乎也因此失去了她的神力:不再被神灵托梦,更无法为人看病、占卜——这个民族,仿佛与神灵隔绝了。
她要成萨满了
在关扣尼童年的记忆里,那原本是一个神灵与鄂伦春人共生的时代——族人们四处打猎,兴安岭森林茂密,河水清澈见底。
那时候每个乌力楞(父系家族部落)都有一两个萨满。关扣尼已经记不得是什么时候,堂哥关伯宝(关金芬的父亲)开始唱起神歌,穿上神衣。她只记得后来,跟堂兄一样,自己很快也成了这个家族第十五代的巫医萨满——一个能与神沟通的人。
那是一天早晨,她走出撮罗子(一种特殊的帐篷),去看那些怀了孕的母马。在16岁那年,她喜欢小马,想要看着它们出生。当她走出门,腰和胸口毫无征兆地剧痛。后来,疼痛越来越厉害,到家的时候,继母阿古站在帐篷边,问她怎么去了那么久。她疼得说不出话,只是哭——后来老萨满说,她的魂魄散了。
那天新的灵魂并未降临部落,马圈里没添上一匹小马,但神灵却降临到了关扣尼身上。已成萨满的堂哥关伯宝为她跳了神,临走的时候,堂哥说:“她要成萨满了。”
堂哥的说法并没有得到族人的认可,关扣尼的爷爷最为反对:“这孩子是要出嫁的姑娘,当了萨满也是人家的人”。但眼瞧着关扣尼一天天病了下去,族人才开始为他制作神衣。人们相信,被神抓的人,都会患上这种“萨满病”,如果不“出马”(出山做萨满),便会一直遭受磨难。终于,堂哥关伯宝再来的时候,带来了大萨满赵立本。
在如今的白银纳,仍流传着赵立本的传说,据说他领了七十多位神,救过无数族人的性命,是族里最大的一位萨满。
与赵立本同时代的还有位大萨满关乌力彦,最大的能力是“吉出仁”——可以到阴间索回孩童的灵魂。她会带着七个叉的神帽,穿着鹿皮的神衣,带着她的狗一起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据说,那时候他们已在阴间,如果魔鬼挡路,那狗就会反击。她还会带上两只鸟,看到死者灵魂,鸟神便会飞过,将灵魂抢走。关扣尼见过老萨满拿着神鼓为人治疗血液病,却也从未见过这招魂的场面。她听说,那时候“鼓会变得一闪一闪发亮”。
如今萨满的家人都会讲述更多神话般的传说来印证萨满们的神通。比如达斡尔萨满斯琴掛说:当年,日本人曾把她的太爷爷拉萨满和三十多个萨满一起抓到一个大房子里,让他们换上神衣,唱起神歌,然后用70车木头点着房子,看他们究竟谁是真的萨满。“大火烧了三天三夜,鼓声也响了三天三夜”,最后活下来的只有两位萨满,她爷爷便是其中之一——“他长长的胡子结了一层冰霜,后背上的铜镜烧得通红。”
“该如何相信那些神话般的传说?”我把那些神迹般的传说讲给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与人类研究所教授孟慧英,她笑着说:“研究萨满教,要首先打破思想上的禁锢。我们不去探讨真假、不探讨好坏。”
神奇的事也发生在关扣尼身上。那一次,赵立本跳了三个夜晚。关扣尼跟在后面敲着神鼓,蹦着跳着,仿佛天生就会那些奇怪的舞蹈。据说她领了两个神灵,一个叫阿你·则勒格,一个是狐仙。老萨满带着小萨满把身衣上的铜镜晃得哗哗作响,那是他们抵御邪灵的防身武器,他们的太阳,可以帮助他们通过那些最幽暗的通道。
本来按照鄂伦春萨满们的规矩,如此的仪式,3年内要每年举办一次,萨满才算真正得到认可。但第三年的时候,地委行署的工作组比赵立本更早找到乌力楞——来的人说:新中国要破除迷信,所以不能再信萨满。
那一年,呼玛河畔举行了盛大的送神仪式。关扣尼从未见过如此隆重的告别,各个流域的鄂伦春人从四面八方赶来。
赵立本带着各个流域的大萨满们宣布就此告别神坛。关扣尼记得,老萨满们最后一次跳起神舞,跳啊跳啊,跳了三天三夜。她坐地上,看着老萨满们沉重的舞步,仿佛向一个时代告别。人们喊着“登都任、登都任”——神飞走了。
没有萨满的时代
在那次送神仪式过后,各个乌力楞(父系家族)里的男人们,把自家的神送到山上,藏在一个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
1953年,鄂伦春人结束狩猎生活从山林迁到白银纳定居。曾当过副县长的关金芬说,“其实那时候的族人仍然相信,虽然送了神,但神灵并没有离开鄂伦春。”
已经告别神坛的赵立本经常在晚上不由自主地唱起神歌、跳起神舞。他的妻子怕惹是生非,便骑在他身上阻止。作为见习萨满的关扣尼也曾有一次偷偷穿上神服——那是告别神坛不久后,她的病痛复发,家人觉得那是神又来找她,便悄悄从山上取回了她的神服。她跳了一次,病居然又好了。
再一次把神送回山林,关扣尼就再也没有见过她的神服。几年前,家人也曾想上山寻找。后来侄女关金芳从一位猎人的口中听说,有人曾在一片被火烧过的山林间见到过两套完好无损的神服,一件大,一件小。关扣尼说,那一定是自己家的3件神服中的两件,缺失的一件因为早年被博物馆借走,而在“文革”时遗失。
当鄂伦春人告别神坛,毗邻兴安岭的呼伦贝尔草原上,达斡尔萨满的鼓声也在那个时代悄然寂静。1957年,斯琴掛的太爷爷拉萨满在去世前告诉斯琴掛的父亲,他们以后不用再供神了,他自己会将神灵一起带走。根据斯琴掛的丈夫巴特尔的说法,在拉萨满死后,斯琴卦的父亲将神像掛在了拉萨满指定的一颗树上。一夜之间,那些物件就真的消失得无影无踪。
直到1980年代,孟慧英教授走遍了呼伦贝尔和兴安岭的每一条河流,却怎么也无法再找到仍然出马的萨满。那时候,有人对达斡尔族的萨满做过调查,有名有姓的萨满只剩下4位。孟慧英和研究者们只能从老人们的嘴里听到那些关于萨满的故事,后来他们也找到了那些做过萨满的老人,但在经过一场场运动后,很多人都开始害怕再公开穿起神服。
萨满们也不愿意随便跳神。据说前些年,曾经有地方组织萨满为学者们表演,出于无奈,萨满开始跳神,但是在跳的过程中他们不断地发怒。萨满说,“神灵”对被拉来为人表演很气愤,自己的这种行为也会遭到神灵的惩罚和诅咒。
直到1990年代,白银纳的老萨满孟金福才开始公开跳神。1992年,纪录片导演孙曾田为此拍摄了一部纪录片——《最后的山神》。那一年,大兴安岭地区的暴雨酿成了60年来最大的洪灾。当年的老萨满们一共举行了三次祭祀。秋天那次,孟金福用神歌呼唤着早已远去的神灵:
特耶咧,特耶咧,特耶咧,
神啊,神主,
我们送走了您几十年,
如今我们想念您,为此请神保佑我们平安
神灵回来了
1995年,关扣尼一病不起。社科院的孟慧英教授当时正好在大兴安岭,她在在医院里见到躺在病床上吃力地喘息着的关扣尼。关扣尼说,自己得了心脏病。两天前,她还告诉家人“你们给我送两只鸡来”。
家人请来老萨满孟金福,孟金福说,那是神灵回来找他了。于是当天下午,家人从乡里的展览馆借来了萨满神服。几个老人,决定去林子里跳神。
藏在林子里的河流,是人们偶然发现的。那河流安静得没有一点流动的声音,整个河面犹如镜子,照出每棵树木的倒影——每一次跳神,萨满们都会选择河畔,他们相信,这河是神来的通道。
当人们点起火堆的时候,孟金福驾着他的桦皮船静静地从呼玛河上游飘来,同样没有一点声音——这是鄂伦春人世世代代的习惯,在山林里打猎的时候,不惊动一草一木。
火堆的青烟越来越浓,红色的火苗蹿出烟雾。当木条变成火块,关扣尼便把它们撮到铁锹里,围绕着场地熏烤,“除去一切秽气”。
身为大萨满的孟金福并没有为关扣尼跳神,而是做了她的帮手。他先唱了《请神歌》,病痛中的关扣尼便开始左手举着神鼓、右手拿着神鞭,有节奏地敲打:“神主啊,狐仙,与你分别四十载……”
关扣尼几次请神,几次摔倒在地,又站了起来。后来,她开始呕吐——老萨满说,那是内脏中的病气。
关扣尼的舞步与鼓点在歌声中越来越快,身体不停地旋转,最后她高举起鼓和神鞭,望向天空。人们喊着:“登都任、登都任。”
她最后一次摔倒,神离开了。让孟慧英难以置信的是,第二天,老人竟神奇地出了院。
那晚的仪式后,人们在燃起的篝火上煮了鸡肉。孟金福让大家把吃剩的鸡骨头用柳条包好,放在树枝上。年轻人早已不再为动物举行这样的风葬,但老一辈人仍然相信萨满们的哲学:山林里死掉的一切动物,都会在来年春天回来,如果他们的骨头遗失,便会变得残疾——那是打破了这山林的循环。
后来,孟慧英老师对我说,萨满的神灵让世世代代信奉它们鄂伦春人学会如何与这山林相处。孟金福从不用套索去狩猎,因为那样不分老幼的猎杀,山神不会高兴;他扒下桦树皮做船,割桦树汁饮用,却不将它们砍掉,因为这样明年树皮会重新长上……
2000年,老萨满孟金福去世了——那个天人合一的时代从此渐行渐远。
城市里的萨满
1990年代,当兴安岭的孟金福再一次唱起“神啊,神主”,呼伦贝尔的斯琴掛正被同一个梦折磨。她总会梦见一个白胡子老头来找他,对她说:“你若信我出了马,病就好了。”丈夫巴特尔说,睡梦中斯琴掛便会又说又唱。自己一度以为妻子得了神经病。
在成为萨满以前,斯琴掛曾是小学的数学老师。斯琴掛自己觉得:她从14岁开始便害了“萨满病”。因为经常得病,她最终不得不提前退休。48岁那年,她出马成为萨满,病竟然好了。
比起那些山林间的萨满,斯琴掛要现代许多。她拿着苹果手机,住在离海拉尔城区只有十几分钟的鄂温克旗。每天上午,她都会坐在写字台前,像开诊所一样为那些上门的人看病、咨询。每一次,她拿起一串念珠,将一端绕在手里,攥紧,另一端自然凑成一根柱形,然后自然倒下。她说根据倒下的轻重,便可以给人诊病。
过去的萨满,每天能有一个人来上门求医便已经很多,但斯琴掛的屋子里却总排满了人。来卜卦的鄂温克女人说:“我们自己家早已没有了萨满。”
人们一个接着一个向神龛跪拜,供上钱物,一个上午供台上便有了一两千块。每一个看病的人会带来白酒和牛奶。问诊的最后,斯琴掛拿起它们一边念着什么,一边向瓶子口噗噗地吹着。巴特尔说,这样的奶、酒就会带有神力。看病、问卦的人拿回去每日敬天、敬地。
不过,这些其实早已不是古老的萨满法术。熟悉斯琴掛的研究者都知道,她其实既信萨满神灵也信藏传佛教,每年还要去海拉尔旁边的寺里上香。
10月17日的这天下午,斯琴掛的一位女弟子来看“萨满病”。上午来的人太多,斯琴掛体力显得有些透支。一年前,她很不舒服,于是去北京跑了几家医院,查了心脏、查了脑袋,后来医生说她可能有些过敏。她想也对:“拿来让我吹(气)的,都是最劣质的白酒,每天还有香熏着,能不过敏么。”
斯琴掛有着很多无法考证真实性的传说故事。其中一个流传在学者圈子的故事是:2002年,她曾让一位来自东北的学者,不要坐某日的飞机。学者觉得奇怪,因为他正是定了那日的航班。他将信将疑地改了机票。几天后,那架飞机果然坠毁在大连海域。
真正让斯琴掛有了名声的是2004年。那年她参加了长春举办的“第七届国际萨满学术会议”,她在会上念了丈夫帮忙写的一份发言稿《我怎样当萨满的》。会议结束不久,国内外学者纷纷前往海拉尔巴彦托海镇参加斯琴掛的斡米南(萨满的升级仪式)——这让她自此扬名国际学术界,还被授予了“世界著名萨满”的称号。
在中国最北部边疆,不知不觉重新活跃起来的萨满信仰,似乎还远远无法实现那样的理想——人们更多怀着不同的私欲找到萨满,仿佛这是最便利的途径。这也难怪呼伦贝尔当地学者苏日台说:“要想了解真正的萨满文化,如今可能只有到博物馆了。”
尽管如此,藏在民间的萨满教,仍然守着人们的道德底线。孟慧英记得,有个男人曾找到斯琴掛诉说自己如何不顺。斯琴掛说,他往牛奶里兑了水,做了昧良心的事,让他找个敖包忏悔。
“神”飞走了
孟金福去世后,关扣尼成了鄂伦春最后的萨满。
当呼玛县副县长的时候,侄女关金芳曾偶然参加过一场关于萨满教的国际研讨会。那次见到了俄罗斯的鄂伦春人,对方说:俄罗斯的鄂伦春人仍然保留着跳神的传统,最老的一位萨满已经106岁。
对方接着问她:“你们还跳神么?”她莫名失落,不愿多解释,只说早就不跳了。
鄂伦春的萨满文化濒临消失。73岁那年,当地文化部门提出,让关扣尼找个人传承萨满,把萨满的仪式保留下来。关扣尼开始并不愿意,但后来省民委的领导也找到家里。家人商量决定,让关扣尼当护士的女儿接任萨满。
像关扣尼16岁那一年,人们为她和女儿孟举花一人做了一件神衣。
2008年,白银纳乡的鄂伦春人定居55周年,呼玛县文化旅游部门为关扣尼筹办了一场盛大的传承仪式。为了推广旅游文化,当地请来了不少记者。当时的《大兴安岭日报》仍然刊登了报道《萨满关扣尼有了继承人》。那些日子,家里每天都有记者上门。有记者问:怎么就指认女儿是继承呢?——似乎没有人能说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8月的一个晚上,呼玛河畔再次响起了关扣尼的鼓声。在过去,这样的传承仪式本该跳上三天三夜,但这一次只跳了一天。
侄女关金芬说:那晚神来了,却借着关扣尼的口,说了些没有人能听懂的语言。在场的人没人能听懂。“神生气了”,关扣尼最终“被”重重摔在地上。
一直从事萨满研究的孟慧英教授从未见过如此情况,“一般萨满上神,都会说他们本民族的语言。”关金芬却觉得,那晚关扣尼说的是神语,只是鄂伦春人如今已经没人能听懂。
没有人知道那晚老人究竟说了什么。但这场仪式仍然草草收场。后来,关扣尼一直责怪自己。在最开始,她觉得是因为现场记者太多、“灯光太亮”;后来,她又觉自己让女儿出马太急。那一晚,族人们显得灰心丧气,有人说,“不太好,就是不太好吧”。
神灵的事似乎得到了应验。孟举花没能成为新一代的萨满,第二年死于一场车祸。
从此,这成为了关扣尼的一块心病。见到关扣尼的那天,斯琴掛分析:按照萨满的规矩,孟举花应该算孟家的后人,只接了关家的神灵,孟家的神灵自然会生气。
在鄂伦春人的传说里,第一位萨满被人们称作尼产萨满(满族人称“尼山萨满”,达斡尔人称“雅僧萨满”,传说故事大致相同)。她死的那天,想害她的人们谎称请她跳神,却在她跳到高潮时将她投入枯井、扔下石头。最终,她被活活砸死,她神衣上的彩色布条却飞上天空。
(感谢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孟慧英女士、哈尔滨社科院研究员邱时遇先生对此文提供的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