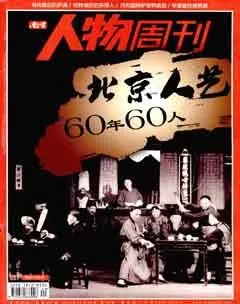50濮存昕 走向自由
2012-12-29 00:00:00布衣
南方人物周刊 2012年40期




80岁的王贵还在回味,9月份上演的小剧场话剧《天鹅之歌》。
小丑在台上肆意“洒狗血”,与观众随意互动——“那是濮存昕吗?”这位空政话剧团老导演故意问。
是濮存昕。是上世纪90年代后,银幕上的儒雅小生、坊间传说中的“师奶杀手”、公益广告中的艾滋病宣传大使。
“排演《天鹅之歌》,没用多长时间。我跟何冰说,生活中可以犯错误,可以是一个被人瞧不起的人。但在舞台上非得让人瞧得起,哪儿输都不能在这事上输。”濮存昕想说,他是一个演员。
听说演戏像父亲,他哭了
1973年,濮存昕18岁,在黑龙江建设兵团当了5年知青。
要回城,当演员是一条途径。练小品、背诗歌、学声乐——拜中央歌舞剧院男高音王嘉祥为师,可机会总是阴差阳错,直到1976年,空政话剧团招生。
考试时,他选择表演小品《刷马》,添加噱头,“有点京剧《三岔口》味道”,“考官觉得比较有生活,特别满意。”
学员班里,他与李雪健同一寝室,一起跑龙套。上世纪80年代初,李雪健在王贵执导的《9·13事件》里演林彪,声名鹊起。他演出场不到3分钟的飞行员,还错过电视剧《蹉跎岁月》的拍摄。
他继续演小品,当B角。一次表演炒鸡蛋,他做得聚精会神。虽是无实物表演,他不忘用手指把蛋壳里的蛋清刮一刮。这一动作令王贵印象深刻,另外,“小伙子脸形、身形也挺漂亮”。
濮存昕由此获得了第一个男主角,在王贵执导的《周郎拜帅》里演周瑜。“我让他和王学圻同演这个角色。不分AB角,一人一场,谁演得好谁多演。”王贵说。
濮存昕按捺不住问演小乔的肖雄,他与王学圻,谁演得好?“王学圻演得好。”她率直地回答,令他深受刺激。
“好,像你父亲,儒雅风流。”上演过程中,王贵表扬他。不想,他竟哭了。“他父亲苏民是人艺副院长,学养深厚,为人认真,性格难免融入表演风格。他爱他父亲,但不想在表演上像他父亲。”王贵指出濮存昕早期在舞台上的局限,比较拘谨,太过儒雅。
人艺老演员蓝天野看了《周郎拜帅》,找王贵商议,人艺要排《秦皇父子》,想借濮存昕扮演太子扶苏。
“他正演戏呢。”
“没关系,我们可以等。”
“濮存昕的机会来了,他能到北京人艺——中国戏剧的最高殿堂去演戏。”王贵当即表示,好,我们一起来培养这个年轻人。
1985年,人艺新春舞会。蓝天野把濮存昕叫出会场。听到消息时,濮存昕“脑子的魂呜呜地飞”,“心忍不住狂跳”,冥冥中,他想到了“落叶归根”。
没开悟的时候
“人艺有这么多演员,非要上外面借人?”时任院长于是之问。
“那我就不排了。”蓝天野也不多说。第二年,五六月间,濮存昕进入人艺剧组。
“演得不好,令蓝老师有些失望。”他的概念化表演、附在台词表面的情绪、不高级的创意等,让蓝天野在他独白时,多次叫停。见他不开窍,排练场有一块道具石头,蓝天野一脚踢过去,没踢开,反而把脚踢疼了,一个人在那儿倒吸凉气。
人艺艺委会审戏,曹禺、于是之都来了。审完戏后,曹禺开诚布公,台词不清楚,听不明白,这里也包括老同志。扮演秦始皇的老演员郑榕低着头。
濮存昕向于是之请教,于先生的话却让他云山雾罩——“你要明白这个角色的人生目的、理想是什么,他为什么这么做,再去分析产生动作。” 若干年后,他才理解,于先生说的是表演规律。
见他郁闷地坐在角落里,郑榕叫他出来,“孩子,台词可不能这样说啊。为了你最高最核心的目的,你得有轻重缓急地念台词,台词要有思想,要研究,表达潜在的意思。所谓潜台词,就像溪水,上面的一片叶子跟着水流呀流,到了一个地方就形成小漩涡,叶子就打转儿,尔后就平稳了,又跟着水流呀流。水就是一个人的思维,永远是流动的。”
“现在回头看,都是因为做演员的底子没打好。进了空政话剧团,跟着王贵演戏,他的表演要求多夸张。《周郎拜帅》一上手就是能乐式表演方式,等于还没学会素描,就玩起现代派。可人艺要的是现实主义,如果是美术界这就叫古典现实主义画派。我虽然尽量照其要求在做,但还是不住地想表现什么。念台词就是声嘶力竭用劲,以为叫激情饱满。没办法,人到没开悟的时候,别人掰开揉碎,往你耳朵里灌,也没用。”
《秦皇父子》演出后,尽管私下有议论他的表演“怎么看着磕磕愣愣”,但人艺还是留下了他。
又出了一个演员
1993年,濮存昕参演田壮壮的电影《蓝风筝》。
时值中国第五代导演抨击以往银幕上表演的概念化、雷同化。田壮壮便是其中之一,他要求演员表现自然,不要太过理性。“一旦开拍,他很少找你设计。”有一次,濮存昕想和导演“谈谈今天的表演想法”,田壮壮瞪起眼珠子:你累不累呀?
他告诫自己,戏剧和电影在表演上有分别,别夸张,别过火。“但表演习惯还是不自觉在摄影机前露馅。
哎呀,惨不忍睹。看样片时,他脱口而出。摄影师侯咏掉过头来,半开玩笑,你也知道呀!他再次受挫。
这一年,他在话剧《鸟人》里扮演心理分析师。他不自信,“这部戏全部是一种荒诞的环境,用惯有的思维和创作方法还真不行。而我在之前也没接触过荒诞戏,有点懵了。”
第一次彩排后,他对采访记者坦言,还没进入状态,“上台前,腿肚子会转筋。”记者也直言:看了连排,你的表演不如林连昆、梁冠华出色。“我那时的表演还停留在表层,紧张,不放松。”
“渴望出成绩,渴望成名,我期待了很长时间。30年前,没人理我,没人找我拍电影、电视剧。那种受压抑、被机会捉弄的感觉,我经历多了……”濮存昕曾向戏剧理论家童道明袒露心迹。
那时,他经常到景山公园,闭着眼睛练灵感,张开嘴巴念台词。郑榕的话,他从未忘记。演员高亚麟比濮存昕晚进空政,他记得那时每天早上,全团只有两人晨跑,一个是主演《便衣警察》的胡亚捷,一个是濮存昕。他还和一块跑龙套的同学感慨,任何人的成功,都是有道理的。
“又出了一个演员。”1989年,谢晋执导电影《最后的贵族》。首映时,男主角濮存昕接受采访,谢导在一旁欣慰地说。
影片里,他手捧鲜花走向女主角,童道明看后打心底说,真干净。他告诉濮存昕,“这种感觉是从内到外、从外到内的纯净。这是你最可珍惜的艺术素质。”
接下来,谢晋拍摄《清凉寺钟声》,濮存昕主演明镜和尚。为体验生活,“开拍前,我曾在上海圆明讲堂生活了一天。
“天才蒙蒙亮与他们一同起床上早课,……当走队列时,我排在最后,身后好多里弄里的大妈大婶,她们都是居士。”女居士们直愣愣盯着他,从没见过这么高大英俊的和尚,你是从五台山来的么?
高亚麟大声笑道,一朋友从外地来空政,无意中瞥见濮存昕在跑步。于是,那位女粉丝疯了似地冲去房间打电话,你知道我见到谁了——濮存昕!
稍有名气那会儿,濮存昕一家三口还蜗居在空政宿舍里。平房,没有卫生间。最尴尬的一次,电视热播《英雄无悔》时,他上公厕,一帮老少爷们在背后指指点点:看,这是高天。
得意之作《哈姆莱特》
《纵火犯》是他和林兆华的首次合作。当时,林兆华拉他演戏里一个救火队员,几乎没台词,穿着防火服在台上跑。见他不太乐意,林兆华鼓动说,“来,放松一下,到我这里练练。”
参演《巴黎人》,他第一次感觉表演“有自己真实体验的东西了。演员演角色时要有自己,不是演别人,要坚信——我就是”。
连排时,林兆华为看其他人而来,却敏锐察觉到濮存昕的变化。演完后,他张开双臂,过来拥抱说,终于松弛了,太好了!
1990年,林兆华建立艺术工作室。最初,杨立新、梁冠华等演员都曾与他有过合作。
“他们后来回来了。没人和他排戏,他来找我。”林兆华邀濮存昕主演《哈姆莱特》。
“我怎么可能推辞?”1981年,他在上海部队文工团演出时,观看了老艺术家孙道临配音的电影《哈姆莱特》,大为震动,“心说自己别演戏了,绝不可能演到别人那份上”。没想到埋藏在记忆深处的梦,能够得以实现。
对于林兆华,重排《哈姆莱特》另有意义。1989年,他的好友,上海青年话剧团导演胡伟民突然逝世。他曾流泪说,排演《哈姆莱特》是好友生前未了的心愿,他要去完成。
夏天,工作室开始了3个月艰苦排练。大家都知道,没什么报酬,除了不想按传统方式排演这部莎翁名著,其他都在探索中。
“当我们在排演场上每走一步都觉得艰难时,导演就让停下来,先念台词。”有时,他干脆睡在地上念,寻找感觉。极富哲思的台词,让他想到了插队时牧马,日头晒得人懒懒的,他躺在田间地头,思虑自己的前途。
“我是现代人中的一个哈姆莱特。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有着哈姆莱特式的感受,我用自己真诚的心理矛盾和动作逻辑表达哈姆莱特的生命,这是最重要的。甚至我在这部话剧的排练过程中,也曾真切体会过‘默默忍受还是挺身反抗’的痛苦。我像哈姆莱特一样骂着自己,同时也强烈地感受着个性、自由被压抑的愤怒,这是我与角色融合的最重要的一点。”
他的这番体悟与林兆华的思考相通。林兆华想透过戏传达,“我们今天面对哈姆莱特,不是为了面对为正义复仇的王子,也不是面对人文主义的英雄,我们面对的是我们自己。”
1990年年底,《哈姆莱特》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小剧场上演。
当看到濮存昕在台上念起“生存还是毁灭”时,童道明感到“他确实像进入哈姆莱特的精神和灵魂的状态”。
“过瘾极了,有种天马行空的感觉,连我自己都被自己感动了。”他后来向童这么形容。
谁的心中都有索尔尼斯的影子
“林兆华在表演上给了我一个空间,让我知道原来还可以这样演戏。”濮存昕说。
但父亲并不欣赏他演的哈姆莱特,“他们认为故事就是故事,好像只能是写实画派。我们却在这部戏里,加了一点毕加索的玩意儿,他们不喜欢毕加索。”
2005年,易卜生逝世百年。林兆华排演了大师的作品《建筑大师》。濮存昕主演索尔尼斯。
两年后,电影《兰陵王》导演胡雪桦向童道明坦言,上世纪80年代,他与濮存昕在王贵导演的《WM,我们》中,是一个角色的AB角。那时,他还看不出对方的艺术前景。可在上海看过《建筑大师》后,他大为惊讶,认为濮存昕已具有大演员的风范。
提起索尔尼斯,濮存昕身子向前倾,眼里闪着光芒。童道明评价他在这部戏里,进入了从未有过的“大自由、大自在”。
在林兆华设计的极简空间里,情景被抽干,濮存昕蜷腿坐在一张红皮沙发上,成了索尔尼斯。他使用“评弹艺人”的叙事手法,深沉自如地展现索尔尼斯对妻子的冷酷、内疚,对助手及情人的压制与利用,对青春的渴望和惧怕。鹰一样的女孩希尔达的突然闯入,让他发现了真实的自己。
白岩松看完戏的当天,给他发来一条短信:我们谁心里都有索尔尼斯的影子,可谁也不可能成为他,要不然一定会死掉。
多年前,濮存昕主演契诃夫的《海鸥》时,莫斯科大剧院导演叶甫列维夫启发他,如果你能从外部,尽可能平静地把内心汹涌的激情表达出来,你的表演将会再上一个台阶。
“这么多年在艺术上的探索,今天在有些作品中做到了。”他有自信。因为索尔尼斯,他被媒体评为“中国最形而上的演员”。
假如我能更勇敢
“怎么看待戏剧?好比我们对灯的认知,认为一定要有灯泡,要有电源。完全不能想象它是液体的,那还会是灯么?林兆华就敢将灯做成液体的。
“他当初喜欢的是宋丹丹、梁冠华这样的演员,而不会是我。我的进步过程,也是他们所没有的。”他说不清,自己具体哪一天灵光骤现,“肯定是慢慢积累所至”。
十多年前,童道明曾问林兆华,为什么选择濮存昕。林兆华说,濮存昕具备成为大演员的气质。其次用功,他也许不能很快找到人物的感觉,但相信通过努力,一定能够找到。有他在自己踏实。第三是为人很正。最后,他热爱戏剧,如果有好戏演,愿意推掉高片酬的影视剧。童道明将他们二人的合作,比为人艺创始期焦菊隐和于是之的联手。
“濮存昕是个敏感的人,有时敏感到了伤感。‘我总觉得于是之不太欣赏我。’我不止一次听他这样说。濮存昕大概曾有过一个心愿: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于是之相信自己的能力,欣赏自己。”
童道明透露,由于对现实主义作品持不同观点,人艺有些人不满于是之支持林兆华对戏剧的改革,“在人艺60周年会上,于是之的艺术几乎被埋没”。林兆华事后得知,说要批就批我好了,干嘛要批老于呢?
那天濮存昕没有参会,他和母亲、妻子一同去医院,看望已经失忆的于是之。
于是之是怎样的?濮存昕忽地立在我跟前,“他会看透你心里想的。他什么招都懂,就是不支招。这才是真正的高人。”
敬佩之余,他说绝不做于是之第二,“于是之担任院领导时,太痛苦了。《洋麻将》里,你看他出牌的神情多么纠结,那是内心的真实写照。”
他曾在书中说,“2003年4月11日,上级任命我做人艺第一副院长。……这时又为什么答应了呢?……更大的动力是,想为林兆华导演提供更大的艺术空间。他毕竟年纪一把了,有个好的戏剧环境很重要。……现在人艺需要一个艺术总监,林兆华可以担当起这个角色。没想到的是,我的提议遭到了反对,甚至剧团里面也是异议之声,上面的意思更是,林兆华要退休,不应当担当职务。这让我很不开心。接受这个职务后,剧院还给了我一间新办公室,配了奥迪车,但我觉得这都有如囚笼一般,完全把我困住了。”
童道明清楚,某个周末,濮存昕骑车来到北京市委,将辞呈放在了传达室。
采访结束时,濮存昕平静地说,如果我能够像林兆华一样勇敢,在关键时刻不在乎任何批评,我会是一个更棒的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