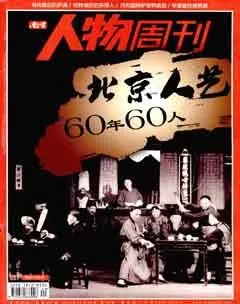25于是之 大师不能满街走
2012-12-29 00:00:00李宗陶
南方人物周刊 2012年40期



1992年7月16日,于是之和他主演的看家大戏《茶馆》最后一次登上人艺舞台。这是第374场。
伴着大傻杨的数来宝,大幕缓缓拉开。第二代《茶馆》四十多位演员已在百年老店“裕泰”里各就各位。但演着演着,王掌柜卡壳了,说不出台词,蓝天野巧妙地接了下去。于是之望着已出场的郑榕,叫不出“常四爷”,郑榕就见他脑门子上的汗,哗哗往下流。跟秦二爷一场对白,于是之也吃了螺丝。总共4处。他的手是抖的,腿也在抖。
两三年前,于是之就已有上台偶尔忘词的现象,这是患病后的表现。那一晚,从开演前他坐在镜前慢慢化好妆、逐一摸过每件道具、拨拉过柜台上的算盘珠子起,就已经是一场不寻常的告别了。
漫天的纸钱扬起,王掌柜拿起搭在椅背上的腰带,返身走向后台,一场悲剧就这样结束了。
谢幕时,于是之几次走向前台向不肯停止鼓掌的观众鞠躬致意,或致歉。有观众喊:于是之老师,再见了。又有人喊:是之,你好;是之,别走。于是之淌着泪走下来,喃喃道:观众太宽容了。他有些踉跄地走回化妆间,险些撞在门上。
1993年参加《文汇报》55周年纪念活动,于是之已经不能说话了。老友林连昆握着他的手,代他发言,他在一旁频频点头。讲到至情处,两个老头都掉眼泪,在场者无不动容。
演绝了
60年前,北京人艺上演开幕大戏《龙须沟》,主角程疯子的扮演者,是于是之。
这个人物在老舍先生的剧本里是这样的:“他有点神神气气的,不会以劳动换钱,可常帮忙别人。他会唱,尤以数来宝见长……原是相当不错的艺人,后因没落搬到龙须沟来。”
焦菊隐先生排演《龙须沟》,用的还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剧理论,要求演员在舞台规定情境中“生活生活再生活”。他给每位演员发两个笔记本,要他们记下体验生活、分析剧本的心得。
于是之把疯子定为“旗人子弟,唱单弦的;不是‘革命的候鸟’,只是个可怜人,倘若不是北京解放,他是没有活路的”。他花了很长时间泡茶馆、学唱单弦,写了6000字人物小传,才把这个纸上人物请到了台上。上一辈人艺人,大抵是这样做活儿的。
程疯子让于是之一举成名。人们口口相传:可不是么,石挥的外甥,遗传!于是之后来写了篇《信笔写出来的》,澄清说:“他不是我的亲舅舅,我母亲的娘家姓任不姓石。我所知道的只是我母亲管他母亲叫四姨,我则称他的母亲为姨婆婆。”不过,他从小受石挥、石诚兄弟感染,先被同学拉去演戏,后由石诚介绍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祖国剧团倒是有的。那年,他18岁。
剧作家黄宗江1946年就认识于是之,最初对他演戏的评价是“称职”。但程疯子把他给震了:“那是他演得最好的几个角色之一,可以说演绝了。这出戏可以说奠定了人艺的基础,也奠定了于是之的基础。此后《茶馆》里的王利发,也让他给演绝了。”
“但他最好的戏,是《骆驼祥子》里的‘老马’,比《茶馆》还要精彩。就十几分钟戏,把一个老车夫刻画得那么生动、深刻。我觉得更多是因为生活的积累。于是之演这种老拉车的太熟悉了,这就是他早年生活里经常见到的,一招一式一举一动,都来自生活。”
黄宗江说:“表演上,不能说他就一定是最好的。可是想想,在20世纪后半个世纪,没有超过他的。”称他为“一代演员”。
于是之在台上的气场不是那种“我来了”的霸气型,不怎么张扬,也不显山露水,只在不经意间,把人物的神和气带出来,让人记住、回味、难忘。
台上台下,行业内外,多少人喜欢、佩服他的表演。姜文念大三的时候,童道明问,看过多少回《茶馆》,姜文说,已经记不清楚了。而中戏表80班排演《骆驼祥子》的时候,有位负责老师对班主任张仁里说:“老张,你什么时候来我的课堂看看,姜文活脱脱一个‘于是之第二’。”
上任了
曹禺曾说:“是之谦称是我的学生,其实很多方面他是我的老师,尤其他的艺术和他的道德品质,我非常喜欢他。”
可能因为这份喜欢,于是之在57岁被任命为北京人艺第一副院长,转向另一种人生。曹禺郑重地对他说:我把剧院交给你了。很多人都说,这对人艺是幸,对于是之,是不幸。
都知道人艺有个焦菊隐先生创立的演剧学派,于是之是这个学派的领军人物。他内行,有眼光,知道人艺需要什么,于是在80年代自然而然走到一个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位置上。
戏要好,剧本是关键。写出《天下第一楼》的何冀平记得,当时人艺最核心的部门不是院长办公室,而是编剧组,组长是于是之。“创作环境非常宽松,不用坐班,人艺也不管你在干嘛,可以说就是整天‘供着’你,把你当宝一样看着,你能感受得到。但于是之每周都会组织我们六七个编剧一起聊天、吃饭、喝酒。后来他当了副院长,工作很忙,但编剧组每周一聚雷打不动。”
郭启宏记得他把于是之从会议室叫出来、交上调人艺后写的第一个本子时,于是之眼睛一亮:有啦?写的什么?《李白》。
何翼平说,于是之每次都是恭敬地双手接过剧本,就像是接过你的心血。他会把自己关在家里,认认真真至少看两遍。
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总有些复杂。分房子、搞福利,于是之一定是首先想到编剧,他曾把自己的房子让给李龙云。“编剧组当年有7个编剧,个个不是省油的灯,个个都不好伺候。但我们就感觉是被捧在手心里,被爱护着。”
苏民说,于是之实际上是在“文革”后为剧院积累了一段时期的原创剧本。林兆华说,那是一段人艺创作的黄金期。于是之的艺术感觉和鉴赏力,他的号召力和凝聚力,让北京人艺在80年代浮躁之气已经抬头时,充当了一个稳健的角色。
舒乙说,这段人艺历史上的小小复兴,是用两条腿走路的,一中一外。于是之调回英若诚,请来3个国家的4位名导演给人艺排戏。托比·罗伯森,排莎士比亚名剧《请君入瓮》;阿瑟·米勒来指导《推销员之死》,开创了洋戏土演;查尔斯·赫斯顿,《哗变》;1991年,于是之在身体备受病痛折磨的情况下,赶到首都机场迎接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总导演叶甫林莫夫,来指导契诃夫的《海鸥》。
他着意培养青年导演。中戏的任鸣,是于是之给中戏院长徐晓钟写信要来的。1987年任鸣刚毕业就进了《太平湖》剧组,任林兆华的副导演。外援来访期间,于是之特意安排他做大师们的助手。“他就是要薰我,这种培养让我受益终生。”如今已是人艺副院长的任鸣说。有一次,他向任鸣敬酒:来,我跟未来干一杯。
濮存昕也是他由空政话剧团调到北京人艺的。之前被借调演《秦皇父子》中的扶苏,濮存昕曾经请教过怎么理解这个角色。于是之说,一个人的命运、坎坷,总是跟他的追求有关。许多年后,濮存昕才真正明白其中的涵义:演戏需要文学能力,那是演员对人、对生活、对历史的理解。
很多人都认同于是之不适合做官,他的身体也是在那8年任期里垮掉的。但李龙云觉得,回过头看人艺的那批“保留剧目”,没有一部不是在于是之主持业务期间创作、演出的。包括林兆华走出的非现实主义路子,也都得到过他的理解和支持。就培育创作、以知心朋友的身份非常内行地鉴定剧本、帮助作家进行修改、把那些文学色彩很浓的文学搬上舞台等等而言,能够做到于是之那种地步的人,凤毛麟角。“我甚至想过,如果于是之自始至终只当那个剧本组组长,而不去当那个副院长,或许他能一直工作到今天。但我不知道他能不能耐住那份寂寞。”李龙云说。
王蒙记述过他出任文化部长前的一个小插曲。有一天,忽被中央领导召见,参加会见的还有唐达成、徐惟诚、于是之等人。领导开宗明义,让提新的文化部长人选,又问:“你们几个人行吗?”于是之把头摇得像拨浪鼓。
回去后,于是之有一点动心。后来一想:我还是在剧院眯着吧,好歹还能逮着功夫演点儿戏。对于那一辈还记着立身、立言、立功的人,权力是一种诱惑,更是一种责任。他们沧桑、纯良又有些驳杂的心,恐怕未曾计算过要为之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因为他们,还没有今天这点儿脆弱的自由度。
复杂了
于是之的书架上,有一幅莎士比亚小像,书房里高悬自书的“学无涯”三字。学历上,他初中毕业。骨子里,他是个勤奋的书生,狷介的诗人。
他爱读书。郑榕和杨立新都对他在百忙中逮着一点空就拿本书看的样子,印象深刻。当领导后他说,我最大的乐趣是读书,最大的苦恼是没有时间读书。他谈到与上代人艺前辈间的文化落差,说只有静下心来,向书本讨教学问。
他的笔墨文章都好。舒乙说,于是之的文章极短,文笔精粹,立意奇妙,而且品位很高。于是之曾给苏叔j4eKxNPtukAHH8s2fMu5JgmiuZra/V4AKB1vixJHF10=阳念过他写的《祭母亲》,苏流泪了。
于是之最初练书法,是为了演好毛泽东,练的是毛体。后来临了许多帖,钟情于宋代米芾。他在书法上下过大功夫,发展出一种似米非米的行书,笔意苍古,字体劲健。
1979年,于是之陪赵丹去灯市西口丹杮小院看望老舍夫人胡絜青。一时兴起,三人展纸研墨。赵丹画了一张《杮杮如意图》,胡絜青在枝头添上一只朱喙小鸟,于是之题字。画完几幅,赵丹发现自己没带印章,于是之忽然说,我给你刻一个。拿来一块洗衣皂,切巴切巴刻成一枚不规则小土豆形状的“阿丹画印”,老舍女儿舒济在一旁看得又惊奇又佩服。
戏剧、美术评论家柯文辉甚至断言,于是之字和文的造诣,在北京乃至全国演员中都是数一数二的,只是他做得很随兴,无心插柳的样子。
柯文辉曾经张罗着把他的书法“推向社会”。但很快,于是之对他说,上面号召要搞严肃文艺,卖字太不严肃了,穷就穷吧。柯文辉说,字还没卖呢,他就觉得自己犯了错。一方面,可以看出他心里雷池太多,另一面是书生的清高之气还在。剧评家杨景辉记得,有位大商人曾出高价请他写一块招牌,他谢绝了:我不卖字。
晚年于是之写过一幅“留得清白在人间”。写完,他跟这幅字合了张影。
童道明说,于是之是一个对为人禀性极为看重、对虚假和庸俗嫉恶如仇的人。在他面前,你不敢装模作样和虚情假意。
但李龙云发现,有一阵于是之私下里爱谈曾国藩的“驭人之道”。此道,无非是上司对下属的“权谋”,堂皇些,就是善于使用干部、调动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他本一介书生,却想懂一点“驭人之道”,这与他的心性不符。于是他,很苦。
“我在旁边,看他对所谓‘权谋’的理解和实践,发现他对一些骨子里原本轻蔑的被他讥为‘名利之徒’的人,施舍起名利却出手慷慨——那的确是一种施舍。在满足他们的背后,他又是那样冷漠和蔑视。他几乎具备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全部复杂与矛盾。”
累垮了
于是之有了大名声,还是只去街边小铺子剃头,把富贵名利看成淡云轻风。他身上确有王利发、程疯子这些北京平民朴实无华的品质,同时又透出一种他独有的不显山露水的高贵和尊严。
有一回,几位记者称他大师,他听了两夜睡不踏实。他问老友,什么叫大师。人家告诉他,以前无古人的审美内容和审美方法,在艺术史上开宗立派的不朽人物,叫大师。于是之说,那请你写篇文章告诉大家,大师不能满街走,我不是大师,只是个普通演员。
童道明说,一个演员具有自己的风格相对来说还是容易的,但像于是之那样既有风格又有风骨是很难得的。陈白尘曾致信他:做戏与做人是一致的,有些人只是会做戏而已,未足与兄并列。
一个对做人有要求的艺术家当上了行政工作者,人情、品格遇上政策、权谋,他又要做人又要做戏,不分裂也难。
老伴李曼宜是连小组长都不让他当的,说他实在是不太会当官。因为出国、分房子、评职称这3件事,于是之被人堵在家门口骂过街。他也只能等骂街的人走了,才把刚倒上酒的杯子摔在地上。
有一次,他和前辽宁人艺院长李默然去广州开会,在饭桌上突然犯晕,险些摔倒。李默然扶他回房后,两人聊了一些心烦之事。李默然说,“我感觉我们俩这种思维和追求,不是当院长的料,我已下决心,今年年底最迟不过明年,坚辞不当了。是之老兄,不怕得罪你,我劝你也别干了。”但于是之心里还放不下领导的重托和同志们的希望。李默然说,“完了,将来你肯定累垮。”
后来,于是之终于想明白了,他对记者说:“尊重知识分子,尊重人才,不是给个官当就算尊重了,关键在发挥他们的特长,施展他们的才华。干部专业化,不等于让知识分子当官。”他也常常讲起“一个内行变两个外行”。他甚至对医生说,您给我写上:这种病不能当领导。相知60年的苏民说,如果让他一辈子当演员,他就得其所哉了。可是,晚了。
焦躁、暴躁、愁烦,任职8年里,冠心病、脑梗、老年痴呆症一样一样找上门来。于是之最后留在人艺影像资料里的形象,是嘴不由自主地、嚼口香糖一般总在动着,那是颚部神经出了问题。他常常不能用完整的句子表达出一个意思,但这个国家级的艺术殿堂仍然需要他。1992年,40周年院庆让他不得不抖擞精神,开会、出版,拜望前辈、迎迓领导,他的嘴,总在不由自主地、嚼口香糖一般,动着。
从1992年起,思维和语言抽丝般从这个以说话为生的人身上一寸寸抽离。到2008年中,他不再发出任何声音。如今,他躺在北京协和医院一个清洁的病房里安睡,这一觉已经睡了4年。老伴每天去医院陪他,告诉他发生的各种事情。“我知道他懂。他人在,我就觉得家没有散。”
敬重他的人也没有散。濮存昕扶着父亲苏民去医院看他,童道明固定在每年的正月初三下午去看他,姜文今年春节也去过。已经半身不遂的林连昆曾用左手一笔一划吃力地写下一行字:“是之我很想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