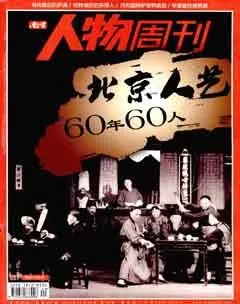12焦菊隐 先生先去也,一戏一丰碑
2012-12-29 00:00:00余楠
南方人物周刊 2012年40期



如果不是天上那轮圆月,很多人不会意识到3天前是元宵佳节。刺骨寒风呼啸而过,月光冷冷的银辉笼罩着熟睡的北京城。这是1975年2月最后一天的深夜,黄历写着:“2月28日,农历正月十八。宜:作灶,扫舍,平治道涂;忌:出行,祈福,行丧。”
潘小丽突然惊醒,没有任何来由,只感觉胸口异常难受。她看了一眼时间,不到凌晨5点。没过多久,传达室传来了通知:焦世宁,协和医院来电话了,让你赶紧去。焦世宁是她10岁的儿子。在医院住院的是她前夫,二人在1966年6月离婚。
焦世宁一生都不会忘记那天经历的一切。在医院的太平间,他见到了父亲的遗体,身上什么也没穿。这是“军工宣队”针对父亲的“反动罪行”下达的命令之一,“不许穿衣服,只能用旧床单包裹火化。”父亲的遗体在冰冷的太平间已经停放了两小时,焦世宁扶起他时,“后背还是热的”。
这位一丝不挂的死者是导演焦菊隐,一代大师在凌晨5时18分走完了跌宕一生,终年70岁。
焦世宁身旁、同父异母的姐姐焦世安没流一滴泪,“我的泪已经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流干了。”父亲离世前这十来天,都是她在医院照顾。现在,她只觉得“悬着的心放下了”。被癌症和绝望折磨了这么久的父亲,解脱了。
我逃不过这一劫了
1964年的一天,正在家中伏案工作的焦菊隐接到医院的电话,妻子潘小丽刚刚分娩。“带不带把儿?”焦菊隐问。电话那头的小护士没明白这是在问孩子的性别,“不带把儿。”听到答复后,焦菊隐重重地砸下电话挂掉了。过一会,电话再次响起,反应过来的小护士连忙纠正:带把儿,带把儿!
兴奋不已的焦菊隐放下手头全部工作,脱光了衣服,举着一杯葡萄酒在家中满院子跑。那一天,很多街坊都清楚地听到干面胡同这个小院里传来的狂喜:我有儿子啦!
这个孩子就是焦世宁,他是焦菊隐在59岁这年获得的人生礼物。与潘小丽结婚前,焦菊隐有过两段婚姻。他和第二任妻子秦瑾育有两个女儿:大女世宏、次女世安。第一任妻子林素姗曾为他生下两个儿子:毛毛(世缨)和贝贝(世绥),后来都不幸夭折。
多年后,焦菊隐依然为最爱的毛毛早夭深感自责。他曾对秦瑾说:当年我为了办戏校(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每天要看戏,接触各种戏曲、曲艺,每天回来都晚,毛毛已经跟阿姨睡了,客厅里一桌子麻将。我总是不与他们招呼,一个人上楼,读书或睡觉。我觉得对不起这个孩子。我爱他,却从没关心照顾过他。
“焦先生排戏做事较真,骂起人来特别损,招人恨。”对很多和他共过事的人来说,儿媳牛响铃透露的不是什么秘密。当年在广州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导演创作会,焦菊隐曾当众指着一位名气不小的导演说:你那个脑子里就是一泡屎!秘书张定华也曾回忆:当年排练《明朗的天》,一位演医生的演员拿着一顶礼帽正准备上台,焦菊隐突然说:你拿个帽子怎么像端个尿盆似的!当时这位演员极其难堪。
恨焦菊隐的人不止一次骂他“断后”,焦世宁的降生,带给了他前所未有的幸福感。每天下班之后,他第一件事就是闻儿子的尿布,怕伤及婴儿皮肤,所以不许有半点肥皂味。儿子兜里必须准备3块手绢,擦嘴、眼、手分开专用。
1966年元旦,焦菊隐深夜之际依然在伏案写日记。在这些思虑深重、心惊胆战的文字中,已经出现了“群魔”这样的字眼。这不是他第一次感到害怕。1957年“反右”时,人艺贴了很多揭批他的大字报。他不敢看,经常悄悄约前秘书张定华到长安街纺织部附近,打听大字报上的内容。因为市委领导和院党委书记赵起扬的保护,他没被打成右派。但这一次,他不会再那么幸运了。
“走资派所包庇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老反革命”、“头号黑帮”,这些帽子很快就扣在了焦菊隐头上。“红卫兵”把他从原来住的院子里赶出来,与妻儿隔离,他的新家是厕所前面一个不到八平米的潮湿阴冷的小平房。他不能再做导演,每天的工作是打扫大院。妻儿单住的小屋不许挂窗帘,红卫兵随时要检查,确保他们没有和焦菊隐偷偷见面。母亲后来告诉焦世宁:父亲每天打扫时,眼睛都在偷偷寻找儿子的身影。夜里12点以后,窗户上会出现一个人的帽檐,开门一看,很快就没影子。那是想念儿子又害怕牵连他们的焦菊隐。
焦世宁出生时,父亲在家里养了一只小猫。它像家中一员,陪伴着焦世宁一起长大。红卫兵冲到小屋,告诉潘小丽:要么掐死这只猫,要么掐死你儿子,两个只能留一个!小猫后来被活埋。即便如此,母子的劫难依然没有结束。因为是“狗崽子”,焦世宁刚端起的饭碗随时会被打翻在地。
焦菊隐给妻子写了一封信:我知道有很多人帮我说话,但是这一回,我逃不过这一劫了。我同意离婚。他对妻子最后提出两个要求: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不能抛弃儿子;不能给儿子改姓。
老舍啊老舍,带我走吧
从王府井南到西单,贴满了有关焦菊隐的大字报。无休无尽的批斗和检查在等待着他。造反派有些吃惊:这位干瘦的老头每次交来的检查都是十几页,张张字迹清秀工整。他们永远不会知道,这些署名焦菊隐的稿纸,本该记录一些完全可以比肩国际戏剧大师的舞台思考。
1950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和外语系主任的焦菊隐,受北京人艺院长李伯钊邀请,执导一部歌颂新北京市政建设的大型话剧。他用7天7夜的工作,一口气完成了剧本修改。这就是《龙须沟》。
“《龙须沟》仿佛是一座嶙峋的粗线条的山,没有生活经验、粗枝大叶地去看,表面上是一无所有的。然而,这里边可全是金矿。”当焦菊隐在一份完全主旋律的作业里渗透进这些思考时,没有人会想到,新中国话剧舞台的源头和一种即将活跃数十年的中国话剧流派已然发端。
首轮连演55场的《龙须沟》,让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不同背景的人艺第一代演员第一次明白了生活和表演的关系,也让一个比新生政权还要年轻的剧院第一次触摸了舞台创作的本质。1952年,北京人艺正式挂牌成立。有着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的焦菊隐离开师大,调任人艺第一副院长。
5年后,老舍将一部为歌颂新宪法创作的四幕六场话剧交到人艺,焦菊隐把这个连名字都没有的剧本看了3天,提出将发生在茶馆的第二场发展为一部大戏,就叫《茶馆》。这部在当年招致批判被文化部停演的新戏,日后成为北京人艺通行世界的名片。
运动的狂风骤雨没有放过焦菊隐,也没有放过老舍。1966年8月23日,身为中国作协副主席的老舍,和作家萧军、京剧名家荀慧生等28人一起,剃着阴阳头、挂着“罪牌”、淋上墨汁,在北京孔庙被红卫兵批斗毒打整整3个小时。那天老舍被打得无法站立,转到附近一个派出所后,又被冲进来的红卫兵一顿痛打。第二天,67岁的老舍在西城区太平湖边呆坐一天,晚上投湖自尽。
几天以后,焦菊隐来到秦瑾家,“我来看看女儿。”
“我多少次想走老舍这条路,为了这两个可怜的孩子,我从护城河边又回来了。她们小小的年纪,读不了书,又当了狗崽子,任人欺凌。我什么也没留给她们,要是再给她们背一个沉重的政治包袱,她们怎么活下去?”他对秦瑾说,“你我多少年有个习惯,每晚上床脱鞋时,总要默念着明天该完成哪几件事,可现在我每晚上床脱鞋时,心里老默念着,老舍啊老舍,我是紧排在你后面的一个,带我走吧!”
在人艺“黑帮”里,焦菊隐年纪最大、职务最高。赵起扬后来回忆:“当时我48岁,焦菊隐已经62岁。他身体不太好,脚和小腿一直浮肿,而且还患有视网膜脱落,视力很差。尽管如此,不论是在批斗会上做“喷气式”,或被连续批斗站5个小时,或劳动时抬两百斤的垃圾箱,或两个人到郊区一上午装满一车沙子等等重劳动,他都毫不含糊地干得很出色。除了我听说他在青少年时受过苦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这个人做什么事都不甘落后,每做一件事都要求自己做好。”
牛响铃至今记得“文革”期间亲眼见过的一幕。那一天,焦世宁回到人艺看望父亲,父母离婚后,他每周可以回来和父亲短暂相聚。当时焦菊隐已经没有收入,每月能领到的是最低的生活费。他用攒了很久的钱,给儿子买了一双新球鞋。牛响铃看见,那天焦菊隐正蹲在地上,给儿子系鞋带。边系边抬头,微笑地看着儿子,脸上没有一丝愁苦,满是幸福。
交代材料比斯坦尼一生的著作都多
“文革”结束后,焦家一封家书被发现。这是焦菊隐在大女儿世宏生日前写给她的祝贺信,其中有这样4句话(大意):我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将来还要做导演的;我现在没有钱给你买生日礼物;希望你一定要努力学习。老书记赵起扬生前跟人讲起这件往事总是会说:焦菊隐一生中最大的愿望就是做导演、排戏,他就是想在中国话剧艺术这块土壤上搞出点真名堂。
“文革”中,已经更名为“北京话剧团”的人艺排了一个歌颂农村干部搞阶级斗争的新戏《云泉战歌》,根据当时针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要“一批、二用、三养”的新政策,“军工宣队”希望听听焦菊隐的意见。
一位深知他执拗个性的演员好友知道没办法拦住他,看戏前来到小平房提醒他:如果非去不可,我有3个办法供你选择:一,看完后一言不发,这样他们就抓不住你的辫子,顶多说你不积极;二,光讲好的方面,一个字也不要批评,顶多说你有顾虑、不诚恳;三,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这可能最危险。我不希望你选第三种办法,因为后果不堪设想。
焦菊隐笑了笑,没吭声。看连排那天,他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特意换了一身半旧但干净笔挺的灰色毛料中山装,一个人走进三楼排练厅,在最后一排坐下。看完后,没人找他,他起身回家。
第二天,军工宣队来听取意见。焦菊隐安静地想了想,说了一句话:政治上刚及格,艺术上只能给20分。这15个字,是焦菊隐一生中最后一次发表创作意见,它至今依然回响在很多人耳边。后来它成为焦菊隐被批为“为黑线翻案”、“死不悔改”、“反攻倒算”,多次遭受大批判的重要罪状。
你为什么非要这样?朋友问他。“你跟我排了不少戏,你了解我。我这一辈子都是凭艺术家良心办事。”焦菊隐眼里含着泪,“我知道,我再也不能做导演了。”
确诊肺癌晚期以后,焦菊隐住进了协和医院。医生没有直言相告,他不知道,这位年近七十的老人精通拉丁文,他扫一眼床头卡就什么都明白了。焦菊隐向组织提了惟一一个要求:让下乡到山西的大女儿世宏回来照顾自己。
其实他心里惦记的是另一桩心事。病床前,他对女儿说:我在“文革”中写了几百万字,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一生的著作都写得多。可惜,全是交代自己反动罪行的材料。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留下来,但还有一些多年做导演的心得体会,一定要把它留给后人。我自信自己还可以再活两年,你要把我说的都记录下来。
准备好纸笔的女儿终究没能记下一个字,对放化疗反应剧烈的焦菊隐病情恶化的程度连他自己都没想到。弥留之际,“军工宣队”负责人问他:焦菊隐,你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问题要向组织交代?看着微微摇头的焦菊隐,负责人向家属下达了3条命令:除了死后不许穿衣之外,骨灰盒只能用最便宜的,7块钱的那种;不许立碑,骨灰盒存放在八宝山公墓地下室。
焦菊隐跟亲人说的最后一句话,是问回京不久的大女儿:你的户口落上了吗?
永远的痛
“焦菊隐在北京人艺尽心致力于中国话剧民族化的创造,奠定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础。他创造了富有诗情画意、洋溢着中国民族情调的话剧。他是北京人艺风格的探索者,也是创造者。”1982年,人艺院庆30年之际,曹禺写下了这段文字。
3年前的5月22日,为焦菊隐平反的追悼大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重新担任院长的曹禺在大会上致悼词。于是之写下挽联:先生先去也,一戏一丰碑。
也是在那个阴雨连绵的5月,“文革”期间彻底停演的《茶馆》复排上演。北京大学一位名叫范西蒙的法国留学生看完演出后,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提笔写了一封信,希望《茶馆》能去法国上演。不知往事的他,写的收信人是:焦菊隐。范西蒙的愿望在1980年的秋天成为现实,《茶馆》代表中国话剧第一次走出国门,在西德、法国、瑞士做了50天的访问演出。西方剧评人称赞它饱含“现实主义风格、中国民族特色,以及完整和谐的舞台艺术形象”,堪称“东方戏剧的奇迹”。
家人将焦菊隐葬在早年夭折的大儿子毛毛的墓旁,他终于有了机会弥补一下翻腾在内心几十年的歉疚。但在病中,他想给后辈留下的到底是什么?
人艺老编剧梁秉堃认为焦菊隐最想写的,来自原来的两大创作提纲:《论民族化》和《论推陈出新》。“它们都是1963年年初,焦菊隐准备为探索话剧民族化和不断推陈出新过程中,所写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与感悟。原本他打算每篇论文要写到3万字至5万字。”
人艺老书记赵起扬生前也专门撰文,描述过焦菊隐的那些未竟理想:他对于话剧民族化的理论只写出一篇提纲,太可惜了,这是一篇影响戏剧发展的一个新课题;另外他很早就想排出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哈姆雷特》;他还想把《白毛女》改编成话剧,构思已经比较成熟。他要将原歌剧后半部分作重大修改,把喜儿这个人物贯穿到底;还有,他不仅要继续进行像《虎符》那样的民族化实验,还想对西洋话剧的各种流派做实验,来滋润丰富中国话剧。赵起扬回忆,“我所知的,只是极小的一部分。”
“夜里,我又梦到了一位眼睛里失去光芒、沉默而又愤懑、几乎不说话的老人,在直愣愣地、毫无表情地看着我……我无言以对。或许,这将成为我们心中永远的痛。”梁秉堃写道,“焦先生究竟还有什么话没有说出来固然重要,甚至于是之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见地,已经写出了几万字的提纲诠释,但这毕竟不是焦先生自己的话,可以想见其损失还是巨大的,这种损失是任何方式都无法弥补的。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尤其重要的是,应当认真思考一下:焦先生何以开始有话不敢说出来,后来又有话不能说出来,最终竟然把一些我们非常需要的话、想听的话又全部都给带走了。我想,这才是必须痛定思痛、永远牢记的沉痛教训吧。”
1985年,人艺导演苏民和戏剧学者左莱等人合写的《论焦菊隐导演学派》出版。6年后,在人艺为40周年院庆举行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通过一大决定:将这一学派正式确定为“北京人艺演剧学派”。
女儿世宏历经20年持续努力,终于将煌煌10卷的《焦菊隐文集》在父亲诞辰百年之际出版。第二任妻子秦瑾也从焦菊隐多年手稿中遴选部分,整理成书。在序言中,她感慨道:“焦菊隐原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外语系主任,他要是专心执教,没准平平稳稳地度过了这一生。我也常想,他精通英、法、德、拉丁文,要是他当初从事翻译工作,没准他能安然活到这个新世纪的来临。”
2012年6月8日,《茶馆》再次亮相人艺首都剧场。贾庆林、李长春两位政治局常委和满场观众一起重温了这部人艺经典。这是《茶馆》第618场演出。在演出说明书上,导演林兆华署名在复排艺术指导一栏。透过铜版印刷的墨香,导演一栏出现的依然是那个熟悉的名字:焦菊隐。
(参考书籍:《北京人艺经典文库:焦菊隐》《记忆深处的老人艺》《粉墨写春秋》《瑰丽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