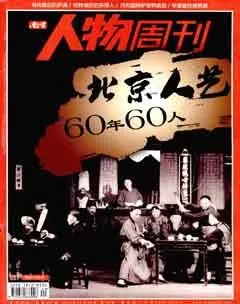01曹禺 我要写出一个大东西再死
2012-12-29 00:00:00李宗陶
南方人物周刊 2012年40期




1983年春,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亲临北京人艺,指导他的经典剧目《推销员之死》。曹禺邀请米勒到家里做客,其间拿出一封信,逐字逐句念给他听。信是画家黄永玉写来的,信中说:“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了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你泥溷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
一旁担任翻译的英若诚为难了,这还翻吗?全都翻,曹禺说。在人艺演员蓝天野看来,这些话,说到了曹禺的心里。
在他天津的祖宅里,有一面墙上曾挂着几十幅表情生动、飞扬夸张的照片,那是少年万家宝看戏归来,一个人对着镜子反复表演的集结:愤怒、甜蜜、遐想、鄙视……从23岁到29岁,这位官家子弟密集地写出了《雷雨》《日出》《北京人》等7部剧本。文学界开始知道一个笔名叫曹禺的青年,许多人说他“有天才”。
然而,从39岁到去世,47年间他再也没能写出一部自己满意而外界也公认立得住的作品。笔下的枯竭和名位的丰盛同时到来: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之一,著名戏剧大师,中国话剧奠基人之一,中国文联执行主席……还有,北京人艺首任院长。
晚年,他在痛苦中煎熬,自称“精神残废”。女儿、剧作家万方说,父亲是被扭曲和异化了的;一直到死,他都没能真正回到那个写《雷雨》时的自由自在的心灵。
在北京人艺的排练场里,高悬“戏比天大”4个字,这是演戏的祖师爷们代代相传的话,也是曹禺经常说的。然而,他这一生,终究没能以自己之戏,招架住那个“天”,甚至连抗衡都未曾有过。
人艺老编剧、曾任曹禺秘书的梁秉堃曾请教八十多岁的曹禺:90年代以后大家都不玩政治了,开始玩哲理,甚至哲理也不玩了,直接玩钱,您怎么看?曹禺答:这些个,都不是艺术的本性。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天”。作为一种美好愿景的“戏比天大”,或者将长久地高悬在那里。
当《雷雨》遇上阶级分析
1933年暑假,在清华大学图书馆二楼阅览室里写出《雷雨》的曹禺,没想过它会成为“中国话剧百年一戏”。
此时的中国话剧也是二十多岁的小年轻,刚从“文明戏”过渡为“爱美剧”。“爱美”,Amateur,业余;“爱美剧”就是非职业话剧,主要是文化人组成的业余剧团和学生剧团在探索尝试。剧目外引易卜生,内有先驱郭沫若、田汉等人的剧本。
这个大户人家的乱伦故事在他的脑子里已经生长了5年,有些人物就活在他身边。比如繁漪的原型就是某同学的嫂子:南方人,会一点评弹,二十多岁嫁给同学的哥哥当续弦。丈夫是个木讷古板的工程师,满足不了她感情上、生理上的需求,于是她就跟小叔子好上了。而曹禺生活的环境里,多有周朴园、周萍的散体。
曹禺花了很大功夫去写剧中人物的小传和札记。剧本中,每一个人物出场前,都有一段简短生动的介绍,文字相当漂亮。曹禺后来说,这些草稿,当年堆满了他的床底。
巴金是在北平三座门大街14号的一间阴暗小屋里,一气读完《雷雨》原稿的。他流泪了,但同时感到一阵舒畅,决意推动出版。许多年后,巴金在给曹禺的信中说,你比我有才华,你是一个好艺术家,你要多给后人留一点东西。
《雷雨》很快被搬上舞台,郭沫若看后大加赞赏,李健吾评论:一出动人的戏,一部具有伟大性质的长剧。今天,它在戏剧史上依然拥有突出地位。通常认为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戏剧走向成熟。
1953年,成立伊始的人艺着手选排优秀剧目,想从院长的成名作《雷雨》开始,此意得到周恩来的赞成。在他的帮助下,剧组找到了体验生活的去处。因为解放后,旧式的权贵大户之家基本绝迹,只有少数遗老能成特例,比如北洋政府高官朱启钤。
朱启钤支持建国有功,蒙周恩来特别庇护,能够延续旧社会的生活:深宅大院,帷幔重重,朱老先生出来见客,左右有姨太太和儿媳搀扶。吃饭时,女眷环列陪侍。这一切,让多数生长在新社会的演员大开眼界,然而半年下来,他们仍然很难进入角色。
演周朴园的郑榕说,按当时搞运动的潮流,采取阶级分析法为《雷雨》中的人物排队:周朴园是极右,鲁大海当然是左……每个演员被要求带着阶级感情去深刻揭露所演角色。于是,扮演繁漪的吕恩哭了:我演了十几年戏,现在我不会演了;过去也演过《雷雨》,怎么现在就不对了呢。
同样不能入戏的还有作者本人。从演员们体验生活到案头功课,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曹禺没有对他们讲过一句自己的意见。剧团有党组织,负责把握剧目的方向。演员白天演戏晚上开会,理清思想,端正态度。
有一天,曹禺悄悄去探生病的朱琳,拿一个小板凳,坐在床前,聊起朱琳扮演的鲁侍萍。
“这鲁侍萍啊,你现在觉得有点别扭是不是。”
“对对,是觉得别扭。”
“你要知道,她这一辈子最爱的就是周朴园。一个人的初恋,是一生不能忘记的。”
1954年,新社会版《雷雨》上演,观众卷着铺盖连夜排队,各地兴起复排热潮。有段录音记下了曹禺当时看戏后的心情——“舞台上的人物不是在我脑子里所想象的那个人物,有演得不够足的,有演得过火了的,不真实的,尤其是被夸张的角色,使我感觉到就不如我当初写剧本的时候那么愉快。”
有一次,被演员长时间酝酿阶级感情弄得又拖又假的台词腔折磨着,曹禺冲进后台对郑榕喊:“快快快,受不了受不了,我那剧本里头没有那么多东西!”
“老同学”周恩来
周恩来比曹禺早11年在天津南开新剧团演戏,因男校没女生,二人都曾演女角,与黄宗江一道,并称为“南开三大女演员”。后来,在人艺,在其他场合,周恩来常亲切地称曹禺为“老同学”。
周恩来的新剧观在18岁左右就已成形,当然与那个“神州暗暗,天地为愁”的旧中国有关。他认为新剧有“感化劝导之功用”,是“通俗教育中之利器”,进一步,有“开民智、进民德”的效力。
1938年,周恩来在重庆给曹禺写了一封长信,谈到《雷雨》和《日出》,并邀请曹禺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做客。在那里,曹禺初识“老同学”,并接触到徐特立、董必武等人。
据万方说,左翼激活了曹禺的热血,带给他一种振奋的新鲜之感,他真心希望那个正在堕落的旧社会被彻底地摧毁,也真心体认文艺创作要服务于某个更大的目标,尽管这个目标是什么,他并不清楚。他想改变自己的生活,想参加革命,想到延安去。“但周总理跟他说,你还是留在这儿。意思是说你留在这儿用处更大。”
国共谈判时,毛泽东飞抵重庆,约请各界人士会谈,也请了曹禺。毛泽东对他说,你写了很多好的作品啊。1940年,毛泽东找到鲁迅艺术学院的负责人张庚说,延安也该演出国统区著名剧作家的戏,点名要演《日出》。为了保证演好,剧组成立了临时党支部。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梁秉堃曾说,老人艺有5根柱子:郭、老、曹、焦、周。周,即周恩来。如果晚上没有工作,周恩来十有八九是到首都剧场看话剧,通常坐在第七排或第八排中间的位置。建国到“文革”前的17年间,人艺先后演出了近百出戏,周总理也看了近百出戏,单是新排的《雷雨》,据说他就看了8遍,每次都有指点。
在许多“老人艺”的回忆里,周总理是懂行的、尊重艺术的首长,也是四十多年里人艺的护航人,但同时,他也是政治上的领航人,代表那个“天”。
查看“大跃进”期间人艺火速成立“炼钢办公室”、几天后在剧场后院出钢的传奇,能撞见恰好来访的日本戏剧家千田的诧异表情。查看三四天排出反映此运动的《烈火红心》的速度,能听到上面的声音:人艺明年应该放个大卫星。
翻阅1961年《潘金莲》被停演的讨论会记录,更能对当时的政治空气、艺术家们的姿态感知一二。比如,“对此剧院的人们不但没有反感,反而把这件事传为美谈。”因为人艺上百出戏,总理仅仅停了这一出。“是啊,周总理对待剧作家和演职员们那种诚挚、友好、尊重和体贴的态度,又怎么会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呢?”
周恩来对曹禺的体贴表现在许多方面。1950年,曹禺与发妻郑秀的离婚是在组织的过问下进行的,郑秀不想离婚而开出的500元赡养费——这在当时是一笔曹禺无力支付的巨款——也是在周恩来的直接过问下由组织出的。“文革”中,周恩来亲自赶到同时关押着彭真、刘仁等人的中央音乐学院小礼堂,从红卫兵手里救出了曹禺。
从旧社会大户人家走出来的曹禺向来礼数周全,小辈来访,临走时他也会恭敬送出门。对周恩来,他是目送汽车远去,再对着车尾鞠上一躬。1976年早春,周总理逝世,曹禺含泪说,仿佛自己的部分生命也随之而去。
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
1952年,周恩来找曹禺长谈过一次,问起他的生活和创作情况。曹禺说,生活很好也很愉快,谈到创作却卡住了。从最近的一次创作《艳阳天》算起,他已经5年没有写出东西了。
“我自己正想写点东西的时候,就感到生活贫乏,自己真正感到的东西,需要的资料没有多少,就悔恨,就难过。中国有句话,“江郎才尽”。我不说才尽,我有没有才,真是个问题。一拿起笔来写现在,就感觉到自己肚子里一无所有。不像从前那时候,拿起笔来顺溜极了。”研究者说,他知道应该怎么写,就不会写了,写出来,也就不会好。
除去“文革”10年空白,三十多年里,曹禺成形的创作总共只有两部半。一部是《明朗的天》,写协和医院的一群知识分子接受改造,但写完后他感到荒诞:“我也是个‘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怎么写别的知识分子改造好了,实在是捉摸不透。”翻案之作《王昭君》是周恩来派下的任务,意在“歌颂民族团结”。《胆剑篇》是“集体创作”风行时,领着于是之、梅阡创作的,当时全国各个院团都在重写卧薪尝胆的故事,用来号召正经历“三年自然灾害”的老百姓扎紧裤腰带。
曹禺不是不明白。1956年,他在谈《家》的改编时说:“写剧本不应该老是被政治概念拖着走。作者所以被政治概念拖着走,这说明他还是落在政治的后面,作者的生活、思想没有赶上政治的要求,因此在写作的时候常常处于被动的状态。”
在蓝天野眼里,曹禺是一个带点孩子气的、很天真的人。万方说,父亲天然有一种对人的兴趣,哪怕坐在轮椅上被推进公园,他也在观看来来往往的人,留意他们的穿衣说话,留意他们的关系。女儿万昭说,父亲是一个很感性的作家,他这个人就是一团感情,但他的感情总是容易受周遭环境的影响。
曹禺谈到过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那个缥缈精灵爱丽儿:最可爱,最像人。她为主人效忠,施展千般能耐,待功德圆满,向主人要求,恢复她原来的自己。又谈孙悟空:他保唐三藏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到了西天,后来在一片慈祥、圣洁的氤氲里成了正果,被封为‘斗战胜佛’,慈眉善目地坐在那里,不再想花果山,不再想原来的猴身。
1991年他写下一首短诗《玻璃翠》——
我不需要你说我美,/不稀罕你说我好看。/我只是一朵平常的花,/浓浓的花心,淡淡的瓣儿。/你夸我是个宝,/把我举上了天。/我为你真动了心,/我是个直心眼。/半道儿你把我踩在地下,/说我就是贱。/我才明白,/你是翻了脸。/我怕你花言巧语,/更怕你说我好看。/我是个傻姑娘,/不再受你的骗。
他在“文革”期间的表态文章被剧作家沙叶新归入“表态文化”。殊不知当年他每每过不了关,不得不从《红旗》杂志上抄口号,把自己骂得不是人了才算过场,回到家里难受得直抽自己嘴巴。
6T6IcePzNE8aWYDA/ZHXaoUueR6V6sVrm7fxiukp7t8= “文革”好像一幕10年大戏,演着演着也就演完了。其间,老舍投了湖,焦菊隐的骨灰装进了一个7块钱的骨灰盒,66岁的曹禺重回人艺,担任院长。他对人艺、对舞台还是一往情深:“我是爱这个剧院的。因为我和一些老同志在这个剧院天地里,翻滚了30年……戏演完了,人散了,我甚至爱那空空的舞台。”
他还说,舞台是一处魅惑无限之地,是地狱,是天堂。一场惊心动魄的好戏,是从苦恼到苦恼,经过地狱般的折磨才出现的。只有看见了万象人生的苦与乐,才能在舞台上得到千变万化的永生。只是他的生活已被置换、抽空。
复出后,曹禺的社会活动非常多,每次回到家,就只剩下疲倦和沮丧。他对女儿说,我知道写不出来,我用社会活动来填补痛苦。他因神经衰弱而服用安眠药,每次吃了药,整个人才能放松下来,很多心里话才能说出来,他一个人,自己对着自己说。
80年代末,曹禺决心抛开诸多应酬,找回原来那个自己。他把自己关在上海的寓所里,重拾起解放前未完成的剧作《桥》。他给女儿写信谈,找人谈,费了很大的心力,常常夜里醒来趴在那里想写下去,可总有那么多想不通的关、过不去的坎,最后,心气越来越弱,终于没能写成。
万方在父亲身后整理遗稿时,看到了这一时期曹禺留下的大量剧本大纲和对白残篇,它们大多只在稿纸上开了一个头。
万方说,创作不像制造产品,也不像科学研究,有一个客观标准。文学创作完全是依靠人的生命,如果生命被扭曲,很难写出东西。父亲那时常对她说:“我觉得我不知道被一种什么无形的东西锢得这么紧,总是放不开。”
万方看着晚年的父亲依赖安眠药寻求安宁。有一天清早醒来,她看到父亲满面是血,玻璃渣子插在头发里,样子骇人。在药物的作用下,他夜里昏昏沉沉一头撞上书橱,自己却浑然不觉。
那段时间,曹禺枕边总放着一本《托尔斯泰评传》。有时,他读着读着突然撒手,嚷嚷起来:“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我要写出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干。”
她时常被父亲房里突然爆出的一串呼喊惊醒:“小方子!我要跳下去!我为什么要这样活着,每天用嘴活着!托尔斯泰那么大岁数还要离家出走,我也要走!”第二天早晨醒来,他又怏怏自嘲,“就我,还想成托尔斯泰?”
病榻上的曹禺在心境灰暗时,会找来弘一法师的书,翻到其中一页,念给万方听:“水月不真,惟有虚影,人亦如是,终莫之领。”他放下书本,静一静说,“这是另一个世界,和马克思的世界不一样,和资本主义世界也不一样。你觉得如何?”
曹禺去世那天,于是之涕泗滂沱,许多人没见过他哭得这样伤心。于是之说,“中国诞生过许多剧作家,我心目中的曹禺是最杰出的。我读过他的每部剧本,感受到作家的天才和灵性。我也曾跟随他学着写戏,从中体悟到他的睿智、严谨和热情。他有怀霜之心,凌云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