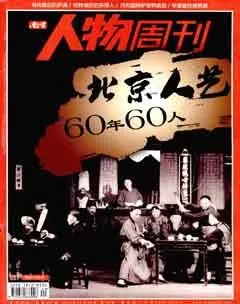标准像
“我的诗里没有美好的事物/它是高速公路上的抢劫,压迫,还有结核病人咳出的血/我的诗里也没有贵气的事物/它是死亡,流汗,还有来福枪的枪托……”这是越南文学工程(Viet Nam Literature Project)创始人Dan Duffy最喜欢的一首阮志天的诗。因为要写越南流亡诗人阮志天的讣闻,我试着给Dan写信提问,其中一个问题是:“有人觉得,阮的诗歌太过直白,失去了美感。你怎么看?”在回信里,他引用德国作家布莱希特(Bert Brecht)的话作为回答:“如果有人说你不是诗人,你就告诉他们:你们不是人类。”
一位共产主义世界的流亡者和一位马克思主义作家隔空站在了一起,显示出文学对政治的无可逃避——写作此稿时,互联网上关于莫言的争论仍未停止——关于这件事情,我的一位台湾朋友说:无需用“现实政治”的角度思考所有事情,但切莫忘记所有事情的“政治意义”。
那些为作家辩护,要求“让文学的归文学”的人,或许有意无意窄化了“政治”的含义,但更糟糕的恐怕还是那些拿着“现实政治”的尺子对着作家比划的人。即便是Dan也在邮件里特别说明:与布罗茨基类似,阮志天对诗性语言的雕琢,使只有懂得他们母语的人才能真正欣赏他们的创作(我用大白话演绎一遍:即便骂人,也请骂得有音律美),而我们这里一些可爱的喜欢借酒浇愁的人儿,却只看到阮志天的某一品性(譬如,“爱自由”,这当然没错),从而急吼吼地给诗人画出一幅“标准像”——这样的事情见得多了不免心生忧虑:你会觉得他们满怀热情与道德感,却把世间最美好的事物都变成了一些符号和姿态,而他们所追求的,至少在旁人眼里,也凝固成了另一种意识形态。
羽戈曾在《签名,还是不签名?——关于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一文里,分析昆德拉和哈维尔对于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不同态度:哈维尔认为应该签,因为这是人们重振士气、恢复公德心的开始,也能拓宽公民社会的生存界限,终将令权力者收回利齿。而昆德拉则抵制某种大义凛然的道德强化,他恐惧的是一种冠以自由民主之名的专制主义。而最终,在我看来也是最重要的,他们能够理解彼此,他们的分歧是生活方式的分歧,而不涉及道德(勇敢VS怯懦),在追求自由上,他们依旧是同路人。
阮志天去世后,我搜索了西方和越南的媒体,越南媒体只字未提(一位朋友的朋友,越南前媒体人,抱歉地给我回信:“不好意思啊,其实我都没听过他的名字”),而英美大报基本都刊登了他的讣闻。再进一步搜索,有意思了,虽然阮志天1995年即流亡美国,但几乎找不到除了讣闻之外的其他主流媒体报道,而即便是讣闻,也能看出他们对他有多陌生(《经济学人》甚至弄错了他在英国使馆内的细节),可以想见,大多数流亡者,只在两个很短的时间段里“存在”:从到达那一刻起,他们就被期待成为一个符号,一副“标准像”,永远摆出固定的POSE,直到逝去。
驱赶他们的权力者自然是“万恶之源”,可是他们也无法包揽世间的荒谬。索尔仁尼琴在《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里描述了自己流亡之初的感受:我再也不想发表任何声明了!但西方媒体还是蜂拥而至,希望他说点儿什么。说什么呢?“说我身处自由世界感到十分高兴?或是说,我非常喜欢德国的公路?”可是,“一切重要的内容我在莫斯科都说过了。”他后来到了苏黎世,媒体也一路追到瑞士,某个黄昏,天完全黑了后,他来到房子背面的阳台,想透透气,突然,强烈的探照灯亮了起来,他又被记者们逮住了。他拒绝他们拍的标准像,从阳台离开了,“又吃了几颗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