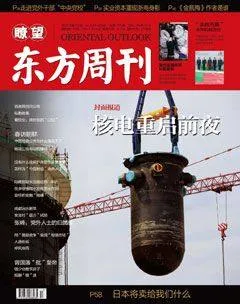私塾故事

念口簧
书塾里面,除了打,另一令学生味同嚼蜡以致反感的是囫囵吞枣的背书。
当时中国私塾里,几乎所教的都要背。一般幼童开始背的是《三字经》等蒙学书,上课的情况一般是:
我把书交给老师,他念一遍,我跟着念一遍。他看我已经会念,就命我回到自己桌子,高声朗诵,直到记牢为止。因为《三字经》有韵律,句子短,每句都是三个字,所以记起来并不困难……每句念若干次,我认为可以丢掉书本背得出来时,再拿书到老师那里,背朝着老师和书本,背诵书中的原文。老师认为我真能背诵了,于是他再教我四句新的。(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
本来儿童的记忆力强,加上《三字经》、《千字文》这些蒙学书都是句短而有韵的,所以背书不算很苦。到了背四书五经,就渐渐进入苦境。尤其成问题的是只背不讲,这一点许多接受过传统教育的人都认为是一种虐政。
四书之中,《论语》、《孟子》比较易背,虽然不讲解,但学生略有一些认字基础,还可以有个概略,《中庸》则不易对付了。五经之中,《左传》较受欢迎,《诗经》也还可以。至于一致认为难背的,大抵是《书经》,连唐代韩愈也认为佶屈聱牙,加上没有讲解,学生根本不知道这些古老东西究竟说些什么,用广东话说,只是念口簧,当时虽然应付了先生,久后自然又忘了。
这种囫囵吞枣的背诵,全国情况差不多:齐白石在湖南闭塞的地方是这样读“白口子书”,冯友兰则因为为官的父亲辗转于各地做事,因此由略通文墨的母亲课读,也是以“包本”为目的。
什么当时会流行只背不解呢?这种教法又已经持续了多少代呢?我所看的传记作者,对于自己所受的这种教育的深远历史,都有体会。“这个一间房子的私塾,各方面都是传统式。所教的课程和教法全是传统的,我想多少个世纪以来都没有变过。”这是搞历史的蒋廷黻的感受。
以自传记录中国近代变迁的书中,以我所见,写得最深入,最有历史感的,是蒋梦麟。他是这样看背书这种老式教育的:
在老式私塾里死背古书似乎乏味又愚蠢,但是背古书倒也有背古书的好处。一个人到了成年时,常常可以从背得的古书里找到立身处事的南针。在一个安定的社会里,一切守旧成风,行为准则也很少变化。因此我觉得我国的老式教学方法似乎已足以应付当时的实际所需。自然,像我家乡的那个私塾当然是个极端的例子,那只有给小孩子些无谓苦难。我怕许多有前途的孩子,在未发现学问的重要以前就给吓跑了。(蒋梦麟《西潮》)
这短短一段话已包含了背书的好处、形成这种教育方式的背景和背书的流毒三层意义在其中。死背书的教学方法,也有当时的原因,这在后文再述。当时的教育问题是,为孩子制造苦难的私塾几乎遍及全国,而太多有前途的孩子早就给吓跑了。
逃学
背书和打两种虐政混合使用,落到后来,相当多私塾都给小孩以苦难,因而也造成许多小孩的“堕落”。胡适本人成了名学者,胡适所读的书塾却造成不少“堕落”学生。
若按胡适所述,成败的因素有时和学生的资质完全无关:“我们家乡的蒙馆学金太轻,每个学生每年只送两块银元。先生对于这一类学生,自然不肯耐心教书,每天只教他们念死书,死背书,从来不肯为他们讲书。”于是他们自然毫不觉得读书有趣味,因为全不懂得书中说的是什么。因为这个缘故,许多学生常常逃学。只有胡适一个人不属于这两元的阶级,因为他的母亲渴望儿子读书,所以学金特别优厚。她嘱托教者为胡适讲书。因而念的几本书虽然有许多是乡里先生讲不明白的,但每天总遇着几句可懂的话。
有时不喜欢读书更涉及相当偶然的个人因素:与胡适同一书塾的堂兄弟,因为自小与父亲在外地长大,口音和家乡的塾师不同,往往读“错”字音而被打。(胡适《四十自述》)于是这些天资不笨的孩子讨厌读书,他们的出路自然是逃学,宁愿躲在田里睡觉捱饿,也不肯读书。
这些“堕落”的小孩于是以不成才的多,写成自传的更是绝无仅有。不过也有些逃学的小孩最后事业有成的,五岁多一点的蒋梦麟,读《三字经》读得莫名其妙,恨透了家塾生活,于是趁老师不在意的时候,一溜烟跑回家中,躲到母亲的怀里,第二天由奶妈送回塾中,而老师也佯作不知他逃过学。毛泽东十岁时也因为教师常常打学生而逃学。他这一逃,怕挨家里打,不敢回家,向县城方向流浪了三天。被家人找回后,他的家人和教师对他都没有呵责。(蒋梦麟《西潮》;毛泽东《毛泽东自述》)
沈从文是真正长期逃学的“堕落”小孩,他后来成为著名的文学家,可说是这些“堕落”的小孩中的异数。沈从文的自传中谈完家庭第一件事便是谈逃学,《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实实在在是一阕逃学的赞歌。
虽然逃学会受家庭和学校双重责罚,在学校还要自己把板凳搬到孔子的牌位前,伏在上面受笞,但“我的心总得为一种新鲜声音,新颜色,新鲜气味跳。我得认识本人生活以外的生活。我的智慧应当从直接生活上吸收消化,却不需从一本好书一句好话上学来。似乎就这样一个原因,我在学塾中,逃学纪录点数,在当时便比任何一人都高”。
逃学有什么事可做呢?可以去游泳,天气好时便到城外山上去玩,捉蟋蟀,偷园地里的李子枇杷;天气不好也可以到庙里,看人绞绳子、织竹器、做香,看人下棋、打拳,以至相骂。有时又去看杀人处留下的尸体,拾一块小石头,在那污秽的头颅上敲打一下,或用木棍去戳戳,看看会不会动。沈从文认为,他的一切关乎人生的早期阅历,都来自逃学时所接触的大自然,可以说没有逃学就没有文学家的沈从文,他是少数从逃学中得益的孩子。
就是这样的沈从文,进了新式小学后,虽然“照例什么都不曾学到”,但却不用逃学了,因为学校不背诵经书,不随便打人,也不必成天坐在桌边。每天不只可以在小院子中玩,互相扭打而不为先生约束,七天照例还有一天放假。学校既不严格,四个教员中又有两个是表哥,于是想外出的沈从文大可请假呢。(沈从文《从文自传》)
私塾先生
学塾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童蒙,小者三四岁,大者到十多岁。学生之中也有十七八岁的,但数目很少,而且待遇与童稚学生不同。多数塾师,尤其穷乡僻壤或学历不高的,大致都是负担差不多今天的幼儿园至初中程度的教学工作。所以塾师被谑称猢狲王。这些教育工作者没有固定资格,学问水平和社会地位,在各处有很大差别。当时读书的目的,以功名为主,未能在功名路上平步青云,弃儒从商又不甘或没有机会,面对的唯一出路是教馆,对读书人来说,是有点不得已。纵使像萧公权,请得王贻运的弟子来当教师,他却以为大材小用,对着学生大谈文章义理。这样的教师不过是多一点名士风流,并不比牟宗三所言不自然的先生、秀才的寒伧酸气,咬文嚼字为高。(萧公权《问学谏往录》;牟宗三《五十自述》)
又因为师严道尊的想法影响,他们的形象多是着长衫,拿戒方,一脸严肃,不苟言笑,只会叫人背书。其实他们中有许多固然是教书混日子,但不少是心地仁厚的,十中也有一二做到循循善诱,启发学生读书的兴趣,有自己的一套教育主张。像张治中、马叙伦、萧公权都曾受益。
部分初级教育工作者学识不高,《勤有功戏无益》一文中已提过杭州嘲笑塾师无学识的故事。亦有以为塾师没有学问之余,对待学生的严刻是更大的问题。在较为乡村而文风不盛的地方,村塾除以上两个问题之外,还有另一易于腐败的原因——报酬少。按齐如山的记录,一个学生一年付的钱极少,每人每年不过小制钱五百文,合十个学生,才五吊钱,这个价钱请不到外村的先生,只得请本村的人。这种塾师往往在教书之外,还有很多事要做,例如自己的家务、庄稼、赶集;由于塾师会写字,在乡村中有这种技能的人不多,以致村中各种写账、婚丧,都要找他;塾师无论如何在乡民眼中是知书识礼的人,口舌是非的调停也会把他请去理会。于是一年有一半时间不在书房中,小孩白喊了一年,学不完《千字文》的不少。(齐如山《齐如山回忆录》)
至于薪酬方面,齐如山所言的小村塾,薪酬不高,但教者也不算是全职。在学风好的地方,坐馆还算是薪水不低的工作。按包天笑记苏州的情况,处馆先生有分等级,以科举级别为单位,未中过秀才的童生,等级最低,馆谷最少;中过秀才的高一级;补过廪,文才又好的,再高一级;举人又再高一级。进士而为塾师的应该没有,除非教王公大臣的子弟。
即使童生而处馆,待遇也不算十分低,包天笑所记是二十四块钱一年。蒋廷黻记在湖南是三十块钱一年,是乡间普通工人收入的五倍。如果学生考中秀才,还有谢礼,而且不愁没有人来请他当老师。萧公权记在 1910年代,他的老师薪金是纹银一百两,在当时四川是十分丰厚的。
许多人家里没有大负担,并不靠那些钱来过日子,但是风气流行,倘还考上秀才举人之类,就自然有传予下一代、教学相长之想。
在荒僻之区,并非人皆能读书,所以塾师不多,但有些地方,例如湖南蒋廷黻的家乡,读书人多,处馆先生也有供过于求,有些失业的,变成近乎乞丐一样,名为寒生,揩那些已有职业的读书人的油。他们时常去拜会私塾,希望至少能吃一餐饭,或再弄几文钱。一般塾师也不失礼义,练就了一些专门艺术,在殷勤之中,有对付方法。有时请学生帮忙招呼,学生不必如教师般拘谨有礼,因而可以用冷僻的句子去考问来人,如果没有学问,寒生只得羞愤而走,若有学问,那么一顿饭和一些资助就少不了。
黄炎培记一个很具体生动的例子,一个读书人,进入学塾中,很客气地问教师的姓名,然后立刻索纸笔写一首诗,把教师的别号两字写进诗里,得到教师大加称赞,得以吃了一顿酒饭,拿了轻微的一笔钱离开。比这更不堪的,是穿着破长衫,手拿折扇,在长长的街上,一面漫步,一面朗读诗文,在街上三来三往,伸手依次向街旁的商店或人家文雅地接受薄薄的馈赠。(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黄炎培《八十年来》)这样的读书人,黄炎培的家乡直称之为文丐,比鲁迅笔下的孔乙己真是不遑多让了。
尊师重道
中国人谓天地君亲师,师是五伦之一。师严然后道尊,无论塾师水平如何,如何为学生所不喜欢,当时塾师还是受到社会上一般人尊敬的,因为他们都属于读书人。虽然他们属读书人中低下的级别,多是考不到功名的,若是举人已是相当了不得。然而士农工商四民,以士为首,凡是读书人,都是选了读书科举这条路为终身之途。他们会写字,比周围许多不识字的农民、妇女强得多,而且读的是圣贤之书,有资格参加科举,说不定会高中状元。因此做塾师虽然收入不多,但地位并不算低。
在重视教育的地方,对教师是相当尊敬的。冯友兰是书香世家,父亲是进士,在地方做县官。县衙里的师爷虽然自命为老爷的老师,看不起少爷的老师,但老爷每天要陪着教书先生吃饭,因为在冯家的规矩,教书先生的地位是很高的,每顿饭必须家里有一个主要的人陪着吃。
浦薛凤生于江苏,少时随父去人家处馆,东家每季送季节鲜花数盆,花谢派人取回。江南的风气,出外处馆是一种清高的职务,包天笑说在苏州待遇不只靠馆薪,膳食可能更重要,由东家供给,而且另开一桌,有荤有素,比较优厚,有时还请先生点菜,十分恭敬。家有宴会,教师坐首席。(冯友兰《三松堂自序》;浦薛凤《万里家山一梦中》;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
王若望的父亲在江苏一个小镇的学校教书,学生的家庭都是农户,供饭由每一家轮着供四天,农民平常不易吃肉,但给老师送饭每顿饭必有肉有鱼有菜。菜是自己种的,鱼到河里捉,肉则到街上买。(王若望《王若望自传》)。王父所教已不是私塾,但有很多与私塾相似之处。
据同在江苏的钱穆所述,其家乡“虽系远离县城四十里外小镇,其时居民之生活水准知识程度亦不低。然其对果育(按:小学校名)诸师长皆备加敬礼。不仅有子弟在学校之家庭为然,即全镇人莫不然。因其时科举初废,学校初兴,旧俗对私塾老师皆知敬礼,今谓新学校尤高过旧私塾,故对诸师敬礼特有加。……(倩朔师)每周往返,当其归舟在镇南端新桥进口,到黄石虚停泊,几驶过全镇。是日下午四五时,镇人沿岸观视,俨如神仙之自天而降,其相重视有如此(钱穆《师友杂忆》)”。所言可以范围旧式书塾和新式学校的情况。
以上几人除了冯友兰,都是江浙地方生长的,江浙地方在清时出了最多状元,文风之盛,在尊敬师长上亦可见一斑。
有时敬老师的礼节到了有点可笑的程度,易君左说每次给先生泡茶,不由女仆,因为由女人侍候老夫子是不敬的,总由老家人敬谨担任。先生架子十足,四平八稳端坐,见到老家人送茶送点心,从不理会,这样才显示师道的尊严。(易君左《大湖的儿女》)
由小孩子几岁发蒙的仪式,亦可见家长对孩子入学十分重视。当日孩子都穿上整齐衣服,有的提一灯笼,上写状元及第,又带一根葱,喻意聪明。有的请附近有功名的、学问为人敬仰的人教念几句书,取一个好开始,如马叙伦的父亲请解元穿上礼服为儿子破蒙。解元是以第一名中举人。会试第一名称为会元,殿试第一名的称状元。三次考试都是第一,即所谓连中三元。
而在洗脸水都不足的地方,小孩子四岁初上学之前,第一件事就是洗净手脸。(齐如山《齐如山回忆录》)齐如山在河北长大,当地缺水,很少洗脸洗澡,其诚敬之情可知。
前面我们讲过许多初等教育的荒谬现象,似乎初等教育受人忽视,这可说是某种程度的现实,但同时又不是真相。中国国土大,各地的条件又差别甚远,所以每方面都有相当复杂的表现。总的来说,当时的人是很重视初等教育的。
计算机大王王安说:“也许是因为实际上中国能念书孩子比美国少,我觉得中国人比美国人更看重小学教育。事实上,我始终对美国小学教师这样不为学术界和公众敬重,感到很讶异。”(王安《教训》)。

李昕:
北京四中这所学校的特殊不仅因其高超的教学质量,而且因其聚集了大批干部子弟。本书描写的是特殊年代的四中,那是整整一代人终生难忘而又不堪回首的青春年代。
《暴风雨的记忆:1965- 1970年的北京四中》
北岛 曹一凡 维一 著
三联书店
2011年3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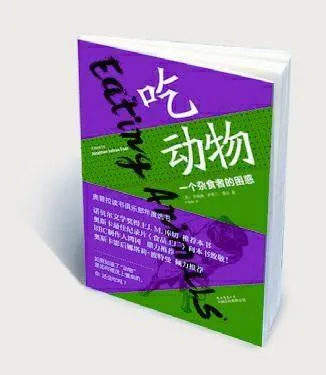
曹东勃:
本书巧妙结合哲学、文学、科学和作者的卧底经历,突出展示现代工业社会中,为了让肉更便捷地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环境、政府和第三世界付出的代价。
《吃动物:一个杂食者的困惑》
【美】乔纳森.萨福兰.弗尔 著
卢相如 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10月版

李公明:
一个有思想深度的批评现实主义画家,左翼前辈,把自己的头颅提在手里在山路上前行的革命者,在向日葵地里狂饮醉卧的颓废者,从党国的牢狱到为劳动者呐喊的画室,还有什么能比这些更能充实台湾左翼美术史的篇章呢?
《寻画——吴耀忠的画作、朋友与左翼精神》
林丽云 著
INK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社
2012年3月版

亚伯拉罕. F. 洛文索:
本书对在转型之后建立民主或多头政治的分析方法与规范性视角,提供了一个不只是对学者,而且对政治参与者同样有价值的视角。
《威权统治的转型》
【美】吉列尔莫.奥唐奈
【意】菲利普.施密特 著
景威 柴绍锦 译
新星出版社
2012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