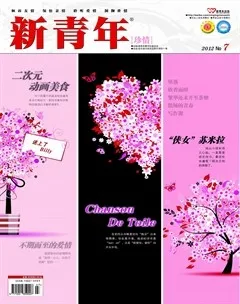吐鲁番的阿拉木汗
辽阔的远方
有一种信念在召唤
行者匆匆
走在寻梦的天堂
火车一直在欢快地唱。火车也在唱歌了,唱的歌曲是多么豪迈有力啊,那不就是我们此时此刻的心曲吗?啊,也许用更准确的声音来模拟,应该是那个大家都熟悉的声音:“前进,前进,前进进”,我的胸腔有一股热血开始汹涌澎湃。
20点49分,这里的太阳渐渐向西倾斜。我感觉到,太阳下山的西域有无边无际的苍凉笼罩着我和我乘坐的火车,因为那时候的慢车车窗关得并不严实,刺骨的寒气开始侵人,从窗口望出去,可以见到沿线的水潭和河流都浮着一层白蜡般的薄冰,路边的草地上不时还有一摊摊雪渍。虽然是坐在火车上,但我感觉下面的大地就是一块很大的船板,我们就在船板上迎风破浪。而前方,是一片临近暮色的大海,水天之间是一种苍凉浩茫的壮美。
戈壁滩向远方浩荡荒凉地延伸着,火焰山随着这种延伸昨夜之梦一般渐渐地移向侧后,开始变得遥远而模糊。这时有一种奇特的地形像另一种梦境开始进入了我的视野,明月说那是吐鲁番盆地。说是盆地,其实还是广袤的戈壁滩,看地势呈北高南低倾斜,北面高处再去那是茫茫白雪的天山。偶尔在烟霭朦胧中看到旷野上竖起的一根根柱状物,还有残垣断壁样的景象。那些奇形怪状的山体,峭陡的坡度,倾斜的荡漾,歪扭的弧线,展现着不可思议的破碎、凝聚和组合,时高时低,欲倾还立,充满了凝固和忍耐的力量,相互呼应又相互排斥,集恐怖与悲壮于一体,最终连绵成雄壮的一片,虽凝滞不动,却仿佛在一夜之间就会随着地壳的运动而变幻换形,又会随着长风的吹拂而游移。
21点10分左右,天还没有真正黑下来,列车缓缓停在著名的绿洲城市——在夏日有火洲之称的吐鲁番上。这里比哈密稍暖和,据手机上的短信提示,温度是-7—-2℃。
列车一停稳,我就迫不及待地对明月说,你在这儿看行李吧,我下去看看,我早就想看看吐鲁番了。在新疆的众多城市中,吐鲁番的名气不会亚于首府乌鲁木齐,因为吐鲁番的特产不仅仅是葡萄,还有姑娘。此时即使列车仅仅停靠8分钟,我也要下去看看,虽然伊犁才是我们的归宿,但双脚没有踏上吐鲁番的土地也算不上到过新疆。
一脚“橐”的一声就踏上了冷寂的月台。迎着干冷的西风暮色,踩着坚硬的地板,我在心里说,吐鲁番,我的双脚真正踏上您的大地了,尽管几分钟后我就要离开您,但这也应该算是到过您这么著名的地方了吧。
吐鲁番的姑娘一朵玫瑰花,
你圆圆的绣花帽开在阳光下,
眉毛上染着碧绿的乌斯玛,
海娜花涂上美丽的手指甲。
……
车站的广播正在响亮地播放这首动听的歌,我记得好像是一位叫巴哈尔古丽的维族女歌唱家唱的。在南方的时候我便多次在光盘里欣赏过,现在来到了它的原产地听,虽然歌声也是从光盘里放出来的,但心理上有一种在南方没有感受到的十分地道、原汁原味的感觉。这动人的歌声又诱惑着我产生一种冲动,驱使着我在站台上默默地寻找,寻找一位像玫瑰花一样的吐鲁番姑娘。
在月台上边走走,便可看到很多维族人在推着售货车行走叫卖,卖烤馕卖各种水果的,都是中年人,此时上下列车的维族人也很多,真是面孔与表情跟内地人卓然不同,听歌里把吐鲁番姑娘唱得那么美丽,真想仔细地看看。可惜眼前的不是中老年人就是小孩,还是男性居多,年轻的姑娘几乎看不到一个。但犹不甘心,便在人群中东张西望。唉,也许像玫瑰花一样的吐鲁番姑娘,离这儿还远吧,那首我早就熟唱的《阿拉木汗》不是这样唱的吗:
阿拉木汗住在哪里?
吐鲁番西三百六;
阿拉木汗什么样?
身段不肥也不瘦。
……
吐鲁番西三百六,啊,美丽出众的阿拉木汗,遥远的阿拉木汗,我在这里大概是看不见你的了。只好安慰自己,下一次到吐鲁番一定要下车去市内外逛个够,特别要去吐鲁番西三百六十公里的那个地方,那里有歌声中的阿拉木汗。
在有点儿留恋有点儿惆怅中,我走到一家水果摊前,从两位眉毛长长、五官轮廓分明的维族大嫂那儿买了两个烤馕和一小袋苹果。一边付款,一边还在东张西望。这时,我的眼睛仿佛在黑夜中一刹那间看到了光明,那是真正的光明——从一节车厢旁边,鹤立鸡群般走来了一位维族姑娘,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她比旁边的女性甚至许多男人都高出一头,还有她高挺而端正的鼻子——特别注明,她的鼻子虽高耸但不是鹰勾,因而非常适合东西方人和维汉人的共同审美——她黑而修长的眉毛下,深陷的眼眶里有一双忽闪而放出利光的眼睛。因为她惊人的精神和光彩,让我无法猜测她的年纪,但能看得出是一位很年轻的姑娘,她穿了一件淡红色皮大衣,将上身包裹得严严实实,下边是较厚的裙服,尽管如此,依然遮不住她高挑美好的身段,身上自然流溢着一种飘逸的美。她手提一只颜色鲜亮的红皮箱,脚上的高跟黑皮靴“咚咚”地敲击着站台上的水泥地板,很干练很飒爽地走向出站口。
我从侧面看她,她经过了我的面前,我看见她有着苗条而又丰满匀称的身材——有一种女人,不管身上如何包装依然掩饰不住她的美好身段——她的披肩的长发栗红卷曲,红瀑一般滚动而下。一张有点儿像西亚女人的脸轮廓分明,高高的眉宇,衬出有深度但恰到好处的眼窝,里面是一对黑亮亮的,绝对是黑亮亮的大眼睛,啊,大眼睛,她透射出一种异常的我们不可能有的犀利的光。初春的傍晚,一阵冷峭的风拂来,我闻到了一股玫瑰花一样幽远鲜润的淡香,也是我从来没有闻到过的花香。啊,真像那位MTV上的阿拉木汗!哎呀,也许她已经感觉到我在专注地看她,她稍稍地转过头来,迅速地朝我瞅了两眼,靴子依然“咚咚咚”地敲击着地板。刹那间,有两道尖尖的闪亮直击过来——我分明接触到了她的目光,那明利的目光,快速的目光,就像蛇信一样闪耀跳跃着,离开了。
她居然没有戴我想象中的小花帽,头发也没有结成我想象中的七根又细又长的辫子!欣赏她,真的就像欣赏一朵玫瑰花啊!她绝对就是来自吐鲁番西三百六的那位阿拉木汗,呵呵,我终于在这人流匆匆的吐鲁番车站看到了歌中所唱的阿拉木汗,传说中才有的阿拉木汗,而且是我最欣赏的那些美丽的阿拉木汗之一,她是多么新潮,却又保有着那种我说不清的自己民族的特质,她是属于他们的民族的,却又融进了这个时代的潮流。
我有些恍惚,但这时听见列车员在用汉语大喊准备开车了,随即维语广播也响起来,我清醒过来,赶紧快步跑向自己的火车,一边跑一边还要向那姑娘回望,再度产生的恍惚中似乎也看到了她在回望的身影,那明亮的眼光在人群中一闪而逝。我心中的光亮也随着那逝去的闪光消失了,只剩下一腔无法言说的惆怅。
回到座位边,明月正焦急地看着我,埋怨我不抓紧,让她担心。我赶忙向她赔笑脸,心里的真正的想法是,尽管我当年曾梦想娶一位维吾尔族姑娘,尽管明月不是阿拉木汗我有点遗憾,但她毕竟也是阿拉木汗故乡的明月,是伊犁的明月,是天山的明月。此刻的我,恐怕还有一些比北京的出租车司机自诩为皇城根儿因而骄傲自满还要真实一点的优越。哦哦,阿拉木汗,吐鲁番的阿拉木汗,我打心底里感谢你啊——阿拉木汗!
列车仿佛也带上了我绵绵的惆怅,长长地叹息一声无可奈何地启动了。这时看窗外,城市的灯火突然“哄”地响了一声就全亮了起来,富贵逼人般荡漾着,而从楼群的空隙间望过去,遥远的天边夜色朦胧,橙色的光亮缓缓飘逸。我在自己有点迟滞的脑海里,仿佛又看见了那位像玫瑰花一样鲜润幽香的维族姑娘,那位赶回吐鲁番西三百六的阿拉木汗,在风影浮动光影游弋里飘然闪现,又飘然而去,她回眸时那又大又亮的黑眼睛仿佛在说话,那栗红卷发随风拂动的洒脱,那一袭西服大衣冬令裙服的飘逸,使我耳边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响起那首歌:
她的眉毛像弯月,
她的腰身像绵柳,
她的小嘴很多情呀,
眼睛能使你发抖!
阿拉木汗住在哪里?
吐鲁番西三百六!
……
在这支幻觉的歌中,我带着一颗有点儿惆怅也有点儿渴望的心,悄悄儿地离开了吐鲁番……
奇怪的是,后来我多次来到吐鲁番,也多次在吐鲁番的街市上走过,尽管见过的美女也不少,也认识了几个叫古丽的姑娘,但再也没有2003年初春经过这里在短暂逗留时产生的那种感觉。“吐鲁番西三百六”,如果算三百六十里已经超过了达坂城,2007年春天我就到了达坂城,可还是没有找到那种感觉;如果算三百六十公里就基本到了乌鲁木齐,那里地大人多,就像歌中所唱的“维族姑娘是满街跑”,但我也暂时没能找到。最近这一次,也就是2011年7月26日中午,再次坐着火车经过吐鲁番,也在一种盼望的心情里下了车,在站台上四处张望,除了按照我姨婆的要求,下去买几个茶叶蛋之外,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想寻找、想看看是否还可以碰见当年那位像玫瑰花一样的吐鲁番姑娘。可是,除了看见几个汗流浃背的上落客,我没能看见我留存心中的那个倩影,那个玫瑰花一样的吐鲁番姑娘。尽管一再失望,我还是决定以后还是要坐着火车多走几次吐鲁番。尽管至今没有发现类似于当年的那位美丽高挑带点冷意的阿拉木汗,但是,每次经过这里,经过吐鲁番,我都有一种非常渴望的念想,我都有一种不同寻常的真正触动心底的感觉!
阿拉木汗阿拉木汗,你今天已经到了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