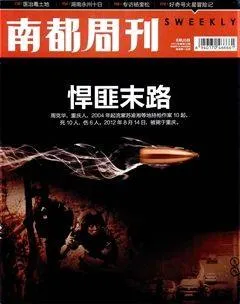信息社会的丑闻传播
一组所谓“庐江不雅照”突然在网络上疯传,引发狂欢,也引发不安。
狂欢与不安之间的对立,反映了两种不同的道德取向,核心是如何对待他人隐私。“狂欢派”认为,官员没有隐私,照片显示官员涉嫌参与其中,那么转发就是为了打击可能的腐败。而“不安派”则认为,未经审慎确认便转发,完全置他人隐私于不顾,无端给人造成困扰,甚至带来不可挽回的名誉损失,是非常不道德的。
我的个人立场是“不安派”。我看到了那些照片,但我不转发,因为我认为照片本身不宜转发,对于转发的后果,我也感到不安。
但是我不能认为出现转发狂潮是因为其他人的素质低。不可否认,对于不雅照,网民的转发动机中会涉及到窥私欲、幸灾乐祸、轻率、隐私保护意识不强等等。但终究不能断言,人们使用的通信工具越来越高级,人们的素质就越来越低级。转发不雅照这种事情,与人们的道德认识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与信息社会本身的许多特点密切相关。
从宏观来考察全球信息社会,就会看到,涉及某种隐秘事态的影像信息在网络上广泛传播,且不受控制,这种情况不仅大量出现,而且深深蕴含在信息社会的内在结构之中,不可分割。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断言,信息社会必然是丑闻涌现的社会。
我很赞成约翰·汤姆森在《丑闻政治:传媒时代的权力与透明度》一书中提出来的观点:由于数字技术的发展,原先国家掌握的机密技术,例如窃听、跟踪、秘密摄像等等,变成了大众技术。于是,监测、曝光、传播各种官场丑闻,成为新的权力。不幸的是,官场丑闻的确很多。
也就是说,丑闻轻而易举地获得大量传播,第一个条件就是技术扩散。就像核武器扩散导致严重的安全威胁一样,通信技术的大众化扩散,导致信息安全问题与隐私安全问题。
有一部著名的影片叫《窃听风暴》,在片子里,前东德时期的秘密警察长年监听一位著名剧作家,将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录在磁带上。这个故事,很像奥威尔写的《1984》,“老大哥”通过一套精密技术,严格掌控人们的一举一动。
比较一下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不雅照事件,就会发现,情况已经有了根本性的颠倒。匿名者上传材料,大量网民转发,瞬间形成围观局面。这样带来的结果是,官员或者名人,非常容易面对丑闻指控,且澄清不易。
另一位学者约翰·厄里在《全球复杂性》一书中,也专门讨论过信息社会条件下的“丑闻涌现”问题。在他看来,大量的信息以丑闻的方式被传播,还因为以下两个条件。
首先是标准化犯罪。他的意思是说,权力、财务、性事,是犯罪故事的三个标准要素,而权力滥用元素是核心。因此,满足窥私欲的不雅照固然容易传播,而一旦与权力或腐败的联想挂钩,传播行为会更疯狂,变得无法控制。
其次一个条件来源于品牌脆弱性。在信息社会中,品牌效应严重依赖于传播。任何好的品牌宣传,都需要拉近与受众的距离。但是距离越近,暴露的机会越多,就越脆弱。举凡大公司、名牌产品、名人以及政府公信力等等,都是品牌。品牌需要在密集的信息流中反复维持和强化自身,但是,密集的信息流中必然包含大量的丑闻,或潜在的丑闻。越是大品牌,越是丑闻缠身,几乎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丑闻对谁而言都是一种丑,环保组织极力揭露污染情形,对于当事的公司品牌而言,是丑闻。贪官污吏被揭露,对于政府而言是丑闻。微软也好,苹果也好,其品牌均享有盛誉,但是,这正是由于多年来,多个团体的多种丑闻指控,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压力,迫使他们不断修正其经营方式,包括提高代工厂的工人待遇。
因此,对这次不雅照的热播现象,不用急着下道德评判。不如把品牌看作是一种信息秩序和信息策略,同时,把丑闻看作是相生相克的另一种信息秩序,另一种信息策略。不同的力量、不同的权力、不同的诉求,在不同的秩序和策略下集结起来,构成信息社会中的两军对垒与权力制衡。他们之间的黑白与善恶,并不容易用传统的道德标准去衡量。这当中,可能存在熊彼特讲的“毁灭性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