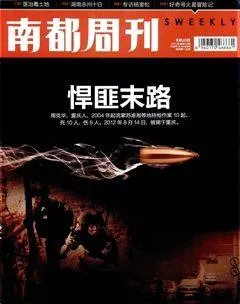让普通人的故事进入聚光灯
舞台上,“奶奶”无力地坐在椅子上,“孙子”正俯伏在奶奶的脚边,安慰着奶奶,其他演员,正在另一边的“缤纷世界”自由飞翔。“孙子”看到出神处,他的“化身”也飞到了另一头的精彩世界。“小时候,奶奶是我依靠的墙,可是现在,奶奶却变成了让我不能飞出去的墙……”
五个演员正在动情地表演,伴随着简单的配乐。在舞台一侧不足2米距离的两张椅子上,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终于忍不住流出男儿泪,旁边的主持人体贴50多个观众,各有感触,几个年轻人和长者,也悄悄擦起了眼泪……
然而,台上表演的并不是精心排演的剧本,而是舞台边那个年轻男孩的真实故事。这个小伙子一直希望出国参加工作假期,边打工边旅游,见识外面的世界。可是,挚爱的奶奶年纪很大了,他担心一旦远行,奶奶有什么事他会赶不回来;同时,申请工作假期是有年龄限制的,如果此时再不申请,他将永远错过。
听完年轻人的讲述不到一分钟,演员们即兴演出了以上的一出短剧——这就是“一人一故事”剧场,也就是“Playback Theatre”,是一种即兴的剧场活动,1975年,首个一人一故事剧团由美国的Jonathan Fox、Jo Salas创立,在香港,这种表演模式也有十多年的发展。在“一人一故事”里面,所有的一切舞台元素,灯光、服装、道具、背景等等都做到极简,却将人最真实、复杂的情感展现出来。
好像上面提到的这场言遇剧团的“一人一故事”演出,舞台就设在工厂大厦里一个大房间,这里是他们平常的排练房,公演时,就摆上六十个座位,座位前的空间就是表演区了,和观众的距离不到两米。舞台的灯光就只有几盏简单的射灯,也没有特别灯光效果;演员们的统一服装就是T恤配黑裤子,只是以不同颜色的T恤以示区别,大家都光着脚;道具只有几张木椅和一些彩布,还不一定都用得着;表演区一边,摆着两张椅子,“领航员”,也就是主持人就和被邀请上台的观众坐在那里分享故事。
言遇剧团
Mercy 和 Eddie是香港言遇剧团的创办人和联合艺术总监。两个人对“一人一故事”剧场有着相同的理念,因而走到了一起。
“我们相信每个人的故事都值得被聆听,彼此的生命会在故事中相遇。每一个故事都是重要的,我们能在相同里找到共鸣,在差异里体现接纳与尊重。”这是言遇剧团的信念,也是让团员们走到一起的信念。有趣的是,并不是每个团员一开始接触“一人一故事”就感兴趣的。有的团员,甚至因为对这种表演形式感到厌恶,包括创办人之一的Eddie。
Eddie在学校时修读“社会工作”,并对戏剧有着浓厚的兴趣,最初接触“一人一故事”时,是被它的表现形式所吸引。当时他觉得,“一人一故事”正是一种服务社群的应用戏剧模式,但观看了几次不同剧团的一人一故事演出之后,他却对这个戏剧模式产生了反感。
Eddie认为一人一故事应该是服务观众的,但在早期他观看的一些演出里,剧团似乎在为自己的表演欲服务:领航员,也就是主持人,在引导分享者时常常没有照顾到分享者的感受,而是以一种强势的方式去要求、套取观众的故事,甚至在分享者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硬要去深挖,以致触碰到分享者伤处;而演员在表演时,又往往带有过于夸张、煽情的色彩,乃至以一种批判的眼光去演出分享者的故事。虽然从现场观众的反应来看,的确也有很多人在看了表演之后感动流泪,但Eddie看到的更多是一种伤害。因此,Eddie一度觉得,他再也不想接触此种戏剧模式了。
直到后来在英国读书,一位老师再次向Eddie提起一人一故事的概念,邀请他观看了一场一人一故事,才引起了他对这种即兴戏剧模式的重新思考。回港后,Eddie拜访了香港一人一故事剧场圈子里面比较具有影响力的创作人Mercy。
Mercy本来就在社会福利界工作,主要服务于小区剧场。对于Mercy来说,她一直都希望通过戏剧在社会层面对人造成影响。Mercy相信,“一人一故事”的表演形式,应该是以一种真正的聆听心态,而非抱持批判的眼光。她希望,可以将分享者的故事以艺术的形式去呈现,作为一份礼物回赠给分享者的同时,也送给观众。Mercy的这种理念,和Eddie对一人一故事的理解不谋而合,而刚好Mercy原来所在的剧团也刚刚解散,于是,两人联手创办了言遇剧团。
来自广州“一人一故事”的“同声同气”也不时到香港交流取经。他们的剧团总监郑春晖表示,香港有自己的演艺学院,对发展剧场比较有优势。但是,她觉得言遇剧团最大的优势,也是最值得学习的地方在于,他们是真正了解这种剧场形式的故事价值,是在打开一个平等的分享空间,不强求观众,也不取悦观众,而是真正尊重观众。
即兴的能力
对于观众来说,表演者的即兴能力是最神奇的。对于Mercy和Eddie,即兴的能力并不是那么的神秘。所谓即兴,其实只不过是包含以下几个元素:敏锐度,即如何去聆听和感受观众的分享;创意,将故事转化为戏剧;行动,也就是表演的能力;脑和身体的平衡,有时候我们是先思考计划再做动作,有时候本能反应的动作会引领思考,两者就要取得平衡;还有就是搭档之间的互动,相互之间信息的吸取和给予。这里面,既有演员个人的修行,也有相互之间的合作。
“一人一故事”的演出人员,包括了领航员(即主持人)、乐师和演员。演员自然就是演出故事的主要构成,但领航员和乐师也非常重要。
Eddie和Mercy都是经验丰富的领航员。按照Eddie的说法,领航员其实有点像导演,除了把握演出的整体节奏,还要根据分享者的故事和他本人讲述的重点来引导提问,接下来再思考演出的模式,比如说是使用三段故事的模式,还是自由演绎的模式等等。举个例子:当分享者讲了他在两个城市生活的不同感受,领航员就会让分享者除了选一个人演自己,还会请他选两个演员分别扮演两个城市,这相当于接下来的表演,强调的是他和这两个城市的关系。
但领航员比影视剧导演更多了一重任务,就是要照顾分享者和观众的感受。因为作为领航员,他必须要带领全场观众进入分享和聆听的状态,营造一种安全、亲和、活泼的交流气氛,这样,观众才乐于分享自己的故事。“因为我们的宗旨是服务分享者,服务观众,希望大家可以通过看别人的故事来感受自己。”Eddie说。领航员要懂得察言观色,不能对分享者的痛处咄咄相逼,相反,要因势利导,同时也要适可而止,让分享者在安全舒服的气氛中,通过自主倾诉而得到心灵上的释放。在一次演出中,有一名观众在分享她的感情经历时欲言又止,领航员就不再问她具体的事情,只是关心她的心情感受,让她将心中郁结说出来。
乐师是“一人一故事”里面的又一重要角色。简单的音乐,不但让故事锦上添花,更是即兴表演的节奏和结构。言遇剧团的乐器很简单,主要是口琴,也有手鼓等各种简易乐器,好几个团员都可以充当剧团的乐师角色。而有乐队经验的阿Ky是言遇剧团的主要乐师。
“虽然做演员和做乐师都讲究合作,但还是挺不一样的。”阿Ky 说,“做演员时,精神更紧张,要比乐师记住更多讲述的细节,有时候,分享者的一些关键话语,是要一字不变地变成台词的。而乐师,所留意的主要是分享者的各种感受,要听到他情绪上的变化,把握整体气氛就可以了。” 作为乐师,要给出故事的起承转合,但同时也要留出空间给演员响应。但有时候,演员在响应时,也会比乐师先一步进入下一个故事阶段,乐师的配乐就要配合做出转折——给予和接收,合作就在此间产生。
相对于演员之间的亲密互动,独处一边的乐师似乎有点“孤独”,但其实也是透过空气和演员、观众互动的。阿Ky相信,音乐就是空气的震动,而空气的震动是会影响气氛的。
言遇剧团的乐器很简单,也很特别——60多件乐器,都是团员们各自一件件慢慢积累起来的,其中正式的乐器有口琴、吉他等,也有儿童玩具琴,甚至是捏一下就会发出怪叫的“橡胶鸡”。阿Ky最记得,有一位德国的“一人一故事”资深艺人,就特别赞赏言遇的乐器——乐器可以很简单,只要用对地方就很好。
聆听的艺术
聆听的艺术是“一人一故事”最关键的一环。Mercy和Eddie指出,很多时候,我们在听人家的故事时,往往会将自己的经验代入,结果就会按照自己固有的思路去想象事件,乃至将聆听变成了满足自己的倾诉。但事实上,每个人表面的事件相似,背后却各有各的隐衷和故事。真正的聆听,就是要尊重这些故事的原貌,而非加入自己的主观臆想,或者将自己深深投入,以致影响了演出。比如说,有一场在四川为地震灾民举办的演出,当时的演出团队本身也是当地的受灾者,一听到台下观众的故事,演员们就感同身受泣不成声。“这需要一种情绪管理的能力。我们要将自己放空,带着尊重去聆听,而不只是一味想着自己。”Eddie说。
“但又不是以一种纯粹的第三者身份去听,这是一种平衡。”Mercy补充道。聆听,更是一种旁观的理性和同理心的感性之间的平衡。如果不能同情叙述者的感受,不去体会他们的感情,聆听也不能真正到达内心,更遑论代入叙述者的心理,去将故事重新整理演绎出来。就像Mercy说的:“演员不能只是一个机器人,要做到故事在‘我’里面,这样才能表现出演员的生命能力。”
艺术感、社群能力、仪式和个人成长,这是“一人一故事”创办人提出的四大要素,也是言遇剧团培训和彩排的着重点。而所谓个人成长,很大部分就在于聆听和尊重,从中学会清晰地聆听对方,而非只看见自己;同时要有一种自觉性,了解什么事情会对自己有正面或负面的影响,有什么事情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外的。
正是这种犹如朋友般的聆听,营造出一个温馨的分享空间,有时,这种分享的气氛更能延续到演出之后。比如上面提到,那个年轻人分享过他既想离家追求梦想,又舍不得离开年迈奶奶的故事,演出过后,纷纷有观众走到该年轻人身边,和他分享自己的经历和感受。有同样年轻的观众,和分享者诉说其实自己也有类似的境况;也有年长的观众表示,其实自己也有晚辈,但通过这次分享和演出,她对自己的孙子似乎也更多了一份理解,还鼓励年轻人迈出梦想的一步。当晚的演出不止一个分享者。而更多分享者和观众都表示,原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自己是这样的,从此引起了他们对自己的更多思考。诉说了多年前的感情问题的小敏,通过观看演出,才发现原来自己当年的伤口其实并未止血,只是一直压抑着。相反,同样是说了感情问题的Ann却知道,她已经可以站起来重新开始了。
剧场以外
和其他的“一人一故事”剧场相似,言遇剧团主要是服务小区,接受不同的团体邀请进行演出。言遇剧团是个业余剧团,因此每年大约接受十几场受邀演出,除此以外,还有每月的公开排练。 “商业机构邀请的话,我们是严谨地收费,但是如果小区团体,或者是慈善团体,我们又会区别对待,每年一度的公开演出,也是免费对公众开放,有点像是劫富济贫吧。”Mercy打趣道。
而事实上,言遇剧团的十四个团员,包括Mercy和Eddie都另有正职,剧团只是他们的“业余活动”。他们当中,有中学教师、医护人员、社工、自由身剧场演员等等。每次演出,团员们都只是收取车费补贴,在剧团成立之初,甚至连补贴也没有。每次演出的收入,都投入到剧团的经费上面,比如说,租用排练场地。所以在公开演出的时候,剧团还会在开演前设置小吃摊位,也算是筹募经费的一种方式。只是,就凭着“相信每个人的故事也有无可取代的价值,在人与群体互动的分享过程,我们同时发现自己活在当下的内心世界,以及与社群之间产生的联系”这个信念,14名来自各行各业的人走到了一起,组成了“言遇”。
除了两名团员本身就有一人一故事的演出经验以外,大部分队员都是Mercy和Eddie亲自培养出来的。每年言遇都会举行一些训练班,Mercy和Eddie就从中物色人选。
“我们觉得,既然是一起组团,那么我们对于一人一故事的理念就要相同,那么我们自己亲自训练就是最好的寻人途径了。”Mercy说出了心中的考虑。当然,并不是培训班的每一位成员都成为了“言遇”的成员,寻找队员也不是训练班的核心目的。“在变迁迅速及生活忙碌的时代中,通过剧场推动故事分享的艺术文化,让每个人于其中都能真诚相处,使个人价值得以被珍视。”——剧团的宣传单是这样写的,但其实,Mercy和Eddie要传递的,还是聆听和尊重。于是乎,一些他们举办的工作坊,甚至不是以教授表演为目标,而是讲述如何去聆听。
Alex是一名戏剧教育的硕士毕业生,本身就对应用戏剧很感兴趣。参加了“言遇”举办的工作坊之后,回想起过去自己对待学生时,其实会有点“说教”的感觉,也意识到有时候听别人说,其实不过是想讲自己的事情,而并非真正的聆听。之后,Alex作了自我调整,面对学生的意见,即便不同意,也怀着尊重和忍耐的心情,不再轻易判断对错。
而团员阿Ky在参与“一人一故事”之后,在不断的练习和表演中,更对“选择”有了更多的理解:“我们其实每时每刻都在选择。比如说,团员在表演时做出了某个动作,你就要选择如何去响应,是相对的行动还是顺势而作?你是接收对方的‘给予’还是‘给予’对方一些信息?一场演出下来,起码有200多个‘选择’,我就从中去反省。或者有些选择不是最好的,但是最不好的‘即兴’就是犹豫。做人也是这样的,对于别人的意见,或者各种事物,是接受还是推却,我们最少要有反应,不要犹犹豫豫,要相信自己的选择和决定。”
“所谓个人成长,很大部分就在于聆听和尊重,从中学会清晰地聆听对方,而非只看见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