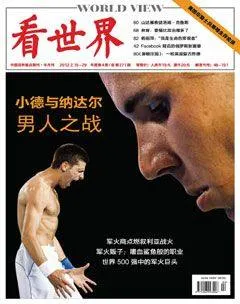杨丽萍:“我是生命的旁观者”
2012-12-29 00:00:00马帅
看世界 2012年4期


“孔雀窝”里
“孔雀窝”是一家自制民族服装的小店,位居云南省歌舞剧院旁边。在店里,店员谈不上多么主动。游客如果愿意,可以驻足观赏,不用担心叽叽喳喳的店员前来推销些什么。这条街叫北门街,附近有闻一多曾经主持过的北门书屋、云南唯一状元袁嘉谷的府邸、海鸥翔集的翠湖,游人匆忙的步伐之间,大多随意地一瞥。
如果没有人说破,人们只能从悬挂的招贴画和“店长推荐”里揣测,为什么这里的服装风格看似是艳俗搭配,却能浑然天成地打破民间所谓“红配绿,看不足,红配紫,一泡屎”的服装禁忌。就像前不久人们在春晚的舞台上看到的杨丽萍,她拖着沉重的羽毛衣裳,用那种来自山里、来自土地的肢体语言,再次征服了挑剔的观众们。
曾经听说一个有关春晚的民间版本,说2012年的龙年春晚,本来希望杨丽萍来跳开场舞,这大致内容是用“龙凤呈祥”来表现喜庆安详,一龙一凤,两大舞者,但杨丽萍毫不犹豫就拒绝了,因为她不会跳凤凰,而且云南也没有凤凰:丛林里交尾的孔雀、村寨里发情的水牛、生长的缅桂花叶子、溪水里游走的鱼,都可以模仿,但凤凰,没人见过。
在昆明,本刊记者听到这样的传说:杨丽萍跳舞最不擅长模仿,如果要她模仿谁的舞姿,她会捉襟见肘,会让人干着急,但如果只描述好一个框架,然后让她循着感觉自己设计一套舞蹈,“惊为天人”一定会迅速爬上观舞者的心头。这个传说和“孔雀窝”的设计理念不免有些相似。
其实,这并不是不谋而合。“孔雀窝”店主正是杨丽萍的三妹杨丽燕。2003年,杨丽萍编导并主演了原生态歌舞《云南映象》,杨丽燕是《云南映象》的服装设计,从幕后走到台前以后,她开了“孔雀窝”,“窝”意味着自然的舒适感,就像服装的选材多使用纯棉和纯麻。
窝里的民族服饰,不少出自杨丽萍姐妹之手,因为她们在服装上的审美观相差无几。
云南“老表”
昆明的市民似乎都能说两句有关杨丽萍的轶事,“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几乎是云南人们的共同认识。
因为高而瘦,11岁的杨丽萍在西双版纳农场学校领操,站在桌子上的她,被西双版纳歌舞团的军代表看中。她听说加入歌舞团有30元的月薪,于是去了:因为她还需要帮助养家。后来,杨丽萍自己的《云南映象》歌舞团,补助最初也是50元一个月,但水涨船高,现在骨干演员已经能每月赚到4000块了。
有意思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有一个体态特征,即是身材修长、手长脚长,和杨丽萍的体态相似,杨丽萍要求他们每天练舞要练到出一身大汗。杨的舞蹈观是:每个动作要像从地里长出来一样。据说,在排练《云南映像》的时候,是没有音乐的。杨丽萍习惯了没有音乐的排练,她的舞蹈《月光》就是这么来的,要演的时候才临时配上音乐,音乐是吕克·贝松的电影《雨人》的插曲。记者从参观过《云南映象》排练的人处听说,在排练的时候,只有杨丽萍带着“老表”们,在舞台边顿足拍地。
与江西人用“老表”来表示亲昵不一样,在昆明人的语言里,“老表”有两种意思,一是指比较熟识的朋友“阿表哥”(男性)和“阿表妹”(女性),二是指衣冠不整,穿着邋遢,讲着异地口音的男人。
杨丽萍歌舞团的人的确是“老表”,他们来自哈尼族、彝族、佤族,有的人是在大山里放牛,因为嗓音洪亮而被采风路途中的杨丽萍所发现;有的人是因为在庆祝丰收的时候,舞蹈跳得很狂放;有的人是因为能够像村寨里的长老(巫师、祭司)一样,发出神秘而深邃的呐喊。他们现在都住在昆明,虽然不太习惯城市的生活,但都舍不得离开歌舞团了。因为杨丽萍也舍不得让他们离开。
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在这里能够无拘无束地跳舞。他们是打心眼里热爱跳舞,哪怕在周末的夜晚,在与“孔雀窝”毗邻的翠湖边,他们也要相聚跳上一段。
其实,杨丽萍也有“老表”的特征,据说,当年她被西双版纳歌舞团录取以后,还在单位附近开垦荒地种菜,她还想着养家,她甚至从菜上看到旺盛的生命力。
舞蹈与生命
旺盛的生命力也如实凸现在了杨丽萍的作品里,2012年春晚里的《雀之恋》固然令人难忘,但在湖南卫视的春晚里,杨丽萍和她的侄女小彩旗出演的《春》,更能让人想到萌动的生命。
这段舞蹈,通过姨甥二人头发的缠绕、纠结,以此表现生命的生长;而在2009年,刚刚10岁的小彩旗就和歌手萨顶顶合作过《万物生》,小彩旗敲云南少数民族祭祀时候用的神鼓、萨顶顶演唱,同样表达了对于生命萌芽的热情。
因为《雀之恋》,“孔雀窝”在新年伊始的时候,迎来了不少客人,这其中不乏一些年轻人,他们是冲着小彩旗来的。在查询“孔雀窝”的地址时,记者无意间在贴吧里看到,不乏有人说要暑假去昆明,以期望在“孔雀窝”里见到放假的小彩旗。
如果不是与姨妈杨丽萍、与歌手萨顶顶的合作,人们也许不会注意到小彩旗,她是杨丽萍四妹的女儿,天生就是跳舞的料。《云南映象》、《藏谜》、《云南的响声》,在杨丽萍的代表作中几乎都能看到小彩旗的身影。
杨丽萍没有自己的孩子,她的丈夫是一个美籍台商,尽管公公婆婆都希望有自己的孙子,但当杨丽萍知道怀孕需要增肥、停止跳舞的时候,她拒绝了生孩子的要求。家庭关系一度紧张,丈夫甚至飞回台湾去了,但最后因为妻子的执着,他终于理解,并把制作经费调给妻子。
也许还保留着母系氏族的遗风,云南的少数民族一直保持对长姐的敬畏,白族的杨氏姐妹亦然。小彩旗因为一直和杨丽萍一起跳舞,感情深厚,杨丽萍也一直视为自己的女儿。在小彩旗的眼中,杨丽萍不但会教她怎么跳舞,还会给她买衣服,带她吃大闸蟹。她还在读书,暑假的时候有时在“孔雀窝”玩耍,人们已经把她视为杨丽萍的接班人了。
因为现年54岁杨丽萍已经把《雀之恋》当成了自己的舞蹈终结之作,她在准备舞台剧《孔雀》,这台剧将讲述一个女舞者的故事,被视为杨丽萍的自传体兼告别之作。
曾经有人问过杨丽萍:“你是为了舞蹈才不要孩子的吗?”她回答说:“有些人的生命是为了传宗接代,有些是享受,有些是体验,有些是旁观。我是生命的旁观者,我来世上,就是看一棵树怎么生长,河水怎么流,白云怎么飘,甘露怎么凝结。”
对于杨丽萍在舞台上的神话,有人宁愿理解为一种“灵魂附体”,在云南山野之间,这样的传说并不少见。用杨丽萍的四妹的话来说:“她觉得自己是神,不过,神也没什么了不起,神不过就是有一技之长的人,寨子里有很多这种灵魂附体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