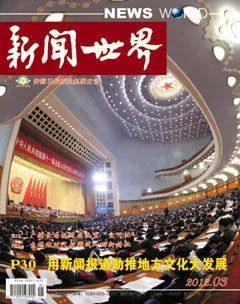有关“诗言志”产生之初的几个问题
【摘 要】“诗言志”能够成为中国诗学的核心命题,不仅仅在于其形成了对中国诗学影响深远的诗教理论,更在于这个命题包含了丰富的内涵。本文认为“诗言志”产生于殷商时期,或者是更为久远的舜帝时代。“诗言志”产生之初应当是祭祀巫术文化语境下“人-神”关系的诉说,后来经过不断发展,诗才开始表达人的怀抱志意。“诗言志”还包含着一个如何才能言志的问题,并与音乐理论紧密结合在一起。
【关键词】诗言志 缘情 音乐
“诗言志”一直是中国诗学的经典命题,朱自清先生称其为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①。早在上个世纪,朱自清先生即著《诗言志辨》一书,对此命题进行了详细论述。受西方文化“理智/情感”的影响,今人看待这个命题,多认为“诗言志”只讲政治之怀抱,而不讲情。而近年来,出土的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馆藏的战国楚竹书中关于先秦儒家性情问题的论述,也给我们带来了儒家诗论的新认识。我们需要重新反思,“诗言志”能够成为中国诗学的核心命题,不仅仅在于其形成了对中国诗学影响深远的诗教理论,更在于这个命题包含了丰富的内涵。
“诗言志”,这个命题显然是历经一代代构建起来的。可以说,“诗言志”是个“历史积淀”的产物。因此,我们需要返回“诗言志”这个命题产生之初去探索这个命题的丰富性。
一、“诗言志”之产生
对于“诗言志”,我们首先面临的一个比较头痛的问题就是它的产生时间。首见“诗言志”是《今文尚书·尧典》中舜对他的乐官夔所说的一段话: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上述这段话是否真实可靠,“诗言志”是否产生于年代久远的舜帝时代?赞同此说的有顾易生、邻木虎雄等。支持战国说的有蒋善国、郭沫若等人。而陈良运先生在《中国诗学体系论》一书中,则提出 “诗言志”观念应当形成于秦汉之际。②
《尚书·尧典》产生的确切年代在学界仍然是一个争议比较大的问题,至今尚未达成一致。但《尚书·尧典》一书的成书时间和“诗言志”这个命题的产生时间应该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徐复观先生认为,对于《今文尚书》的文章应分三类来看:一是根据口头传说整理、记录的,如《尧典》、《皋陶谟》等;二是经整理过的典籍,如《甘誓》、《汤誓》等;三是传下来的原始材料,如《商书》中的《盘庚》及《周书》等。③对于根据口头传说整理的这些材料,我们不能像“疑古派”那样一概否定掉。近年来新的地下出土文献也为我们提供了“诗”与“志”的新材料。曹建国先生根据文献材料证明殷墟卜辞就存在“蔽志”的描述。“依据战国简、周原卜辞殷墟卜辞,以及《尚书》、《左传》等传世文献所记载占卜‘蔽志’,则舜的时代产生‘诗言志’的观念是完全有可能的。”④而在春秋时期,“诗言志”已经成为了当时社会的共识。因此,在目前情况下,我们还是认为“诗言志”产生于殷商时期,或者是久远的舜帝时代。
二、“言志”与“缘情”
从古至今,人们一直都在思考着“诗言志”和“诗缘情”的关系。“志”与“情”究竟是一体还是对立,两种观点莫衷一是。特别是五四以来,受文学是感情产物的影响,这个问题更是引起了极大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志”是以理性为主导的怀抱志意。朱自清在《诗言志辨》认为“志”是与“礼”结合在一起的怀抱。另一种观点则“志”是意与情的结合,代表人物有罗根泽、郭绍虞、王运生、顾易生等人。
应当承认,在不同的时期,“志”的含义是不断变化着的。闻一多先生在《歌与诗》中认为“志”有三个内涵:记忆、记录和怀抱,并“代表了诗的发展途径上三个主要阶段”。叶舒宪先生则在《诗经的文化阐释》一书中认为:“诗言志”也就是“诗言祝”、“诗言寺”。把与宗教祭祀相关的诗歌唱词和民间自由传唱的歌谣韵语作为上古诗歌的两种发生,这是非常有见地的。因此,《尚书·尧典》所记载的“诗言志”应当是巫术文化语境下“人—神”关系的诉说。意大利历史学家维科在《新科学》中认为人类的原始文化史是一种诗性文化:古代异教民族把一切涉及占卜预兆的事情都归原到约夫这种想象的共相,所以这些民族生下来就具有诗性。他们的诗性智慧是从这种诗性玄学开始的,诗性玄学就凭天神的意旨或预见这方面来观照天神。⑤顾祖钊先生在《华夏原始文化与三元文学观念》一书中对华夏巫术文化和“诗言志”的产生有着很详尽的论述。然而又把“志”解释成“天之意志”(简称天意)则是我不认同的。作者又举《墨子·天志篇》“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此处只能解释“志”与“意”想通,而不能证明“诗言志”之“志”即是“天意”。正是诗所表达出来的“人意”与“天意”相互交感,才有可能达到“神人以和”的境界。
因此,“诗言志”之“志”最初应当是表达祭者的意愿。从实践层面来看,宗教祭祀的诗歌唱词和民间自由传唱的歌谣韵语都有可能产生“诗言志”的观念。但由于当时特殊的书写条件及文化集中上层,被记录下来的应当只有和宗教祭祀相关的“诗言志”。到了西周时期,“诗言志”才慢慢开始从神的诉说转向了人,用诗来表达自己怀抱。《诗经》中出现了一些“作诗言志”的篇章。春秋时期,“赋诗言志”则成了当时社会政治活动不可缺少的环节。到了先秦儒家这里,“诗言志”才和诗教理论结合起来。然而,无论怎样发展,我们都不能简单地把“志”看做纯理性的思想,还是要笼统地看做“怀抱”。
三、诗与乐舞
闻一多认为:上古歌诗由分途趋向合流。而陈伯海则认为:“歌诗的发展自不会由分途趋向合流,反倒是由一体走向分化”,而“诗的因数曾长期隐伏于歌谣之中,而后才分离出来,最终取得自身独立的形态。”⑥“歌”与“诗”到底是合流还是分途?我们仍不能确定。但我们能肯定的是:上古的诗一定和乐舞有着密切关联。
对于“诗言志”,我们关注的重点一直是“诗言何志”以及“诗言志”是怎么一步步确立起来的。而海外汉学家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特别注重诗如何才能言志。诗作为一种符号,必须和乐舞结合在一起才能更好地发挥言意的效果。对于《尚书·尧典》的这一段话,郝大维和安乐哲说:“用语词表达心志,用诗赋论争,都要用乐器加强诗的效果,这一过程也就是增强语言表达的精炼、微妙性以及表达的潜力。”⑦同样,高友工也认为:第一句,诗言志,一直被确定认为是中国诗学中最著名的命题,但人们忽略了同样重要的第二句话:歌永言,这第二句话恰恰提醒我们,只有在音乐理论这一语境中才会对第一句加以正确的理解。“永”一词的准确意义是难以解释的,但它的要旨是,用以交流的普通语词必须转化得更为集中更为形式化。就语言而言,这一切可以通过重复、延宕以及其他的形式变化来完成。将“诗言志”和“歌永言”合而论之,便构成了后来的音乐理论的核心……
“诗言志”能够成为中国诗学的重要命题,不仅仅在于儒家诗教理论和政治建构的结果,还在于这个命题具有很大的阐释空间,历代都有影响。
参考文献
①朱自清,《诗言志辨》[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4
②陈良运,《中国诗学体系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33-48
③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M].台湾商务印书店,1969:589-590
④曹建国,《楚简与先秦》《诗》学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234
⑤顾祖钊,《华夏原始文化与三元文学观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60
⑥陈伯海,《释“诗言志”》[J].《文学遗产》,2005(3)
⑦[美]郝大维、安乐哲,《通过孔子而思》[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75
(作者: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11级文艺学研究生)
责编:刘冰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