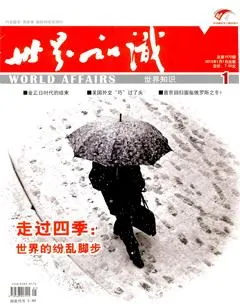东欧民族分布的“马赛克现象”
二战后,东欧成为一个地缘政治概念,指那些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冷战结束后,地缘政治上的东欧为地理位置上的中欧和东南欧所取代。几经分裂,如今这个地区由原来的八个国家演变成13个国家,另外科索沃已经单方面宣布独立,但包括中国等许多国家尚未承认。在东欧这块面积只有127万平方千米的大地上,国家多,民族更多,由此产生的各种关系尤为复杂,因而有“万花筒”之称。其中,民族分布的“马赛克现象”就成了认识这个地区发展的复杂性和曲折性时不可或缺的视角。
你中有我,我中有他
马赛克本是建筑上的专有名词,指的是用小石块或有色玻璃碎片拼成图案,从而产生一种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东欧国家民族多,既有多个不同的南部斯拉夫民族,也有多个非斯拉夫民族。仅从语言学上看,东欧的主要民族就涵盖了印欧、乌拉尔两大语系,拉丁、斯拉夫、乌戈尔、阿尔巴尼亚四个语族,西斯拉夫、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东拉丁、匈牙利五个语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十种语言。更为复杂的是,这里的许多民族并不是各自划地封闭为国,而是相互跨界而居,你中有我,我中有他。就有独立国家的民族来说,匈牙利族人在罗马尼亚有特兰西瓦尼亚、在塞尔维亚有伏伊伏丁聚居区;塞尔维亚族人在波黑有塞尔维亚共和国、在克罗地亚有东斯拉沃尼亚聚居区,主要居民为阿尔巴尼亚族人的科索沃也有塞尔维亚族人聚居区。除此之外,阿尔巴尼亚族人还广泛地分布在马其顿、黑山等国,斯洛伐克人分布在匈牙利、捷克等国,马其顿族人分布在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等国,克罗地亚族人分布在波黑、匈牙利等国,斯洛文尼亚族人还分布在克罗地亚、匈牙利,穆斯林、吉普赛人和犹太人也广泛地分布在东欧各国。民族分布的这种“马赛克现象”,是东欧社会发展多样性和相互关系复杂性的物质基础。
民族分布“马赛克现象”的衍生物
不同民族马赛克式的分布,一方面把这个地区的民族色彩编织得五颜六色、赏心悦目,可另一方面也在这个地区造成了许多“热点”或“难点”问题,带来许多剪不断、理还乱的国家间、民族间、文化上的恩恩怨怨。
首先是跨界民族聚居区归属的争端。特兰西瓦尼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属于匈牙利王国和奥匈帝国,1920年才被划归罗马尼亚。科索沃在长达上千的历史中交替地属于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塞尔维亚人说科索沃是“可爱的故乡”,阿尔巴尼亚人称科索沃是“文明的摇篮”。在东欧,差不多所有相邻的国家之间都有此类问题,只是影响程度大小不同而已。某一地属于哪个民族还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在深层次上,它们映射的却是一些民族的辉煌和另一些民族的悲哀。无论是辉煌还是悲哀,当事的民族都久久难以释怀。
其次是宗教文化上的纵横交错。东欧地区是天主教文化、东正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交汇处。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是天主教国家;塞尔维亚、黑山是东正教国家;罗马尼亚绝大多数人信奉东正教,少数人信奉天主教;保加利亚和马其顿两国多数人信奉东正教,少数人信奉伊斯兰教;阿尔巴尼亚多数人信奉伊斯兰教,少数人信奉天主教和东正教;波黑是伊斯兰教、东正教和天主教并存。当宗教文明成为大国或强国对外扩张、争夺地区和世界霸权工具的时候,不同宗教文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就会出现。各种宗教文明的大国载体都强调自己的优越性,于是,一方面由它们支撑的不同宗教文明都显现出严重的排他性,另一方面大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披上了“神圣”的即宗教的外衣。在单一文化区域看不到这种文明冲突,但在多种文化交汇的中东欧可就完全不同了。近现代发生在中东欧的许多冲突和战争,如奥土战争、俄土战争、巴尔干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波黑战争和迄今尚未尘埃落定的科索沃独立等,都有宗教文明冲突的色彩。
再次是大国影响上的差别。一般而论,天主教是西欧的宗教文明,东正教是东欧(俄国)的宗教文明,伊斯兰教则是奥斯曼帝国的宗教文明。处于天主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交汇处的中东欧地区成了东西方大国势力博弈和此消彼长的场所,从而使这一地区依附于不同大国的民族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到了近现代,中东欧国家的社会发展更是笼罩在大国的阴影之中,而大国决定这些问题时都要考虑自己的文明属性所及,“马赛克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些大国共同参与的“杰作”。比如,1912年欧洲六大国在伦敦决定阿尔巴尼亚独立时,圈定的国土和人口都不及阿尔巴尼亚人所希望的一半。再比如,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等国的“出生证”也是由《凡尔赛条约》的制定者根据自身的利益和需要开具的。这些“出生证”都带有种种限制条件,所以由此诞生的中东欧国家成为或有“内伤”或 “肢体不全”的“残疾国家”,背后潜藏着无限的危机。英国学者帕尔默说:“很可能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少数民族,其中一些人安于他们的境况,一些人从最初就吐露过他们的敌意,许多人在经历多年令人沮丧的不平等待遇后,终于满怀怨恨。”
向心力与离心力
这种 “马赛克现象”造成的最大问题之一是跨界民族认同与界内民族分离的问题。比如,某些跨界民族对其所居住国的认同感差,而对界外母国的认同感强,从而产生相悖的向心力或离心力。除了“大阿尔巴尼亚”的主张和科索沃独立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外,在游走巴尔干地区的时候,我还注意到了一些其他现象。波黑的塞尔维亚族人聚居区的东正教堂前悬挂的是塞尔维亚的国族;在马其顿,斯科普里老城边上也有一尊阿尔巴尼亚民族英雄斯坎德培骑马挥刀的雕像,一些阿尔巴尼亚族人聚民区悬挂着阿尔巴尼亚的国旗。我访问黑山的波德格里察的时候,一位阿尔巴尼亚朋友从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来看我。我们一起去一些地方旅游的时候,他几乎像在阿尔巴尼亚一样自如。我询问其中的缘由,他告诉我这里居住着许多阿尔巴亚族人。在匈牙利2010年议会大选时,斯洛伐克比其他国家更在意结果,因为这似乎关系到在匈牙利的斯洛伐克族人的地位。反对来,匈牙利也同样关心在斯洛伐克的匈牙利人,2009年就抗议过斯洛伐克修改语言法,认为它歧视匈牙利族人。2009年3月,匈牙利总统绍约姆·拉斯洛应邀前往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的一个匈牙利族人聚居区参加历史纪念日活动,罗马尼亚方面大为不满,收回专机的降落许可,迫使绍约姆改乘汽车前往。
类似的情况几乎在中东欧任何两个相邻甚至不相邻的国家中都有,它们所映射出的问题是相同或相近的,那就是一个主体民族在外的少数民族对居住国的认同感不强,而且有程度不同的离心力,同时对境外的“祖国”有强的亲近感。这种反向原向心力或离心力都在不同程度上对这些少数民族的所在国造成了伤害,也易激起不同民族间的敌对情绪。诸如大阿尔巴尼亚主义、大塞尔维亚主义之类的民族主义政治思潮的出现也都与民族分布的“马赛克现象”有着密切关系,这些思潮共同的表现对外是普遍的扩张,对内是对少数民族的否认、歧视和同化,内部民族关系、相邻国家间的关系以及地缘政治都变得复杂起来。
更为重要的是,从长远的视角看,“马赛克现象”最大的消极后果或许使欧洲的一体化停留为美好的梦想。冷战期间的欧洲一体化是在同一个文明区域内进行,各成员的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相近。而冷战后的欧洲一体化不仅范围是跨文明的,而且扩展的驱动力是带有浓厚情感色彩的“政治征服”。因此,观察、评析欧洲一体化发展的前景时,除了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这个世界通行的背景外,不能忽视中东欧特有的多元化的文明底色。几十个规模大小不同、社会发展程度不同、政治文明背景不同的国家能够和谐得像一家人似的吗,不远的将来能联合成一个超级国家吗?即使欧盟能将中东欧所有国家都吸纳进去,但是,由于民族分布的“马赛克现象”及其消极衍生物,欧盟最多也只能是哈布斯堡王朝那样的超级国家,形式可以维持,但很难永存。更悲观地说,在历史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欧洲的常态,大国争霸也是欧洲的常态。中东欧正处于三大文明交汇处,也是统一欧洲的裂缝地带。在内部离心倾向和外部拉拽效应的双重作用下,作为一个超级国家的欧盟是可望不可及的,统一的大欧洲更多的还是美好的愿望而已。
(作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