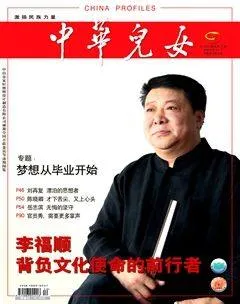胡圣虎 归去来兮北大“狂生”
2012-12-29 00:00:00刘之昆
中华儿女 2012年12期



导语:十年后,胡圣虎从部队转业回到湖北,任职省直机关工委研究室副主任。似乎从这时起,他才真正毕业,踏入社会,开始自己规划人生
主句:机遇与命运却不像胡圣虎所言。他认为只能修身的冷门专业,在某些特殊部门却成了急需的人才,加之胡圣虎世代“赤贫”的出身和出众的成绩,1987年毕业后他先去了外交部,继而参军入伍,分配到军队特殊要害部门,做了与他所酷爱的书法毫不相干、但却与所学专业密切相连的“机要工作”,而且一干就是十年。
1984年10月1日,国庆35周年天安门广场阅兵式后,举行了盛大的群众游行。当北大的队伍行至天安门广场时,两名学生突然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标语,此举震撼人心,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此标语的书写者,正是时为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大三学生的胡圣虎。
燕园才子有狂名
1982年高考文科外语类招生时,出台了一项新政——不考数理化,只考外语、语文、政治、历史和地理。偏居湖北省仙桃市毛咀镇的高三复读生、文学怪才胡圣虎因为这项政策而创造了奇迹。由前一年只够上中专的成绩一跃成为1982年全省文科外语类第一名。被赫赫有名的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录取。
消息传来,整个村庄沸腾了,县领导也十分激动,乡村中学首次冒出了全省高考状元,当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财政拨款四十大元重赏。胡圣虎说他像一个在梦境中追逐彩云的傻孩子,今天可以驾着这朵彩云去北京了。
北大无疑是中国知识界的精神灯塔。1982年9月,胡圣虎走进北大校门,心中的那份神圣与自豪不言而喻。记得刚入校时,系主任季羡林,老教授金克木等都亲自来看望他们,慈父般师长们的问长问短,让他感到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他忘不了就在入学当年三个月后,一股寒流突袭北京,一些南方来的贫困学生在瑟瑟寒风中病倒了。季羡林等老教授心急如焚,他们纷纷捐款,买来了洋布和棉花,并组织大家通过自己的劳动来献爱心。从小跟着兄长做过裁缝的胡圣虎轻车熟路,大显身手,把自己的做好了,又指挥班里的十位女生为贫困学子缝制了十余件棉衣。
棉衣虽出自胡圣虎等人之手,却饱含着老教授们的关怀和一片心意。这种“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情感,叫北大学子难以忘怀,并把它变为一种“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巨大力量。
在北大的5年(东语系比别的专业多一年),他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最令胡圣虎骄傲的是,他是当时在图书馆呆的时间最长的学生。他知道什么样的书分布在哪个馆里,哪本典籍放在书架的哪个部位。每到周末,他买上几个馒头,早上进馆,晚上出馆,去得最多的是三楼东面的那间古籍室。那里全是善本和工具书,很少有学生去那里,在那里他却有大快朵颐的快感,他在这里碰到并结识了朱光潜、宗白华、邓广铭、吴小如等名教授,并与他们交上了朋友,不懂就问他们,边学边问,常学常问,不耻上问,于是肚子渐渐鼓了起来,将很多教授都不放在眼里了,在北大渐渐就有了“狂”名。
八十年代初期的一个晚上,几名研究生相约来到社科院钱钟书先生家,还是大二生的胡圣虎拿着根一尺多长的竹笛,也紧随诸师兄之后。众师兄将所研究的课题一一向钱先生汇报,钱先生也将众生应读书目一一列出。轮到胡圣虎了,他指着手中竹笛说:“我是研究乐经的。”钱先生见胡圣虎年龄小,个儿也小,故意开玩笑,“月经?那是医生的事呀?”众师兄哄然大笑。但胡圣虎一本正经侃侃而谈——
刚才众师兄向钱先生请教了四书五经方面的情况,但中华元典是“四书六经”,对第六经,也就是“乐经”,古文经学认为,乐毁于秦火,我认为这是站不住脚的。秦始皇焚书坑儒,许多书籍在民间仍然得以保存,重新整理当非难事。中国的诗不叫诗,叫“诗歌”,在人民群众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的情况下,诗得以流传靠的就是曲调。在古代,这些曲调是固定的,也是被老百姓掌握了的,要不然,就流传不开。由于清末简谱才传入中国,中国的古曲调大部分“失传”了,但我认为,是没有被发掘出来,原来的“律吕”、“工尺”通过对照可译成现代乐谱。两千年来,自称“大师”的和被称为“大师”的人不少,但通四书五经的不通音乐,通音乐的不通四书五经,所以,乐经迟迟没有被发掘整理出来,这真是中国文化的一大憾事……
听了胡圣虎的话,钱先生陷入了沉思。只见先生缓缓站起来,踱着方步: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呢?可惜,我对这一领域涉猎甚少,后生可畏啊!希望你做成这件前无古人的事情!
从此,胡圣虎与钱先生论“月经(乐经)”的故事在北大校园传为美谈,更令其名声大振。
北大5年,实际上也是他的书法技艺从理论到实践全面提高的过程。
当年,北大名师云集,王力、朱光潜、宗白华、季羡林、金克木等数十位大师,都是书坛大手笔,在这样浓厚的艺术氛围之中,经过李志敏、陈玉龙教授的耳提面命,经过京城众多名家的悉心指点,胡圣虎眼界大为开阔,书法进步很快,继之声名远播。未几,便与中文系曹宝麟、国政系白谦慎、图书馆系华人德、历史系张此夫四人一道,并称为北大书法“五小虎”。在校园,他将顽童式的到处题词又上了一个台阶,树枝、抹布、手指、筷子上绑棉花都可以当笔使,宿舍的墙壁、课堂的桌椅、女友的掌心,甚至厕所的门板都是他的“宣纸”,最经典的还是在“三角地”宣传栏不断地出海报、写通知,整个北大校园,到处都是他的手笔。1984年国庆游行那幅标语在“秘密策划”时,两个生物系的同学之所以找到胡圣虎,当然是因为他的书法名气;但那幅标语从最初酝酿的七八个字,因找不到大的毛笔和合适纸张,最后被浓缩成“小平您好”四字经典,并以抹布作笔被写在床单上,这事绝对只有胡圣虎想得出来并且能办得到。
不能不说却不能多说的毕业故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社会结构急剧变化,一批新兴的一夜暴富阶层迅速崛起,而构成这一阶层的不少人要么是文盲半文盲、曾经的社会边缘人物,要么是一批大小权贵子弟。被誉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心理失去了平衡,大学生空怀报国之志,难成济世之才,于是厌学风陡涨,“读书无用”、“六十分万岁”在大学校园里迅速蔓延。堂堂北大,同样不能幸免。
王利芬做节目好,部分得益于她对人的判断与解读。“我原来的专业是文学评论,看过很多长篇小说。文学作品也是在刻画人物,表现人生。在电视节目中我接触这么多优秀的人,我也是在观察他们的人生,他们怎样判断事物,怎样渡过自己的难关;观察他们怎样判断他人,怎样做出决策。应该说原来文学专业所学的都是非常有利于我的。你跟什么人同行,你就大概能够从什么人那里学到什么东西,这个是很重要的。”
纠结也来源于此。在《新闻调查》的三年多的时间里,王利芬一路狂奔,看不到身边的人,好像还是校园里,只管埋头苦读,能得到好成绩就是好孩子。
“我真可谓埋头拉车不问路,只懂得做事,不懂得做人,只懂得向前冲,不懂得两点之间的距离有时并不是直线最短。只懂自已的能力就是一切,就像一个考高分的高中生,不懂得即使有能力,让别人的感受不好也是一种没有能力的体现。”
长于理性分析的王利芬,多年后这样总结那段日子。不知概括性的语言背后藏着多少无奈。
梦想就是坚持
调查记者做得风生水起,她却又转身离开。
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进行了十几年,经济改革是国家的主题,在全球经济浪潮裹挟之下,民众迫切了解中国社会的运转机制,那么要懂经济。跟时任台长赵化勇谈完之后,王利芬接手新栏目《对话》制片人,调入央视财经频道。
当时整个栏目组只有一部电话,一个分机,四个人——两个主编,两个助导。只过了一年,王利芬就让《对话》成为了央视二套的王牌节目。她的秘诀之一是为《对话》打造的“81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负责到人,环环相扣,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