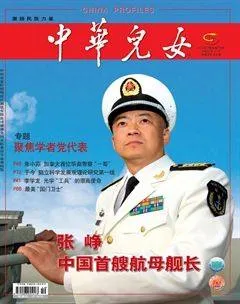行走沙海的“铁驼”
不断向前的车辙,是他们追逐石油的方向,是他们丈量人生的标杆
“沙漠运输是沙漠石油勘探不可缺少的条件,没有沙漠运输,沙漠石油勘探寸步难行”。熟悉沙漠石油勘探开发的人都有这样的共识。
20多年来,塔里木的沙漠运输人奋战在荒凉艰苦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以风沙为伴,以车辆为家,如吃苦耐劳的骆驼,为塔里木油气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不断向前的车辙,是他们追逐石油的方向,是他们丈量人生的标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石油野战军精神,在他们的血液中汩汩流淌,激励着他们不畏艰难,永远向前。
他们是一群特殊的塔里木石油人,人们称他们为:沙海“铁驼”。
侯秉仁 600公里的“远征”
这是一个“老沙漠人”的故事。当时30岁的侯秉仁和同事从罗布庄前往沙漠南缘的安迪尔,拖运一只50吨大平板车的车箱,以便向塔中一口即将上钻的井上运送钻井设备。按照计划,来回600多公里的路程,两天时间返回应该是绰绰有余的,更何况他们开的是空车,大平板车在去的途中连车箱都没有。没有想到,这600公里的路程,他们竟然走了一个月的时间。
由于道路坎坷不平和车况不好等原因,仅从罗布庄前往安迪尔的300公里,他们就用了6天时间,返回的旅程更是一波三折。
河沟的桥头,到处立着“限重10吨”的标牌,而大平板车光车箱就长19.5米,连同车头自重达20多吨。为了不压坏桥梁,侯秉仁他们只好一次次停下车来,在桥边整修便道。由于他们行进的路途都是无人区,四野茫茫,一片荒凉,即使出钱,也找不到人帮助。有时三个人汗流浃背地忙上一整天,也修不出一条便道来。
好不容易“移动”过了且末县城,来自阿尔金山的山洪又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白花花的太阳光下,浑浊的水流从眼前漫卷而过,公路在几股水流之间时隐时现。侯秉仁他们见水并不太深,就决定一个人在前面引路,另两人开车趟水而过。可是,在一段弯路处,侯秉仁驾驶的大平板车的车身突然向一边倾斜过去,他赶紧加大油门,但打滑的轮胎卷着泥沙在水里不停地空转着,任怎么折腾,它仍然陷在泥水里,前进不得,后退不能。
傍晚时分,侯秉仁他们遇到了来这里察看路况的道班工人,他们说,据气象预报,明天这里还会有特大洪水。他们更加焦急起来。这大平板车价值上百万元,是队上拉运特重钻井设备的宝贝,它要是被山洪卷走,不仅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还将耽误向井上搬运钻井设备的时间,影响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的总体钻探部署。
“无论如何都要保住大平板车!” 侯秉仁说。整整一夜,他们三人不眠不休,忙着在车前掏泥沙,垫木头,累得精疲力尽。天亮以后,他们又赶紧在车的迎水面堆泥挡水,一直忙到中午,终于在大平板车的右侧筑起一条20多米长的压着红柳枝的堤坝。
可是,未等他们好好喘口气,呼啸的山洪就夹杂着草屑、泥沙,气势汹汹地向堤坝压来。仅仅几分钟,一米高的堤坝被冲得无影无踪,滔滔浊浪包围了大平板车。
三个人大半天的心血倾刻间化成了泡影,可是水还在一个劲地往上涨,大平板车面临被淹没的危险。
“快堵排气孔!”侯秉仁一声呼喊,三个人立即抓起擦车布、毛巾和衣物,“扑通扑通”地跳进洪水,钻进车底,把车桥上的排气孔死死扎住。
深陷洪水中的大平板车暂时安全了,而此时,侯秉仁他们的干粮已经吃完,只从后备箱里找出几个发霉的干馕。侯秉仁让另外两个同事赶紧步行去且末县城,请求救援,他自己则独自留在荒凉山野,守护大平板车,这一守就是三天三夜。
前两天,大平板车像一座被洪水包围的孤岛,直到第三天中午,洪水才逐渐消退,大平板车露出了整个轮胎,象一个病恹恹的壮汉,斜斜地歪倒在淤泥里。
这三天三夜里,侯秉仁一直被焦虑和痛苦煎熬着。发霉的干馕啃得他嘴里流血,浑浊的泥水喝得他肚子发痛,腹泻不止。抬头望见远处阿尔金山连绵重叠的山峰,他忐忑不安,害怕再次爆发山洪;低头看看深陷在洪水中的平板车,想到井上正等着拉运的钻井设备,他心急如焚。
第三天下午,去“搬救兵”的两位同事带着救援人员到来时,他们眼前的侯秉仁已经消瘦得失了人形。闻着同事带来的饭菜的香味,侯秉仁热泪滚滚。
侯秉仁他们回到罗布庄的时候,已经是第31天。
张国良 搏击沙尘暴
张国良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沙漠”,他几乎经历了塔里木沙漠运输人的所有艰辛。比如,在荒凉戈壁滩上喝漂浮着牲畜粪便、里面蛤蟆乱蹦的涝坝水;茫茫沙海里车坏被困,写好遗书躺着等死;冒着零下40℃的严寒在夜里进行长途搬迁,眉毛和胡须上挂着冰凌,脸和手多处被冻伤。
但是,让张国良最难忘的还是那次搏击沙尘暴的感受。
那一次,张国良带着车队往塔中腹地的井上运送生活物资,途中遭遇沙尘暴,狂风连续刮了五天五夜。“井队上快要缺粮断水了。”一想到这些,张国良就心急如火,他决定顶风而行。遮天蔽日的风沙中,他们只能开着车靠感觉缓慢前行。白天,他们还有插在沙梁上的三角旗做导向,到了夜晚,前进的道路变得更加艰难,在风中走一截,就必须停下来辨别方向。
当张国良他们走到一个大风口时,风沙变得异常猛烈起来。呼啸的狂风卷着沙粒,疯狂地在空中翻卷。疾速掠过的沙流,活像巨蛇闪动的信子。天地一片昏暗,道路已被黄沙埋没。沙粒撞击着车体,发出一阵阵沙啦啦的乱响。在一处凹地,走在最前面的一辆车陷进了松软的沙窝里,阻碍了整改车队的前行。
张国良推开车门,跳下车去察看。“井队上的人正盼着咱们呢,咱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钻井。只要能在这道沙梁前挖开一条通道,车子就能冲出去。”张国良说着,拿起铁锹带头冲进了沙尘暴。
由于风沙太猛,大家一下车,立刻被冲击得摇摇晃晃。大家一字排开,背向风头,躲开迎面而来的飞沙,飞快地挥动铁锹挖通道,他们甩出的沙子立即被疾风冲开,飞撒向远处。而背面卷过来的沙流,又迅速把大家刚刚铲开的沙窝填平。
飞沙打在人们的脸上,生疼生疼,嘴里也飞进了沙土。大家只好脱了上衣包着脸部,一声不吭地闷头挖沙。可是,最娇嫩的眼睛却无法保护。只几分钟,几位司机的眼睛就被飞进眼里的沙尘蜇得受不了了,不得不躲进驾驶室,而张国良依然在风沙中坚持着。飞起的沙子不断地打进他的眼里,他硬硬地瞪着眼珠,一任泪水流淌,直到眼睛疼得实在无法忍受了,才钻进驾驶室暂时躲避。
驾驶室里,先钻进来的同事正在用一只手掰开自己的眼皮,另一只手举着矿泉水瓶子,歪着头冲洗眼里的沙子。“瞧你的眼睛里,尽是沙子。我给你也冲冲吧。” 同事说。
“算啦。还得下去挖路,冲了也还得进沙。”张国良说着,抓过单衣包住口鼻,又扑进肆虐的风沙中继续挖路,同事们也赶紧再次扑进风沙。渐渐地,每个人的眼窝里都淤塞了沙尘,每个人的鼻孔里都被沙尘堵塞,沙尘积成疙瘩,一抠一个湿块。
四个小时过去了,被困的车辆终于被救出来。可是,由于张国良在风沙中挺的时间最长,他的眼睛里已经塞满了沙土。虽然眼睛血红肿胀,却失去了最初的疼痛感,只觉得眼前模模糊糊,看不清东西。而眼皮早已经僵硬麻木,无法自然闭合,眼睛只能直勾勾地鼓着,像机器人一样。同事们被张国良的样子吓坏了,赶紧让他躺在驾驶室的铺位上,用清水反复为他冲洗眼睛。
第二天清晨,张国良一觉醒来,觉得双眼酸疼之极。拿镜子一照,镜子里那个怪异的形象让他又害怕又好笑:外眼角爬着两行干涸了的细沙痕迹,两处内眼角依然往外流着带泥沙的泪水;鼻孔里壅塞着两疙瘩温呼呼的泥沙团,用手指一掏,便往外流水,裹挟着泥沙直往嘴唇、下巴上流淌。
这样的怪异情形在张国良身上一直持续了几天,真不知道他的身体里到底刮进了多少沙土。
“你们都知道眼睛里进了东西睁不开的滋味,可有几个人感受过眼睛里进了沙子合不上眼皮的滋味?”多年以后,当张国良对年轻人说起这段独特的经历时,他的眼睛里闪烁着一个驰骋沙海的老沙漠人的自豪与坚毅。
陈世文 驾驶“航母”闯沙海
在沙漠运输车辆中,载重量50吨的美国肯沃斯车最为高大威猛,堪比军队中的“特种兵”,被司机们称为沙海中的“航空母舰”,钻井所用的超宽、超长、超高设备都由它来运送。陈世文就是一个开了20年肯沃斯车的优秀驾驶员。
肯沃斯是所有特种车辆中最难驾驶的,14个前进挡,两个倒档,16个档位的车不少人见都没见过。在沙漠里开肯沃斯,不仅技术要过硬,而且还要经验丰富,行驶中的线路选择、车速调节、转弯控制等一点都马虎不得。由于长期在实践中钻研,陈世文给井队送推土机时,七八十公里的沙漠路,他根本不用捆绑,推土机运到现场,最多也就位移三四厘米。
一台肯沃斯车价值几百万元,其中一条轮胎就4万元,一块钢板4000元。夏天,为了避免沙漠高温造成爆胎,陈世文每天跑车总是起早贪黑,避开高温时间。为了尽量节约钢板,他发明了一种卡子,每当钢板出现裂纹或是发现疲劳点时,他立刻用卡子卡住两头,以此来延长钢板的使用寿命。
驾驶肯沃斯这样的“航母”具有较大的风险性与挑战性,因为它拉运的都是体积庞大、价格昂贵、生产急需的钻井设备,司机的一点差错都可能造成巨大的损失。而且沙漠里路况不佳,每次走的路线、路况不同,拉运的设备也不同,每出一趟车都是对司机的一次挑战。20多年来,陈世文凭着高度的责任心和精湛技术,一次次安全、优质地完成了运输任务。
一年夏天,陈世文驾驶着肯沃斯车,连续两天两夜在塔中运送钻井设备。白天沙漠里地表温度高达70℃,驾驶室内即使开着空调也有50℃,空气火辣辣地象被烤糊了,闻得见车轮胎被灼烫后发出的热乎乎的橡胶味。一路上,陈世文不停地喝水,一天要喝30多瓶矿泉水,人都快虚脱了。红色工衣变成了白色的,上面结满了白花花的汗渍,穿在身上硬邦邦的,象穿着铠甲似的难受,只好脱了衣服,光着膀子开车,反正沙漠里也没人。即使这样,他也必须开个把小时就停下来,下车吹一会儿风,虽然那风也是火辣辣的。两天两夜里,陈世文没有吃一顿热饭热菜,就靠方便面和凉水果腹。当最后一趟设备运到井上时,刚打开车门,他就觉得眼前一黑,一头从车上裁了下来。
还有一年,由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石油勘探如火如荼,钻井数量大幅度增加。陈世文驾驶着他的“航空母舰”在沙漠里马不停蹄地奔忙。在井队搬迁任务最紧张最繁重的时候,他几次主动顶替有病或有事的同事,让他们休息,自己则连轴转,这边刚下肯沃斯车,接着又上奔驰车,车歇人不歇,从这口井又转战另一口井。那一年,陈世文在沙漠腹地工作了334天,抛开为同事顶岗的工作量,他完成货物周转量近40万吨公里,完成单车计划任务的212%;完成产值135万元,创利润40万元,完成单车计划利润的328%。
“陈师傅在我们车队,论资历,他是‘元老’;论技术,他是‘专家’;论贡献,他是‘功臣’。他就是我们运输队的一面旗帜。”说起陈世文,他的同事们赞不绝口。
“最喜欢听到塔里木油田又有大发现、油气产量又上新台阶的消息,因为那里有我们沙漠运输工人的汗水。”这是塔里木石油人陈世文心中一直坚持的朴素想法。
责任编辑 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