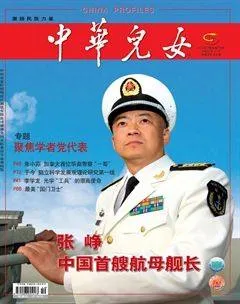活着,应是怎样的信仰
不知从何时起,我有了一个口头禅,当有人问我过得好不好,就会漫不经心甩出一个词——“活着”。
在很多场合,也都听到过不少人会发出类似慨叹——“活着呗,还能怎么着?”
不是刻意矫情。拿我来说,谈不上富贵,倒也算衣食无忧。我不属哪种教徒,也还有点文化偏好。不论是现实,还是精神,原本不应该有这种没着没落的深沉无力感。
但是,有一种无助,已经在血液中流淌。一些拥有更多物质与精神财富的人,不也都是像我一样,觉得“活着”实在不易?
说到“活着”,绕不开作家余华,绕不开他的《活着》。
20年前的九月,余华小说《活着》横空出世;今年,孟京辉的话剧版《活着》打动了很多人,连余华都说,他看哭了。20年的时光流逝,余华更明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时间并没的赋予人们“活着”更多的价值元素,这才是悲哀。
这20年来,我读过余华的小说原著,看过张艺谋的同名电影,还有那部改名叫《福贵》的电视剧。现在,也很想去看孟京辉的话剧。看得次数很多,每次,都会绝望地想,一个人,一个中国人,活了那么久,怎么还是要活得那么惨?
读小说《活着》时,我在上大学。那时,日子过得有点惨。整整四年,我都在打工中度过,挣的钱,除了供学费生活费,还得用来养家。不过,想到小说中福贵那样凄凉绝望,还觉得我自己生活多了些亮色。更何况,那时心里总是装着一句诗——“相信未来”。于是,活着,累也不觉累,苦也不觉苦。
累终究还是累,苦也终究还是苦。这些年,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表面上拥有的越来越多,但一觉醒来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可能一无所有。很多人也不像《活着》主人公福贵,曾经是赌徒,是败家子,输光一切开始苦难历程。他们一直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可是,总有一种力量让人泪流满面,人生不是输在牌桌上,而是输给失范的公权力,输给无良的资本,甚至,输给看不清摸不着的人性。
我们这代人,站在生存、生活、生命的镜子面前,映照出来的自己的表情,仍然是长期艰难奔突后的极度疲乏。还有很多人,已经无法保持站立的姿式,躺着、趴着、睡着。永远不能站起来的,还有死亡。
“一想到死,人就会特别善良。”——孟京辉的话剧版《活着》。《活着》这部作品用死亡传递了震憾与伟大。在现实中,有太多的中国式非正常死亡,并没有像《活着》里那些苦难者一样被叙说和回忆,他们的生活方式,从某种意义讲,无异于一块石头,一朵野花,或一只飞禽走兽。
比艰难“活着”更残忍的,也就是一些人曾经的“活着”并不知晓。那些不被知晓的苦难,让在现实中活着的人们更容易失去方向。
我觉得,个人在太多的苦难面前,如果找不到救赎路径,人格与性格就会慢慢改变。比如,我现在就觉得自己活得越来越没有锐气。而我们这代人,也慢慢变成胆小、沉默、被动、逃避安于现状、没有冒险精神的东方的羊,生活在一个未曾死去的阿Q时代。
在雨果的《悲惨世界》中,曾经逆来顺受的主人公冉阿让,在主教的怜悯和保护之下,终于重新主宰着自己的命运。活着,就应该让命运更加充满厚度,就像作家乔叶在小说《最慢的是活着》中说,“活着这件原本最快的事,也因此,变成了最慢。生命将因此而更加简约,博大,丰美,深邃和慈悲”。
现在,我们活着,要看到更多的博大和丰美,要摆脱太多伤怀与沉重,有必须有笃定的文化信仰,有坚实的制度正义,来为苦难的人性找到出口,实现生命的价值救赎。这是因为,人不应该永远只是为活着而活着的,而是要为活得更有意义而活着。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