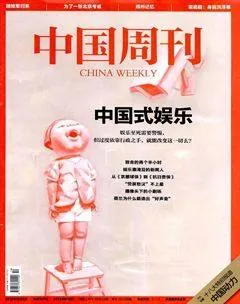郑州记忆
2012-12-29 00:00:00田野
中国周刊 2012年10期




中原大地厚重的黄土之下,深埋着无数的文明与杀戮,但今天,这一切烟消云散,现代化的进程恍若在一张白纸上重新书写。
五一假期,我在郑州给父亲置办了一套新房。父母原本居住的郑州郊区那个村庄即将要彻底被电厂的烟囱、轰隆隆的铁路线,还有喧嚣的商贸城淹没了。儿时记忆中那个宁静富饶的村庄已经不在,也不再适合作为父母的养老之所了。
当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过去,大跃进式的中国城市化进程终于轮到了郑州这样的中部城市。那些门类繁多的制造业工厂从深圳、上海等沿海城市开始往纵深的中国腹地转移,这些在漫长的农业文明中浸淫了的土地也随之沸腾起来。对于大多数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的人们来说,这样的变化带给他们的多半是兴奋。在过去30多年东部沿海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他们只是来去匆匆的打工者,如今,工厂终于开到了家门口。
在这场蓬勃展开的城市化运动中,郑州这座多年前我曾经熟悉的城市变得陌生起来。这些年的异乡生活告诉我,短暂的兴奋过后,它给生活在这里的个体带来的还会有拆迁、污染,以及并不总是公正的财富再分配,与沿海那些地方经历过的不会有什么两样。
但父辈和儿时亲朋们的兴奋分明是真切的,我的惆怅也便显得有些矫情。在纠结中,故乡一点一点面目模糊起来。
从郑县到郑州
我把父母的新居选在了城北,因为靠着邙山、黄河,很多郑州人认为,那里是上风上水的风水宝地,但于我,只是因为离黄河更近些。严格说来,黄河不能算是郑州的母亲河,淮河才是,因为郑州人喝的多是淮河支流的水,但地理上的接近,黄河也便成了母亲河,更是这座城市的标识之一。
小的时候,是甚少去黄河边的,光秃秃的黄河大堤漫长而枯燥,野草荒滩,实在没什么可观之处,也不招郑州人待见,那个时候,人们多半认为火车站附近那些巨大的各式农贸市场、商场百货才是郑州。记忆中关于儿时郑州最多的片段,就是跟着父母无休止地在各式零售百货、批发市场里来回奔波,他们忙着做生意,我则忙于吃,豆腐脑、肉夹馍、冰糖粽子,还有回族人的羊肉串。
我18岁离开了河南,那些熙熙攘攘的市场年复一年地改造着,也消失着,渐渐也就无可怀恋了。偶尔看到关于黄河的影像,倒会不自觉生发出一丝怀乡之情。地理意义上的景观总是能最有效地承载人们的某种情感。于是,每次回去,得空总会去那条宽阔的黄河大堤上溜达,那里十几年如一日的野草荒滩,到了枯水季,河道中厚厚的黄土,随风扬起,漫天飘散,提醒着这个城市的底色,它建筑于被中华农耕文明史浸染最浓郁的中原腹地之上。
在现代城市的意义上,郑州的历史一点也不长。在20世纪之前,它都乏善可陈,直到1928年才正式建市,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拜清政府修建的那条京汉铁路(如今的京广线前身)所赐。
京汉铁路为什么不选择穿过当时的首府开封,不选择更声名远播的洛阳,却选在了当时位于这两大城市之间的小县城郑县?正史野史有很多说法,但比较可信的是《清史稿·交通志》上的记载,在当时工程技术和资金条件下,张之洞设计铁路具体线路时,把黄河桥看做修筑京汉铁路最紧要的环节。开封一带的黄河,是著名的悬河,被称为黄河的“豆腐腰”,如果选择从开封建桥,不但投资大,建成后风险也很大。因此,京汉铁路线路才拐了一个弯儿,从郑县附近的花园口穿过黄河南下,至于另外一个名城洛阳则偏西距离稍远也被放弃。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当年张之洞笔下那道弯开启了郑州这座城市20世纪的城市化历史。1949年以后,郑州取代开封成了河南的省会,在那个全民勒紧裤腰带搞基础工业的年代,人们对于城市的想象便是工厂,郑州也不例外,八大国营棉纺厂占据整座城市大半块地方。郑州最早的一批市民,除了少量郊区前来做小生意的农民之外,便是铁路局和棉纺厂的工人了。在父辈们的描述中,对于那些能在铁路、煤矿以及棉纺厂上班的被称之为“正式工”的人们是艳羡极了的,他们这些来自郊区农村的小商小贩顶多是在大工厂的门口卖卖水果蔬菜什么的。
不过,历史的发展却相当吊诡。到了1990年代前后,小商小贩们的郑州繁荣起来,而“正式工”的郑州则日渐衰败。那些年,铁路局和棉纺厂区成了郑州贫民窟一样的所在,而各式各样的购物广场、批发市场则光鲜亮丽,人声鼎沸,有个叫亚细亚的购物广场甚至一度成为了这座中原城市最大的招牌,声播全国。
我读完大学才发现,我所成长的这座城市的历史进程与沿海地区原来有着相当大程度的错位。上海、深圳、广州等城市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工业化才是城市发展最大的主轴,郑州逐渐破产的那些原本优质的棉纺厂、自行车厂等等产业都转移去了沿海城市。
大约经过了十年左右的时间,进入21世纪时,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工业化已近完成,到处都是林立的高楼,俨然一派世界都市的气象。而郑州这时候工业萧条,几乎蜕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农贸市场,各色批发市场和长途汽车站占据了城市的中心,终日里是无序的喧嚣。也就是那些年,我开始越来越讨厌回到这里,不仅仅是因为物理意义上的混乱,更有弥漫在整个城市里的狡诈、市侩和随时随地的坑蒙拐骗。
形态低端的商业模式并没有给这个城市带来足够的富庶,却孕育了最糟糕的社会氛围,缺少起码的法治观念和商业伦理,机场、车站、饭店、商场等人流最多的地方里,那种底层社会间的互相伤害无时无刻不在发生。
那些年,河南人在外的形象相当糟糕,作为省会的郑州怕是要承担最大的责任。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想不明白,在乡土社会的环境中,那么忠诚、敦厚、善良的人,何以进入城市后会变成另外一副模样?或许这是人们脱离乡土社会的熟人社区,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需要人际关系再造的环境,一段必不可少的适应期?
作为一个整体的郑州,这种形象和文化意义上的自愈也是最近几年才慢慢完成的。郑州所经历着的城市化是另外一种原生态的中国式城市化。它从农耕文明最深厚的中原腹地生发出来,撕裂着传统,锻造着另外一种形态的文明。
历史也似乎是跟河南人开了一个玩笑,承载着一亿人口的中原腹地,现代化生长并没有从那些有着悠久城市史的地方开始,而是从一片白纸上起步。这一切很大程度上都应该归功于那条京广线。被这条铁路线改变命运的远不止郑州一座城市,铁路还塑造了另外一批新兴城市,比如新乡、漯河、驻马店等。历史上,中原曾是名城荟萃,比如洛阳、开封、安阳、周口、南阳等等,如今却都因远离了现代交通大动脉,而落伍于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转型。
拆出一个新城市
尽管千城一面的城市化进程已被批得体无完肤,但对于大多数普通人以及城市的执政者来说,这一点也不能打消他们对美好城市生活的想象,而那些想象,无不是以已经建成的大都市为蓝本的,远的如纽约、东京、香港,近的如上海、深圳、广州。
从城市需要高楼大厦、需要公路和立交桥、需要宽阔的广场,到需要公园湖泊、需要绿树和文化景观、历史底蕴,中国人的城市想象其实也在不断完善,这些被需要的都要实现,有的就维护,没有的就人造。
对这种主流的城市想象的追逐,郑州和很多内陆城市一样,大约是在2000年以后才开始的。那个时候,在这个城市的东部,政府提出来要建设一个新区,有超过150公里的耕地都被划入其中,最终选择的规划方案是日本当代著名设计师黑川纪章提供的。
2005年,在还是一片荒地的新区,我曾经跟黑川纪童有过一次深入采访。那时,他的设计方案正在遭受诸多质疑,其中最核心的一点便是他要在这个极度缺水的北方城市挖两个巨大的人工湖。在我将人们的质疑转述给他听时,黑川纪章相当愤怒,“我们不能因为这里缺水,就不去挖湖,就像不能因为这里是沙漠,我们就不去种树,人类生来本就是要改造世界的。”他说要建设的是一座“共生城市”,这本就要改造自然,甚至是再造自然。
那种改天换地的气魄,一点也不像外表看起来谨小慎微的日本人,倒让我想起了新中国前30年的景象。在郑州的西部,就有一座“文革”期间开挖的人工湖,名为西流湖,取“引黄河水西入郑州”之意,曾经给这个一马平川、缺少山水景观的平原城市带来过不小的兴奋。但是,当我记事起,这个西流湖便已经逐渐干枯萎缩,成了郑州最著名的垃圾池。
不过,人们改造自然的冲动不会消失,尤其是当他们认为掌握了更加强大的工程技术后。黑川纪童的方案赢得了很多郑州市民的认可。最近一次回去郑州,又去了一趟东部新区,如今改名为郑州新区,那两个人工湖也已经挖好了,周围高楼林立,与五六年前相比,恍若跨越了一个世纪,这已经大大超出了已经去世了的黑川纪章的预想。记得当年他跟我说,最担心的就是政府没有钱,执行不了他的规划,从而闹得个半途而废。但如今他们又有了更大的造城梦想。
就郑州而言,不仅仅是东部新区,南部城市边缘,宏阔的南水北调大运河也即将通水了,北部的黄河滩区则在动工建设一个上千亩的黄河湿地公园,就连西部那个早就干枯了的西流湖也在被重新开掘。一个建筑在平坦耕地上的北方干旱城市,短短几十年间居然也恍惚有了一派四水环绕的水乡景象。这样的变迁让人不得不感慨,掌握了现代工程技术和经济发展带来的财富和政治威权改造世界、重塑文明的能量。
曾几何时,拆迁是东部城市的专有名词,但现在,正在向中西部的大小城市蔓延,郑州也不例外,要拆除的不仅有城中村,为了将那些通往郊区的公路拓展、绿化,政府搞了一个绿色廊道建设计划,公路两侧30米的绿化带吞噬了连片的习惯于傍路而居的村庄,那些失去住所的农民也统统被规划进了城区。
这种现代化的进程在学者和舆论的叙述中是残酷的甚至是血淋淋的,在现实的行进中,也会有极端的案例,但更多时候是以一种更庸常的方式在展开。我的父辈们,他们只会去精打细算赔偿的数额,最近的两年,不断有儿时的伙伴、亲戚会打电话过来或者咨询或者求助,大多数时候都是跟拆迁有关。于是,我也渐渐了解了许多这个城市关于拆迁的种种标准,在这样一个经济体量和社会发展程度的省会城市,600块钱一平米的拆迁补偿标准,在我看来实在有些荒谬,而且这样的标准,也完全是政府单方面制订的。很多时候,我会鼓励他们坚决捍卫财产权,只要你不同意,政府部门就不能强拆。但我那些书生意气式的建议,在他们看来是万万不可取的,他们更想托我找找认识的官府里的人,看能不能多要点补偿,真的找不到,也就作罢了,真正起来为自己的利益抗争的总是少之又少。
最深沉的底色
我18岁以后,求学、工作走过了中国大部分的省区,我发现,对于人情关系的看重、对于官员的崇拜和敬畏,程度上少有能与我的故乡河南人相比的。
最近一次回郑州,我找一位多年前就相识的老前辈叙旧。那是一个典型的书生官员,对郑州有着异乎寻常的热爱,如今,他已经在这座城市身居要职。我的几位亲朋知道后,不厌其烦地向我表达跟他拉拉关系,谋点利益的想法。我自然做不到。但我知道,我曾经的那些同学、亲朋,其间发迹者多半是藉此类门路。几乎每次回老家,我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久而久之,我成了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另类,关系也便疏远起来。
敬官畏官、顺从懦弱,这恐怕是农耕文明中最深沉的底色,而只有快速的城市化和现代化才能将其慢慢消解,又或者这种底色会将现代化弄成另外一副面貌?谁知道呢!
大多数时候,百姓总是最容易妥协的那一方,只要给他哪怕一丁点利益或者说希望,他都会选择顺从,历史滚滚向前的车轮总是能轻易地碾过他们的身躯,在我的故乡河南,尤其如此。
在郑州的北郊,有一个叫作花园口的小镇,当年抗日战争,当日本人逼近中原时,那些掌握着国家武力和权力的精英权贵们带着枪炮、细软一溃千里,南逃而去,蒋介石想到的阻敌进军的方式居然是掘开黄河大堤,用千里黄泛区来抗日。
掘堤处就在郑州市区的头顶,泛滥的黄河没有能阻挡住日本军队的南进,却淹死了89万中原普通百姓,而当年他们甚至还去掘堤现场帮工。
抗战结束后,没有人去追问决策的合理性,人们只是默默地回到自己的故乡,在那一片黄泛区之上重新开垦,房屋、村庄、农田、城市很快就又顽强地从这片土地上生发出来,直至今天的高楼林立、欣欣向荣,那些累累白骨已被深埋以至于再也无从寻觅。
用更长程的历史视野来观照这片土地,中原大地厚重的黄土之下,深埋着的还有无数的文明与杀戮。即使是在郑州这座一直被外界视为新城的城市,也挖掘出了3600年前的商代早期城市遗址,从而被国家确认为中国八大古都,其后刘邦项羽在“楚河汉界”两侧的攻防杀戮、三国时的残酷的官渡之战等等,都在是郑州展开,在漫长的历史上,辉煌的文明创设与兵祸连结后,留下的白骨填满了这座城市的地下时空。
但今天,这一切仿佛都烟消云散了,现代化的进程恍若在一张白纸上重新书写。
多年以后,当我站在新区那个高楼环绕的湖泊边上,却又由衷地尊敬起那个年迈的日本设计师了,他费了巨大心血给郑州留下的这座新城,确如他当年所说,要尽力用现代建筑构造的视觉形象承载着中原文明的厚重。那栋中原福塔、大剧院、湖泊还有与周围建筑的巧妙布局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着他的承诺。夕阳西下时,它们带给我的视觉感受与北京、上海、广州等摩天大楼城市有着本质的差异。在遥远的未来,这或许会成为郑州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因为在这个想象力匮乏的时代,他多少还是能够让你隐约感受到那种叫作文明的东西。
至于历史、文化,还有故乡,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无处可寻也就不寻了吧。或者说人们终会找到新的故乡,开启一段新的历史。在不远的将来,黄河之滨或许会崛起一座千万级人口的现代都市,那里或许不再是我的故乡,但肯定会成为更多人的故乡,肯定会让更多热切期盼着城市文明的人们所热爱。
现在,我开始和父亲一样,热切期盼着那条纵贯中国南北的京广高速铁路的通车,这样从北京回家便只要两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