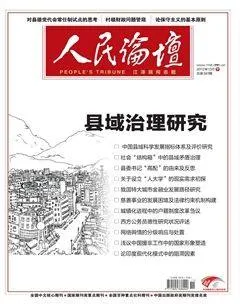族群性视角下的乡镇农民工调查
【摘要】从劳动过程理论出发对“中国结”生产基地—浙江东阳画水镇的农民工进行了调查研究,描述了该产业工人的生产、生活情况,并以族群性归纳其劳动关系、社会关系的特征。最后总结出在关注城市农民工的权益的同时,也需要将目光投向乡镇农民工,需要制定合理的社会政策,让中西部的农民工享受到东部乡镇发展的成果。
【关键词】乡镇农民工 劳动过程 族群性 中国结
农民工研究亟待实现“从抽象工人走向具体工人”,即从他们从事生产劳动的角度对其加以更为细密的描述和更加深刻的理解。劳动过程理论将研究的重点返回到了生产的中心,不仅着眼于工人如何通过劳动活动把原材料转换成产品,而且更进一步揭示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族群指在社会文化体系中,客观上具有共同联系,主观上形成认同的群体。笔者将以籍贯、亲缘为基础的族群性带入劳动过程中,对东阳画水镇上从事中国结产业的农民工进行调查,进而研究族群性如何影响乡镇农民工的劳动与社会关系。
东阳画水镇“中国结”业调查的基本情况
中国结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画水镇74个行政村中先后有60多个村做起了中国结,有63%左右的农户从事中国结的生产加工,不少经营户由此发家致富,年产量占到了全国的60%左右,从业人员达1万余人。随着产业的扩大,外来农民工成为编织环节的主要力量。
课题组对600名农民工进行了问卷调查,先后走访了岩下、华阳、永乐、旭光、建胜、陆宅等村。样本结构为:中国结是细致的手工活,按理说应多为女性,实际上男性占了57%,这是因为编织一些品种需要力气;年龄以中青年为主体,平均年龄为33岁,与城市中的农民工相比年龄偏大;已婚占85%,83%的人与家人居住在一起,夫妻一起打工是常见现象;文化程度偏低,小学占54%,初中占42%,高中以上只占4%;籍贯上,非农业户只有2人。农民工大多来自中西部地区,贵州籍占76%,四川籍占12%,湖北籍占5%,江西籍占4%,湖南籍占3%。各省农民工不是分散的,而是集中来自几个县,如贵州集中在开阳县、翁安县、太阳县。
中国结的生产劳动情况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工种与技术。中国结主要包括绸布结、平结、毛结等,成品包括圈、鱼、布娃娃、流苏等。除了最常见的编结外,还有割板、喷漆、纺带、做板、缝纫等工种。样本中编织的人数占79%,其余为辅助人员。二是工资。除了看护机器的工作是按月计酬外,其他都是按照编织数量来计算工资,熟练工一天能赚90元左右(旺季)。三是工作时间。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间为10小时左右,上下班的时间没有明确规定。
族群性与农民工的劳动关系
劳动的连结。调查样本中,85%的农民工外出打工最主要目的是“赚钱”。族群性使农民工在外出前后形成了一个消息网,80%的人是经老乡或亲戚的介绍才到画水镇的,自己找工作的仅占15%。94%的人与家乡的亲朋保持良好联系,只有6%的人很少与家乡的亲朋联系。中国结业大多是中小型的家庭作坊,每户有七八个至几十个工人。82%的务工者选择在作坊工作。作坊中会有二三人与老板保持多年的雇佣关系,他们通常技术熟练,为人忠厚,被老板及老乡信任,他们既充当介绍老乡前来工作的角色,也充当作坊师傅的角色。
性别分工。农民工往往以家庭为单位来到东阳画水镇打工。这和城市工业区的务工情况差异很大,原因之一在于,画水镇提供了多种人力劳动工作,并且文化程度要求不高。男人从事搬水泥、运输、塑料业,女人从事服装、中国结、工艺品,老人与小孩可以做串珠子的活。原因之二在于,计件制手工活提供一定的自由度,“做手工活,我可以看着孩子”、“爸妈在这边,我可以帮些忙”、“我可以过来带孙子,同时赚点钱”。此外,随着中国结编织周径的增大,这就需要男性从事这一行业。调查显示,87%的男性从事大号编结,而95%的女性从事中小号编结。
季节性赶工。中国结业一般按件计酬,多劳多得,72%的农民工会选择加班多赚些钱。在夜晚的灯光下,每家每户匆忙地进入布洛维所说的“赶工游戏”。中国结业存在着明显的季节性因素,雇主每月通常只发700元左右的生活费,务工者赚到的钱要到年底结算。九月前的五个月是生产销售淡季,农民工的活也会减少,有些人甚至找不到工作。这时,不少农民工会选择在画水镇上找些其他工作贴补家用。等到旺季到来时,务工者及其家庭成员会聚集在中国结作坊,工作也变得非常忙碌,常常是连吃饭的时间都挤不出来。
族群性与农民工的社会关系
劳动互惠与市场末端。在多元族群的社会中,族群相互提供重要的服务,从事互惠的职业。当地政府明白外来劳动力带动了三大产业的发展,雇主更是明白失去工人意味着什么,他们会表现出尽量善待作坊中的外地务工者,特别是手艺娴熟的人。96%的人表示去年年底未遇到拖欠工资的情况。而个人遇到困难时,“找老板”占到了2/3。族群性使雇主与工人的联结变得更为顺利,由于老乡同在一处,务工者选择“固定一家工作”为83%。农民工的工作惠及了当地族群。中国结最初由当地农民生产,编织技术对外保密,但随着业务量的剧增不得不将编织环节让给外地农民工。当地不少人开始进入生产、设计、销售环节,并通过临近的义乌商品市场销往全世界。在生产链中,农民工只占据了生产的未端。当问及“有没有与当地人发生争活做的现象”,96%人选“没有”。农民工相对低廉的工资无法积累创业资本,身处异地又无法融入经营环节,有20%的人表示“想过自己创业做中国结”,但大多承认困难比较大。
次文化与居住隔离。家乡认同和本地认同成为群族认同的两面性。对家乡的认同主要体现在对老乡的高度认同上,当务工者遇到不错的行业时,他们就会相互告知。在画水镇上,贵州人、四川人占据了中国结业,湖南人则占据了塑料业,亲友与老乡是在慰藉感情的时候最先想到的群体,比例分别达到85%和74%,贵州的农民工还会不定期的喝酒聊天。对于此地的认同在于,画水镇同为乡镇,72%的人表示比较适应这里的生活,“大城市呆不习惯,压力大,还是这里好,这里也有农田”。他们会参加一些当地的娱乐活动,57%的人表示会与当地人交朋友。但总体而言,农民工仍处于流动的“次文化”中,对外地人歧视的现象虽然不多,但毕竟存在。农民工想要真正融入到画水镇的生活当中还存在一定的困难,一个例子是农民工的居住点与当地人处于不同的区域,在画水镇上,越来越多的村民在周边建起了新楼,而条件不好的老房子更多的是租给了外来人口。调查显示,72%的人是自己租房,来自同一个地区的人往往会彼邻而居。
乡乡差别与偏下流动。画水镇先后涌现了服装、绣花、塑料、中国结等特色行业和特色村,现已经成为浙江较为发达的乡镇。75%的农民工表示满意当地的生活环境,“办暂住证不要钱了”、“孩子上学比较容易”、“派出所态度挺好”。当问及“您觉得管理部门的政策如何?”33%选择“对我们蛮重视的”,36%选择“一般”,13%选择“忽视我们的需求”,18%选择“说不上来”。不足之处在于农民工并不能享有村民的利益,比如医疗、分红等。农民工向画水镇的流动表明了地区之间发展的差异,不仅是在城乡之间,也体现在乡乡之间。有1/5的人早在2000年前就来到了画水镇,现在的年龄接近40岁。在问及外出打工时间的问题时,73%的调查对象选择了“常年在外,春节回家看看”。总体而言,农民工的流动呈现水平甚至偏下状态,水平流动指有近五成农民工从未去过其他地方打工;偏下流动指另一半人有城市打工的经历,但多数从事超市、保安、电子、建筑、清洁和公路建造的工作,来画水镇的原因在于,“城市工资低,开支大,而且不自由”、“干不来城市的活儿,不习惯城市的生活”、“能和家人呆在一起”、“文化不高,找不到工作”、“年纪大了,能力不够”。调查表明,14%的农民工表达了定居在此的愿望,15%的人表示不一定,而更多的农民工只是暂居在画水镇上。
结语
通过对画水镇农民工的描述,我们可以发现一群被城市大工业挤压至乡镇工业的务工者,他们的流动是自发的,也是被迫的。值得欣慰的是他们通过族群找到了合适的工作,与家人聚集在一起,这也是他们最为简单、质朴的要求。劳动密集型产业更易受到经济周期的影响,乡镇农民工的谋生历程面临着更多不确定性的因素。在关注城市农民工的权益的同时,也需要将目光投向乡镇农民工。课题组认为中西部的发展是这一群体安定的最终保障,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制定合理的社会政策,让中西部的农民工享受到东部乡镇发展的成果。
(作者为上海大学社会学博士研究生、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蓝领工人阶层的培育”研究成果,项目编号:09YJC84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