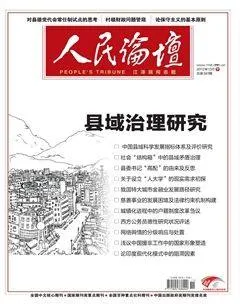县域治理需要“顶层设计”
以2002年起在浙江、湖北、河南、广东、江西、河北、辽宁等省份先后开始的“强县扩权”改革为标志,县域治理改革已经走过了十个年头。在十年县治改革过程中,积极推进“省管县”的战略及其实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同样不能忽视的是,在社会转型的复杂性和改革的系统性作用下,县域治理仍然是一个有待攻坚的难题。
县治改革的背景和内在逻辑
对“市管县”县域治理模式变革的主要原因,首先是伴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以地级市来带动县域经济发展的模式出现了诸多弊端和问题。主要集中在:一是“中央—省—地级市—县”的四级管理体制增加了行政管理成本,降低了效率;二是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实力较弱的地级市不仅没有办法辐射周边县,甚至和县域经济产生竞争关系,制约了县域经济的发展。所以,原有体制已经不能满足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客观要求。
其次,伴随着城镇化进程加速,县域治理在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与社会治理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已经成为社会转型和改革深化的关键点。这主要是因为:第一,作为地方政府,“县”是联系国家和社会的中间环节,县级政府代表中央对社会进行治理,成为了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重要环节。第二,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进程已经由区域经济的“中心城市”逐渐向“县”一级下移,“县”作为城市和乡村的“过渡带”成为城乡一体化的“节点”,也成为城乡矛盾凸显和聚集的核心地带。因此,县域治理成为关乎未来改革成败大局的战略重点。在这样的背景下,变革传统县域治理模式成为大势所趋。
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中央对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县域治理变革的战略目标也随之发生变化,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解放县域经济,通过财政和行政两条路径的“放权”来为县域经济发展“加油”,缓解“市管县”体制造成的县域经济动力不足的弊端,同时通过“省管县”的模式逐渐实现“市县分治”,理顺二者的发展竞争关系。第二,逐步压缩行政管理层级,提升行政管理效率,同时转变政府职能,在省一级政府放权的同时,增强县一级政府的执政权能。因此,十年改革,其根本性质仍然是经济体制转轨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体现了国家治理格局中资源和权力在省、地级市和县三个层级之间配置的变化。当然,也可以反过来说,县域治理改革,实际上是经由资源和权力配置在省、地级市和县三个层级之间进行调整,进而实现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深化的过程。
县治改革的成绩和困局
十年来县域经济的发展和治理能力的提高是有目共睹的。一方面,不仅为县域经济的发展松绑,同时也缓解了市县竞争可能产生的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束缚和抑制,在一些东南沿海省份,对盘活区域经济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省直管县的改革,为政府治理的扁平化和高效化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奠定了组织和管理基础。但同时也应该发现,“省管县”的改革存在着一些弊端和问题。第一,受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因素限制,“省管县”的县域治理模式的适应性还存在着障碍。这种障碍实际上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有些地区,“市管县”的模式仍然存在并切实发挥着作用,“中心城市”对周边县的带动作用仍然比较明显;另一方面,“省管县”存在一个管理范围和管理能力相匹配的问题,在县的数量较多的省份,“省管县”的模式给省一级政府提出了超出其能力的管理要求,实际上省级政府很难做到为所辖所有县都提供充足的资源、权力和管理以及公共服务。
第二,“省管县”的体制改革并不是单方面的县域经济发展的问题,必须配套相关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包括机构设置、人事管理体制的改革等等,还有管理和服务理念的“软件”升级,这些变动是系统性的,并不仅仅是财政管理的问题。这里面实际上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政治体制改革能否配套进行,能否在特定时间内完成由“四级政府”向“三级政府”体制的变革,并且能够从机构设置到组织管理以及制度建设系统性地适应转变的过程。另一个是能否克服打破和重组利益格局所面临的阻力。无论是组织或体制的惯性还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都会成为矛盾产生的潜在因素,增加改革的成本和治理的风险。
第三,由“市管县”到“省管县”,市县之间的关系从隶属到分治,如何理顺省、地级市和县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难题。尤其是在城市化进程中,一些地级市已经将县纳入自身发展规划中,甚至是城市发展的行政区划中。因此,在不调整行政区划的前提下,城市郊县的“扩权强县”根本无从谈起。一旦市县分治,都要从省级政府那里获得资源和政策支持,就会在实际上造成二者的竞争关系。
第四,十年县域治理改革的成绩和经验表明,“省管县”的模式之所以有生命力,关键不仅仅在于放权,还在于省一级政府能够激活县域经济,以及能够在放权的同时做好管理和服务工作。放权不等于放任,“管好”是重点。如果不能在省一级政府形成对县域经济的统筹发展,对那些本身就缺乏经济活力和持续发展能力的弱县来说,“扩权强县”就成了空话。
第五,“省管县”是一方面,“县”能不能适应这种模式,能不能顺利承接“赋权”,找到自身特定的位置和角色是另一方面。也就是说,在我国长期的垂直行政管理体制中,层级关系明确,基于计划经济中央集权的影响,县级政府往往缺乏主动性和能动性,能否承担省级政府放权,并且激活县域治理的潜能,同样也是关系到县域治理改革成败的一个关键要素。
深化县治改革仍然需要顶层设计
目前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摸着石头过河”的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建设的客观需要,因此,“顶层设计”的理念实际上是国家治理科学化和系统化的一种尝试和倡导,也是政府从高端的战略角度着眼,为社会建设以及社会管理进行系统设计的过程。县域治理改革从试点到渐次铺开,我们也已经走过了“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理应进入到系统设计的层面。从当前的现实来看,有两个最根本的原因决定了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县域治理改革必须引入并强化“顶层设计”:第一,县域治理改革是一盘“大棋”,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均衡决定了这盘棋不可能一刀切,必须整体系统规划。第二,当代中国,长期以来的强国家和弱社会模式导致社会变革往往是“自上而下”的,在“中央—省—市—县”的旧体制中,县是相对积弱的环节,需要来自中央的整体规划和省级政府在地区内的统筹安排;而对于地区内的强县,也同样需要来自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制度规范和整体的制度支持等方面的系统设计。因此,未来的县域治理,应当强化来自中央和省级政府的“顶层设计”。
首先,要通过“顶层设计”来系统规划“省管县”的治理模式的整体进度。因为各地区实际情况不同,甚至各省份内部也存在着历史和现实发展的差异,因此,需要在中央和省级政府两个层面来系统设计县域治理的进度安排。根据全国和各地区实际,需要合理地在“市管县”和“省管县”的模式继替中设置缓冲和过渡带,提倡因地制宜地采取“复合行政模式”,即设置“财政”和“权力”在地级市和县级政府之间的多种配置方式。对于县域自主发展动力和潜力不足,需要地级城市带动的,以及在县设置数量过多的省份,可以采取多种县域治理模式并存的方式,不必急于在形式上变革。
其次,要通过顶层设计,尝试在全国范围内以及各省范围内进行行政区划调整,以匹配省、市、县的规模和比例,便于“省管县”模式的深入推进。“省管县”的一个重要障碍就来自于个别省份所辖县数量过多、规模过大,给省级政府的治理带来过大的压力,不利于“省管县”模式的功能发挥。由于我国政治体制的中央集权特征以及各省在行政区划方面的实际情况差异性较大,只有在“顶层设计”层面,才有可能提出这样的系统设计方案,并通过中央和省政府的垂直管理权力来实现。
再次,要通过顶层设计,在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层面提供与县域治理改革相配套的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县域治理改革需要理顺主体关系,尤其是如何实现资源和权力在省、市、县三个主体之间的优化配置,以实现这三者的“正向博弈”。这就需要在国家和省级政府层面科学考察各省下辖地级市和县的具体实际,本着优化县域治理,进而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来系统设计基于“省管县”模式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制度。这些制度应该能够明确三个主体之间的责权利以及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体制中的定位,并且能够激发三者之间的资源整合机制,最大限度激发县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潜能。同时,顶层设计还应当在全局范围内思考如何在改革过程中尽可能兼顾各方利益,在最大限度规避风险和降低成本的基础上理顺三者之间的关系,并且顺利完成包括机构和部门调整以及人员安置在内的制度的细节设计。
最后,顶层设计最终服务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这里既包括改革的路线图设计,也应当包括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各级政府的行政和服务理念和水平的系统提升。这不仅仅是确保县制改革走向成功的基础,也是国家治理不断走向善治的根本动力。
(作者为河北大学政法学院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