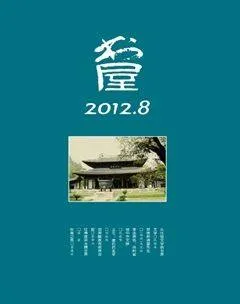是辩驳 更是唱和
一
从法国回来后,李健吾在北平盘桓了一段时间。期间,他与卞之琳交往甚多,成了很好的朋友。他们一起参加朱光潜家的“读诗会”,一起到“太太的客厅”听林徽因的如珠妙语,一起编辑《文学季刊》和《水星》。
1935年夏天,郑振铎就任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聘李健吾为外文系法国文学教授。于是,李健吾来到了上海。然而,迎接他的却更多的是疑忌和鄙薄!这很正常,毕竟他是一个仅仅二十八岁的北方青年,虽然曾留学法国,但并没有什么显赫的学位,一来就是教授,总让人感觉不舒服,看着不顺眼。更何况,他性格奔放外露,了无挂碍,便越加容易招人非议。在巴金的劝告下,他移居真如乡下,深居简出,伏案写作,用刘西渭的笔名发表了一系列文学批评。这些文章,都刊发在《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书评”专栏,后结集为《咀华集》出版。
值得注意的是,《咀华集》的书评文章,除评巴金的《爱情三部曲》和《神·鬼·人》、评罗皑岚的《苦果》之外,其余的八篇文章,都是对“京派”作家新作的评论。李健吾表现出了对“京派”年轻作家创作的巨大热情,对他们的新作一一品评,不遗余力地称赏。虽然萧乾、李广田、何其芳、卞之琳等“京派”年轻人早已为文坛所注目,但李健吾对他们的热情褒扬,无疑进一步扩大了他们在文坛上的影响。及时地报道“京派”的文学成就,向文坛推荐“京派”年轻作家,李健吾仿佛成了“京派”文学成就的宣扬者,或者说是“发言人”。
身在上海,却重在宣传“京派”,与李健吾在上海受到的冷遇有关。因为,这使他无比怀念北平时期,与一群年龄几无悬殊的年轻人携手共歌的岁月。可以说,写这些文章,是向上海滩展示才华,也是他怀念北平和谐的文学氛围、思念过从甚密的朋友的表现。何其芳、卞之琳、林徽因,等等,无一不是他深深思念的朋友。于是,卞之琳的《鱼目集》1935年12月出版后两个月,李健吾就写了《〈鱼目集〉——卞之琳先生作》〔1〕(以下简称《〈鱼目集〉》)。文中,他先是对包括卞之琳在内的现代派诗歌进行了高屋建瓴的分析,赞其“已然离开传统的酬唱,用它新的形式,去感觉体味揉合它所需要的和人生一致的真淳;或者悲壮,成为时代的讴歌;或者深邃,成为灵魂的震颤”,并“愈加淳厚了”〔2〕。
然后,他发现了卞之琳诗歌的“现代性”——这是最早关于卞之琳诗歌“现代性”的论述。他论断现代派诗“着眼暗示,而形式又那样谨严,企图点定一片朦胧的梦境,以有限追求无限,以经济追求富裕”,代表着新诗发展的新潮流〔3〕。卞之琳即是这一潮流的“少数的前线诗人”之一。
最后,他对卞之琳的诗歌进行了解读。当然,是那种李健吾式的印象主义解读。先说,读这种诗必然产生,也允许产生几种合理的解读,因为这种诗“在字句以外,在比喻以内,需要细心的体会,经过迷藏一样的捉摸,然后尽你联想的可能,启发你一种永久的诗的情绪”。再谈对《鱼目集》的总体认识:“他离爱情那样远,这里不见一首失恋的挽歌。”即使“《新秋》那样轻快”,“《海愁》那样温绥”,依然“不徒感伤,但是怎样忧郁,如若你咀嚼卞之琳先生力自排遣的貌似的平静!”〔4〕对《圆宝盒》,他说:“用《圆宝盒》象征现时,……那‘桥’不就隐隐指着结连过去与未来的现时吗·”如若不是,那么,“这象征生命,存在,或者我与现时的结合。然后我们可以了解,生命随着永生‘顺流而行’,而‘舱里人’永远带有理想,或如诗人所云:‘在蓝天的怀里’”。对《断章》,他说:“我们诗人对于人生的解释·都是装饰。”因此,“这里的文字那样单纯,情感那样凝练,诗面呈浮的是不在意,暗地却埋着说不尽的悲哀”〔5〕。
李健吾对中国的现代派诗歌一直看好,《〈鱼目集〉》之前半年就写了《新诗的演变》〔6〕。在这篇回顾近二十年新诗发展历程的文章中,他对发端于李金发的现代诗歌的发展前景表达了相当乐观的情绪,并预言,“最有绚烂的前途的,却是几个纯粹自食其力的青年”;在诗歌取消歌唱的共同努力中,“真正的成绩”,就出自这“几个努力写作,绝不发表主张的青年”〔7〕。这几个青年,就是后来被称为“汉园三诗人”的李广田、何其芳和卞之琳。
二
1929年秋,卞之琳考进北大英文系。1931年春,徐志摩拿走了他的一束诗稿,后选出《群鸦》等四首刊登在《诗刊》第二期上,并决定编成一集,取名《群鸦集》出版,后因徐遇难而未果。卞之琳说:“第二年(1931)初,徐志摩来教我们英诗一课,不知怎的,堂下问起我也写诗吧,我觉得不好意思,但终于老着脸皮,就拿那么一点点给他看。不料他把这些诗带回上海跟小说家沈从文一起读了,居然大受赞赏,也没有跟我打招呼,就分交给一些刊物发表,也亮出了我的真姓名。这使我惊讶,却总是不小的鼓励。”〔8〕因此,初登文坛的卞之琳被普遍认作是新月诗人。陈梦家说,卞之琳是“很有写诗才能的人。他的诗常常在平淡中出奇,像一盘沙子看不间底下包容的水量。如《黄昏》,如《望》都是成熟了的好诗”〔9〕。
沈从文更是对卞之琳赞美有加,说他“善于运用平常的文字,写出平常的人情”,文字“单纯简略”,“风格朴质而且诚实”,预言“朴素的诗将来最好的成就或者应当归给之琳”,〔10〕1933年5月,他甚至在抽屉里还有几张当票的情况下,拿出三十元资助卞之琳自费出版了第一部诗集《三秋草》。也就在当月,朱自清说,《三秋草》是“一本波俏的小书”,表现的是“你和我都熟悉”的“平常”“味道”,“作者观察世态很仔细,有时极小的角落里,他也会追寻进去”;“他用的是现代人尖锐的眼”,在“平淡无奇”中发现“精微的道理”;艺术上也有创新,意象与意象之间“跳得远”,虽然笔下仍是清清楚楚,但他们之间的“桥却拆了”,由于“联想”出奇,比喻也“用得别致”,有时候“不但没有桥,连原来的岸也没有了”〔11〕。沈从文则假借卞的口吻说“我讨厌一切,真的,只除了阿左林”〔12〕。他笔下的卞之琳,是一位多情的诗人,带有颓废和悲观的色彩,是一位极具悲观情绪的思考者。
不过,从诗的政治功利观、大众化诗歌艺术观的立场,左翼诗人对卞之琳的诗歌进行了批判。蒲风评论《三秋草》时,把卞归入新月派,这没有什么不妥,却又给他扣上了“格律派”、“唯美主义”的帽子〔13〕。与李健吾的《〈鱼目集〉》几乎同时,—位署名李磊的青年作者写了《〈鱼目集〉和〈孤帆的诗〉》,拿《鱼目集》和左翼青年诗人孤帆的诗集《孤帆的诗》对照,认为《孤帆的诗》正面反映了底层人民的痛苦生活,而《鱼目集》则“没有内容”,充满了“幻想”、“华宴”、“睡眼朦胧”、“孤独”、“灰心”,“暮色苍茫”等等,实际上否定了《鱼目集》〔14〕。应该说,这些评论指出了卞诗以及其他新月派、现代派诗人确实存在的疏离时代的不足,但忽视了这些诗歌关注人生的—面,对这类现代派诗歌艺术上的积极意义也缺乏正确估价。
卞之琳性情柔和、含蓄内敛,他后来回忆说,他不赞成办“狭隘的存心反左的派性刊物”。李健吾宣扬“京派”、提携朋友的用心他心知肚明!但左翼诗人对他的否定不能不让他心有戚戚。于是,在李健吾《〈鱼目集〉》之后两个月,他写了《关于〈鱼目集〉》。
他首先说,李健吾对《鱼目集》—些诗的解释,有的与自己创作意向“差不多”,有的“出我意料之外的好”,有个别地方则如李自称的“全错”。关于《圆宝盒》与《断章》,他说:
可是您起初猜“圆宝盒象征现时”,……显然是“全错”。您后来说是“我与现时的结合”,似乎还可以,但我自己以为更妥当的解释,应为什么呢·算是“心得”吧,“道”吧,“知”吧,“悟”吧,或者,恕我杜撰一个名目,理智之美。
《断章》……我的意思也是着重在“相对”上。〔15〕
然后他谈了自己关于诗歌解读的看法:“我以为纯粹的诗只许‘意会’,可以‘言传’则近于散文了。”但解读是有必要的,即使不确切,也“未尝无助于使读众知道怎样去理解这一种所谓‘难懂’的,甚至于‘不通’的诗。”
针对他的诗歌“没有内容”的评价,卞之琳说:“大概特别在中国,评诗是更容易的事情了。”“我们可以说橘子没有栗子的内容,可是我们可以说橘子没有内容而栗子有内容吗·”他认为:“材料可以不拘,忠君爱国,民间疾苦,农村破产,阶级斗争,果然可以入诗,风花雪月又何尝不可以写呢·”而且无论是“吟风月”或者“吟血泪”都要有“痛切的感觉”,而且要经过艺术的“适当的安排,适当的调度”;“未经艺术过程者不能成为艺术品”。最后他义正词严:“随便人家骂我的作品无用,不合时宜,颓废,我都不为自己申辩,惟有一个罪状我断然唾弃,就是斩钉截铁的‘没有内容’。”〔16〕
由于李健吾并没有说他的诗歌“没有内容”,因此可以断定,卞之琳的答辩针对的不是在肯定他的诗歌是一种创造性的美学成果的前提下对之进行解读的李健吾,而是对他的诗歌持否定态度的左翼诗人。于是,我们明白了,在《关于〈鱼目集〉》中,他为什么那么少见的义正词严地反驳关于他的诗“没有内容”的指责,也就明白了辩论中,两人虽都有负气的成份,却并不伤和气,仍然是很好的朋友。1937年春天,卞之琳到上海翻译了法国班亚曼·贡思当的《阿道尔夫》。这本书是李健吾推荐,借给卞之琳“法文原本”及“一本英国版的译本”,“并且还留我在家里小住以完成译事”的〔17〕。1946年6月,卞之琳乘船离香港往上海,依然住在李健吾家。之后他们的友谊历久弥香,1990年,八十一岁高龄的卞之琳还写了《追忆李健吾的“快马”》。
三
李健吾自信、好胜,对批评的尊严看得极重。他曾说过:“我菲薄我的批评,我却不敢过分污渎批评本身,它有它的尊严。正因为批评不是别的,也是一种独立的艺术,有它自己的宇宙,有它深厚的人性做根据。”〔18〕因此,面对卞之琳关于《鱼目集》解读的反驳,他又写了《答〈鱼目集〉作者》。
开篇他就感叹:“了解一个人虽说不容易,剖析一首诗才叫‘难于上青天’”。至于原因,他说:“一个读者和一个作者,甚至属于同一环境,同一时代,同一种族,也会因为一点头痛,一片树叶,一粒石子,走上失之交臂的岔道。”而且,“明白清楚是作者努力追求的一个目标,是作品本身的一个要求,是读者一种意内的希望,却不是作者达到目标的征记,作品价值的标准,至于读者的希望,在创作的过程中,很少放在作者的心上”〔19〕。更重要的是,即使作者想要表达得明白清楚,由于眼高手低,还存在一个表现的窳陋——如陆机所说的“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情况。
至于诗歌解读,他引用了梵乐希的“一行美丽的诗,由它的灰烬,无限制地重生出来”。然后阐释说:
一行美丽的诗永久在读者心头重生。它所唤起的经验是多方面的,虽然它是短短的一句,有本领兜起全幅错综的意象:一座灵魂的海市蜃楼。
于是,很自然的得出了“一首诗唤起的经验是繁复的,所以在认识上,便是最明白清楚的诗,也容易把读者引入殊途”的结论。在此基础上,转到对卞之琳诗歌的解读,对《断章》,他说:“我冒然看做寓有无限的悲哀,着重在‘装饰’两个字,而作者恰恰相反,着重在相对的关联。我的解释并不妨害我首肯作者的自白。作者的自白也绝不妨害我的解释。与其看做冲突,不如说做有相成之美。”
关于《圆宝盒》,他先“搜寻一己的疏忽”的四个方面,但他依然质疑说:“即使我们顺从作者,把‘桥’看做情感的结合,我们能够三言两语,说明全诗的印象吗·”并坚称自己把“永远在蓝天的怀里”理解为“永远带有理想”,“同样可以说得过去,甚至于接受字面,不妄附会,我觉得更其自然些”〔20〕。
最后,他进一步捍卫批评的尊严:
我的解释如若不和诗人的解释吻合,我的经验就算白了吗·诗人的解释可以撵掉我的或者任何其他的解释吗·不!一千个不!幸福的人是我,因为我有双重的经验,而经验的交错,做成我生活的深厚。诗人挡不住读者。……一首诗,当你用尽了心力,即使徒然,你最后得到的不是一个名目,而是人生,宇宙,一切加上一切的无从说起的经验——诗的经验。〔21〕
十几天后,卞之琳以《关于“你”》作答。他说由于“中国是一个善骂的国度”,怕被人家误会,“本来不想再写这种文字了”,“不过有一点小问题似还有声明一下的必要”。他说了两点,第一,《圆宝盒》中的“你”可以代表任何一个人。第二,诗歌的确难以解说,“这首诗,果如你所说,不是一个笨谜,没有一个死板的谜底搁在一边,目的并不要人猜”,“解释一首诗往往就等于解剖一个活人”〔22〕。
四
1933年夏,卞之琳从北京大学毕业,开始了新的生活。他单身—人,没有家,也没有固定住址,以北平为基地,有时也去外地“转悠”,几年间,日本、济南、青岛、南京、上海、苏州,等等,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成了真正的自由职业者,全身心地投入“自由写作与翻译”。他的那首叫做《候鸟问题》的诗,多少是自况,他就是一只候鸟,为了生活、事业而南来北往。他翻译的马丁(E.M.Martin)的散文《道旁的智慧》,赞美了“走江湖人”,即“游方人”风尘仆仆的旅行生活,赞美了他们“道旁的智慧”。马丁写道:“那种生来就有候鸟习性的人,关在四壁中永远也不会快乐。春天一到,游方人的孩子就不安定起来了,渴慕道上的生活——渴慕它的颠沛,它的艰难,它的自由……”〔23〕这段话几乎可以看做卞之琳当时的“夫子自道”。
李健吾的两篇长文是卞之琳和现代派诗歌研究的开山之作。在他点出卞之琳的现代性特征不久,邵洵美就进一步肯定卞之琳等新派诗人给新诗带来了新的技巧,“不能因为不懂而说这是诗人的荒唐”〔24〕。1936年10月,戴望舒以新诗社名义出版《新诗》,编委是孙大雨、梁宗岱、冯至、卞之琳和他自己,这说明了卞在诗界地位的上升。1937年朱光潜赞誉戴望舒、卞之琳的诗是一种“新技巧与新风格的尝试”,“是向最大抵抗力去冲撞”〔25〕。
赞誉太多,必然引起质疑。1937年6月,梁实秋化名“一个中学国文教员”“絮如”,指责“一部分所谓作家,走入了魔道,故意作出那种只有极少数人,也许还没有人,能懂的诗与小品文”,即所谓“象征派”的“糊涂诗文”。他举了三个例子,第一个就是卞之琳的《第一盏灯》〔26〕。胡适,作为当时的士林之首,支持了梁实秋的观点,但说所举的卞之琳的例子有点“冤枉”,“《第一盏灯》是看得懂的,虽然不能算是好诗”〔27〕。周作人、沈从文以《关于看不懂》为题著文进行了反驳。周作人认为“看不懂”的作品,可能因为“思想的晦涩”,也可能由于“文章的晦涩”,其是非应该有作家和批评家定,不能以中学生能否看懂,“据此以定那种新文艺之无价值”〔28〕。沈从文则从审美的差异性出发,说作者、读者或“欢喜明白清楚”或“欢喜写得较有曲折”。他大力支持了卞之琳等现代派作家,说那些“能在文学上创造风格的作家”“对于新文学的贡献”有功,可以促进“有天才的作家的自由发展”,“孕育了一个‘进步’的种子”〔29〕。
在赞许与批判肯定与否定的不同声音中,卞之琳的诗歌在新诗界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并逐渐扩大了影响。杜运燮后来写道:“我们那一代青年都读过卞之琳的《鱼目集》,《汉园集》中的《数行集》以及《断章》、《尺八》、《距离的组织》等名著。”〔30〕绿原也回忆,抗战前夕自己还是一个初中生,有一次“偶然从同学的案头发现一位前辈诗人的诗集,简直像发现了一盘珍珠,虽然它的题目偏偏叫做《鱼目集》……这位前辈诗人于是引发了我的模仿本能”〔31〕。
抗战开始后,卞之琳先后担任四川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讲师。能够跻身大学讲坛,得力于师友的举荐,更得力于他现代派名诗人的头衔。这头衔的获得,与他和李健吾的论争不无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健吾和卞之琳这来来回回四篇文章的论争,是辩驳,更是唱和!
注释:
〔1〕载1936年4月12日《大公报·文艺》副刊。收入《咀华集》时,成为了《〈鱼目集〉》的第二部分。
〔2〕〔3〕〔4〕〔5〕〔7〕〔15〕〔16〕〔18〕〔19〕〔20〕〔21〕李健吾:《李健吾文学评论选》,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6—87、108、92、94、85、96—98、98—101、40、103—104、109—110、110—111页。
〔6〕李健吾:《新诗的演变》,载1935年7月20日《大公报·小公园》。
〔8〕卞之琳:《雕虫纪历》(1930—1958)(增订版),香港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3页。
〔9〕杨匡汉、刘福春编:《中国现代诗论》(上编),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第153页。
〔10〕沈从文:《〈寒鸦集〉附记》,1931年5月《创作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11〕朱自清:《〈三秋草〉》,1933年5月22日《大公报·文艺》副刊。
〔12〕沈从文:《卞之琳浮雕》,1934年12月1日《大公报·文艺》副刊,署名“上官碧”。
〔13〕〔14〕陈丙莹:《卞之琳评传》,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1页。
〔17〕卞之琳译:《阿道尔夫》,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1页。
〔22〕见1936年6月19日《大公报·文艺》副刊。
〔23〕见1934年6月5日《人间世》第五期、1934年6月20日《人间世》第六期。
〔24〕邵洵美:《诗二十五首》,上海时代图书公司1936年版,第11页。
〔25〕朱光潜:《编辑后记》,1937年1月1日《文学杂志》创刊号。
〔26〕〔27〕见1937年6月13日《独立评论》第238号。
〔28〕〔29〕见1937年7月4日《独立评论》第241号。
〔30〕杜运燮:《捧出意义连带着感情》,袁可嘉等主编:《卞之琳与诗艺术》,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31〕绿原:《人之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