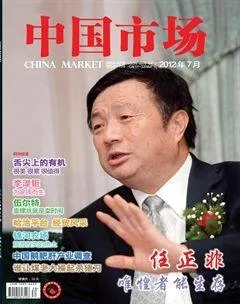中国鹅肥肝产业调查
这是一个不断出现在地方政府招商引资项目表中的朝阳产业,
又是一个因不人道频频招致抗议的没落产业。
2012年1月,英国公司Creek Project计划投资1亿美元在江西鄱阳湖畔建立全球最大鹅肥肝生产基地的消息,迅速引发公众反弹。4月3日,该公司高管不得不宣布暂停投资计划,直到完成包括有动物福利及环境影响专家参与的全面调研。
这是否又是一个“全球都不要,送给中国造”的案例?其中又隐藏着怎样的利益链?
争议不断的英国项目
“我们刚看到鹅肝生产‘不人道’的说法,此前并不了解。”来自江西桑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招商局负责Creek Project招商项目的杨欣宇说。据他介绍,Creek Project是英国一家金矿公司,去年10月来到桑海考察,当时就提出做鹅肝项目,在南昌发改委立项为“家禽养殖”。
当然,“这份意向性协议规定对方必须到环保局做环境影响评价。如通过,才签正式合同。”桑海经济开发区招商局钱副局长表示,没想到对方迟迟未做环评。CreekProject中方代表透露,该公司总部计划近期在德国柏林上市,“资金周转不过来,不会这么快地进资鹅肝项目”。
也许正因为此,截至6月底,占地面积40亩的该项目暂未发现有建厂迹象。但当地发改委工作人员仍然表示,不会因“不人道”因素叫停一个项目。
强制填饲之祸
鹅肥肝被视为法国美食的代表。据记载,鹅肥肝起源于2000多年前的古埃及,兴盛于法国路易十六时期,法国、匈牙利等为鹅肥肝生产大国。
但多年来,培育鹅肥肝所必须采用的强饲法在国际上一直饱受争议。
目前,国内多家鹅肥肝厂也均以“当季禽类发病率高”或“涉及专利技术”为由拒绝参观。
“工作人员熟练地用左手拽住鹅头,右手将一根长铁管伸进鹅的嘴里捅进去,‘砰呲’一声响,高气压就将玉米糊射进鹅的胃里。而那些被填食的鹅翻起眼珠、浑身乱颤,翅膀在狭小的笼具内拼命扑腾。当铁管拔出时,鹅发出凄惨的鸣叫并不停地甩头,玉米糊从它的嘴里甩掉、溢出、再甩掉、再溢出。”记者在一次暗访后做出如上表述。
世界农场动物福利协会一项调查显示,在一些鹅肥肝生产厂 ,强饲插管操作过程造成鹅或鸭痛苦、伤害;过量强饲造成鹅肝脂沉积、肝破裂、肝硬化等。
最后屠宰得到比正常鹅肝肿大6倍以上的鹅肝,这就是人类酷爱的美食——鹅肥肝。
“水至清则无鱼,任何一个行业都有污点。你得允许不合理的东西在一定历史时期存在。”专做鹅肥肝投资生意的杨利君反问:“西方的斗牛难道就人道么?”
正是由于强制填饲饱受争议,西方很多国家逐渐禁止鹅肥肝生产。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议会已通过法案,今年7月1日起,禁止以迫害动物的方式生产和销售一切鹅肝食品。到2019年,欧盟将禁止所有成员国生产鹅肥肝。
西方人想吃又觉得残忍,在此情况下,中国鹅肥肝产业顺势而起。
高利润下的趋之若鹜
“我国自1981年鹅肥肝初试成功至今,鹅肥肝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中国畜牧业协会家禽业分会鹅肥肝产业联盟秘书长陈耀王说。
目前中国肥鹅肝企业多分布在吉林、山东、安徽、广西、云南等地,“吉林做得最大,山东最密集”。
号称“打造中国鹅肥肝第一品牌”的吉林正方集团销售部华北地区郑经理说,鹅肥肝在中国是小众高端食品,多销往中高档酒店和西餐厅。而酒店往往喜欢大肝,越大越容易做型,卖得越贵,“生产商就将鹅肝一味搞大,疯狂填饲”。
正因为此,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表示,10年前中国企业用螺旋推进器将煮熟的玉米粒推进鹅的胃里,一人一天可填100至150只鹅。如今采用气动式填饲器,一人一天可填2000只。“如今我们将一只鹅的肝填大,只需15天。”吉林正方集团副总经理张福君不无骄傲地表示。
那么,15天撑大的利润究竟有多高?
“生产成本每公斤200元的上等鹅肥肝,经加工企业之手就可升至每公斤600元,到了酒店甚至可以卖出每公斤几千元的高价。”吉林德坤禽类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贾财德表示。
显然,有市场有利润,自然就有人趋之若鹜。
“10年前中国鹅鸭肥肝总产量1000吨,目前已达3000吨。”张福君说。受高利润吸引,2000年后,中国鹅肥肝企业数量大幅增加。以山东潍坊临朐县为例:2004年前仅一家大型的圣罗捷公司,2006年就已发展到50多家。目前全国各地鹅肥肝厂总数已超150家,这还不包括那些不露头的小作坊。
肥肝产品质量堪忧
这是否说明鹅肥肝产业在中国就欣欣向荣了呢?
陈耀王最担心的是“鹅肥肝产品质量堪忧”。
“鹅肥肝不能煮得时间太久,往往都是半生不熟就吃的,因此有严格的质量要求。”他说,“一些企业把屠体放在露天的污水池中‘预冷’,不顾卫生,只要取出肥肝,就能卖个好价;更有甚者,为了使肥肝外观好看,用化工原料漂白。”陈耀王说。
在上海等大城市的时尚餐厅里,销售着“源自法国”的鹅肥肝,尽管无从得知这些鹅肥肝的确切来源,但可以肯定的是,除了进口渠道,也有不少国内企业生产的鹅肥肝流入上海。
事实上,“家庭作坊式企业投入少,鹅肝质量差,靠低价倾销获利。”陈耀王说,即使是大企业主,对鹅肥肝生产的高风险也缺乏了解。如鹅肥肝脂肪熔点低,香味极易流失,这对生产鹅肝的冷冻技术要求极高。
陈耀玉指出,很多大企业主急功近利,贪大求洋,盲目投资,其结果绝大多数是亏损的。
曾经风光一时的吉林德莱鹅业就是如此。有媒体报道,2006年5月,吉林德莱鹅业公司总投资9.1亿元,规划年产1000吨鹅肥肝,还曾从匈牙利和丹麦引进设备。然而如今只见该公司厂房大门紧锁,满园荒草。
“只有倒掉的企业,没有倒掉的行业。”在杨利君看来,这是个行业洗牌的过程,有企业倒掉也有企业发展壮大。
自称是第29届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的供应商的正方集团子公司计划今年上市,打造中国第一个上市的鹅肥肝生产企业。
困顿下的一往无前
然而,对中国的鹅肥肝生产者来说最大的尴尬是,原本指望中国鹅肥肝进入国际市场,填补欧盟“2019年禁令”腾出的市场空白,但事实上,出口鹅肥肝实在太难。
正方集团年产鹅鸭肥肝900吨,占全国总产量近1/3,仅少量出口日韩和东南亚国家。而号称产量占到国内市场40%~50%的山东圣罗捷公司,至今却仍未取得法国的出口注册。其副总经理常峰祖甚至直言不讳的表示,“根本就别想了,那标准不是中国企业玩得起的,不符合中国国情。”
中国国情是什么?
中国鹅肥肝生产者认为,中国人的消费习惯与能力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提并论,“中国至今没有一种官方认可的鹅肥肝质量体系标准。国家也没重视这个产业。”杨利君还指出,“匈牙利鹅肝的生产过程也达不到法国人的标准,但是法国对其一路绿灯。法国人不愿相信中国人能生产出他们最高档的一道菜。”
而在动物保护者和环保者看来,实际上,欧盟出台的对熟食品的报表制度和可追溯体系,要求从一件产品可追溯到每个生产环节,甚至包括当班工人。“而在中国,没有一家企业的生产水平可以达到这个标准,”达尔问自然求知社罗凡解释。
2012年3月1日,达尔问自然求知社举行新闻发布会,引用科学报告指出鹅肥肝是发生脂肪沉淀病变的肝脏,“相当于吃油一样”,现场更有营养学家从营养价值评比,以营养价值最高的羽衣甘蓝得100分为标准,肥鹅肝只得2分,处在最末流。
孰是孰非?对中国鹅肥肝生产者来说,这似乎从来不是问题。近年来,鹅肥肝项目不断出现在各地政府招商引资的项目表中。
这似乎正如上述受访的鹅肥肝业内人士所说,外界谴责对行业影响不大,因他们有冒险精神。(编辑/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