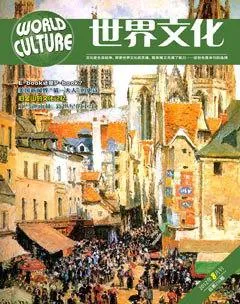天才艺术家:还有多少心思没对世人说
以前,人们会纵容、爱惜地恭维艺术家都是来自天国的精华,意思是说对于这些人的举止言谈,大可不必在意。如此“忽略”他们,我们将错过多少异样的风景啊。
作者手记
对于天才的艺术家,在不同的文化区域中,被人们视为特异的事情,确实是大量存在着的,偶然的巧合,确实可以说明一个规律性的问题,但是在具体的事件上,人们一般都会在享受这份被视为灵异现象带来的奇妙感觉。拉斐尔·桑蒂出生在1483年4月6日,这一天是耶稣受难日——宗教上一个悲壮的日子。而他的死亡日期也是一个4月6日,那是1520年4月6日。
拉斐尔的父母就像为他而来到世上,他的母亲把他哺育到8岁后,去世了。他的父亲又将他教育了三年,也离他而去。现在从零星的记载来看,在他父亲活着的时候,他已经能从事艺术的工作了。好了,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拉斐尔的父母在尘世完成了最初对这位天才的教养之后,被上帝召回了天国,而“拉斐尔”正是《圣经》中天使的名字,事情果真如此?还是完全来自历史的巧合?我们无从知晓。
作为一位敏感,并且极富艺术才华的画家,实在是无从知道拉斐尔桑蒂内心深处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孤儿身份,他也许真的让自己相信,其有着非同一般的身世。有一个场面是被真实记载下来的,画家在弥留之际,让人将他画的《基督显圣容》(1518—1520)搬到床前,这是在坚定自己内心编造的他来自天国这个神话吗?画家短暂且辉煌的生命中,他一直是异性的宠儿,与许多女人交织在一起,这是年轻画家一直在苦苦搜寻母爱的行为吗?他塑造的圣母形象,有着一般画家笔下所缺少的世俗女性的完美性,成为那个时期人文主义艺术的典范,或者说正是这一点,反映出他内心中恋母情结比一般的人更为强烈?
天才们的心思很难让人读懂,他们的天赋异禀已经与一般人有了不小的距离,再加上一些传奇的身世,更使他们有意无意间为自身营造了独特的心理和精神状态,在我们看他们时,就包含了颇多迷离的色彩。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研究者通过蛛丝马迹的分析,认为这位艺术家有同性恋的倾向,这种结论真不好置以可否。
先简单说一下达·芬奇的身世,他有一个私生子的身份,研究发现其母亲的身份低下,他在很小的时候就与母亲分开了。达芬奇是一个早熟的天才,14岁做学徒时已经画得相当出色了。对于这样的孩子,敏感应该是他最明显的特质,这时的他可能就是要用自己的才能证明他的出色与其母亲的了不起,也可以说他没有真正的童年。及至年长,他的心思完全放在对新知识的研究和设计构想上,这有他大量的手稿为证,在那个普通人犹不知科学为何物的时代,没有像虔诚的教士侍奉上帝一样,没有把全副精力投入其中的献身精神,他的科学成就仍令我们现代人瞠目结舌。
在达·芬奇身上兼具了细腻与严谨的气质,也可以把这种特质解释为感性思维与理性思考的表现,或者解释成母性和父性襟怀,当他收留流浪的绰号“撇旦的翅膀”萨莱为学徒时,当看到少年身上的顽劣、聪明、单纯和无所畏惧等等混杂在一起时,还有就是其相貌与他的理想美——他们有相像的地方(应该说达·芬奇有明显的自恋倾向),他看到了自己少年时代的缺失,这时,在他的身上,多少年寻觅的母爱转化成一种母性的情结,对父亲的诸多不满(包括遗弃了自己的母亲),转化为“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父亲。人的特定情感就在一个适合的际遇中得到了释放,而特殊的感情纽带很多时候还是单向的,无疑也会在这个人的情感与思想中成为一种纠结,呈现出复杂的状态。列奥纳多·达·芬奇与萨莱之间的关系,自然也就成为后人的一种错读。
艺术家都有一个敏感的心灵,其实何止敏感,深入地了解到他们的内心,有的时候还极为脆弱。雕刻家罗丹与画家莫奈有很好的交往,他们曾在一起共同办过印象派展览,并且终生来往。而罗丹对莫奈的晚年生活颇有微辞,认为他的生活太过于安逸享受了,画家有自己漂亮的大花园和宽敞巨大的画室,显示着主人的富足。
莫奈也是人,我们先不要看他的物质生活,这些对于他来说,也许都是为了满足心理的某种需要,并不能代表他的人生趣味。他的绘画需要阳光,明媚的光线一直要投射到画家的心里,摈除掉心理创伤为他带来的精神阴影。艺术家敏感的心灵为他作出了选择,兴许他要比其他任何人都热衷于改善自己的物质条件,以此抚平难以复合的心理重创。
他的年轻时代生活极为拮据,不幸的妻子就因患病得不到很好的医治而去世。对于自己挚爱妻子的离世,内心的伤痛也许只有他本人知道。还有一件事是值得一提的,就在莫奈爱妻弥留之际,她的肤色开始起着色泽的变化了——血色在渐渐地退去,这个现象引起了画家的密切关注,不禁脱口读出妻子脸上的色调变化,而忽略了所在场合。作为一个“印象主义”的创始者(印象主义因他的画作《日出·印象》而得名),对色彩变化的敏感就是他的职业病了。
你道莫奈是个迂腐的人吗?错了,印象画派刚出道时,人们不理解,所以很少购买这些画家的画,莫奈把画放到画店里,用不了多久,就被卖出了,于是引起了买家的注意。原来是画家自己托人买回了自己的作品,为的是不要长久地滞留在画店里,给人以没人要的印象。他的画家朋友也公认莫奈有着商人般精明的头脑。
对于艺术家来说,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的酷爱,就是其行为方式跃出世俗的尘格,在常人眼中就显得不合时宜,去菲薄这样的人,只能说明这种非议缺少一种文化的境界。艺术家们就是这样生活的一群。
莫奈在他晚年绘制了巨幅创作《睡莲》,其中光影的灿烂缤纷,成为他的登峰之作。他的《干草垛》系列也成为画家探索光线变化的力作,干草垛成为他的钟爱。画面上几乎表现了光线在瞬间的变化,莫奈用自己的心理感悟,为人们创造了视觉的盛宴。在印象派的作品前,文学性的描述,哲理的分析统统可以置于脑后,你只需要带眼睛来看就可以了,也正是这一点,他才需要平稳客观的心情来观察自然。莫奈要说出自己的真实,他钟情于自然,而并非要表现豪华家具上的迷离光线,以显示其物质生活的优渥,他一生始终驻留在自己的艺术表达方式上,为描绘自然中的光而达到苛刻的程度,以致每隔20分钟就要在另一张画布作画,来适应不同时间段的光线变化。
莫奈对物质的需求,正反映出他对艺术的态度:不要再因为不幸而令情感挫伤,影响到对自然的观察。
真说不好逻辑的思考与表述是为天才们的戏法,还是他们的特异思考显露出的人之常情,会令我们会心地莞尔一笑。萨尔瓦多·达利讲述了自己的一段趣闻:
我献身于各种想干和不想干的古怪行为。我33岁了。我刚接到一位最杰出的年轻精神病医生的电话。他才在《米诺陶》中读到我关于“偏执狂活动的各种内在机制”的论文,他向我表示祝贺,我对这样一个题目的正确科学认识(一般而言,这是极为罕见的)令他吃惊。他想见见我,当面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商定当晚在我位于巴黎高盖街的画室里会面。这临近的会面使我十分激动,整个下午,我都在努力起草一份我们要谈的事情的大纲。实际上,我满意我的各种观点(就连超现实主义团体中最亲近的朋友们,也把它们看成是自相矛盾的心血来潮的产物)会在一种科学的环境中加以考虑。我一心想使我们初次交换意见这件事能正规地、甚至有几分庄严地进行。在等待年轻的精神病医生到来之际,我继续凭记忆画一幅肖像,我正在把它画成诺埃依子爵夫人。这幅用铜版制作的画,搞起来很难,为了看清我画在光洁如镜的褐色铜片表面上的素描,我注意到在反光最明亮的地方能清楚地辨认出我作品的细节。因此我在鼻尖上贴上一块三厘米的方形白纸片来作画,这块白纸片的反光完美地显示出我的素描。
六点整,有人按门铃。我收起铜版,给来访者打开门。雅克·拉康进来了,我们马上开始一场非常紧凑的专业性讨论我们惊奇地发现,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的观点与公认的构造主义论断是对立的、在两个小时内,我们以真正激动的辩证方式谈论着。雅克·拉康离开时,答应定期跟我接触,以便交换意见。
他走后,我在画室里来回踱步,尽力概括我们的谈话内容,更客观地估量我们之间暴露出来的少数不同点。可有一点令我困惑不解,那就是这位年轻的精神病医生不时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这令我不安。仿佛一种奇怪的微笑想掀开他的嘴唇,而他克制着不让自己显出惊奇来。他在致力于对我的面貌(那些使我心灵激动的想法让它富于生气)进行形态学研究吗?当我去洗手时(这个时刻正是人们能最清楚地弄明白不论什么问题的时刻),我解开了这个谜。不过这次是镜子给了我答案。在那两个小时内,我忘记除掉贴在鼻尖上的小白方纸片,以一种客观严肃的语调,极为认真地谈论着先验的问题,却毫没料到我鼻子的可笑样子!可有哪个犬儒主义的故弄玄虚者能把这个角色演到底呢?
从上面引用的画家本人文字来看,萨·达利是在标榜自己的一生将异于常人吗?我看他正常得很!他的天才始终没有把他弄神经,艺术只成为他一生戏弄世人的超级把戏,而没有成为他的生命。一个最好的证据就是在他的晚年,他请年轻的艺术家为他代笔了,事情被揭露出来之后,世人为之哗然。这在凡·高的内心想象中,根本就不可能发生。
《有乌鸦盘旋的麦田》是文森特·凡·高的绝笔,面对这幅绘画,应该请心理学家为我们解读其中的死亡气息。实在地说,这位画家的人生充满了苦难和命运的捉弄,但是他都以对自己艺术的坚强信念,坚韧地活着,可以说他是用自己的生命之火,点燃了艺术的光焰。没有人真正理解他的艺术,兄弟关照他,在他看来或许只是感情的慰藉与支持,挚友保罗高更远离他而去,到了太平洋上的小岛上生活,他再也找不到打架宣泄的对手了,他的理性与感性长久以来一直产生着强烈的对抗,绘画与文字也不能排解越来越拥塞在胸中的积郁,这一切有可能连画家本人也不能清晰地察觉。
在看似一切如旧的生活轨迹中,结果就会突然降临,他日常生活中一个微不足道的事情,就突然使他的思考陷入其中不能自拔,他是将自己视为麦田上的乌鸦了吗?因为它们在盗食成熟的麦穗,他在扣动扳机之前肯定自己是一个完全无用的人了?心灵就在这一刻被捻为灰烬,这一切也都是猜测而已。
奥地利画家埃贡·席勒的艺术风格就像奇异的流星,光华烨烨,1918年维也纳发生大规模的流行感冒,死了很多人,席勒就是一个极为神经质的画家,他害怕极了,把门窗关严,终日恐惧地待在屋中,然而死亡还是降临了,他在28岁的美好年华即回归天国。
画家席勒的死,他内心神经质的易脆也许就是其摆脱不了的梦魇。
读美术史之余,关注此类问题,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去认识艺术家们的艺术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