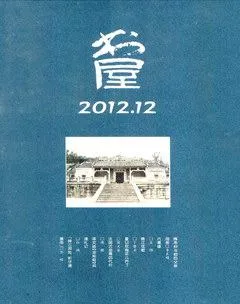读商昌宝《作家检讨与文学转型》
保罗·约翰逊在其著名的《知识分子》一书考量了扮演人类引路人和导师的世俗知识分子成为该角色具有的道德和判断力的资格,尤其是他们对待真理的态度、寻找证据和评价证据的方式以及对待特定人的方式〔1〕。这部毁誉参半的作品对现代化进程中的知识分子进行了深入骨髓的精神考察,展现了这个群体别样的人格面孔,解构了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道德优越感。作者的研究方式和价值取向很具有诱惑性,他将取代神职人员的世俗知识分子放到了显微镜下,用锋锐的精神手术刀刮擦着他们的道德肌体。就这样,一个本该是常识的结论从细微的缝隙中浮出了历史地表。那就是,知识分子并不比古代的巫医或牧师更聪明、更值得尊重。以此为鉴,将其方法和价值取向“中国化”,考察现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知识分子作为启蒙者或者引路人具有的道德和判断力资格不啻是一种有趣的尝试。当然,这种有趣的尝试对于中国的有些知识分子来说将是对其精心包装的社会身份的一种可怕的威胁。某种意义上,商昌宝的《作家检讨与文学转型》(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就扮演了这样的在某些“正常人”看来并不“正常”的角色。
出于对百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考量,学者李新宇认为二十世纪“一次次导致知识分子主体价值失落和文学枯萎的悲剧事件,开始的时候并不是由于政治力量的压迫,而往往是一些文人自身要进行调整”。站在启蒙主义的立场,他还指出,二十世纪中国作家“一个最大的遗憾是作家人格现代性的欠缺”,“大多数作家在这个世纪没有完成人格的现代性转化”〔2〕。《作家检讨与文学转型》一书的问题意识与此论断关联密切。作为对该意识的问题性反应,作者敏锐、准确并不乏学术见地的定位了自己的研究标本,选择了中国大陆政治、文化转型的五十年代这一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更年期作为研究背景。作者以作家的“检讨书”为利剑,直逼问题的核心:五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集体转型的“一体化”行为。至于锋芒所在,作者将瞄准了“这一转型是否是一种出自内心”的自愿行为的追问上。他选择的这把道德的利剑意义独特,正如本书序者李新宇先生指出的,“检讨书是一种特别的文本,包含了丰富的时代文化密码,要考察那个时代作家的精神状况,它的价值的确是别的文本无法替代的”〔3〕。
本书的最大意义并不在于通过心态史的考察来阐释文学转型——当然,这也是本书的一大学术贡献——而是依序探寻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思想改造的大环境中“五四”以来形成的现代文人群体的精神状态、心理嬗变的复杂过程以及精神气质转变的深层原因。作者选择了以朱光潜、沈从文、萧乾等为代表的所谓“反动作家”,以巴金、老舍、曹禺等为代表的“进步作家”,以夏衍、茅盾、胡风等为代表的国统区左翼作家,以丁玲、赵树理等为代表的解放区作家这四类标本,正如作者自己所承认的虽不尽完美,但也可以说,既充分考虑了代表性,又兼顾了现代作家的思想主流。在本书中,作者抓住了他们共同的精神特征,即这群并未完成人格现代性转换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心态上呈现的道德价值准则的明显变动以及原罪思想所具有的典型的非逻辑性和变象性特征,这种心态嬗变的非逻辑性、变象性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史语码。
然而,作者并不仅仅是做解释学的工作,全书也不仅仅是材料的堆砌。在努力恢复历史现场的努力中,作者偏置了冯友兰式对历史“了解之同情”的研究态度,放逐了对以往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而是采用一种拷问的方式,反诘历史,拷问灵魂。同样,在保罗·约翰逊对知识分子的研究中,他关注的也并不是有关知识分子的宏大命题,而是关注他们公开的和私人的档案,尤其当知识分子告诉人们该如何行事时其道德和判断力的可信程度以及他们在生活中是如何管理自己的、对自己的家庭和同伴表现出了几分忠诚、他们所说的所写的是否都是真实的等问题〔4〕。
还需要提及的是,作者更多地关注了五十年代大陆知识分子面对“调整”、“改造”的自身顺服性,这正是作者偏置“了解之同情”的历史研究态度,放逐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反诘历史,拷问灵魂的原因。书中对萧乾心态的分析,细致入微地刻画出了曹禺1957年在《人民日报》上对他的评价,“萧乾是文化界熟识的人,他很聪明,能写作,中、英文都好。但是他有一个毛病,就是圆滑、深沉,叫人摸不着他的底。过去,他曾在混水里钻来钻去,自以为是龙一样的人物,然而在今天的清水里,大家就看得清清楚楚,他分明是一条泥鳅了”〔5〕。可以说,仅仅“龙”或者“泥鳅”的比喻并不能完全概括五十年代萧乾的社会形象,仅仅探讨这两种社会角色及其转换的过程而不对影响其角色转换的以“清水”、“浑水”为表征的社会生态进行分析也会使研究价值偏离预定轨道。文本中,对这方面的处理显示了作者对问题的敏感性和认识的深刻性。而对曹禺,作者借助他“戏我两忘”社会角色的构型,深入探讨了曹禺转变中的无奈。事实上,在不依不饶的道德追问背后,对上述作家“检讨”心态的关联性探讨构成了对五十年代社会政治、文化转型期间知识分子现代人格转型失败原因的回答。
不可否认,这种以心态史研究为核心的思想史研究在文学史观方面体现了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的探求结果,不仅仅丰富了文学史的描述语词,某种程度上也颠覆了围绕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文学史书写的文化思路。可是,以“表象”、“体验”、“想象”为技术关键词的心态史研究,将研究对象孤立地放到历史舞台中央的历史描述必然导致历史叙述的个性化、文学化,从而有悖于“真实性”为教旨的历史叙述,造成对历史事实认识的虚无化与历史叙述的随意化,从而陷入历史虚妄论的泥淖。另一个方面,这种研究还会导致历史研究的“碎片化”。事实上,这当然会影响文学史知识观念的配置,也会影响对历史宏观价值的评判。因此,如何选择具有普遍意义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材料,如何确定对研究对象普遍意义进行衡量的价值标准等问题就随之而来。好在作者在本书的书写中并没有摆出作为历史必然的权威阐释者的叙述姿态,从而规避了研究主体对研究对象在思想上的主观压迫,以彰显自我的个性化的学术探究,体现了一种客观的富有张力的文学史叙述姿态。
众所周知,单向性的史料堆砌构不成学术研究,但是学术研究肯定离不开研究史料的堆砌。而学问只有做到弥伦群言,辨证然否,钩深取极,独抒己见,方为真学问。“作家检讨和文学转型”的话题虽不属于当下热销的“跨界研究”,但注定了对材料的重视和依赖,这对作者来说是一次大的考验。要想做出“花儿”来,必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尽可能发现的材料进行细致的梳理和筛选,并进行重新的排列组合,呈现出序列性的意义,让思想在意义繁杂的史料上开花。熟悉现代中国文学史料的研究者们明白,囿于国情,本书中丁玲的“检讨”在当下的大陆很难找到。但是,不把这部分史料坐实,关于丁玲思想的转轨论证很难具有说服力。对于这份检讨书的获得,作者在后记中谈到:“值得一提的还有,丁玲的检讨在我做论文时未拿到全文,都是间接引用材料,直至2009年才辗转通过美国大学图书馆找到。”〔6〕除此之外,书中对朱光潜“自由思想的折戟与学术的转向”的论述部分充分发掘了当事人的思想检讨材料,如《关于美感问题》、《致留美某同学》、《从参观西北土地改革认识新中国的伟大》、《从土改中我明白了阶级立场》、《最近学习中的几点检讨》、《我是怎样克服封建意识和买办思想的——最近的学习与自我批评》、《我也在总路线的总计划里——学习总路线的几点体会》、《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百家争鸣,定于一是》、《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些体会》、《我们有了标准》、《不能先打毒针而后医治》等检讨或类检讨的文章。其中,《从土改中我明白了阶级立场》一文刊载于1951年4月13日的《光明日报》。但是,翻阅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的《朱光潜全集》却不见本文的踪迹,这篇文章的发现与征引对于朱光潜研究的意义不言而喻。正是有了这样的史料意识和检索、收集材料的功夫让这本“不讨好”、“不讨巧”的著作在材料上闪着思想的光芒。这一点从《炎黄春秋》、《二十一世纪》、《文汇读书周报》、凤凰网、人民网、新华网、搜狐等相关媒介刊发和转载著作中相关文章就可见一斑。
不可回避的是,真正想回到历史现场并对其中现代知识分子的心态做出精准的分析仅仅是一种学术的理想,这需要更为丰富的分析个案,也需要更为准确的史料支撑,尤其需要对特殊历史时段的客观认识。这就是作者在文末提出建立一种“检讨学”研究的理想所在。事实上,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下,拿什么去问候历史转折期已经沉淀的知识分子以及他们的思想嬗变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注释:
〔1〕〔4〕(英)保罗·约翰逊:《知识分子》,杨正润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69、2页。
〔2〕李新宇:《百年中国的文学遗憾》,《作家》2000年第四期。
〔3〕李新宇:《作家检讨和文学转型·序》,《作家检讨与文学转型》,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5〕曹禺:《斥洋奴政客萧乾》,《人民日报》1957年8月23日,第三版。
〔6〕商昌宝:《作家检讨和文学转型·后记》,《作家检讨与文学转型》,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3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