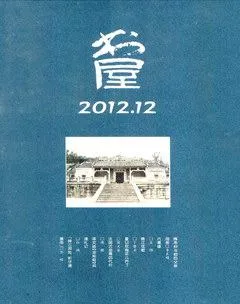阿索林在中国
第一次知道西班牙作家阿索林(1875—1966,民国时期多译作“阿左林”)是在读周作人《看云集》的时候,书中有一篇《西班牙的小城》,那是读了徐霞村、戴望舒合译《西万提斯的未婚妻》之后写的书话。周作人说阿索林的文章好而且特别,读他的小品,对西班牙的那些小城感到一种牵引。他联想到别的几本关于西班牙的书,觉得伊比利亚半岛东西杂糅破落了的古国有些像是梦里的故乡。他还感叹道:“要到什么时候我才能写这样的文章呢!”当时就曾想,得到周氏如此亲切的赞美,该是怎样的文章呢?只是因为懒惰,没有马上把集子找来一读。
以后又读到唐弢《晦庵书话》中的《阿左林》,谈的也是《西万提斯的未婚妻》。作者提到,师陀和傅雷都曾向他借过这本书。何其芳《给艾青先生的一封信》谈到《画梦录》所受的影响,举出的几个中外作家中就有阿索林和巴罗哈,巴罗哈是与阿索林同时代的西班牙作家。以后又在不同时间看到别的中国作家谈论阿索林的文字,渐渐地,这个名字便印记在脑子里了。
我阅读的第一篇阿索林的作品是卞之琳译《上书院去的路》。虽然为作者自传体小说《小哲学家自白》中的一章,但在笔调上完全可以说是一篇短隽散文。六百字的篇幅,把一个八岁的小男孩对于上学的害怕心理写得含蓄动人,跃然纸上。每一个词语,每一个句子,都让人感到是在作者的心情里浸润过的,味道亲切而醇厚。文章写葡萄藤的卷须转黄,“我”知道已经到上学去的时候了,忧郁也随着浓了起来;看到随身携带的物品整理好了,他感到了愁惨的日子一天天地临近;最后踏上了去上学的旅途,害怕的心情也到了顶峰。当可以隐约地看到高楼的白尖顶、闪耀在阳光里的教堂圆顶时,一种说不出的难过袭来,他感觉好像被从乐园的欢愉中拖出,扔进了一个地洞的黑暗了。于是,他试图逃跑……从容不迫的叙述,俭省的笔墨,把人物心理写得很有层次,细腻深入。《上书院去的路》不论是叙事,还是写景,都非常简洁、真切。对干粮、衣物、银食器、建筑物叙述和描写,构成了人物活动的场景,牵动着人物的情思,富于十九世纪西班牙的小城和乡野气息。
由《上书院去的路》的牵引,我曾读过卞译《阿左林小集》,那纯熟、亲切的译文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最近,又通读了阿索林作品的三个中译本——《阿左林小集》,徐霞村、戴望舒合译《西万提斯的未婚妻》,与徐曾惠、樊瑞华合译《卡斯蒂利亚的花园》,进一步走进了他的艺术世界。阿索林用他那富于魔力的笔触,描写了一个个西班牙小城和村庄中的人物,从王公贵族、主教女尼到工匠贩夫,他们活动在一幅幅十九世纪末的西班牙风情画中。文章潜心表现平凡生活的诗意,发掘他们内心深处的悲哀和温暖。并由这众多的人物,有意识地刻画出西班牙的国民性——在坦然的外表下隐忍的素朴、坚强、虔敬、安命。作者有时也G7gVYTDwZIiZOcWWuI0o6Q==在文章里使用“西班牙的国民性”和“西班牙民族的心灵”这样的词汇,显示出这些文章总体的叙事目的。阿索林与同时代作家巴罗哈、乌纳木诺等知识分子同属于“九八年一代”,他们面对西班牙的江河日下,曾主张激进的变革,全面地“欧化”;但不久,又转向重新发现传统的价值,要求保存西班牙的国魂,发起了一场西班牙现代的文艺复兴运动。这种思想态度决定了阿索林众多散文和小说的主题和情感基调。为表现西班牙的真实面目,阿索林告别该国传统文学的浮夸和做作,创造了一种新的平静亲切、细致蕴藉的文体。徐霞村在《一个绝世的散文家:阿左林》一文中介绍说:“阿左林的最大的发现是把日常的东西——一朵花,一个罐子,一个桌子的正确的名字连合起来,而造成一种迷人的文体。在他的散文里,长句和比喻是不存在的,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一些精细而清晰的朴素的描写。”
在现代中国译介的外国作家中,阿索林算不上一个十分响亮的名字。一般读者不用说,就是现代文学研究者知道他的人也不在多数,研究论文更是寥寥无几。然而,阿索林是难忘的,散发出持久的艺术魅力。阿索林像是一座远离尘世喧嚣的乡野小庙,不断地引来几个来自中国的艺术朝圣者。他们停下跋涉的脚步,走进小庙,这寒庙里便因此升起几缕袅袅的香烟。戴望舒和徐霞村大概是最早走进小庙的中国人。前者还曾于1934年8月到西班牙旅行,写过四篇“西班牙旅行记”,其中的《西班牙的铁路———西班牙旅行记之四》写道:“我,一个东方古国的梦想者……怀着进香者一般虔诚的心,到这梦想的国土中来巡礼了。”在他们的身后,跟着一批艺术的朝圣者。人数不算多,却构成了现代文学史上一道旖旎的风景。曾卓曾在《阿左林小集》一文中约略地查点过:
在中国,他不为一般读者所注意是当然的,在目前的中国,这也是应该的吧。但就我所知,在作家们中间,受他影响的人也颇有几个。如:《画梦录》时代的何其芳、李广田。芦焚(师陀)似乎也受他很深的影响,他的《看人集》、《江湖集》中的某些作品,颇有一点阿左林的风味,而最近出版的《果园城记》,其中的《说书人》、《邮差先生》、《灯》等篇,与《西万提斯的未婚妻》中的几篇描写人物的散文,在风格和气氛上,更是非常相近了。
曾卓说话的时候是在1946年,这以后恐怕还要加上不少几个人物,其中重量级的要数汪曾祺。他写过一篇《阿索林是古怪的》,称“阿索林是我终生膜拜的作家”。显而易见,对阿索林着迷并深受其影响的主要是京派一路的作家。这派作家着力于表现乡土中国的村镇,意在重塑民族的性格,他们从阿索林那里得到了思想方法上的启示和感情上的共鸣,改变了在“五四”启蒙心态下对于较为单一的价值取向,同时在文体上也找到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榜样。
阿索林作品的中文译本只有薄薄的三册:《西万提斯的未婚妻》(戴望舒、徐霞村合译,上海神州国光社1930年3月版;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重印,易名为《西班牙小景》)、《阿左林小集》(卞之琳译,国民图书出版社1943年5月版,1980年代以后《西窗集》的修订本收有《阿左林小集》的全部译文)、《卡斯蒂利亚的花园》(徐曾惠、樊瑞华合译,作家出版社1988年10月版)。在中国,关于他的研究并不多,大约有近二十篇漫话式小品和研究性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