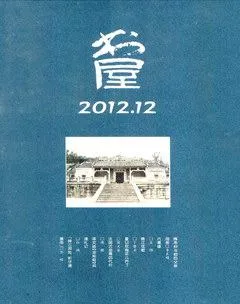法国式浪漫的代价
2010年4月《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法国存在主义作家波伏娃的女权主义名著《第二性》的书评,那是因为《第二性》问世六十年之后,美国才出版了一个未经删节的英文全译本。第一个英译本出版于1953年,出版商请了一位退休的动物学家帕旭雷(H.M.Parshley)为译者,出版商的妻子布朗茄·诺夫(Blanche Knopf)在一次去法国的商情侦探旅游中得知了这本书,印象中以为那是一本供高雅人士看的性爱手册。出版商对译者说,波伏娃好像患有“言语腹泻”症,所以,帕旭雷将九百七十二页的原著精简了百分之十五。
1946年波伏娃开始写作此书时,法国妇女获得选举权才不到一年。在天主教的法国,生育控制直到1967年都是非法的,对从事堕胎者的终结处罚是死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当充满女权主义极端怒火的《第二性》于1949年出版时,就连加缪这样的左派存在主义作家都抱怨说,波伏娃给法国人丢了脸。而梵蒂冈自然将其列入禁书之列,美国《大西洋月刊》的评论者则指责该书充斥了“存在主义的怒骂”。
波伏娃劈头便写下了她的名言:“女人并不是天生为女人,而是成长为一个女人的。”这正好是颠倒了关于贵族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培养成的“格言”。波伏娃控诉了女人在社会中的二等公民这一事实,举了生物学、生理学、人种学、人类学、神话学、民俗学、哲学和经济学的事例来佐证她的论点。在“已婚女人”一章中,波伏娃大量援引了弗吉妮亚·沃尔夫、科莱特、伊迪丝·瓦尔登,索菲亚·托尔斯泰等人的小说和日记;同时也考察了从斯汤达到D·H·劳伦斯等男性作家如何来再现女性形象的。然而波伏娃的偏激倾向体现在她对婚姻制度和母亲身份的偏执的敌意;从青春期到断经期的每一个女性生殖系统的方方面面都用了同样的恶言恶语加以抨击,诸如“母亲的奴役地位”,乳房喂养的“充分奴役性”,“女人荒唐的生殖力”等等词语,比比皆是。总之,在波伏娃看来,做女人是一种“诅咒”(Curse)。正是这种偏激,为《第二性》赢得了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中的经典名著地位。
书评作者格雷(Francine Du PlessixGray)的另一个说法倒使笔者吃了小小一惊。她说在波伏娃和萨特的不同寻常的伙伴关系中,萨特是更为循规蹈矩(The More Conventional)的一方!以前读了英国保守主义历史学家保尔·约翰逊《知识分子》一书,虽然知道约翰逊偏见重重,但仍然以为萨特的名气更响,是一个波德莱尔式的寻欢作乐的风流人(Dandy)。约翰逊说,波伏娃“这位杰出而意志坚强的女人几乎从他们第一次见面就成了萨特的奴隶,而且纵贯她的成年人生一直如此,直到他死。她成了他的情人,替代妻子,厨师和经理,女保镖和护士;而在他的整个一生中,她从来就没有得到过任何法律和经济上的地位”。看了格雷的文章,才知道约翰逊是在胡说,明明是萨特向波伏娃求婚,而被波伏娃拒绝了,并说萨特不要“太傻”了,而且波伏娃在萨特之外,也同美国作家尼尔森·阿尔格伦(Algren)有过热恋。不过在格雷看来,从六十年后的今天来看《第二性》一书,它的诸多偏激的论点已经过时了。那是因为在美国和欧洲,尽管在男女薪水平等上还有颇大的差距,但是妇女在就业和家庭婚姻中都有“性骚扰”法律的保护,社会舆论也倾向于男女的社会平等。
奇怪的是,虽然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大量引证了劳伦斯和沃尔芙等英国作家的众多作品,但是她却根本不提自己国家的诸多同胞作家的浪漫风流韵事,当然也就压根没有从这些风流韵事中看出女性在法国传统社会中占据着一种如何不利的地位:至少在拿破仑时期制定的法律条文中,女性如果被发现有婚外情,丈夫立即有权要求离婚,不然女方即面临牢狱之灾;而如果是男方发生婚外情,法律则是含混不清。法律不过是现在社会的写照。1892年,后来两次当上法国总理的左派政治家克里蒙梭尽管自己有过多次婚外情,然而一旦发现他的美国妻子也有婚外恋之后,则毫不犹豫地诉诸法律,让妻子在坐牢和被驱除出境之间做出选择。所以,波伏娃所说的“做女人是一种‘诅咒’”,在1949年的法国仍然是一种社会现实。法国最著名的作家文人的风流韵事也许是他们写作的灵感源泉,因而就像他们笔下的虚构故事一样惊心动魄,伤感婉丽,有时虽是两情缠绵婉恻,但从另一种文化的角度来看,则是百思不得其解。法国式浪漫的代价是女人成了社会中的二等公民。
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法国社会仍然处于一种历史性的转折期,旧体制中留下来的制度和习惯已经让位给新兴的平民制度,然而旧的习惯势力却仍然拥有巨大的力量;有时这种巨大的惯性力量恰恰体现在那些激烈批评旧势力的伟人身上。比如,维克多·雨果,爱弥尔·左拉,大仲马和小仲马以及古斯塔夫·罗丹都是法国当时批判旧势力的旗手,新时代的代言人和鼓吹手,其中雨果和左拉乃至被视为是“社会的良心”,至今他们和大仲马一起都显要地躺在巴黎左岸的先贤祠里。然而,如果我们来仔细体会一下他们那些风起云涌的婚外风流韵事,却会发现旧的文化势力的惯性依然主导着他们的行为和思想品味。在法国,任何婚外的性伴侣都称为情人(Mistress)。法国人还专门创造了一个“被包养的女人”(Femme Entretenue译成英文:Kept Woman)的特有用语,与中国人所说的“二奶”相当接近。小仲马的剧本《茶花女》和左拉的小说《娜娜》所描写的就是典型的“被包养的女人”。法国式的浪漫成了一种由社会的道德意识默认的潜规则:一个文化名人可以有多位情人,但是不会轻易与妻子离婚,也不会轻易离开旧情人。
1843年9月初,雨果刚刚过了不惑之年,已经发表了《东方之歌》(1829)等多部诗集和《死罪犯的最后一日》(1929)等小说。当年2月17日,十九岁的心爱长女丽奥波亭与雨果的最大的崇拜者的弟弟夏尔·瓦克雷(Charles Vacquerie)结成了伉俪。踌躇满志的雨果自7月中旬以来就携带着情人朱莉·德劳(Juliette Drouet)沿着卢瓦河一路度长假,当时正滞留在法国南部的西班牙边境。9月9日早晨,他在当地的一家咖啡店里读到了一则令他终生都痛心疾首的报道:三天之前,他的女儿与丈夫在塞纳河下游的一次私人游船活动中,不幸翻船身亡。道德意识强烈的雨果此后在一系列诗作中都表露了悔恨交加之情,乃至说这是“上帝对他的不忠行为的惩罚”。然而在其八十三岁的漫长生涯中,雨果有过数不清的情人,甚至他的妻妹朱丽(Julie)都是他的情人,不过直到1868年他的妻子阿黛尔·福榭(AdeleFoucher)去世,雨果始终是一位名利双收的体贴的丈夫。1881年2月26日是雨果的七十九岁生日,第三共和国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五十万人的游行队伍,由参议员们率领,紧接着一个五千人的音乐家方阵,奏着《马赛曲》,走过雨果所住的十六区迪亚劳大道(现在的雨果大道),向这位法国的文化偶像致敬,雨果则带着两个孙子在阳台上不断向游行队伍挥手,为时六个多小时;游行队伍从雨果的寓所一直走到市中心的香舍丽榭大道。到1885年5月22日雨果逝世,全巴黎的两百万人更是都参加了他的葬礼游行。雨果也是唯一的一位死后当即进入先贤祠安葬的文化大师。
以《茶花女》(1848)一剧出名的小仲马则是大仲马与一位服装师的私生子。只是《基督山伯爵》和《三个火枪手》的作者良心发现,在小仲马刚满七岁时就认领了这个儿子,从而有合法权利把儿子从母亲手中夺过来护养,送入上等的私立学校。大仲马因他的多部畅销著作是一个相当富有的名人,但是他喜欢给他所供养的情人送高档的礼物,所以总是入不敷出。特别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茶花女》的故事正是根据作者的亲身经历写成的:一位平民作家爱上的是一位特别喜欢白色茶花的青楼女子;作家的父亲得知之后,怕茶花女的名声影响儿子的前途,便在背后说服茶花女放弃她也心仪的作家。正是因为这段刻骨铭心的伤感经历以及私生子的身份,小仲马曾多次著文激烈反对家庭不忠。然而他的结发妻子当时却是一位俄国的有夫之妇娜德佳达·纳里施金(Nadejda Naryschkine),在与她经历了多年的私密恋爱之后,终于在1864年她的丈夫去世之后,小仲马与娜德佳达结成了百年之好。娜德佳达是公主出身,任性而疯狂;在他们未婚之前就生下了小仲马的女儿柯莱,当时只说是领养的孤儿。等到结婚之后,娜德佳达经历了两次流产,又生下一个儿子之后,脾气变得更加乖戾,从冷淡到极端的嫉妒。然而小仲马在他的浪漫婚姻出现裂痕之时,却先后又投入到了三位情人的怀抱之中。一位是比他小几十岁的亨丽特·艾斯卡利(Henriette Escalier),另一位是可爱的演员爱弥·德斯克利(Aimee Desclee),还有一位是美丽的奥梯丽·福拉豪(Ottilie Flahault)。后两位不太在乎小仲马的婚姻,那位年轻的亨丽特却始终念叨着何时能够与他结成名正言顺的伉俪。然而像所有法国看重婚姻却又风流倜傥的文化名人一样,小仲马一直等到发妻1895年4月去世之后,才于同年5月同亨丽特正式结成夫妇。当时他已经是七十二岁,到12月便撒手人寰了,弄得小仲马的女儿柯莱愤愤不平地冲着后母说,“你是否冲着钱财才与我父亲结婚?”
美丽时代的另一位文化大师爱弥尔·左拉自从1883年出版了《娜娜》一书之后,已是法国文坛家喻户晓的小说家,他的二十多卷的长篇社会史系列小说《罗根-马奎家族史》到八十年代末也几乎快写完了。迫近于知命之年的左拉与太太阿丽克山珏结婚已有二十多年,尽管多次咨询过医生,但却始终没有孩子。左拉只能无奈地说:“我的作品即是我们的孩子。”因为他太太年轻时曾有过一个女儿,出生之后便送给了孤儿院,所以问题很可能是在他身上。1888年左右左拉太太找了一位高挑而秀丽的杰妮·罗泽(Jeanne Rozerot)做家里的女佣;杰妮很早就失去了母亲,左拉太太感到她很像自己早年丢失的女儿。到1991年11月,左拉太太霍然接到一封匿名信,透露说:“现住圣拉泽尔路66号的杰妮·罗泽夫人生下了两个你丈夫的孩子。”就在同一天,左拉在晕头转向之中给一位好友发电报说:“我妻子绝对是要发疯了。我很怕会有一场大灾难。你能够到圣拉泽尔路去一次,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吗?请原谅我。”后来左拉太太又得知,大的女儿取名丹妮丝,小的儿子名叫杰克。左拉毕竟是一个文雅的君子,至少在两年里,嫉妒得发疯的妻子一直对着他尖叫,他只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两年之后左拉还含着泪水,对好友评论家达德(Daudet)说:他常常“害怕他妻子会谋杀他的情人和他的两个孩子,看见他们的血溅满了他一身”。然而到九十年代中期,人们则会看到左拉带着他的情人和两个孩子在卢浮宫附近的杜乐丽花园里散步,仿佛一切都已归于平静;左拉太太也依然掌管着府上的家务。1898年1月,左拉为“德雷福斯事件”挺身而出写了致总统公开信“我控诉”一文,随后他受到政府迫害不得不逃往伦敦避难,几个月后左拉太太赶到伦敦看望丈夫。1902年,左拉终因“德雷福斯案件”在巴黎寓所被杀手堵住烟囱,因煤气中毒而死,住在同一屋檐下的太太则侥幸被抢救了过来。
《第二性》一书在中国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出了中译本,至于它在中国女权主义者中有多大影响,那就只有天知道了。九十年代前还能听到演员刘晓庆“做人难,做女人更难”那样的叹苦经,笔者孤陋寡闻,现在这样的感叹恐怕早已被“淘金热”的故事所淹没了。最能显示社会人心的,其实是那些用来描叙女性的语言的演化。比如在当今中国大陆,那些芳龄在三十以上还没有找到对象结婚的能干女子被毫不客气的称之为“剩女”。《新民周刊》用“平常心”描述了当前中国的“剩女焦虑症”,并说:“有调查显示,六成人认为‘剩女’只是被婚姻剩。除了没有婚姻,她们在其他方面往往都很优秀,这些‘三高女性’(年龄高、学历高、收入高)的人生虽不完整但可能很精彩,而消费是许多剩女的一大乐趣。”而四十岁以上仍没有成家的女性则被冠以“熟女”的标签。据说“熟女”一说来自于日本的A级片;所谓“熟女不仅仅是性成熟。真正的熟女应该拥有独立的经济、相对成功的事业、丰富的人生阅历”。又据说,“熟女往往还有个坏毛病,那就是喜欢教导别人,因为熟女的阅历丰富,自以为什么都经历过了,往往喜欢对男人指手划脚”。更为可笑,也更为可悲的是,那些离了婚还没有找到新男人的女人,居然自我嘲讽般的自称是“败犬”或“犬女”,言下之意,大概也是来自于孔子自嘲般地自称为“丧家之犬”。毫无疑问,这些言语上对女性的渺称不仅仅显示了对女性的不尊重,同时它们也反映了当今女性在现实社会中的实际地位。
再回到波伏娃的《第二性》一书。它在中国恐怕也已经过时了,那倒不是因为它所呼喊的女权在中国已经实现了,而是因为中国的文化基因与西方的差别太大。某些西方女性要争取的自由,在中国由于国情却是不在话下的。比如中国女性唯一超过法国女性的自由,是对自己身体的控制,要什么时候堕胎都是自由的,而在天主教的法国,堕胎至少会受到舆论的谴责。同样,这也是由于中西文化基因的不同而造成的。正如英国现代诗人艾略特说的,个人在文化势力面前实在是太渺小了。中国女性在走向男女社会平等的道路上,也依然是“路迢迢其远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