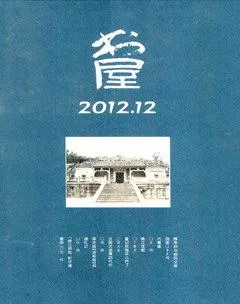锦江弦歌
威尔基的讲演
1942年10月2日,我还是成都光华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二年级的学生,我和同班的两个挚友从大学部得知消息,美国共和党的威尔基(Wendell Werekie)与已三次连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竞选失败后,就被罗斯福派为特使,访问英国、苏联和中国等反德、意、日法西斯主义的同盟国。那两天威尔基来到成都,下榻于有名的“华西坝”,这是华西协和大学、金陵男大和女大、齐鲁大学这四个外国教会在中国办的大学所在地。它在成都南面近郊,紧靠着成都市内。威尔基讲演的会场就在“华西坝”的足球场的草坪上,坪上临时搭了一个木板台。我们三人从成都西郊光华大学所在地,有十里之遥的“光华村”骑自行车赶去了。
我们到达会场不久,约有三百多的燕大学生举着“燕”字校旗从城内陕西街燕大校本部整队到来了。这个新在成都复校的大学的师生的到来,立刻受到华西坝几所大学的学生的很热烈鼓掌欢迎。
威尔基快步到场了,他穿着咖啡色西服,陪同他到场的有新任成都燕大的代理校长梅贻宝博士,他穿着深灰色中式布长衫,被公推为这次威尔基讲演的翻译。威尔基讲演很有风趣、幽默,梅校长的翻译也非常流利、通畅。威尔基讲演一开头就说:“今天,我能向这么多的大学生讲话,我感到很高兴,尤其是由中国很有名的大学校长为我讲话作翻译,我更感到非常荣幸。”
当时会场出现了一个情况是,威尔基讲完一段话后,其他各校到场的学生在等着梅校长翻译成中文之际,在燕大的学生群中马上响起了很热烈的掌声和大笑声,而其他学校的到会的学生却等到听完了梅校长的翻译后才有反应。
在此之前,我虽然也知道燕大是很有名的大学,但我这次却亲身感受到了,燕大办得好,学生的英语水平很高。
我考入成都燕大
解放前,全国各大学都是在暑假才招考新生,但不是全国大学统一招考,而是由一个大学一个大学地分别招考或由三四个大学联合招考,所以那时的高中毕业生要多次参加大学的考试,往往是一个高中毕业生会考取好几个大学,最后上的都是自己很想上的大学。
1942年秋,燕大内迁到成都复校了,全校共有学生三百多人,其中有从北平赶来的恢复学业的学生一百五十多人,另外还从抗战大后方招考了新生一百多名,全校大约有三百多学生。但1943年后,成都在附近双流等县扩建了飞机场,来了许多架美国“B29”的有五个机头的巨型轰炸机,以便更能轰炸东京等日本城市和日本侵占我国的城池,因此就急需熟悉英语的翻译,而燕大就有二十多个学生出于反法西斯的爱国热忱去充当了美空军的翻译。1944年冬,日寇为作垂危挣扎,又大举进攻河南、湖北、湖南及广西桂林等城市,一直攻占了邻近的贵州独山城。眼见抗战大后方的四川岌岌可危了,我大后方爱国青年学生为了救1EXOxSFXgr4xflJGV+2K/A==亡,都表示要“投笔从戎”去参加抗战,而国民党政府当局也借此动员青年参军,他们发出了“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许多爱国青年学生都纷纷响应。而燕大又有多个学生去参军当翻译了。鉴于学生人数的又突然减少,成都的燕大即破例在1944年寒假招考新生了。
我是在1944年冬季从成都光华大学附属中学高中毕业的,我希望上大学,继续深造,于是利用寒假,好好温习功课。成都燕大破例要在寒假就招考新生的讯息传来,我和同伴毕业的挚友江璞、薛孔礼(后改名为薛辉)都去报考了。江、薛二兄报考的是物理系和数学系,我报考的是法学院的政治系。
我报考了成都燕大的政治系,是有主客观原因的,第一,我父亲一直是个科级公务员,抗日战争前,他还能靠工薪维持生活。抗战发生后,物价不断上涨,他膝下有四个子女,我居长,大妹妹是中学生,年纪较小的弟、妹也都上学了,我父亲负担加重,遂入不敷出,生活日益困难。但我的两位伯父都是四川有名的银行家,尤其是我的第二个伯父,更重视栽培我们这大家庭中求上进的子弟。他见我勤奋好学,成绩好,上初中了,就很爽快地提出,要担负我全部的学费和生活费。上世纪三十年代末,他从重庆迁回成都居住,干脆让我住到他宽敞的家里。他很爱我,很希望我上大学的经济系,将来好接他的班,但我却对文史科很有兴趣。他却担心我成为生活清苦的教员,他不大赞成,为了不辜负他的殷切厚望,我只好折中,报考了也多有应用性的政治系。
第二,我也上了由上海内迁到成都的光华大学附属中学,为时约有六年,但是也由于物价飞涨生活困难,大学部的教师多兼任中学部的教员。比如,我在初中时的国文和历史的教师都是大学部的教员兼职的,他们教课都很好,特别是历史课的老师,曾宪楷是曾国藩的曾孙女,她学问渊博,她给我们讲清代史,从康、雍、乾盛世直到嘉庆、道光的衰败,丧权辱国,讲课既很简明扼要又很生动具体,使我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我上光华附中高中后,英文课老师徐复君也教得好。他是江苏人,上海“圣约翰大学”生物系毕业,当年他既在成都光华大学执教,也在我们中学部教英语他讲的英语是很标准的伦敦音,使我们受到很好的英语发音训练。他采用的教材都是西方学古典文学名著,如莎士比亚的戏剧代表作,英国名作家王尔德的《快乐王子》等著名寓言和法国作家莫泊桑的著名小说《项链》等。在他的谆谆教诲下,我们的英语水平更大有进步。这样,使我又愿意考入大学的文史科。
第三,我报考成都燕大的政治系,更重要的是盼望师事学术大师萧公权。萧先生是早年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学生。1926年,他留学美国,在美国名校康奈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即回到清华大学任教授,并专治政治思想史,成为这方面的权威教授。他是江西泰和县人,清末其父久任为邻近成都的崇庆县的“教谕”(主管县教学),遂有他的很多家人留居该县。抗日战争发生,萧先生乃携家回到成都,在成都光华大学和四川大学任教,并家居成都光华大学内的教授住宅区内。萧先生学贯中西,德高望重,很受抗战大后方学术教育界人士的尊崇。其内侄薛孔礼是我的同班知交,他的儿子和两位女儿也在光华附中上学,我们也有往来,我因此常到他们的家向萧先生请教,而萧先生也很和蔼可亲,对我的学习多有指点。
萧先生学问大,但生活简朴,他只“士”而不“仕”,不求做官发财,但很关心时局,讲求民主自由,他成为我学习的榜样。燕大在成都复校后则特聘他到政治系执教。我因此更盼望考入成都燕大。
成都燕大代理校长梅贻宝博士曾撰写有重要的回忆文章《记成都燕京大学》,文章告诉我们燕大在1942年复校后,首次招考新生,仅在成都和重庆两地报名投考的学生竟逾三千多人,而该校招取的学生也一贯采取少而精的原则,以求燕大好的传统精神的保全与传承。此次录取的新生也不到一百人。1944年寒假燕大破例的招考新生,仅成都一地的投考生就有一千五百以上,但这次只录取了五十来人。
我还依稀记得,那天考场是在“华西坝”,考生坐满了几个教室,我报考的是文法科,虽然要考理科,而试题却比较浅显易答,但国文和英文的试题却有很大的难度。国文除要求写一篇自传外,还有很多有关中国文学史上的难题须作出解答。而英文的考卷一发下来,就使我们考生都很惊讶结舌,考卷有好几大张考题,真是“五花八门”,有英文译成中文的,还有中译英的,另外还有许多问答题、填充题、改错题,考试时间同样都是两小时。我始终埋头赶答,考试时间已经到了,我才勉强交卷。
我这次考成都燕大以后,好多天都忐忑不安,担心自己能否被录取,我的伯母请一位与成都燕大有联系的人去打听我的考试成绩。多天以后,有了回音说:数理科和英语的考试成绩都及格了,国文考得最好,成绩已近九十分,一定会被录取。几天以后,成都燕大在陕西街校本部发录取的新生榜了,录取的五十多位新生,理科的录取生约占三分之一,其余则是文法学院录取生,而这当中,由于新闻系的考生最多,所以新闻系录取生也多达十余人,而我在十多名法学院的录取生中竟名列第二,江、薛两兄也考取成都燕大的理学院。我家的长辈都为我考取了燕大而感到高兴,我的一位姑父是原北平辅仁大学毕业生,他特别表示庆贺。他说:“燕大也和当年的北大、清华一样,是很难考取的著名大学。这孩子考上了,实在是喜事。”我父亲曾在北平上过学的同事也向我父亲表示祝贺说:“令郎能考上燕大,真是令人高兴的事。我有几位朋友,从燕大新闻系毕业不久,就因为在大报上多写出好文章,现在已成为很有名的记者。”
很重要的历史抉择
1945年春,我与江、薛两兄都入学成都燕大了,我因此才多了解到燕大许多重要的历史情况。
燕大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燕大的校歌也有很多名句表达其办学宗旨,如:“良师益友如琢如磨,情志每相同。踊跃奋进,探求真理,自由生活丰。”“人才辈出,服务同群,为国效荩忠。”这校训和校歌都是1919年司徒雷登接管新建立的燕大后制定的。他一再声称,办燕大,绝不是为培养基督教神职人员,而是要为中国造就多方面现代化的人才。后来久任燕大校长的大学者陆志苇也着重指出,办燕大是用美国出的钱,但它是在为中国培育人才。因此,燕大就富有勤奋为学,十分爱国爱民的好传统,好校风。
从鸦片战争起,我国即遭受列强的侵凌,尤其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日本更侵占了我东北三省,进而企图霸占我国华北等地。“华北之大,已难安下平静的书桌”。而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对中国很有感情的司徒雷登就能与中国爱国的青年学生同呼吸,他一贯同情并大力支持了这些爱国学生运动。1935年,中日《何梅协定》签订时,司徒雷登已预见到平、津处境危险,为此他开始考虑燕大的去留。“卢沟桥事变”发生,平、津失守,北大、清华等校决定南迁抗日大后方,而燕大司徒雷登虽然经过反复权衡,选择了留守,但迫于内外压力,他仍然怀疑留守北平是否得当。比如毕业于燕大社会系本科、后为清华大学的研究生、进而留学于英国的费孝通就致函司徒雷登,强调指出了燕大留守北平的决定是违背了中国政府关于阻止日本势力在中国生根的原则,日伪政权将利用此事鼓吹中日友好,从而葬送燕大的美名。
已经是1938年6月了,司徒雷登对燕大是否留守北平的问题还在摇摆不定时,他的好友高厚德的一席话却打动了他,使他做出燕大留守北平的最后决定。高厚德说得好:燕大的最高理想是为中国人民服务,而不是单纯为某个政治势力服务。在人类生活中有许多基本关系,政治关系只是其中的一种。所以燕大必须在沦陷区坚持下来,为沦陷区人们提供受教育的机会。高厚德还举例说:当年耶稣并没有设法逃出古罗马人的统治,而是在压迫中继续他的事业和使命。
司徒雷登对这意见深以为然,他也认为反抗未必都是明火执仗上前线,就地反抗也是一种反抗,而且是一种更坚韧、更无畏的反抗。
他决定燕大继续留在北平办学,这也很快成为燕大师生的共识、信念。
北中国的沙漠中的孤岛绿洲
抗日战争发生后,中国的教育机构,如北大、清华、南开等著名大学,包括天津南开中学都内迁到抗战大后方,在这样的情况下,沦陷区的学生,要么不上学,要么被迫进入日伪控制的学校,接受奴化教育。本来只有这种两难选择的陷区学子,因燕大还坚持在北平办学就有很好的新的出路。
正如有人确切记述所说,为最大限度地满足沦陷区学子的需要,燕大招生规模急剧扩张。以前燕大每年录取的新生约百人左右,但1938年秋,抗日战争发生后,当年秋季入学的新生就有六百零五人,为历年录取新生最多的一次,到1941年秋季开学,燕大学生人数竟由七、八百人达到了创纪录的一千一百七十八人。当年到北平燕大上学的不仅只是华北学子,还有许多学子是来自已经沦陷于日寇的江南地区的学子,他们多是成绩优秀的高中毕业生。因此,燕大学生质量没有降低,反而更有所提高。也因为如此,燕大校园更洋溢着抗日的爱国气氛,遂成为北中国的一大抗日阵地、沙漠中的孤岛绿洲,涌现出众多的可歌可泣的事迹。
司徒雷登是1919年来北平任燕大校长的。但1927年以后,国民党政府规定,凡是大学校长,包括外国教会在中国办的大学,都须由中国人担任校长之职。司徒雷登虽然为燕大最主要的主持人,则改名称为“校务长”。抗日战争时期,燕大还坚持在北平办学,司徒雷登遂再任校长,燕大校园还挂出了美国旗帜,表明这是美国办的学校,禁止日军入校,在这特殊情况下,燕大师生还可以开会研讨国际形势、抗战时局,听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英语电台广播;甚至偷听抗战大后方和延安的电台广播。
燕大作为沦陷于北中国的一大抗日中心,也是大批输送爱国人才给抗战大后方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一大基地。当时具体负责人是司徒雷登的重要助手,美国教授夏仁德博士(Dr.Randolph C.sailer)和燕京研究院毕业生侯仁之,他们都是燕大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一般大学则是“学生训导处”)主持人,但后面的主管者则是司徒雷登。侯仁之说,司徒雷登曾有明确的指示:燕大校方愿承担这些去抗日大后方或抗日根据地的全部费用。“凡是要走的学生,临行前他都要在临湖轩(他的住处)设宴践行”。在这践行会上,司徒雷登还说:他希望燕大学生无论是到大后方还是到敌后根据地,都要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起到桥梁作用,以加强合作,共同抗日。据统计,抗战爆发后,燕大有两百多个学生去了延安等抗日根据地。
司徒雷登在抗战期间还常常顶住日本占领当局的巨大压力。比如有一天日本宪兵来到燕大西校门前,蛮横地要求须搜查学生宿舍,抓一个共产党员。司徒雷登则强硬拒绝,声称:燕大是美国人办的学校,受到治外法权的保护,任何外国人要进入燕大校内搜捕学生,都必须得到美国驻北平领事馆的批准。由于司徒雷登寸步不让,日伪当局从此不敢再来找燕大学生的麻烦,只好在校外抓捕燕大抗日的学生。日伪占领者也在沦陷区大力推行奴化教育,他们借口增进中日文化交流,要派“日本教授”来燕大任教。司徒雷登也顽强抵制,表示燕大宁可关门,也不能牺牲学校的独立性。但燕大并不反对美国“哈佛燕京学社”等处推荐来校执教的蜚声国际的日本大学者。日本很著名的考古学家鸟居龙藏因此来燕大工作了。他反对侵略中国,埋头治学,指导中国学生的研究的工作,而绝不与日伪占领当局合作。1941年12月,日美开战,燕大被日寇占领关门后,他“拒不食周粟”,宁肯让两个女儿打工以勉强维持生计。日寇占领当局明令出版禁用英文写的著作,他仍以“哈佛燕京学社”的名义出版自己英文著作《辽代画像石墓》,而且该书的序言竟然是已成日寇阶下囚的司徒雷登写的。
在日本占领北平期间,燕大办学经费很困难,一位日本高级军官去见司徒雷登,询问燕大是否可以接受日本有关方面的一笔可观的办学补助金,司徒雷登也一口拒绝。
一天,燕大校园里还发现了一枚炸弹,司徒雷登相信这是日寇用来恐吓他的,他也宣称:“我宁叫日本人像炸南开大学一样把燕大炸掉,也绝不会同日寇合作来贻我们全体学生之羞。”
陆志苇的刺刀下的演说
燕大有两人最受司徒雷登的尊重和信任,一位是前面已讲到的美国教授夏仁德博士,一位也是留学美国著名的心理学、语言学家陆志苇博士。1926年,司徒雷登路过南京,见到陆志苇,他们一见如故,志趣相合。翌年,陆志苇即举家北上,出任燕大教授、心理学系主任,1933年,又继任燕大校长。抗战开始后,司徒雷登又再直接用“校长”之名。但陆志苇仍在校领导的决策层内。
陆志苇也很爱国、耿直。1940年,燕大物理系助教冯树功骑自行车经过西直门外白石桥时,被一辆横冲直撞的日本军车碾死。燕大校方即向日占领军当局提出书面抗议,并在燕园贝公楼大礼堂召开了追悼大会,追悼会由陆志苇主持,他悲痛地走上讲台,声音嘶哑地说:“我……我讲不出话了。”这时他以捶胸说:“我这里好像有一块大石头,压得我喘不出气来!我只觉得当今世界上弥漫着一股貌似强大的势力,正控制着我们,压迫着我们,正是这股势力夺走了年纪轻轻冯先生的生命。这股势力一日不消失,类似的悲剧肯定还会不断发生……”讲到这里,他喉头硬塞,泪水长流。人群中很多人在饮泣,随即爆发出一片嚎啕大哭。
这时在场的日本军方面代表表现十分不快,拂袖而去。
外国友好人士的热情支援
同白求恩一样,燕大也出现了积极支持参加中国抗战的外国友好人士。除美国教授夏仁德外,还有一人值得介绍,其人叫林迈可(Michael linlday),1909年出生于英国,后入牛津大学,获得了政治学、哲学、经济学的硕士学位。毕业以后,1937年12月,他应聘到燕大创办导师制并任导师。想不到他在来华途中与同船的诺尔曼·白求恩相遇并成了好朋友。来燕大后,他住进了司徒雷登的寓所燕大临湖轩,收了八名实行导师制学生,其中唯一的女生李效黎后来成了他的妻子。他来华后,了解到许多我八路军艰苦抗日的情况,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他利用日寇不好多限制英美人的活动,多次去了我抗日根据地。他先去冀中,受到冀中军民的热烈欢迎,再去晋察冀边区,在聂荣臻的五台山司令部见到他的好友白求恩,详细了解到我八路军很缺乏药品和通讯器材后,遂决定在这些方面给予支援。他回到燕大后,就与我地下工作人员取得联系,设法把药品、通讯器材送到抗日根据地去,他从我抗日根据地带回了一些抗日的宣传品和资料,就请他的学生李效黎翻译成英文,请英国很著名的《泰晤士报》、《卫报》登载,大力揭露了日本鬼子在中国的暴行和中国军民抗日的英勇、艰苦情况。
1942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事件发生,翌晨,日本宪兵正要进校逮捕他们夫妇时,他俩已先从收音机广播得知美日开战的消息。他们遂偕也是燕大教授的班威廉夫妇乘了司徒雷登的小卧车疾驰到西山抗日游击区,与我抗日部队联系上了,他们更直接加入我抗日战争的行列。林迈可当了聂荣臻的技术顾问。在他的帮助下,晋察冀边区抗日司令部队装上了不少老笨重的发报机,训练了许多机务人员。而李效黎则随他做了翻译工作。1944年夏,他们到了延安,受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热情接待,并委以重任。林迈可任我十八集团军第三局通讯组顾问及新华社英语顾问。李效黎则一直做他的随身翻译。
日寇的“眼中钉,肉中刺”
燕大在抗战爆发后,仍坚持在北平办学,燕大的爱国师生,包括司徒雷登为首的许多对中国友好的英美友好人士都奋不顾身地积极地不断开展抗日活动,这样,日寇即把燕大这些师生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珍珠港事变发生,日美宣战后,翌日,日军即占领了燕园,解散了燕大。司徒雷登被拘捕、软禁了,二十多位燕大教授,其中有陆志苇、张东荪、洪业(煨莲)、邓之诚等大学者,还有在燕大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的主要成员燕大研究院的毕业生侯仁之都被捕了,起先关在沙滩北大地下室,很快即投入日军的监牢。这些爱国志士都表现出英勇不屈,即使被监狱日寇拷问、凌辱、殴打也勇于对抗,他们都有很强烈的爱国情操。
对燕大的英美籍的教授,如夏仁德等则都被送到山东潍坊日寇的集中营拘禁。而学生则一般遣散离校回家。如林则徐的五世孙,1941年秋入学燕大、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出任我驻美国纽约的联合国大使凌青(原名林墨卿)学长就写有一篇回忆录,文题为《难忘的“十二月八日”》,记述燕大学生被遣散回家离校的情况:1941年12月8日,日寇占领燕园,解散燕大,一般学生都被赶出学校。过了一天,北平伪政府为了表示其“美意”,特别让这些学生回燕园取回自己的私人行李。而令人愤恨的一幕发生了:“当同学们排队,带着自己的行李,依次登记,准备走出校门时,一个日本兵突然从队伍中把一个同学拉了出来,说他动作慢了,就把他戴的眼镜一把抓下,扔在地上,同时左右两个嘴巴打过去,清脆的“拍拍”声音震惊了每个排队的同学的心。日本兵一边打一边大声喊着:“美国人在太平洋上大大地不行了……”他们以为我们这些学生肯定都是“亲美派”,但没有想到,这只会更加激发中国青年的爱国热情。现在校友们回忆起来,都表示对这一幕无法忘怀,亡国奴万万当不得,当了,就准备随时遭遇难以承受的侮辱和迫害。
于是,凌青学长当年很快就去了延安,投身于抗日斗争前列。
燕大在成都复校了
1941年12月,北平燕园被日寇占领,燕大被解散,很多人都没想到不到一年,燕大就在成都复校开学了。
事情也很凑巧,1942年10月7日,燕大在成都复校开学,也正是美国特使威尔基在出访反法西斯同盟国之后,也来到中国,以加强同盟国之间的团结,威尔基由重庆转到成都,也在这一天在成都华西坝向许多大学生发表了很好的讲演。当时许多重要的报纸都做了报导,说燕大在成都复校开学了,所以燕大就把这一天看作是成都开学的纪念日,匆忙间燕大就没有另外什么纪念活动。直到翌年这一天,燕大才隆重地举行了在成都复校一周年的典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