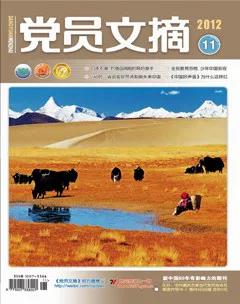哪怕只剩下一个读者,我也要这样写
“博士大还是县长大?”七年前,在莫言被授予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时,得知喜讯的父亲曾这样问他。如今,莫言获得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不知道父亲会作何感想。
2005年12月,莫言在接受荣誉博士学位时发表演讲,回顾了自己的创作生涯,那个在高密山头放牛的“炮孩子”,是如何成长为一个世界知名的作家。今天,回过头再去听听他的自述,你也许会更了解他。作为作家,莫言对文学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认识。
写作冲着一天三顿饺子开始
1957年,我家来了个大学生邻居。他讲,当年他在济南时,认识一个山东省比较“腐败”的作家,一天三顿都可以吃饺子。我们当时一年也吃不上一次饺子。
所以,我想我最初对文学对当作家的梦想,就是冲着一天三顿都可以吃饺子开始的。
后来,我把村里的书借来看了以后,才真正有了关于文学的概念。在我们村子里,有《三国演义》、《聊斋志异》、《隋唐演义》等几种古典章回体小说。
我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比如帮别人干活,跟别人换东西什么的,把村里的这几本小说都看完了。当时我以为我已经把天下所有的书都读完了。
笔名“莫言”
和喜欢讲真话有关
我从小就是一个非常爱说话的孩子,在我们农村把这种孩子叫做“炮孩子”。后来我写了小说叫《四十一炮》,里面就有一个“炮孩子”,其中也有我个人的经历。也因为我喜欢说话,喜欢说真话,给我们家里带来了很多麻烦。
所以过了几十年以后,当我要写小说准备发表时,使用的笔名叫“莫言”,就是告诫自己要少说话。事实证明,我一句话也没有少说,而且经常在一些特别庄严的场合,说出实话来。
我觉得讲真话毫无疑问是一个作家宝贵的素质。如果一个作家讲假话,不但对社会无益,也会大大影响其文学作品的品格。因为好的文学作品,肯定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在里边,尤其是真实地反映了下层人民群众的生活面貌。
我的很多小说一旦发表以后,有些读者不高兴,因为我把有些黑暗暴露得太彻底。当然我不会迎合这样的读者,而牺牲自己文学创作的原则。在我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后记里,最后一句话就是说“哪怕只剩下一个读者,我也要这样写”。
中国文学如何跟世界对话?
中国文学真正能够跟世界对话,真正超越了狭隘的阶级观念,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的。这时候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在大量阅读翻译过来的西方小说。这大大开阔了这批中国小说家的眼界。
我上世纪80年代的几个作品带着很浓重的模仿外国文学的痕迹,譬如《金发婴儿》和《球状闪电》。到了《红高粱》这个阶段,我就明确地意识到必须逃离西方文学的影响,一定要写自己的东西,自己熟悉的东西。
这就需要到民间去寻找,真正丰富的文学资源还是隐藏在民间。当然我说的民间并不仅仅是荒凉的偏僻的农村,城市也是民间。这才有了《檀香刑》和《生死疲劳》。
所以包括我个人在内,中国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实际上是借助了这两种力量。我们借助了翻译过来的西方小说,对我们自己的文学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然后又从民间寻找到丰富的资源,这才有了当今中国小说的现状。
有的人为了获奖,将作品特意贴上中国标签。什么是中国标签,我不知道。我在《檀香刑》后记里面说,我想在语言上有自己的特色,根本不是想写给外国翻译家看。
一个作家不可能把自己的写作追求限定在一个什么奖上,也没听说哪一个作家为了得什么奖而调整了自己写作的方向,改变了自己写作的方法。而且,即便你想改变,变得了吗?
该怎么写,还怎么写;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在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是懦夫,是可怜虫,但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
(摘自《钱江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