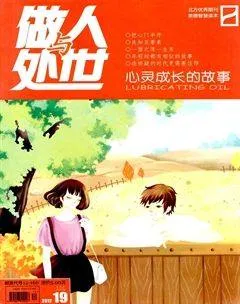白衣飘飘的年代
记得台湾导演侯孝贤说:“生命中有许多吉光片羽,无从名之,难以归类,也不能构成什么重要意义,但它们就是在我心中萦绕不去。”大学时光对我而言,就像散落一地的吉光片羽,虽然段落零散跳跃,但我依然悉心收集,认真整理。这些美好的光阴,似乎轻轻一吹就能融化在空气里,但夜深人静之时却足够让你欢笑流泪。
身在中文系久了,似乎每个人身上都能嗅出书卷气。一群文艺青年聚集于此,自然极具乐趣。课堂上,听师长口若悬河地讲起文学史,那份台上的神采飞扬和台下的兴致勃勃遥相呼应,闪烁出睿智的光芒;课下读世界文学,在新年钟声敲响之际骄傲地宣称2012年的第一秒是果戈理陪我一起。就连平日八卦也都会讲陆小曼林徽因的情事,为三毛与荷西的爱伤感,然后整个寝室一同叹息。
回想过去的几年,最精彩的要数课堂上的师生互动,最留恋的也是各位老师的音容。记得爱穿白衬衫的系主任,总是吓唬我们会挂科的郭郭,每每课前都必须登上校园的小山锻炼的有恒老师……在他们的讲授下,我们讶异于金庸、穆旦与徐志摩的“亲密关系”,逐渐了解了书法与篆刻,感叹霍小玉的敢爱敢恨,为阿喀琉斯之死无可奈何……中文系的课程永远正统庄严却又生动,治学方式始终恣意随性又包容。我们私下里流传着一句乌托邦式的口号:“融化在文学与青春之中。”读书、写字、看电影、摄影……文艺的元素便犹如一条长链,永无止境,意味隽永。
“小鹿,活动经费表格做好了吗?”“学姐,这是各个学院上交的征文。”“明天下午3点到会议室开会。”我一一应答着,有条不紊地处理着接踵而来的事情,活动前繁复的前期准备工作,对我而言已经驾轻就熟。
已经走过的大学岁月中,最值得怀念的便是参与社团活动的点点滴滴。在这个镁光灯追逐的舞台中央,所有才华横溢之士都能一展风采。于是,当其他同学在寝室里上网冲浪,在被窝里大睡特睡时,我与伙伴们商量着招新的事宜,迎着寒风去拉赞助,为校刊审核稿件,冥思苦想着下期文化沙龙的主题。从大一时的freshman蜕变成整个部门的领导者,其中付出的艰辛恐怕只有自己知道。我曾写策划书至凌晨3点,清晨6点在火车站拍摄春运照片,做暑期图书馆志愿者,组织电影书籍专题讨论……这些日子既忙碌又充实,虽然辛苦但极具成就感。某天寝室卧谈会,当同学们在恐惧未来工作与人际关系的时候,自己大一时可笑的神情一下子出现在眼前。我忽然发现,那个满脸青涩、冒失粗心、在人前说话甚至会语无伦次的孩子,在参加了形形色色的实践活动之后,不再幼稚与迷茫,她已逐渐学会了坚持和沉静、谦和与理解,她做事更加细致,面对挫折更有底气,解决问题更具信心。
如果要我说出一所大学的灵魂所在,图书馆无疑是首选。三年里的无数个午后,每当我置身它的怀抱,始终都感到平静而安心。在繁杂的表格、喧闹的课外活动之余,关掉手机,信步走进某个阅览室,徜徉在排排书架之间,便犹如走入了一个无人的岛屿。指尖流连触碰到的是曹雪芹、林清玄、汪曾祺……多少次,我沉醉于安娜迷人的眼,为柳生哀怨的神情静默,读《红楼梦》时整个人仿佛都清澈明净,而读《水浒》时又豪放如男儿。合上书页,天马行空的思绪便满世界地跳跃。此刻,阳光斜斜地照在脸上,半圆形的窗子将整个房间都反射得温暖明亮,加上这满室的原木清香,多少似水光阴也都变成了匆匆一瞥。说来可笑,我心底最纯净的初恋,便是图书馆的邂逅。也许无须开始或是结局,只要捧着书,默契地相视一笑,这个尘封多年的愿望就算是达到最无上的圆满。当然不管怎样,这栋有着孔雀蓝屋顶和哥特式钟楼的建筑,都注定成了白衣飘飘年代最唯美的回忆。
凤凰花花开花落,校园里又响起了熟悉的毕业歌。我知道终将有一天,自己将离开这里走向另一个开端,可是对于学校的怀恋却不会随时间的打磨而削减。不在学校的日子里,我常常会想起它开阔的胸怀,想起它在对待学术和恋爱上所表现出的一视同仁:想起它自由包容,任由学子们以自己的方式翱翔天空;想起它无声的美好,那份纯美往往不经意之间让你动容——记得一次清晨读书,在绿树和鸟鸣之间,我忽然真切地感受到象牙塔所独有的静谧,那时候胸中充溢的感动无法言说,只是知道世间再不会有如此纯净的微风。
去年夏天的尾巴上,我为学校拍摄了一组照片,算是真实的记录,也是纪念。镜头里飘扬的鸢尾花、鲜艳的红王子锦、悠闲晒太阳的小猫、树下三三两两看书的同学……无一不展示着独有的魅力。我为这组照片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用的是莎士比亚的诗句:我可否将你比作一个夏日。想了想,又在心里默念,可你却比夏日更加可爱温存。
编辑 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