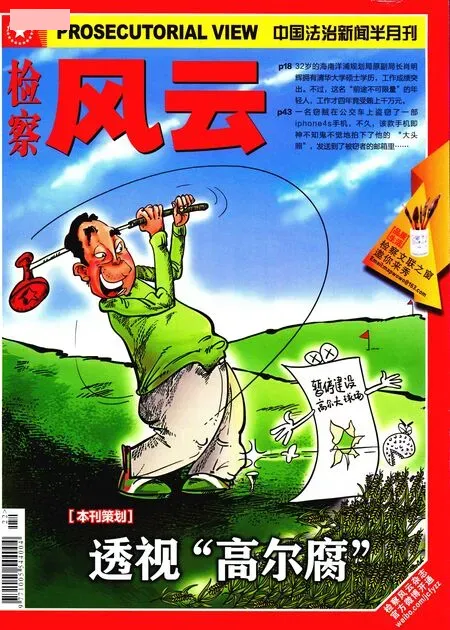跨国追凶20年
文/李有观
跨国追凶20年
A 20-year Multinational Arrest
文/李有观
1990年9月15日上午9时,美国纽约市接连发现了三个装有尸体的垃圾袋。经调查,警方将犯罪嫌疑人锁定在一个身高为1.52米的黑山籍男子身上,但因证据不足迟迟无法起诉他;从1995年6月起,五名比利时女性遭相似手段迫害;当该男子移居到阿尔巴尼亚时,又有一名女性以同样方式被杀。为何在20年后,这个全球性连环杀手才被审判。
1990s一起纽约碎尸案,疑凶秃顶男子朱尔利克去向不明
1990年9月15日上午9点左右,在美国纽约的布鲁克林区,一位钢铁公司的女老板在开车途中发现了路旁有一个巨型黑色垃圾袋。她想要去移动那个袋子,却发现袋子正在慢慢地往外渗血。她连忙拨打了911,该警区负责命案的刑警肯·维兰一个小时内赶到了现场。他察看了那个垃圾袋——里面全是尸块。
维兰迅速地围起了警戒线,等待刑侦技术人员的到来。就在这时,一个当地居民走了过来,告诉他在这个街区又发现了一个可疑的垃圾袋,上面爬满了苍蝇。维兰在袋子里发现了两只胳膊和一条腿。几个小时后,维兰在附近又发现了第三个装着躯干的垃圾袋。
经法医鉴定,这些尸块属于一个身高在1.71到1.74米、体重约88.4公斤的女性。尸检报告指出,受害人是在死后被凶手用带锯、钢锯和切肉刀肢解的。在没有指纹和面部特征的情况下,即使维兰核实了失踪人员的相关资料,他也无法确定死者的身份。
正在维兰警官对案件一筹莫展的时候,他在9月26日接到了失踪人员管理机构提供的一个线索:在布朗克斯区,一位名叫玛丽·比尔的61岁妇女在黑色垃圾袋被发现的当天失踪。玛丽·比尔是一名房地产经纪人,同时兼职做法庭翻译。她和几只狗一起住在一间小房子里。“如果有一天你没有看到我出门遛狗的话,一定要来找我。”她曾经对一个邻居说。邻居发现玛丽·比尔有一天早上没有去散步,于是报了警。警察通知了她最亲近的亲戚——住在芝加哥的妹妹和侄子。他们告诉维兰,玛丽·比尔的左脚踝最近受了伤,照了X光片。经检测,发现相关数据互相匹配,这就说明受害人正是玛丽·比尔。
维兰开始调查玛丽·比尔的生活背景和人际关系。他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说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玛丽·比尔曾经为一个名叫斯马约·朱尔利克的前南斯拉夫男人和他的第二任妻子之间的监护权之争做过法庭翻译。朱尔利克是秃顶,身高仅1.52米,但玛丽·比尔似乎觉得他身上有吸引人的地方。
维兰查看了玛丽·比尔的电话记录,发现截止到她失踪的那天,她和朱尔利克之间都有“频繁且定期”的电话交谈。里面多为色情聊天。而且在玛丽·比尔被害的前几天,她曾经对朱尔利克的妹妹克里西克说:“朱尔利克太让我伤心了!我这辈子还从没遇到过有人这样伤害我。”
有个邻居报告说,最后一次见到朱尔利克是在9月15日。
朱尔利克是在前南斯拉夫与阿尔巴尼亚交界的普拉夫长大。1971年春天,他与第一任妻子和三个孩子一起移民到了美国纽约。在此期间,他有一些违法记录:1974年,他怀疑有人闯入他家,于是向那个人开了枪,之后被判谋杀未遂;8年后,他因为一个行人碰到了他车子的顶部而用木棒痛打此人;他的第二任妻子指责他曾想把自己从五楼扔出去。在他们离婚争夺对孩子的抚养权时,玛丽·比尔充当了法庭翻译。
1990年6月,朱尔利克在布朗克斯买了一栋住宅,和他的第三任妻子亚戈维克住在那里。玛丽·比尔正是那次住宅买卖的中间人。
1991年1月,维兰拿到了搜查那栋位于布朗克斯的房子许可证。厨房水槽里堆满了碗碟,餐桌上两个烟灰缸之间放着一把刀。犯罪现场专家在屋子里喷上了鲁米诺试剂,结果在厨房的墙壁上和两个黑色的垃圾袋上出现了斑斑血迹。化验结果显示,那些血迹与玛丽·比尔的相符,尽管当时的法医技术无法取得更精确的结果。由于找不到可以在立案过程中协助的证人,也没有人知道朱尔利克的下落,地区检察官决定不强行提出起诉。
在维兰退休后离开警界的几年,另一个名叫托马斯·希克伊的刑警接过了这个案子。1994年,希克伊和朱尔利克的第三任妻子亚戈维克通了电话。此时他们已分居,女方住在比利时。亚戈维克否认在第一时间知晓玛丽·比尔的死讯,但她声称朱尔利克的妹妹克里西克曾在一封信中指出朱尔利克就是杀人犯。随后刑警找到克里希克,若她不说实话就会被逮捕。之后克里西克出现在一个大陪审团前,在宣誓后回忆说,1990年9月14日上午,朱尔利克来到她家,说:“世界上已经没有玛丽这个女人了。”
克里西克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玛丽当时正在他家“睡觉”。
“她为什么会睡在你家?”克里西克问。
“她已经死了。”
“她是怎么死的?” 克里西克继续问道。
朱尔利克告诉妹妹,他用锤子砸在玛丽头上,打死了她。
1995年1月18日,纽约布鲁克林区所在的金斯县检察机关以谋杀罪起诉朱尔利克。剩下的问题是如何找到他。朱尔利克曾在比利时居住过一段时间,但当地警方还是无人知道他的下落。比利时警方坚持认为他已回到了前南斯拉夫。
又过去了近10年,办案刑警维兰和希克伊都已经退休。2004年,纽约警察局悬案大队警官詹姆斯·奥索里奥重新打开了这个案子,他再次查询有关朱尔利克的信息,但结果依旧令人失望。
21C初巴尔干地区又现碎尸案,追踪数年,疑凶在黑山共和国落网
2006年11月初,美国联邦调查局一位名叫迈克·克拉克的官员在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西北10英里的一个湖边又打捞出了除了手之外的女尸。像以往一样,在遇到疑难案件时,阿尔巴尼亚警方会向美使馆寻求帮助。克拉克去了停尸房,他很快意识到无法从尸体上得到什么线索:医生们已经把尸块拼接起来,却把两条腿弄反了。加之没有制冷设备,这具无名女尸已经开始腐烂。无奈之下,克拉克只好向联邦调查局请求帮助。
五天后,美国三名刑侦专家前来协助克拉克调查。
物证专家加里·赖内克非常失望地说“所有可能出现的物证都消失了。”画像专家克雷格·阿克利和丹·伯明哈姆在停尸房中的尸体旁沉思:“它在说什么?要告诉我们什么?”最终他们作出了一个相同的结论:“这种情况下圈定出犯罪嫌疑人显然是不可能的。”
当晚,克拉克在宾馆里征求了三名专家的意见。大家达成共识:应把尸体运回美国以便进行更好的尸检。
克拉克在征得联邦调查局总部特许后,将这具无名女尸装入一个衬着铅皮的棺材送上了去华盛顿的飞机。
画像专家阿克利从阿尔巴尼亚回来,还在关注着那起谋杀案。后来在一次案件协办工作中,他遇到了上文提到的警官詹姆斯·奥索里奥。交谈时,阿克利说起阿尔巴尼亚之旅的情况,奥索里奥突然插了一句:“我正在追捕的一个逃犯可能也在那个地区。”
阿克利问起追捕逃犯的原因。“谋杀。”奥索里奥说。他详细地描述了玛丽·比尔一案的情况,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犯罪嫌疑人朱尔利克早已逃离美国,目前住在巴尔干地区。奥索里奥还描述了比利时蒙斯市1996至1997年间发生的好几起尚未破获的谋杀案,那时,朱尔利克正住在比利时。这些案件中被害的都是女性,且都被分尸。美国刑侦专家和警方都认为,他们面对的犯罪嫌疑人可能是一个全球流窜的连环杀手。
在查到朱尔利克的出生地属于黑山共和国之后,克拉克即刻去寻找当地执法部门配合调查。克拉克找到当地一位曾在联邦调查局一家学院学习过的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名叫米奥德拉格·斯蒂乔维奇。
与斯蒂乔维奇取得联系以后,2007年2月初,克拉克将一份文件交给这名学员,其中包括一张电子合成的朱尔利克的照片,因为美国人已有15年之久没有见过他的照片了。斯蒂乔维奇迅速浏览了一遍之后说:“如果他在这里,我们一定会找到他。”几天以后,斯蒂乔维奇告诉了克拉克一个好消息:一个监视小组已经找到了一个和朱尔利克的信息相符的人,但唯一不符的是他的名字:他用的名字是斯马杰·图尔加。
在警方采取行动之前,克拉克想通过指纹证明这个人就是犯罪嫌疑人。2月8日晚,克拉克接到电话,被告知经鉴定指纹相符。
两周以后的一个晚上,数十名黑山警察包围了朱尔利克的住处。在他开门后,警察们迅速将其围住,给他戴上手铐,推进了一辆警车。
当黑山的检察官们翻阅纽约警方提供的文件时,克拉克正在调查阿尔巴尼亚和比利时尚未破获的谋杀案。他无法放过这些与玛丽·比尔谋杀案的有很多相似之处的案件。但他并没有使比利时当局信服。克拉克说:“他们知道朱尔利克,也曾尝试过把他放在谋杀案发生的时间范围内,仍旧一无所获。”比利时警方相信,朱尔利克早在1995年6月(这是蒙斯市第一起谋杀案发生的6个月之前)便已逃离比利时。因为比利时警方已经确定他并非“蒙斯屠夫”,所以没有丝毫讯问他的兴趣。
2008年3月19日,朱尔利克在法庭上大声阅读了一份声明,声称自己无罪。“这是联邦调查局历史上最大的阴谋”。说罢,他坐下来,一言不发。
视线回到美国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当地的检察官找来了证人们,让他们通过视频会议作证。朱尔利克和玛丽·比尔的亲戚、邻居、房东与同事一个个地走进小型会议室。一台摄像机将他们的陈述传送到了4600英里之远的法庭上。朱尔利克的第三任妻子亚戈维克被警方找到后,也通过视频会议系统给出了证词。当询问她对玛丽·比尔被谋杀有何了解时,亚戈维克称,朱尔利克的妹妹克里西克曾告诉她,朱尔利克确实“犯了一些事”。
与此同时,朱尔利克的律师正想方设法钻法律的漏洞,以使关键证人克里西克在法庭上回避发言。在黑山共和国,与被告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有权回避作证,但这种做法在美国还没有得到认可。最终,克里西克选择了回避作证。这一变化使得跟踪了该案近20年的美国金斯县的检察官们有些不知所措。要知道,当年就是根据朱尔利克的妹妹克里西克的证词才决定起诉他的,如今却只剩下一些间接证据和朱尔利克的嫌疑行为。朱尔利克的儿子质问道:“有人见到我父亲杀了玛丽·比尔吗?你们有这样的证人吗?”
由五名黑山法官组成的陪审团于2010年6月22日开始审议此案。 10天后陪审团作出了一致决定,审判长起身大声宣读判决:朱尔利克因谋杀判处12年监禁,因私藏子弹判处4个月监禁,另外支付100欧元的法庭费用。在宣读判决书时,朱尔利克并未表现出任何畏惧。
2011年对凶手的采访
2011年冬天,美国记者尼古拉斯·施米德勒来到监狱对朱尔利克进行了采访。已经71岁的朱尔利克蹭着地面走进了接见室。“我看起来是个危险人物吗?”他问道,然后坐下来,接着说:“他们以为我是个大个子,就像‘山姆之子’(美国纽约的连环杀手)一样。但是没有任何理由给我判刑,因为我不是杀人犯。”
朱尔利克的律师告诉记者,他已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内容主要是质疑朱尔利克厨房中血液的来源,他们称这些血液可能是被害人玛丽·比尔意外割伤留下的,并不是厨房作为杀人现场的结果。”律师同时强调,该案没有证人。(朱尔利克的弟弟告诉记者,妹妹克里西克的证词是在遭受巨大的“心理折磨”之后给出的。)
记者问朱尔利克和被害人玛丽·比尔是什么关系。朱尔利克聚精会神地听着,下颌不停地左右动着。他说玛丽只是充当了自己购房的中间人而已,并无其他关系。但证据显示并非如此:通话记录、电话录音、看见他们俩在一起的邻居,还有两人坐在沙发上的照片。朱尔利克不得不承认说,“通过她的介绍我买了房后,我们的关系近了一步。她帮我把孩子带到我妹妹那里”——监护权之争的结果——“我因此很尊重她。”
记者给他听了那些情色录音。在那段录音里,朱尔利克提议在玛丽·比尔的房间里做爱,因为他们已经在他家里做过爱了。“那不是我,”朱尔利克说,“声音是伪造的。那不是我。不,不。那绝对不是真的。”
在了解到朱尔利克从没有被问及发生在蒙斯的谋杀案之后,记者问他是否在那里杀害了那些女子。“你也认为是我干的吗?”他说,“那些认为我是谋杀犯的人真是可耻。想想看,一个1.52米的小矮人如何杀掉7个女人,又将她们分尸?他们指控我杀了7个女人,但只是因我杀了玛丽·比尔而定罪。我真没有杀她,这是个骗局。可怜的玛丽,我为她感到难过。”
朱尔利克有些恼火了,记者也感觉到他的耐心在慢慢消失。于是记者继续问他,如果他不是纽约警方和联邦调查局认为的那个全球连环杀手的话,他该如何解释与他关系亲密的一个女人在纽约被谋杀,另外五名女性在比利时以相似的方式遇害?在他移居阿尔巴尼亚时,又有一名女性被杀呢?难道朱尔利克只是坏运气的受害者吗?
“这很奇怪。”朱尔利克耸了耸肩。然后把手放在了记者的左腕上,沉思片刻说道:“这些尸体被发现也许是命运。”
命运?记者施米德勒问他这可能是什么意思。
“我的命运,”他说,“就是被指控。”
编辑:陈畅鸣 charmingchin@163.com
助理编辑:刘雨濛 liumangtutu1990@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