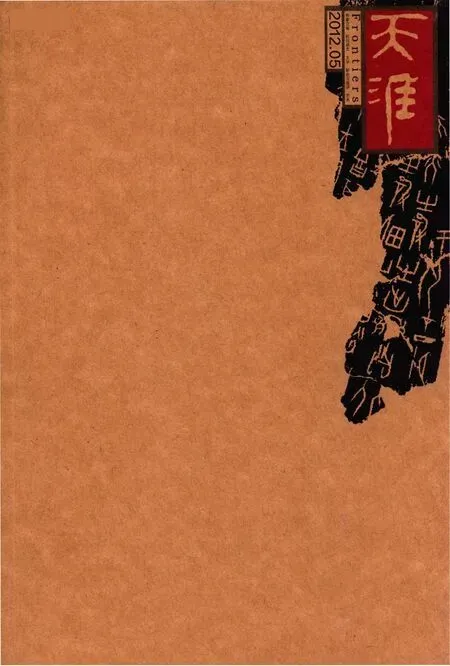乡村爱情故事
李晓君
乡村爱情故事
李晓君
甲
我有一个同事,姓黄,先我一年毕业分到山冈的中学任教。该君在师范学校时,就是个著名的才子,擅长写诗和歌词。有段时间,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尤其是漫长的冬天,乡村阴冷而萧瑟,一个人在屋中呆久了,情绪会显得易怒和焦虑。我们就常串门走动,问对方在看什么书,过去读书时有哪些趣闻,等等。一般我们会在火盆里生起木炭火来。这木炭是向学生家里购的。有的学生家在小镇偏远的山区,每年隆冬,伐木烧炭成为家里的一项副业。木炭火特别暖人,不一会儿,整个屋子便暖烘烘的,但也有不足,就是灰大。黄老师有一双漆黑锐利的眼睛,下巴因为勤于打理,显出一种干净的铁青色。黄老师性格有些急躁,好胜心也强,敢于尝试新鲜事物。这种性格的长处就是,容易做成事。后来的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点。
黄老师英俊潇洒,身上充满活力。他把我也看成是一个才子,因为我当时也写点小诗。黄老师讲得较多的还是他的爱情故事。通常,他会显得难为情但又露出一种自豪的语气说起往事:
他读的师范学校在井冈山脚下一个老区县。毛泽东曾经在那里发动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学校也在一个山岭上,与县城有不短的距离。该县民风彪悍,惧内是该县男子普遍的特点,换句话说,该县女子性情要强,个性桀骜。当然这与黄老师的故事无关。在一次征集校歌的活动中,黄老师——那时还只是个师范生,一举夺魁,成为了全校女生关注的焦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为培养教育人才,把中等师范学校办得红火,录取的生员都是中考成绩优良的学生,因此学校的文化艺术氛围浓厚,思想也活跃。黄老师在一群自命不凡的学生中脱颖而出,心中也颇有些自得,何况他还身兼学校文学社的社长。很快,有个眼睛很大、皮肤很白,貌似神情纯净、面容姣好的女生开始向他示好。依照黄的性情,两人很快就沉醉在爱河中是应有之义。晚饭后,两人经常手牵手跑到学校后面的山坡上散步,靠着生长了几百年的古枫树热情拥吻。山乡的春晚,花香阵阵,树叶飒响。经常也有校联防队员,在黑暗中神出鬼没,冷不丁一束强烈的手电光照射过来,令人不寒而栗。黄和该女生因此学会了在黑暗中与联防队员斗智斗勇,爱得热烈而小心。
有时,学校上晚自习,不够时间出去,在熄灯就寝前夕,黄和女生磨蹭到学生都去了寝室,然后两人在黑暗的教室里匆忙地温习对方灼热的嘴唇……
黄老师讲这些故事时,目光灼人,脸色通红,不时伴随几声“嘿嘿嘿”的笑声,仿佛在讲述一个别人的故事。一般来说,这样的初恋随着毕业钟声的敲响,便会落下青涩、慌张的旗帜。黄老师也不例外。有时,他也会问我的故事,我努力回忆,只能报以歉意的微笑。我还没有黄老师的荣幸,这么早地踏入爱河。
那段时间,黄老师是我交往最密切的一位。我曾经给他画过几幅素描,他都贴在床头。那时,我还坚持在画画,但是兴趣已不像当初在师范时那么浓厚,我对文学的关心已超过了美术。
很多年以后,在县城一个小酒馆里,我和黄老师一起喝酒,席间一位男子还说起,十几年前在“南岭中学”(我们学校的名称)小名(黄老师的名字)的宿舍里见过我的画,当时就认为我是个奇才。可以想见,我的画确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黄老师那时和我一样,是单身汉。在我们中学,类似我们这样的单身汉老师,不下二十个。如果要完整地叙述他们的爱情史,那是几天几夜都说不完的。
仿佛是一夜之间,我们小镇“空降了”好几位女教职工。她们,有的是刚毕业,有的是替职而来。像一群美丽的小白鸽,散落在小镇的各个村小。
黄老师读师范时,虽是著名的才子和情圣,但毕竟是在一个脆弱、虚幻的空中花园,一旦卷起铺盖离开那个象牙塔,来到这个荒僻的小镇,现实生活巨大的污垢便堆积到颈脖处,让人难以喘息。清贫的乡村教师谋生都已乏善可陈,想要获得梦中“公主”的青睐,更是从何谈起?恋爱不易,但交往总是可以的。我们学校的单身汉们对分布在全镇的单身女教职工发起了攻势。他们邀请她们一起来中学玩。所谓的玩,现在想起来,其实也是非常简单:跳舞。
在学校的操场上,跳拉手舞——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时兴过一阵的娱乐:兔子舞、斗鸡舞,以及其他舞种。音响就是一台上英语课用的双卡录放机。伴随着“……go、go、go……”的乐音,大家嘻嘻哈哈、摇摇晃晃地扭腰迈步,显得笨拙和幼稚可笑。但是,当时大家却不以为然。反而像是沉醉在旋律里,动容和深情地舞动着身姿,与舞伴目光相对,微笑地交流,彼此充满着柔情蜜意。放学的孩子们,则闻所未闻地在边上看,这些整天和泥巴、课本打交道的孩子,还从来没见过老师们,在课堂外暴露出这一面。这究竟是给他们带来了不可思议的光亮,还是矮化了老师光辉高大的形象,也是不得而知的。
黄老师的妻子叫李海燕。当时就是和我们一起在中学操场上跳舞当中的一位。她是替职在一个叫“田东”的小学,从事后勤和事务工作。那个小学在我们中学西北方向的一个山坳里,不难想象,是用该村名字命名的。学校其实是不规则的,因为它的前身是村礼堂,是栋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上下两层砖木结构的老房子。校大门侧房是个小商店,无一例外,卖的是些粗陋的学习用品和简单零食,五颜六色,隐没在一些塑料瓶瓶罐罐和木格子之间,在幽暗、清凉的光线里,如同寒碜、拘谨的乡村小孩一般。楼层之间用木板隔断,走起路来“咚咚”作响。教室是暗黑的,白天也要亮起白炽灯才能看得清。李海燕负责学校的食堂,但是并不亲自下厨,而是自己出一部分工资给学校聘了一位村娘做饭。况且,学校的老师大部分家在村里,放学后要回去做农活,所以在学校用餐的老师也就一两位而已。
李海燕和我是同一年分到小镇的。她的家住在县城,父母都是县城小学的老师。一群家住县城的青年教职工经常周一早晨相邀,骑车去小镇的学校上班。李海燕就是其中的一位。当时,我和另外一位姓贺的老师常常一起到李海燕家里去叫她,对于她家也是比较熟悉的。那是一个普通但教养良好的家庭,房子不大——是学校的教师宿舍,但收拾得很干净。我当时并不知道,贺老师经常和我一起去邀李海燕,并不仅仅是出于通常的友谊,而是别有好感。可见,我当时确实愚钝。
李海燕算不上漂亮,但是性格随和、开朗,为人大方、直率。她和黄老师之间是如何种下爱情的种子,没有听他们说及。只能说,中学老师策划的爱情攻略,取得了初步成效。至少有三对教师之间出现了这种处对象的迹象。
黄老师有一辆“飞鸽”牌自行车,是乡村邮递员那种结实、硬朗的款型。那段时间,这辆自行车的使用频率奇高,经常夜里,我在屋中灯下冥思苦想诗句的时候,听到宿舍大门“吱呀”打开了,黄老师——下身穿着牛仔裤,脚蹬皮鞋,一个飞身跨上他的“坐骑”,往西北方向绝尘而去。必须说明的是,我们中学通过山下是条“之”字型斜坡,路面卵石横陈,坑洼不堪,白天骑车都要小心,何况这黑灯瞎火的夜晚?但黄老师的车技也许就在爱情力量的驱使下,在这暗黑的夜里大幅提高的——因为他甚至熟悉这段几十米长的路面上每一块凸起的卵石、每一个凹下的小坑。毫不夸张地说,他吹着口哨,心情极为迫切和愉悦地飞奔而下,瞬间消失在夜风起伏的山下的机耕道上。
恋爱中的男人面目是可憎的,友情也岌岌可危,难以为继。去黄老师房中谈论诗词,听闻他述说风月,享受木炭火烘得全身热乎的快意,已是没有可能了。在这样寂寥、漫长的夜晚,我的诗歌发表频率也高了。古人说“愤怒出诗人”,我想寂寞也出诗人吧!我后来建立起来的一些诗名,和别人忙于恋爱,我却和孤寂的夜晚相守有关。
当黄老师和李海燕关系确定后,便邀请我们去李的学校做客。
那个黄昏,似乎空气里都溢满着酒香。我们一行八九个人,其中正在恋爱的两对,也在聚会的邀请之列。至今回忆起来,那天都像是个节日:田东小学早早散学了,那些平素下课就回家的老师也都喜气洋洋地留下来款待我们。杀了鸡鹅,炉子上正煮着陈年水酒。黄老师亲自在厨房帮忙,我们则聚拢在李海燕的宿舍里,吃着糖果,说着笑话,脚边的木炭火倍增了房间的温暖。那情景就像是在闹洞房一般。
那是赣西一个无名乡间的村小,冬天的夜晚早早来临,丘陵地上的月轮无声地滑行,疏落的村舍周围,有收割殆尽的稻田,寒意使万物噤声不言,在广大、肃静的天地之间,似乎可以忘却人的存在。
然而,我们——一群年轻的教师,以及几个半教半农的乡土教师,却在通宵达旦地痛饮、欢笑。那情景就像是,赶在末日来临之前,挥霍掉所有的欢乐和愁闷。我那时还不太习惯喝酒,小饮则头晕目眩,不能自已。然而,我一直清醒着并没有喝醉,而我的神思,也常在不经意间溜出这礼堂之外,随同山间的夜风,在月光下游荡。那个小学校长,一个穿着军绿色衣服,活像一个村长的络腮男子,席间说去小解,找不到厕所了,结果被我们在楼梯下发现了——已经像一滩污泥一般,他的身旁留着一大滩冒着气泡的尿迹。
在生命的某一时刻,校长扮演了一个孩童的角色,他通过酒——这个媒介,让自己返回了童年。我记得,当初我第一次来到这个乡镇报到,开始我的教学生涯时,是在一个夏日的早晨,我和几个年轻的朋友一起推车来到中心小学的操场——里面已经坐满了等待开会的教师们,有几张脸转过来,望着我们。这几张脸,多少年以后,我都印象深刻:留着胡茬、黝黑的脸上布着皱纹,略带新奇和不乏嘲讽的微笑里,含着巨大的困惑——不知是为自身,还是为我们的命运,眼神则是带着仿佛看着新鲜鸭子放着砧板上等待切割的揶揄和冷淡。这几张脸当中,有一张就是现在酒醉的校长的。
我同样作为一个旁观者,参与了其中的狂欢和词不达意的尴尬。就像我自己后来恋爱,在对异性世界充满激情和忧郁的探寻中,同样显得意味深长。
理所当然,黄老师和李海燕结合在一起了,至今未变。同时和他们恋爱的三对,也都顺利修成正果。当年,参与他们爱情故事的诸君,也都有各自的婚恋,美好、平淡,或者怨忿、抵牾,不一而足。恋爱中的人也如春风夜的桃花,烧灼得何其粲然和艳丽,但也短暂,生活的抒情和高潮部分总是突然戛然而止,从此便进入了另外一条轨道。
乙
很多次,不下于几十次吧,我梦见回到了当年教书的山冈,出现在学校食堂里。说到食堂,那是除了我的宿舍,我印象最深的地方。似乎是,成了家的教师,不常在食堂吃,他们或步行回到乡村的家中用餐,或乘坐中巴车,赶回城里去和老婆孩子一起吃饭。剩下在学校用膳的,其实都是一些单身汉。单身汉们平素各自关在自己的屋子里,或备课,或睡觉,或干着其他无关紧要的事情,以打发时间。因此,食堂,往往成了聚会的场所,成了单身汉教师彼此交流思想和互相调侃的所在。调侃的内容,很大一部分,又都和人身体的缺陷有关:譬如某君长得个头矮小,某君头大与身体极不相称,某君过胖或过瘦,某君臀部过于突出,某君头发过早凋零,等等……极明显地呈现出一种无聊的状态。无聊的好处,就是彼此开心了但不会记在心上。当然,玩笑开着开着,难免就往“下三路”走,这往往将气氛调至最热烈、最欢愉的程度。每个年轻的充满激情和无限饥渴的心灵仿佛都在持久地啜饮着这语言勾画出来的动人的情景之源,无限的满足,当然,之后是更大的虚空。
常常和我们一起开玩笑的,有一位崔姓老师,因为他的家就在学校,他的爱人——在学校食堂工作,他们的儿子,则在完小读书。崔老师和我同在一个教学组,他富有经验并极具耐心,对我帮助不少。我那时还常背着画夹出去写生,偶尔还有一个艺术家的幻梦在心里燃烧。他是我的画作和行为的褒奖者,那双笑眯眯的眼睛总是让人受到鼓舞和备感温暖。或许,他在我身上看到了他年轻时身上的部分,或者年轻时他身上匮乏的部分。可以说,我在他眼里总是那么美好的一个人。
他的妻子,也是一个非常和善、脾气极好的女士,近四十岁,身材匀称,身上有一种淳朴的、逆来顺受的温柔气质。他们的儿子,是一个头大、聪明的孩子,顽皮而不失天真、憨厚,给我们枯燥的教学生活带来不少欢笑。
这一家,是很美满、幸福和可亲的一家。
单身汉们乐于聚首在食堂开玩笑,并且极易滑向那样一个主题,想来和燕女士——崔老师的爱人有关。因为她常常出现在我们玩笑中间,并且,有时她还以过来人的语气主动调侃我们,让我们这些单身汉们时刻意识到自己的匮乏。越是如此,我们越是兴奋,风月素来是最易燃烧情绪的酒精。
然而,我们在玩笑的情境中,往往会忽略掉另一个人,不是崔老师——他有着极大的包容心,并不觉得太太和我们这些小年轻打成一片,有伤体面——而是庞师傅,学校食堂的大厨。庞师傅不到五十岁,但是板寸头发全白了,脸蛋红得就像每时每刻浸泡在酒里,方脸大耳厚唇,长得极精神极壮实——他走起路来,“咚咚”有声。庞师傅不屑与我们玩笑,但是表情也不冷淡,总是喜欢“嘿嘿”笑着,笑得极真诚,极憨厚。
燕女士司职食堂较轻的活,譬如负责给寄宿学校的学生盛米、蒸饭等事项。下厨之类和油烟打交道以及从炉膛里掏灰的工作,则是庞师傅的事。他俩可说是配合默契。南方的冬天,湿寒难捱,老师们喜欢挤在食堂火坑边上烤火——大蒸笼里米饭飘香,下蒸时,庞师傅往往会帮助燕女士一道将五尺来粗的蒸笼从热水沸腾的铁锅上架下来。我们边烤火边嬉笑闲话,有一刘姓老师尤其爱开玩笑,此君也往往被燕女士数落最多。
刘老师就是我们经常拿来调侃的那位,他长得敦实,大头巨鼻厚唇圆眼,也就是说,五官长得都偏大,臀部也大,加之头发浓密粗黑,就像一头小牛犊。此君特别喜欢说话,声音大,动作大,但往往难以说到点子上。他说话有个特点,就是喜欢伸出粗短的食指指指戳戳,指肚子永远朝着下面,而脸庞则喜欢往上端着。人越多,刘老师越喜欢说话,急欲成为众人的中心。有一年,他和一个借读在我们学校的外乡女生恋爱,每天为该女生打饭,甚至帮她洗衣——在此之前,他自己的衣服几乎很少洗过。他因为教物理,还常常假借辅导女生功课,将她留在自己的房里,每每使该女生脸上露出勉为其难的神色。刘老师越是使劲,越是殷勤,也就越使该女生显得难堪。虽然她长得比同龄女生成熟,发育得早,脸经常红扑扑的,但是,她的心并不在刘老师这边,这是极明显的事实。我们都看出来了,但刘老师始终不渝地对自己充满信心。
该女生升上县城高中后给刘老师写了封长信,表达了对照顾她的谢意和自己并不钟情于他、不会再和刘老师见面之类的话。为此,刘老师在房里痛哭了一整个星期——他那与年龄不相匹配的天真和幼稚让我们窃笑。
刘老师的房间对角吊着两根绳线,上面挂满了仿佛万国旗帜般的明信片,都是学生的贺卡——用此种方式展示贺卡,于我是闻所未见的。可知,刘老师本性也浪漫,但他的浪漫似乎有些不着调。
一个星期后,刘老师回到了我们中间,带着他一双红肿的桃子般的眼睛。
他又开始嬉笑如常了,和燕女士之间经常在语言上擦枪走火。同高挑、丰满的燕女士相比,刘老师显得矮了一截,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但行伍出身的庞师傅,则高大健壮,如一堵墙一般。他和燕女士之间的默契当中显出一种细致的、柔软的东西来。有时,我们还会看到,在厨房里,燕女士匆匆递给庞师傅一个苹果什么的。而庞师傅在和燕女士工作时,两人身体时有看似不经意的碰触、摩擦。
起初,我觉得自己想多了,很明显,我对崔老师的好感远大于庞师傅。崔老师是个白净的书生,身体瘦长,说话斯文,手边经常握着一本《红楼梦》或《闲情偶寄》之类,是个有精神追求的人。最关键的是,崔老师身上体现出了一个长者应有的风范,他对我欣赏有加,让我有受宠若惊的感觉,就像一个慈爱的父亲给予一个最受疼爱的孩子一样。可以说,崔老师从他的风度、精神追求、与人为善的平和,都成为了我暗自模仿的对象。多少年以后,我离开了那个教书的乡下小镇,第一个想起来的人,依然是崔老师。
每个周末,崔老师都会离开学校,去往另外一个乡镇——他孤寡的老母亲尚在,这个孝子必定要在那里呆上一晚,侍奉老母。这一点,尤其让我尊敬。但这个夜晚,也注定是崔老师最黑暗的日子。虽然我没见过——但是,学校的单身汉们,尤其是敦实的刘老师言之凿凿地说,那个晚上,燕女士钻进了庞师傅的被窝。可以想见,为了等待这每周一次的相拥而眠,燕女士和庞师傅为此付出的巨大耐心,承受了多少煎熬。
我起初听刘老师说起这事,内心有五雷轰顶、如丧考妣之感。我觉得燕女士绝不可能喜欢上庞师傅。一个外貌善良、贤淑、美丽不凡,一个举止粗俗,言辞木讷,缺乏情趣。燕女士有一个温馨、幸福的家,父子二人长得极像,丈夫可说是有着玉树临风的气质和同周边环境略略错位的高尚情趣,对自己的妻子也是温柔备至、呵护有加。但性是个奇妙的东西,它不以必然的外在优势构成吸引,相反,有时,那种异质的、相冲突的情趣是否更会诱发潜流暗涌的激情?对于尚无异性经验的我来说,只能是无边的猜想而不得要领。
崔老师每次从母亲的身边回来,我们都想在第一时间见到他。自然,那种我明他暗急欲看他如何表现的心理占有一定的成分。但,出人意料的是,崔老师完全像是蒙在鼓里。他的表情看不出有任何一丝的变化:微笑、沉稳、可亲。于是乎,大家似乎都有些怀疑自己的判断是错的,不能相信自己看到的事实——究竟有谁亲自看到燕女士钻进庞师傅的被窝,也是无从考证的。我在山冈教书的五年时间里,虽然一直在流传燕女士和庞师傅的绯闻,但从来就像一个正在孵化当中的鸡蛋,没有破壳而出。
我离开学校到别的单位工作后,还先后接到过崔老师三封书信,皆是用小狼毫写的秀丽、工整的行楷,言语也颇多古雅之词,譬如“××君台鉴”、“××顿首”之类,述起自己的妻子、孩子(他用的词是“拙荆”、“犬子”),充满着诚挚的温馨、亲爱之意,就像是最好的夫妻之间的感受一样。
丙
每年春天,山冈周围的油菜花恣意盛开,成为一片黄金的海洋,火电厂的高大烟囱喘着粗气,两个巨型锅炉也冒着热气,如同一艘陷在由黄花构成的泥泞中的大船。
暮晚的风中传来浓郁的花香,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在暗处积聚、生长。我有一个同学,姓刘名骁,早年与我一道在小城吉安读中专,我读的师范,他读的体校。我在师范的时候学习绘画,班上有不少漂亮的女生学音乐、舞蹈。有一安福籍女生,相貌姣好,沉静而娴雅,颇能吸引我的目光。骁常从体校来看我,我们坐在教室外的长廊下聊天。与他同来的有另一安福籍男生,身体健壮,个子比骁稍矮,相貌、气质上也相差骁远些。安福男生主攻举重,而骁历来是我县乒乓球赛的冠军。与我们一起聊天的,还有其他几位女生,我心仪的那位安福女同学亦在其中。骁因为和我本是初中同学,来我校看望同学,是应有之义。只是后来,我感到,骁的本意并不在此。他似乎对我心仪的女同学也颇有好感。但是,骁并不善于言辞,话不多,且他的意图似乎也一直不很明确,而他的举重同学虽外向多言,但似乎聪明不足,并不深得女生的在意。我那女同学可谓是兰心惠质,黑白分明的眼眸顾盼流转之间,其心意了然若揭。她和骁在我眼中,似乎有着某种默契。常让我在谈话的人群中心迹杳然、幽暗惆怅,便转过头去望花池里的夹竹桃树——在五月的青天白日下,吐放着赤炎如血的花簇,投抹下一湾暗绿的清凉的影子。
有一年暑假,安福女同学还来到我县。我记得和她以及骁一起在县城的影院看了场电影,其时,影院的事业开始衰败,观众不多,影院的设施也比较陈旧,片子似乎也不有名。现在回忆起来,更多的是看完电影,我们以一种很成人化的满不在乎的姿态在街上溜达的情景。
但骁和女同学之间,似乎也没有任何进展,仅此而已。我与该女生的故事,更是乏善可陈,与其说是我们之间的故事,毋宁说是我单方面臆想出来的故事而已。
毕业后,我分到山冈的学校教书,而骁放弃了去县体委,而进了当时炙手可热的火电厂。因此,我们得以又常见面。同年与我们来小镇的,还有中学同学吴。我这里把她叫作吴老师吧,在长埠小学任教。
1991年的小镇春天,油菜花开得恣肆浓艳,黄昏的镇上人影寥寥,偶尔有汽车在灰暗的光线里,在人们的视线中匆匆掠过。骁倚着自行车,站在公路边的白杨树下,等候着吴老师从学校里出来。不同于黄老师和李海燕之间的恋爱,显得明目张胆和真刀真枪。骁和吴老师的恋爱处在一种介乎友情和恋爱之间的模糊状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这场感情中,似乎吴老师的态度要肯定一些、主动一些,但是骁的态度似乎暧昧一些、被动一些。我觉得他们是很合适的一对。
我经常回望来到小镇之初,我们这些年轻的男女,一起骑车去上班的情景。虽然我不在恋爱之中,但是,初涉爱河的年轻朋友们的神情、举止,以及他们因为投入爱情当中从而使自己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的样子,总是那样深深地感染着我,使我也为之动容,并感受到一种既欢快又忧郁的情怀。我因为他们的恋爱,也变成了另外的一个人,变成了一个嫉妒者、一个易怒者、一个思虑者和一个自我的囚徒。
我虽然也次数极少地拜访过吴老师在长埠小学的宿舍,惊讶于其一尘不染,为其馨香、静幽的居室感到晕眩,但坦率地说,处在那个年纪的我,对于稍有好感的女生的房间,都葆有着最大敬意和吸引,容易沉陷在一种自我营造出来的不知放大了多少倍的迷离情绪里。但是,对于骁和吴老师的交往,非但没有妒忌和不快的成分在里头,相反,还有着一种由衷的祝福和成全之意。
我记得,我们这群少年,每年春节都会相互拜年,各自骑着自行车,一家一家同学家里转悠。常年固定下来的,有大约十来位同学,骁和吴老师都在其中,此外,还有其他几位男女同学。当年的印象,觉得吴老师多才而善解人意,骁性情宽厚、为人古道热肠,我与他们的关系都不错。春节拜年节目的开始,大抵始于我们初中毕业以后,十五六岁的年纪,开始进入青春期,对异性的认识,已稍异于从前,注重自我的仪表和内心感受,往往会有夸张的言语和举动。我们在同学家长的热情接待下,吃着糖果,喝着热茶,彼此拘谨而故作放松地开着玩笑,我们越是故意混淆男女同学之间的性别,越是让人感觉到,我们非常在意对方。吴老师和骁的家庭之间是世交,拜年时,他们招呼对方孩子的热情,明显高出我们一筹。这让我们从一开始,就感觉到吴老师和骁之间,用青梅竹马这个词来形容,大致不会相差太远。
我一点不为骁和吴老师之间的交往而感到意外。相反,我觉得他们之间的恋爱,似乎总是处在不温不火的状态,为此暗暗为他们着急。他们的恋爱显得隐秘,连我们这些中学要好的同学,除了我之外,大概都不清楚他们的状态。
有几次,骁和他几个火电厂的同事来到山冈,找我来玩。他们身上穿着运动服装,口音很杂,有本县的,也有外县市的口音。这个时候,骁已经长成了一个高大、健壮的小伙,嘴唇上露出浓密的胡须,而他宽厚、温和的笑容一如以前。他们在我的宿舍坐着、聊天,拿起我桌上的书籍,随手翻着,但兴趣不在于此,包括我们聊天的话题,似乎也总是飘忽不定,很难说得上热烈。我望着面前这个男子,正处在恋爱之中,他的脸上闪现着另外一个女生的面影,在一瞬间,我陷入一种困惑之中——他似乎在初一时,就已经长成了这么高大的个子,在一次体育课上,我因为身体瘦弱矮小,跃起抓不到引体向上的单杠,他粗大的双掌撑在我的腋下,将我举向半空——顿时让我觉得心存感激。骁就像一个可以信赖的兄长一般。他们在我屋里坐了一会儿,就出来了,我陪他们在校园里随意地走走,在教室后面茂密的板栗树下站立了一会儿,他们就返身沿着山坡的小路,回到了对面的火电厂。几次都是如此。
骁和我之间这种清淡、踏实的友情,在和吴老师之间,似乎也没多少的改变。吴老师——当时,剪着短发,白皙的略方的脸上红唇皓齿,明眸善睐,一种洒脱和聪慧的气质端显无疑,她的好脾气和大方的性情,总是会使人备增好感。
油菜花在春天的泥地里炽热地燃烧,傍晚的乡间小镇,空气的花香里掺杂着一种酒的气息,让人神经兴奋。这是个恋爱的季节。我时常在读书写作之余,步出室外,站在坡顶上望着远处,我知道,我的恋爱,还远未来到,我还在为一些抽象的命题和唯美的意象烦恼不已。这是我和孤独博弈的时刻,如果我像其他人一样,陷于世俗的恋爱,等于是放弃内心对于彼岸世界的探索——而那样一个世界,尚在月黑风高的极地,我不打算寻找一个同伴,和我一起冒险。但是我依然牵挂着骁和吴老师的恋情,在这个月明星稀的春夜,周围虫声如潮,此起彼伏,响亮而持久。
骁和吴老师正在高大的火电厂旁的小路上散步,摇曳和湿润的油菜花枝不时拂过他们的腿,在银色的月亮的照耀下,连绵起伏的油菜花像一片淡黄色的波浪。他们的手指没有扣在一起,就连话题,都始终小心翼翼地在爱的字眼之外焦急地打转。
不知是骁没有勇气来表达他的爱情,或者是他对自己的内心仍不很清楚,还在犹豫和彷徨。
有一阵子,我没有去关心骁和吴老师爱情的进展。我的同事黄老师,这时正在积极地筹备他的婚礼,李海燕经常出现在我们中学,黄老师已经不大去往田东小学了,而是整日关起门来,写作青春美文。倒是李海燕常常来看他,与当初黄老师追求李海燕时相反,不明就里的人,一定以为他们的关系是女追男。
一段时间过后,我们得到骁和吴老师的新消息。一位家在本镇的吴老师的同事,追求吴老师成功,而骁也正在热烈追求另一位与他同姓的女子。乍一听到此消息,让我大吃一惊。并深为他们之间惋惜。据说,骁和吴老师的父母,都满意他们的交往,得知他们结交新欢后都很生气,一度让彼此之间的关系紧张。
我们同学之间过年的走动,止于有人开始恋爱。一种新型的更能激荡人心的情感,往往使人对友情表现出漠不关心的姿态。旧有的友情暂时要搁浅在时间荒芜的沙滩上,而让位于桃花盛开的爱情的绿地。这只是友情的假死状态,假以时日,步入婚姻的男女,在米面生活乏味的洗刷中,将渐渐唤醒心中沉睡的过去的友情。
骁和女友恋爱结婚了。吴老师和她的同事也最终战胜了父母的意志,步入了婚姻的殿堂。我设想过,骁和吴老师恋爱成家,会是怎样一种幸福的状态——当然,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设想。
油菜花每年春天,都会在火电厂周围的空地上恣意蔓延,烧灼着碧蓝的天空。时过境迁,火电厂早已衰败,连同我县其他的国有企业,全都破产或改制。就像一个步入残年的老者,火电厂高大的厂房积满鸟粪和尘埃,书写着标语的墙垣已经倾圮,荒草沿着墙根疯长,高过了墙体。只有油菜花每年都像是处女一般,显得生命旺盛而鲜嫩,抛洒着多余的香气,勾起蜂蝶在其间飞舞。而骁和吴老师微不足道的故事,也如同一座小废墟,在时间的深处湮埋……
李晓君,作家,现居南昌。主要著作有散文集《时光镜像》、《昼与夜的边缘》等。
——信息类文本阅读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