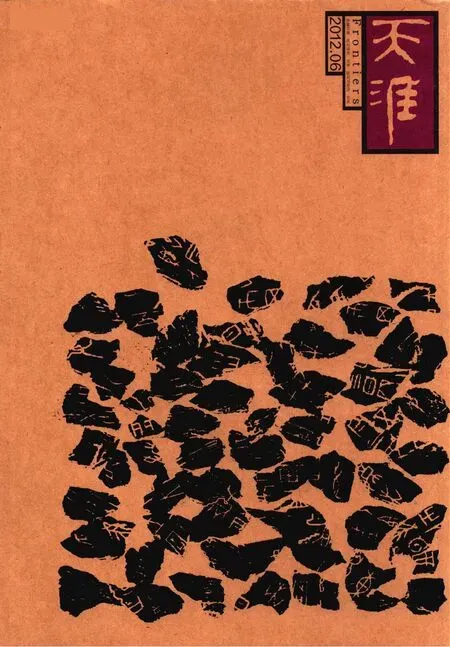半天等于一生
乔叶
天马行空半日
早上起来时,心里有些惴惴不安。隐隐担心天气。因昨晚是太恐怖了。我从来没有听到过那么可怕的风声。可能是依山傍水的缘故,天马岛的空旷和广阔使得风很容易撒娇——但是,昨晚的风真是疯了的风,不是撒娇而是撒泼了。呜呜哇哇,仿佛是在撕扯着什么,抢夺什么似的,那个剧烈,那个锋利,那个没有情理,简直是不能形容。那么厚实的窗户在这样的动静中也不能消停,似乎有一双双小手在敲打着它。砰砰作响。我又害怕又好奇,隔一会儿就掀开窗帘看一下外面。外面,昏黄的路灯下,树只是轻轻地摇摆着——可能是因为距离的关系,看起来居然很平静,但是,风声为什么这么大呢?我真是想不通了。而且这么大的风,却只是很小很小的雨,浅浅地把地面湿了一层。
但是,早上起来,将窗帘拉开,心里的隐忧顿时放下。湖水碧蓝无痕,天空湛蓝无云,真是朗朗乾坤啊。
早餐后,和朋友上了游船。天马岛的精华景观便开始呈现在眼前。当然早就知道天马岛了。知道的渠道来源于巨无霸的传媒势力:中央电视台。这两年,不知道因何而起,中央电视台开始流行起了集结号式的地方旅游广告,菏泽、潍坊、文登、天马岛等则构成了山东的旅游航母,口号便是:“好客山东欢迎您。”
从圣水码头启程,二十分钟之后抵达仙山码头,走了几步路,便看到了缆车站。从缆车上看风景,确实有特别的感觉。因为无需体力,只需视野,随着眼前徐徐铺开的画面,便有看三D的效果,只是这影院是在天地间。正和同坐的朋友感叹着这岛上的石头很是凛冽坚硬,没有多少植被,是典型的北方的山……忽然,缆车停了。而且,怎么就那么巧,我坐的这个,恰恰就停在了最陡的那个坎儿上。
山风微拂,缆车微晃。看看脚下,登山的游人步履悠然。看看身边,硕大的山石巍峨屹立。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四分钟……我怀着忐忑和朋友聊天,东一句西一句,他也温和应答,想来也和我同样忐忑。只是我们都不说。仿佛是怕出口成谶。
就这么骗着自己,我不时羡慕地看着脚下登山的游人们,他们依然步履悠然。我隐隐有些后悔:如果不是对舒适和快捷的贪图,就不会陷入如此境地。这是必然的代价啊。我暗自算着,如果到了最后迫不得已的时刻,我是不是该跳车,如果跳车,该朝什么地方跳,是朝树多的地方跳呢,还是朝土多的地方跳……蓦然,缆车往后轻轻滑动了起来。我几乎要惊叫了,它却又朝前行去。不多时,我们安全抵达山顶的站点,从车里跳下的一刹那我忍不住拍拍胸口。我暗暗想:等到下山的时候,一定不坐缆车了。一定要步行下去。
我们刚下去,缆车便又停住了。我看见几个人穿着“检修”字样的工作服在忙碌着,便上前询问,他们说是在检修缆车。原来是在检修,真是让人虚惊一场。我问他们为什么检修还要正常工作,一个师傅大大咧咧地说:“没事。不会有事。”正说着,缆车又开停了两次。随行的朋友还有几个在缆车里。也是我刚才的位置,于是我们几个下车的人便站在站台上俯视着他们,想象着他们的心情,嘻嘻哈哈地打趣着——他们还不知道缘故,我们却已经知道了,而且已经安全抵达。用我们的轻松来映衬他们的忐忑,确实有一种喜剧感。当然,这喜剧感仅限于我们,在他们看来,这喜剧感是有些幸灾乐祸的。人和人之间,怎么可能做到真正的感同身受呢?
终于,缆车又开始正常启动,我们的人很快集合到了一起,向山顶进发。此时天已经阴了,风也急了起来,看着似乎要下雨的样子。等乘着天车过了女娲石,来到仙乐飘飘的圣水观音时,却又有了短短的晴朗。在甘露寺里略站了站,我们便顺着寺后的步道上了金顶。此时的天气又变了,雨滴渐密。我们起初还不以为意,散淡地走着。等到抬头看天乌云密布的时候,才觉得不妙。大家的脚步也方才急促起来,然而雨已经是越来越大了。有人打了伞,有人没有。我戴了帽子,也不是那么着急。等到大家聚到一个长廊里,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忍不住就都笑起来了。没带伞的那些人终于都还是买了雨衣,继续往下走。——这个情形,哪里能等雨停了呢?谁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停呢?
很快,就又到了下车的缆车站。我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又钻进了缆车里,等到在缆车里坐定,一面想着这缆车不会再停在半路了吧?忍不住就笑起自己来了。自己问自己道:说你什么好呢?典型的好了伤疤忘了疼啊。
雨越下越大,雨衣也不顶事了,鞋湿了,裤子湿了,衣服也润润的了。常在雨中走,哪能不湿鞋呢?这就是无法逃避的事,除非时时刻刻雨具齐全,早有防备。但是,有那样的人吗?有那样的人生吗?
下了山,雨也停了。当地的朋友招待我们在一个特色饭店吃午饭。顿时又换了一番景象:鲜花芬芳,酒香浓郁;觥筹交错,推杯换盏。大家经过一番打理,也都没有了刚才的狼狈,人人衣冠楚楚,笑容靓丽。方才的风雨已经成了谈资。接待的朋友连连地道歉,仿佛自己兼有天公的职责,方才的天气全是他的过错。大家自然客气说没关系。
我没说什么,心里想说的却是:这天气真好。真丰富,真周全。——难道不是吗?这半天,有阴有晴,有风有雨,有走有停,有进有退,有享受有遭罪……什么都有,如一个微缩的全本折子戏。人生的种种,都在里面了。
简直就等于一生。——不,简直就等于一个世界。——不,这不是禅语,这是生活的真意。面对这样的真意,除了去默默领受,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写帐的方式
九莲山位于豫北辉县,和我老家修武县的云台山一样,都是太行山的孩子。在我所见过的豫北山水中,云台山可谓是独一无二的绝色。曾经沧海难为水,因此对于去九莲山看景,我不大有兴趣。九莲山最吸引我的物事,就是传说中的帐书。
进了天门,过了九莲潭,再乘着观光电梯上到天壶瀑布的顶端,便可看见西莲寺了。一踏上去西莲寺的路,便满目七彩斑斓的帐书。上面图案各异,绚丽缤纷,有的是浩瀚的星空,有的是春天的花朵,有的是纯真的孩子,有的是娇媚的女人,还有雄壮的树木,恐怖的蟒蛇,喜庆的龙凤……
帐,是帐幕的帐,而非账本的账。按照豫北地方的解释,帐的意思就是长且宽的布匹,且以白布居多。在我们豫北,某家有人去世,亲友们前去吊唁,一定会去送个“帐”,这个“帐”就是白布,宽都是二尺七,长度呢,则有的三尺,有的五尺,有的七尺,情意厚的,可以更长。
九莲山“帐书”的帐,指的便是这样的布匹。据说很早以前,九莲山就有了写帐的习俗。写帐方式一般有两种,一是文字帐,二是图画帐。也就是在布上写些什么或者画些什么。大的帐有几米、十几米,甚或几十米,小的帐只有玲珑盈寸。写帐都是自觉行为,没有人教,无师自通,仿佛天赐之能。写帐的时候严禁外人观看。据说也不打底稿,下笔便成。写帐人一般文化程度都不高,有的甚至还是文盲,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写帐。更奇异的是,写帐人所写出的帐,自己是不明白的,因此帐写好了,要择期举行仪式,在信众面前将帐打开,请“开帐人”进行“开帐”。“开帐人”就是讲解帐书的人。他们都宣称自己能懂这帐书。但他们开帐的方式也不是用通俗的语言去讲解,而是用唱经或者舞蹈的方式。等“开帐人”开完了帐,写帐人就在神灵面前将帐书焚烧干净,这就是“交帐”。至此,一本帐书的命运才算有始有终地有了完整的交代。
在两条帐空隙间的一块石头上,我看见了那个中年男人。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棉袄,头发乱蓬蓬的,神情黯淡地坐在那里,脚下放着一个黑布袋子,袋子没有系口,露出一叠叠书册一样的布。
“是帐书吗?”我在他对面的石头上坐下来,问。
“嗯。”他答应。
“能看看吗?”
他把帐书取了出来,隔着路,给我递了过来。我翻开,是一组组竖码排放的有规律的符号。当然,我不认得。帐书的边缘已经泛黄了。
“写了多少年了?”
“十年。”
“来交账?”
“嗯。”
他的话真少啊。我把帐书递还给他:“为什么要写呢?”
“心里想写。不写不中,难受。”
“写完就好受了吗?”
“嗯。”他微微笑了笑,“交完帐更好受。”
说完,他起身离去。我默默地看着他的背影,再看看满山满野的帐书,顿觉满世苍凉。忽然想起刘震云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小说的主题是孤独。西方的孤独是人对上帝的孤独,因为可以对上帝赋予无条件的倾诉和信任,所以孤独有靠。而中国式孤独是人与人之间的有限相托和不能言说,所以是无靠的孤独。——这些写帐人,也都是孤独的吧?这些浩浩荡荡的帐书,与其说是他们写给神灵的信,不如说是他们在给自己的心寻找一个渠道和出口。
“帐在心灵。”据说这是作家田中禾先生看过九莲山帐书之后留下的话。我很喜欢。这话说得多么好啊,真是一语中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人都是写帐人。人人都在为自己的心寻找着渠道和出口,有的以歌,有的以舞,有的以剑,有的以土,有的以茶,有的以酒。彼此的差异之处只在于写帐方式不同而已。比如我和刚才这个中年男人。他的写帐媒介是我看不懂的奇码异画,他交帐的方式是将帐书烧掉,他交帐的对象是冥冥之中的神灵。而我呢?我的写帐媒介是最平凡最辽阔最深厚最亲爱的方块汉字,我交帐的方式是将我最想说出的话写出来,我交帐的对象是我自己以及茫茫人海中悦纳我的读者。——呵,这些亲爱的读者,他们不仅是我的交帐对象,同时也还都是我的开帐人呢。
那么,此时此刻,就在这篇正在写着的帐的帐尾,请让我用最庸俗的语句来表示一下由衷的感谢吧:感谢汉字,感谢读者,感谢自己!有了这些,我的帐才能够写下去,交出来!
奈曼旗的宝贝
乔叶,这两个字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重要代码,朋友们有时候会开玩笑叫我“落叶乔木”。也因此每当看到落叶乔木的时候就会有一种亲切之感,仿佛所有的落叶乔木都是我的亲戚。2011年8月,我随着中国作家采风团来到了奈曼旗,又认识了两种落叶乔木——不,准确地说,是重识了它们。因为在这之前就已经认识了它们,只不过到了奈曼旗,它们变了个模样。
它们是杨树和柳树。
奈曼旗位于内蒙古通辽市西南部,科尔沁沙地南缘——科尔沁,我无论如何想不到这三个字会和沙地这个词联系到一起。在来到奈曼旗之前,这三个字只能让我想起绿草茵茵的大草原。且不说清朝时期科尔沁的第一传奇美女孝庄皇后动辄就会在电视连续剧中言道:“我想念我的科尔沁,我想念我的大草原……”单看看地图上这些可爱的名字:连中甸子、黄花筒、下洼、四林筒、林家杖子、上黄花塔拉、朱家湾子……不是花就是甸,不是洼就是湾,怎么会和沙地有关系呢?即使再知道草原沙化这个词,如同玫瑰花这样的词成为屠宰场的代称一样,我也还是想不到“科尔沁”会成为沙地前面的一个定语。
但确实,沙地就在我们的行程里默默地站着,一片连着一片,蔚为壮观。有一些沙地还是寸草不生的白沙地,什么都没有。让人绝望。
幸亏有了杨树和柳树。杨树和柳树,这在中原是最俗常的树木,随便是谁说句话都会带出它们来:“柳树不怕淹,松树不怕旱。”“有心种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杨树叶拍巴掌,遍地种高粱。”“杨叶钱大,快种甜瓜;杨叶哗啦,快种西瓜。”当然它们也常常一起出场,在豫北人人都会背的九九消寒歌里就同时有它们的份额:“七九八九沿河看柳,九九杨落地,十九杏花开。”可见俗常。
但到了这里就觉出它们的不俗常。
先说柳树。柳树到了此地就不叫柳树了,而叫怪柳。因为它看起来确实怪。说是柳树,却不高大,也不粗壮,其娇小情形像是天然盆景,七扭八歪,形态各异,极富创意的造型常常大大超出我的想象力:有的像马头,有的像羊角,有的像拱门,有的像珊瑚……怪是怪的,但一点儿也不恐怖,因它从跟到梢长满了嫩绿的枝条,看起来很是新巧有趣。当地的朋友介绍说,怪柳之所以如此情状,是因为如果要在沙地上存活,它必得顺应这里的条件,用深根抓牢土地,用身形顺应风沙,用所有叶片汲取阳光雨露……也因此,它就长成了怪模怪样的怪柳——突然,我觉得这个怪字极其不准确。这柳树怪吗?不,它们一点儿都不怪。如草原人放牧,海边人打鱼,中原人种地一样,这些不会说话的植物,最听得懂自然的声音。它们根据水分、光照和大地的条件,听天命,尽树事,看似桀骜不驯实则是智勇双全地生长起来,对这里的环境而言,它们其实是最真切地道法自然。
与其说它们是怪柳,不如说它们是乖柳。怪的,是如此将它们命名的人。是那些远离自然的被文明深深异化的眼睛,和心。
杨树在这里也是另外一番模样。不再是茅盾先生在《白杨礼赞》里说的:“笔直的干,笔直的枝。它的干通常是丈把高,像加过人工似的,一丈以内,绝无旁枝。它所有的丫枝一律向上,而且紧紧靠拢,也像加过人工似的,成为一束,绝不旁逸斜出。”在这里,它们生长得虽也笔直,但旁枝多多,到处旁逸斜出。只要能长杈的地方全在长杈,长得繁繁茂茂,野性蓬勃。我曾问当地朋友为何不修剪一下,博得了全车人的嗤笑。回答说:在这沙地长出的绿色谁舍得修剪?这里的植物最重要的审美标准就是绿色,只要是鲜活的绿,那就是好看,那就是美丽,那就得像宝贝一样留着!
我沉默。为自己的愚蠢。看着车窗外肆意生长的白杨树,这在中原最常见的树,忽然觉得心中一阵温热。是的,是舍得不得,这些树,是像宝贝。是不能修剪,是得任它们骄纵地生长,任它们四面八方地撒开了长去,因这些层层叠叠的青枝碧叶啊,确实是这沙地上最赏心悦目的笑容。——当然,对这沙地来说,宝贝们不仅是杨,也不仅是柳,还有柠条、沙蒿、樟子松,以及星星点点不知名的野草……大大小小,疏疏密密,所有生活在这里的,默默生活在这里的绿色,都是珍贵的宝贝。
在奈曼旗中国作家生态林,我种下了属于自己的一个宝贝,那是一棵松树。——宿命般的,又想到了文学。在这个物质日渐丰盈精神上却日渐沙化的时代,文学难道不也是这沙地上的绿色?杨、柳、松、柠条、沙蒿和小草,让我以最敬重的心情重复这些宝贝的名字,这些可爱的代码,如同重复文学大地上那些宝贝的名字:小说、散文、诗歌、文学刊物、编辑、读者、评论者……
向所有的绿色致敬。
沙地在,绿色也在。我相信:沙地在哪里,这些绿色就会在哪里。甚至,绿色的生命会比沙地更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