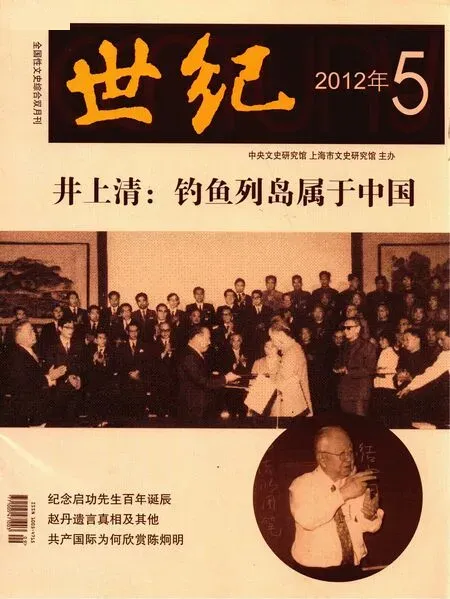科技推动近代经济转型
沈祖炜
近代中国开始了艰难的经济转型,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文明转变。尽管成效不彰,但是毕竟也有进展。其中科学技术的引进,特别是科技力量向经济领域的渗透,成为新式经济成长发展的巨大动力。
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第一位留美归来的容闳为江南制造局引进工作母机,开创了中国机器大工业之先河。在清末兴办铁路的热潮中,詹天佑一展在耶鲁大学学得的机械工程之技术专长,于1909年主持修筑了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中国化学工业的奠基者范旭东,1912年从东京帝国大学应用化学专业学成归国,1914年创办久大盐业公司,1917-1918年创办永利制碱公司,汇聚大批科技人才,成为我国企业发展史上科技兴厂的一个成功范例。抗日战争中,为了保存抗战的经济实力,发动了从东部沿海地区向内地大后方的民族工业大迁移,所搬迁的主要是机器设备,随同进入内地的是大批工程技术人员,由此奠定了内地近代工业的基础。凡此种种,无不显示出科学技术在经济上的重要作用。
在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技术创新可以开拓新的工业制造领域,新型产业勃然兴起可以形成新的消费需求,新的生产力可以打开新的市场。这几乎是一个普遍性的规律。
成功企业家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够看清大势,顺应潮流,成功地运用科技力量,开拓新的产业领域,生产出新的产品。这是企业市场竞争力的体现。近代中国企业,无论是政府主导的官办企业,还是私人资本的民营企业,相对于外资企业而言,都是资本规模较小,市场营销经验不足,技术力量薄弱,管理水平低下。这就使企业在面对外资时显得缺乏竞争力。但是不可否认,近代中国毕竟还是出现了一批具有一定竞争力的企业,曾经在市场竞争中有所建树。
譬如,江南制造局在制造军舰、枪炮的同时,还制造出刨床、起重机、水泵等机械设备,甚至在1921年还为美国客户建造出四艘载重一万吨的货轮。又如,吴蕴初凭借自己掌握的化学知识,经过反复实验、反复试制,生产出中国的调味品——味精,1923年创设了天厨味精厂,所产佛手牌味精打败了日本的味之素,既占领了市场,又获得美国和英国的专利证书,夺得1926年费城、1933年芝加哥两届世博会金奖。由于科学技术的推动,一些中国企业后来居上,在中外企业竞争中成功胜出。1916年开设的中华第一针织厂是上海首家电力针织机袜厂,1920年开设的上海美亚织绸厂以高档绸缎产品独步丝织行业,三友实业社的三角牌毛巾夺回日制铁锚牌毛巾的市场份额,等等。这些事例无不说明,一旦企业插上了科技的翅膀,就会变成翱翔蓝天的雄鹰。
在列强侵华、主权沦丧、经济凋敝的近代中国,从根本上说,只有改变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生产关系,才能拯救民族危亡。这叫革命救亡,确是一种时代强音。但是,我们在关注这一方面的同时,不能忽视另一种社会之声,那就是教育救国、科技救国、实业救国的呼号。这三种救国口号,其实是一脉相承的。教育救国是培养人才,包括科技人才;科技救国是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实业救国则是企业界直接的诉求,认为增强企业竞争力,才是治本之策。这些口号也从一个侧面指出了社会变革的一些根本性问题。
马克思说:“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贝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研判近现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变迁,当然不可忽略科学技术的作用。
以这样的思路来审视中国近现代的社会万象,晚清时期翻译了大批西方科技著作的李善兰、徐寿、华蘅芳、赵元益、贾步纬等翻译家和科学家的功绩值得我们永远记住。同时,近现代史上出现过的各种科技团体也值得关注。因为这些团体是科技工作者活动的舞台,折射出科技进步的步幅。据统计,在20世纪30年代,仅上海一地的学会、研究会就有25个。其中中国科学社1914年成立于美国康奈尔大学,1918年迁回南京,1927年设社上海。该社开年会、办刊物、建图书馆,为科普和科研做了大量的工作。科学有应用科学和基础科学之分,前者直接转化成生产技术,后者也有助于培养人才、启迪民智,间接转变为社会生产力。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科技力量可以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这同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何等相似!在当前中国竭力推进“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时刻,重温近代以来科技推动经济转型的史实,一定可以有所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