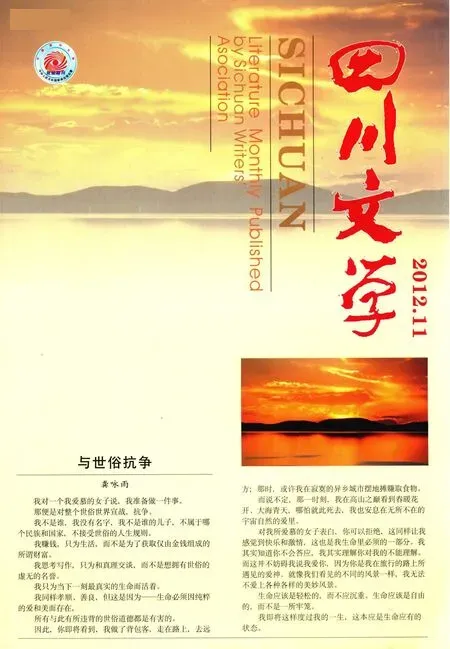别给自己找别扭
□许松涛
遥控器啪啪啪,电视荧光屏上的图像迅速闪过,老伴正看得入神,突然被扫过的频道闪花了眼,肚子里一股气忍不住往嗓子眼里堵:“老别,你神经啊,是不是在家闷得憋不住啊,真的憋不住了就出去遛遛狗也行啊。”老别梗了一下脖子,眼珠子翻了翻,这是他强压心烦的习惯性反应,“老子一看就窝火,什么今年过节不收礼啦,要收就收脑白金啦。一派胡言!胡言!”见老别气咻咻的样子,老伴没有再顶。老别仍顾自嚷:“你不见物价涨得多厉害吗?去年的一勺盐能管得住今年的一碗水吗?”老别在县城的文化馆呆了差不多三十年,退休了,过年的慰问也没见过一张纸片,都过了元旦,也没见单位里来个慰问信,按惯例,每年单位职工总在这个时候发点年货,举行一个聚餐会,年轻人还可以带妻子,今年,冷冰冰的,冷锅冷灶。既有些不适应,也有点迷茫,心里落差是抹不清的,更让他心底不踏实的是那些书法作品的归宿问题。
电视里做得最多的那个广告就是脑白金,一花甲老头与一花甲老太,卡通的,弄时髦,扭昵作态,碰胸,挺肚,扭胯,跳足,拉扯,直看得老别想吐,几次差点晕厥。这样的广告一分一秒都嫌又臭又长,可是就像苍蝇盯上了卖蛋的,怎么也挥之不去,一到年节边,这类大同小异的广告就再次占领观众视野。而让老别烦不胜烦的是,就是送礼与收礼这不堪入耳的词,竟这样直白,风气还好得了吗?这样的广告能播吗?送礼慎重就送给爸妈吗?这能不让人生疑,举一反三,想入非非?
老别有尊姓大名,名册表上姓名栏,填上的是甘应别,到底是什么用意或者有何潜在内涵与寄托,谁也无从知晓,有人破译过,可还是烟消云散,然而人称他老别却日渐声隆。在中华鳖精涨价,并且传得有神奇治癌疗效时,干脆熟悉与不熟悉的人都称他老鳖了。老鳖,好啊。他不计较,甲鱼的别称,水族中一贵族。咬起食物来打雷不松口。这股劲头甘应别也是有的,你瞧他在文化馆搞了这么些年,馆长,副馆长职务与他没份,但也就数他职称最高,为什么,十几个人的馆,拉提琴的,书法的,弹吉它的,写剧本的,唱黄梅的,编舞的,最多告老还乡前弄个中级职称拉倒,而他这个跑民间的,找三寸金莲鞋样,找犁头梢,找纺车,找马桶的人竟然整出了两本当地民间大全的书来,虽说不过是走,拍照,注上说明文字,交待物件的用途,与时间作逆向搜索,在一去不复返的时代里寻找古物旧物破衣烂裳,被常人讥笑还来不及的东西,居然也弄出了大名堂,这还了得,既让馆里一些人赞佩又令人眼红。可是,谁能吃得他那番苦呢。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这也就是他的精神写照——跑烂多少鞋,扔掉几顶草帽,顶过几多暴雨、烈日,大雪没深山,又挨了多少饥,打扰了多少偏僻村庄的狗,花了多少精力与时间,只有他自个儿知道。人们见到他的相片、大名端端正正印在民间神话故事集的封面折叠的上部,作者介绍栏赫然标明为中国民间文艺家会员时,那种捶胸顿足失魂落魄咬牙切齿无地自容的心情真是莫可名状。也就是这样,他有了资格进入本届县政协委员的名册,偶尔参加一次县政协举办的交游活动,议事活动,调研活动;开会,举举手,吃吃饭,他的面孔也就被一些新的隔行如隔山的人们熟悉起来,虽然一听说他是搞杂耍的,被文艺界斥为不是什么正经路子,可是毕竟因了民间文学而有了居高临下观世界的位置。老别运气好!大家都这么认为,瞎猫碰上死老鼠,谁知道这些年兴什么搞民族文化遗产呢,还物质非物质呢,那些粗俗不堪的民歌野调,都以田野调查的名义登堂入室。什么雕树根的,买铜器的,倒卖玉镯文物的,现在都大鸣大放起来,个个都成了第几代传人,第几代高徒,关键的是白纸黑字印刷在书上,一翻田野调查目录,某页第几行某某某,咸鱼翻身了,这世界什么不眼花缭乱啊。
令老别郁闷的是,退休前组织找他谈话,问他最后还有什么要求。老别没过脑子似地跟文化局某位领导说,馆里年初配合省城来县扬桥镇举办的那次“三下乡”活动,省书法家协会与文化馆对接,赠送了十余幅书法艺术作品,都是全省颇有名望的大家赠送的墨宝,现在下落不明,希望局里能予以追回,或者能搞清楚下落,别流失了。局领导在笔记本上认真记录了老别的最后一个要求,从此杳无音讯。又该是新一年“三下乡”的时候了,老别看到电视上又在晃动的本县电视台拍摄的人山人海的画面,忽然,一股恶气涌上心头,作为一个民间文艺家的协会会员,更作为一个从事文化工作几十年的老同志,还是一届县政协的委员,扔出的话,连气泡都没冒一个,他乜了一眼老伴,把想开骂的话吞进了肚里。随手,他给自己倒来一杯水,打开一个小瓶子,手心里有几粒药丸在跳,一仰脖子,张开大口,咕咚一声,厨房洗碗刷锅的老伴在叮嘱:“老别,别忘了吃药啊——”声音长长的,苍苍的,听着很茫远很空洞,这就是老别退休后无数个相同夜晚的序幕。
劳馆长那天对老别的厌烦口气,除了老别本人,其他人还真的以为他做错了什么。而在老别看来,才来两年不久的劳馆长,对他的风格或处世品行,不以为怪。
老别清楚记得,去扬桥镇的那天是元月5号。一大早,就被办公室主任小米催出门,吴副馆长指示,要你赶紧跟上车。今天扬桥镇大广场人多,笔、墨、毛边垫全带上,有十个书法家为群众义务写春联,县里也有两个书法爱好者陪同。天冷,寒风凛冽,老别赶紧带上一辆人货混装的小卡车,将两个县里的书法家全员带上,后备箱里是整卷的纸,整瓶的墨汁,还有一大捆新崭崭的斗笔。车开到镇广场外的一段公路上时被执勤的民警拦截。警察弯下腰,向驾驶座位司机要票,“什么票?”司机一时摸不清头脑。“泊位车号码”。老别一听,糟了,怎么小米不给车号码?况且劳馆长要求在省领导及书法家等下乡团队进入广场前要进入“送文化写春联”的那片区域。立即给吴副馆长打电话,盲音,占着线呢,而警察在挥手,让老别的车靠边,放后面的车进入查验。老别不甘心,但是没办法,警察是不管你是谁的,一脸黑。他上前解释,怎么努力也无用,真是列宁与卫兵。又给小米电话,小米答说,“那号码在吴馆长手上”。“吴馆长人呢?”吴馆长被劳馆长在途中带到同一辆车上去了。这可把老别急坏了。他远远地看见大道上横幅高挂,人山人海,车队与人群拥挤并进,他急得满头大汗,一看时间快到了,而劳馆长的来电又在人群扰嚷中响了起来:“老别老别,你那边准备好了吗?”老别说:“挤不进去,挤不进去。”一句话没完那边的电话挂了,也不知劳馆长听清了没有,老别当机立断,“别指望了,劳馆长在高速路口接省里贵宾,吴馆长的票和人都在那车上,等不来了,我们下车搬吧。”接着,对司机和两位同来的书法会员说声“对不起”,自己就打开后备箱,将宣纸和笔袋墨盒等一一卸下来。司机见状也来帮忙。老别气喘吁吁地拎着最重的一捆纸,扛着一箱墨,走在头里。身后的人跟着往人堆里挤。远远地见到那个放在一幢大厦角落里的横幅,赶紧小跑过去。那里的一排桌子已摆好,劳馆长已早在那里等着了,一见老别就劈头盖脸地批评:“搞什么名堂,这么拖拉,误了正事可不是好说的。”老别正要解释,劳馆长一挥手,“这事就别提了,先把事办好。”见那春风得意相,老别很委屈,却没发作机会。老别急忙与两个同来的人铺上毛边垫,放上笔,再捡好小碗,盛墨汁用。省城里来的书法家已经笑意盈盈地站成一排,仪式还没开始,有村民迫不及待地从老别的手中抢纸。红纸摊开,有人在地上裁起来,书法家们各自将碗里倒上墨汁,匀好笔,展开纸,在折叠出的新印上,开始向那早已准备好的一张打印满满的春联单子扫视,选上恰当的联句,奋笔疾书在鲜红的纸上。旁边是送医药的,送法律咨询的,送农技,小袋化肥与种子的,有硼肥,有油菜籽,医生拿听筒在替人量血压,在把脉,但是最多的是写春联,村民们都喜欢省城来的书法家的字,还有一种心理,就是不用花一文钱,就能拿副春联回家。一捆纸很快就写光了。书法家们最忙,不停地写,没有喘气的工夫,徒手握笔,冻得两手真搓,而广场边的空地上到处都是墨汁未干的春联,被小石头,土坷垃压着。老别闲不下来,要给书法家面前的杯子里添茶水,还要不住地为每个书法家的表演拍照,一个人拍一张不行,要多角度拍,回去放网上晒。然而人把书法家围成一个圆,一堵人墙,推也推不开,扒也扒不出一个口子。他只好钻进人的肘下,再立起来,匆匆忙忙地按一下快门。好在是傻瓜机,不用操心调焦距,特别是局长陪同县委的领导,省委的带队领导,他不能不给他们拍下来,这是相当重要的。回去后不但要立即放到文化馆的网站上,还有晒到政府的网站上,以铁的事实告诉人们这“三下乡”的深得民心和及时雨,是扎扎实实如火如荼,轰轰烈烈的,否则,这些费了好些气力的行为就没有了意义。让老别感到为难的是,他要将每一级领导者的镜头搞成特写。而领导们这时只管秩序,是不会摆“泡丝”的,所以,老别将那架傻瓜机一刻不停地对着迎面走来的面孔和伸出的手,嚓嚓地按着,然后转到下一个。就这样忙活了半天,领导登台去了,而村民们仍然越来越往墨汁碗前挤,带来的红纸已经用完,书法家们的手也大抵直了不能弯,岂料农民们又在附近的商店里买来了红纸,有的竟然表现出人精般的精明,买来了宣纸,要留下书法家的墨宝,放在家里珍藏。最要命的是,正在手忙脚乱的老别被几个村民大着嗓门喊住,一见是几个民营企业的小老板,是朋友的朋友的所在地的仅见过一次面的那几个陌生面孔,这些家伙机灵而真会捣蛋。“甘馆长,甘馆长,请将我的纸递一递吧,我的厂子里要写上……”接着,空际里飞来一个纸团,胯下又塞过来几张皱巴巴的宣纸。老别慌了神,这样下去,还叫下乡写春联吗?那纸团里写的是什么?连忙捡起来一看,全是些什么“马到成功”、“富贵兴旺”、“大展宏图”……这些老乡真逗,把书法家当成自己的秘书了,真是有无穷的创造力啊。老别硬着头皮,只好接过纸,但是不敢让书法家们写。他和这些省城来的书法家不是狐朋狗友,亲兄难弟,仅是与他们同时看见的,早不到十分钟,姓甚名谁尚一无所知,看把这难题出的。老别不断地朝那几个家伙高喊:“等我回去努力,努力,如果可以就托朋友带给你们好了。”那几个人这才心花怒放地离开,但等来的只能是令他们失望。仪式都是象征性的,书法家这么写下去一定会累死,送化肥送种籽也会把家底送空,送医药的也不能真把什么病都看好了才回头,他们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用在这个活动上,然后是开幕式,领导讲话,现场歌舞送戏,然后是填饱肚子上路。待老别回头看看广场台子上响起的音乐戛然而止,主持人的大嗓门在扩音器里不住震着耳鼓,“静一静,静一静,开幕式马上开始,各位请各就各位”,老别发现所有的横幅下的桌子上空空荡荡,洗劫一空,哪里还收得什么笔,什么墨汁和纸张呢,连毛垫也被顺手牵羊了不少,他赶紧去捡拾,将仅有的泼了墨的三四张毛垫抢了回来。
喜庆是喜庆,仓促是仓促,老别不敢懈怠,劳馆长立即让他回到城里将省城书法家们留下,算是对口答谢宴。书法家们手一挥,立即跟上车,本来到既定的金满楼宾馆,坐在沙发上休息,添茶,或吸烟,忙了一大早至现在,近十一点了,也该歇息歇息,可是歇息不了,老别发现有个女秘书模样的人正在铺开一卷宣纸。老别一看,好家伙,这不是刚才那几个民营企业小老板给的纸吗?另一个省城来的书法家,立即写起了几个字。有人裁出斗方式的,有人裁出吊屏式样的。老别刚要张口欲说那纸不能用,就见那女人叫道:“真是墨宝啊,王县长要好好收藏的。”见还有几个人站起来要字,其他书法家却充耳不闻。这样的场合其实是令人难堪的,那些书法家不止是累了,也有种非常不情愿的意思,凭什么要给这些陌生的没头没脑窜出来的人写字呢?只有那个被公推的书法家在写,一幅,两幅,内容字少,又不落款,简直是闹着玩哄小孩子,老别这时有股冲动,硬着头皮说:“书法家先生,你就给我留个墨宝,是那几个群众非要不可的,拜托了哦。”老别不知道自己这么没脸皮,一时性起,喊了一声,又没起作用,损这个面子,也是没办法,谁让老别连人家的纸也用光了呢。此时,劳馆长又来叫老别:“赶紧去催一下,快上菜,围坐。”这是个解围的好机会,可是实在难堪,待老别忙妥进来时,已经没有一个空位是给老别的。老别只好与司机还有两个本县书法家会员,在隔间的小房里简单地要了点菜,酒也没沾,打发了自己。让他耿耿于怀的是,那几个小老板怎么办,字没写一个,连纸也没了踪影,如果不把纸退给别人,还以为老别自己赚了墨宝私吞了呢。然后他就在回家的路上打了电话问劳馆长:刚才那些纸和字都放在哪里了?劳馆长一副吃惊的样子:“哪里什么纸啊字啊,你去问问王副县长的秘书小于吧,除了她收藏了,别的我可不知道啊。”老别吃了一记闷棍,一股怒火喷上发梢,立即翻开县每年印刷一本的领导干部通讯册,查到了那个叫于秘书的电话号码,立即就拨,大约中午那女秘书也被酒精烧着了,或者在政府大机关的日子已久,脾气也挺大的,炸雷的声音传来:“什么?……书法作品?……扯淡!除了赠给王县长收藏的那幅,我什么也不知道!”老别清楚地听得礤地给挂了,这声音好半天在老别的耳鼓里嗡嗡叫。——这个黄毛丫头,好凶啊,特别是最后一句:你去查,查清了再说。简直像一棵恶毒的钉子,深深地刺痛了老别,他朝天骂了一句:“这世道,想抢啊!”引得路人向他侧目,这个老家伙吃错了药?
过了几天,老别还是没有找到向朋友交代过去的办法,是买几张退赔,还是就此不了了之?果然不好做人。还是坦诚点吧,最后,他选择了老实交代,还是有所删节。只提到这纸还存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过几天退还,事实情况确实是这样。当时规定只许写春联,不是送书法作品的。老别也想弄两幅春联回家贴贴过个喜庆年,一看人多,又不是住在乡下的农民,时间还紧,怎么忍心开口?怎么下得了手?也就作罢。好在那朋友也挺磊落,没有责怪老别的半点意思,试想,一个小小的文化馆员能有什么作为呢,除了听人指挥,摆弄,跟班,能有半点讨价还价的自由么?但这正是老别的心里记下的疙瘩。人都是要面子的嘛,作为跟文化混一辈子的老文化人,连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也没抓住,别说墨宝,就是从笔尖掉下来的墨滴也没弄到一份,一根残毛也没拈着,而凭什么那些馆里的十几幅书法作品,自己连见也没见过一面就不翼而飞了呢?就无影无踪了呢?
去年4月,满坡遍野的油菜花开得正浓正艳时,老别正式办了退休手续。此前,老别有心关注那下落不明的十来幅书法,却总是不得要领,几次想试探出办公室小米的口吻,小米那孩子似难得糊涂的样子,一副郑板桥似的脸。既然众人讳莫如深,老别又岂敢贸然冲撞呢。文化馆本来就穷,几间房子承包给几个有点特长的职工了,学琴班,绘画班,舞蹈班,一年向馆里交点租金承包费,其余自理,他们也不闻不问馆里的事;余下的几个正常上班的人,老贾关门在家炮制剧目,昏天暗地,烟头满地,粗劣的烟味连老婆也不敢近前,别说其他人来问津了。“三下乡”活动来临,也许他连通知也没接到,即使接到了,又干他何事呢。馆里问事的是吴副馆长,他接了赠品,却没保管几天,转交出来了。吴副馆长是个怕树叶掉下来打破头的人,他所以能在这个位置,全仗他的守口如瓶和遇事充木偶的习惯,老别小心翼翼向他打听,他也是闪烁其辞,只说是交出去了,去了哪里,不说。这点老别心知肚明。这丫做不了主,也挺不起胸,单凭那天口袋里装着车泊位号而自己还屁颠屁颠上了劳馆长的车不作交待,就可以想见他遇事两头不着调的样。就在老别绕弯子探问吴副馆长那些书法作品的来龙去脉后没几天,馆里刚好开一个短会,会议统一了口径,似乎专是嗅着了他的跟踪骚味而来的,劳馆长理直气壮而又胸有成竹地说:“今年馆里要办几个活动,活动经费没着没落,为了与兄弟单位联络感情,打算将这些书法作品逐一消化,然后交换出活动的经费。”顾名思义,活动一开展,这些作品全都用到公事公办上,用到集体公共事业上,言下之意若再追问下去,也就名正言顺。一幅作品到底值多少呢。既没估价师,也没有机会拍卖,虽然有拍卖的正规公司,也没人提议。老别在会议上以列席者的名义提了个参考意见:是否可以这样,作品拿到公司拍卖行,也好定个价,然后也好用于文化活动。话还没落地,吴副馆长就帮腔了:“那也不知等到猴年马月才开拍,拍了之后又能拿多少钱,靠这个钱活动,那黄花菜都凉了。”劳馆长踌躇了片刻,然后作深思熟虑状:“这几幅作品看来也不是艺术家的什么得意之作,倘若拍卖,怕也拍不出好价钱。我看,倒不如做顺手人情,与地税局或者财政状况好的单位搞联谊活动,表示我馆的友好与大气,再与他们商谈活动中的方案与资金,岂不一举两得?”这是定了调,谁都听得出来。随后是下一个问题,不过是出租的合同号和收费上缴催督事宜,这问题由小米告知,设个起讫限制的日期也就罢了。然后再是下一个问题,老别在这些问题面前,觉得浑身长刺,没有什么实在的。直到后来,果然也没有什么更多的下文,上半年与某局办了个活动,请了市一级的专家讲了一课,算是对这一次开会的回应,也是对以书画换活动的一次创新性实践之举,随之,这个纠结老别的东西没了下文。随后不长时间,老别离回家越来越近,也就没人问津。老别有时夜里睡不着,就猜这里到底是不是自己不知趣,还是故意在与什么人刁难,甚至疑心这里有人私下里早已分赃,只是老别被蒙在鼓里。一想到这里,老别心里就发哽,如吃了苍蝇一样闷得慌,他实在是不吐不快。在最后的一次与组织谈话,也就是退休前的最后一次谈话中,他鬼使神差地把自己内心的疑问端了出来,来谈话的是文化局纪检组的组长和分管文化馆的副局长,他们听完了,记了下来,说:“不清楚。”仅安慰了几句,只是说,“这事也没大碍,我们了解了解,感谢老同志给我们提供的这个情况,我们会向上级反映的。怎么处理,那是上一级的事。”
老别就天天盼,月月盼。一年过去了,犹如石沉大海。他很久没有去馆里了。人走茶凉,有时人还没走茶就凉了。所以他退休后一直不去原单位走动。还是一个篆刻家走上门来,与老别话家常,老别由最近的篆刻收藏谈到字画市场才触景生情起来,一根神经发烫似的,想起自己临离开单位前做的那点让人不快的事,觉得还是有点狗管耗子。反问自己,是不是自己管宽了?
新闻联播里播出现在北京的篆刻市场异常火爆,一枚印章,若是有点名气的篆家,一字涨到一万元。现在的小县城,就眼前的这位也是一枚图章涨到二千余元,况且章坯子得自己准备,如果是寿山石,鸡血石,那简直昂贵得惊人。可是人就是这么怪,却发疯了似地要弄到一枚章什么的,往文化上搽粉,给自己换脸。这都是些什么年头,一窝蜂地疯狂了!
退休后的老别也很少外出走动。老伴怕他脑子出什么问题,故意逗趣他:今天上菜市场,碰到那个刘阿姨,站在一块谈了半天闲聊,说县里某个局长退休了,成天不敢出门,出门也没人理,干脆在省城住了,买了套房,这样落得眼不见为净。老别反唇相讥:“电视都看了没?2.5微米颗粒,省城不比小县城少,去那里找死啊!”声音恶狠狠的。老伴回他:“可不,也有人愿意这么憋死啊,还不如到省城里换着活哩。”老别就呵呵笑:“你激我做什么呢?我又不是那无脸见人的局长。我是无官一身轻,他是不可一日无官,一无官就离进烟囱不远了。”老别也不计较老伴的多嘴,觉得嗑嗑碰碰一辈子也是福气。儿子媳妇也不用跟他们居住,房子也够了,小孙子来玩玩,周日也就其乐融融了。其他时间在家自己养花种草,花是些吊兰、水仙、紫萝兰什么的,然而他更喜欢养大葱,洗澡花,还有从山里带回来的小石子、野水菜、党参,不好看,却同样生机盎然,搬上搬下,搬进搬出。再者就订点书报翻翻,自己做豆浆,浸豆子,剔除霉粒坏粒,洗淘干净,将豆渣洒下,拌些盐、小葱、辣椒酱,那味道也是挺鲜美的。老别心中也就淡漠了许多事。拧什么劲啊,跟谁拧啊?这样的问号已把他问得心如止水。有时老别发现自己像木偶,活得如行尸走肉。他走在夜晚的街灯下,与老伴并行,慢腾腾的,让车、让人,走在人行道的最里边。见人行道上竖出水管子,横出各种车辆,他也绕着走,只要不被车撞,不被人碰,也就算是厚福之人了。他在办公室里呆了那么些年,刚回家时还真留恋那桌子、椅子,想看看那到底又坐了何人。现在不了。压马路是他每天的一个健身活动,早吃晚饭,然后洗毕出门,走一圈两圈回来看新闻,正好喝口水喘喘气,小城里车多,有时走比坐车快,车道上堵塞拥挤,车祸频发,也有一对老伴被大货车撞掉命的,儿子打电话劝他晚上少出门:“看又车祸了。”他还是觉得好人多福多寿,安慰小辈:日子就这样转着转着,安宁、祥和。退休后,反而心净了许多,天坍了有人顶着。老别有时吃惊自己怎么不觉得有责了,不过这样的感觉越来越钝了。
最近他患心脏病、高血压,左心室肥大。少出门,在家里晃悠,气色稍好了点,又出门了,眼看马上要放寒假了,小孙子要来玩几天,得上街买点吃的给孙子。走后街,人还是多,街灯也不甚分明的亮,老远,就看见小街的火招牌——红星炒货。这牌子也挂了三十年了,与计划经济时代一路抗衡过来的。店里很忙。他先在琳琅满目的标品框前挑选一番,看成色和价格,然后在淡瓜子、薯条、红皮花生米前指认给服务员,很快按不同数量装了袋。付了款,出门时被服务员推介栗子。冬天的栗子刚出铁锅,热气腾腾的,鲜亮鲜亮的,散发出迷人的光泽,空气中还飘着熟栗子特有的甜香。他看了看价,20元一斤,太贵了,两年前才七八元钱一斤。这物价翻筋斗像孙悟空,而没人念咒语,头痛的是消费者,特别是工薪族,上两年都说要加大收入分配公平的力度,却年复一年不见动静,那日渐缩水的工资令人兴奋不起来,怎么不让一些人动歪心思呢?上爬,打秋收,他这些年,单位连一份明细表都没见着,就是查账,神仙也找不到痕迹。没有蛛丝马迹的账,谁也记不清的账,怎么查呢?嘿嘿,他干笑了两声,服务小姐问:老人家,要多少?就这些吧。他拎起袋,三十元就易主了。提在手里,一点分量也没有,他让老伴掂量掂量,自我嘲讽似地:“看我这药吃的是不是中毒了?”回到家,老伴帮他倒了杯温开水,早晚服药用的,也可以嗽口保洁。缓了会儿,就去看电视。先看新闻联播,他习惯性地拧了地方台,现在他看地方台很少,新闻联播后十分钟播的一条新闻让他警觉了起来,说是利复平涨价了,每盒要三十元四十元不等,有的地方卖到六十元了,公安部最近侦探出全国几十家利复平造假制假药案,同一时收网,一举破获了价值近30亿元的大案。真是大快人心!老别看到这里,也才扭过头觉得痛快又触目惊心,打假多少年了,牛奶,药品,苏丹红,瘦肉精,就是斩不尽杀不绝,还有医院报销的药械,让病患也承受不了。这些包袱都扔给老百姓,到最后还不得倾家荡产?小小的降压药因为生产权,定价权,操控在两家制药企业的手里,他们明为两家相互竞争,实则是同一个班底,公司的人员几乎在两家担负相应职务,这样的猫腻一玩出来,国人能不咒死那些狼心狗肺的王八羔子吗?老别一生气,赶紧换台。这一按正好是本县的新闻调查节目,好久没来光顾了。他一看,那不是自己本单位的头儿吗?怎么被公安机关带了铐,在被告席上剃了光秃?那个劳馆长,是从文化局副局长的位置上被揪出来的,公诉人控诉:某某某,因犯有贪污收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他见到劳某人铁灰着脸死猪般坐在被告席上,真是替他难过,老伴说:那不是你单位的头儿吗,怎么成了阶下囚呢。老别慢条斯理地回话:我就知道他,迟早会有这一天。老别心中那一团闷了多年的棉花,忽然云淡风轻了。
老别想唱歌,想唱《花好月圆》,张了张嗓子,嗓门却打不开,只觉干得厉害,“老别呀老别,真是一只鳖,该昂头了。哈哈哈……”小房子里猛然响起空荡荡的声音,很好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