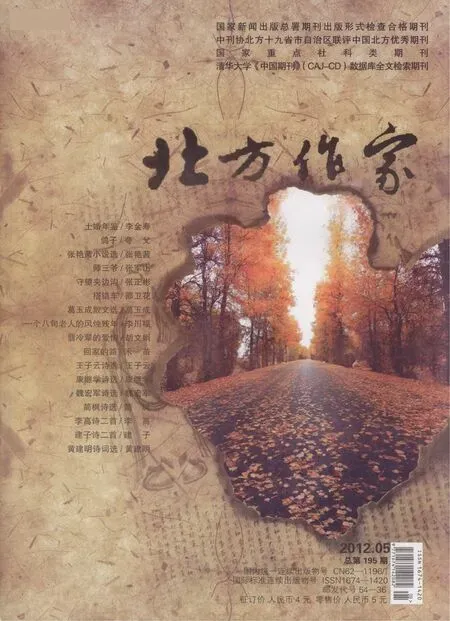那双褐色的眼睛
张艳茜
2002年,在我搬到31层新居的时候,出国六年,已在加拿大定居的小叶回来了。
回来探亲的小叶,还带来了她的一头卷曲的黄发,褐色眼睛的两岁儿子。这个儿子,真像个玩具娃娃,粉嫩粉嫩的,抱在怀中软软柔柔的,令人疼爱不已。让玩娃娃玩大的女儿桃桃狂喜不堪,傻乎乎地对我嚷:妈妈你也要给我生个这样的小弟弟!我笑着说,你妈妈老了,这块“地”恐怕闲置太久,已经荒芜了。不像你小叶阿姨那块地依然肥沃,撒下种子就能长出庄稼来。惹得桃桃一阵抱怨,让你生弟弟,哪里是让你种什么庄稼哦。
很为小叶感到庆幸,她没有被沉重的生存压力压垮,在最初极为艰难的寂寞的日子里,也没有逮着个人就随便嫁出去。和小叶一拨出去的许多女孩儿,真有抗不住了,眼一闭连“黑人”都嫁了的。
小叶熬过了那段日子,小叶等来了爱她的加拿大绅士吉诺比利,小叶还在37岁时有了这个玩具娃娃。只是这玩具娃娃,没有吉诺比利的一对蓝蓝的眼睛,眼仁竟是褐色的。小叶对我说,这都是想你想的啊——因为你就是褐色的眼睛啊。我狐疑地仔细看这玩具娃娃的眼睛,再照镜子看自己的眼睛。果然,她不说,我还真没有发现,我的眼仁的确是褐色的。但是,小叶再说想念我,再有本事,也难以让这小比利遗传我的基因哦。不过我听说,怀孕的女人想谁多一些,孩子就会像谁多一些。但我敢肯定,视爱情如生命的小叶,不会在十月怀胎的日子里,突然友情至上的。我了解小叶,虽然我时常不了解我自己。
有了这个可爱的混血小宝贝的小叶,美丽中增添了一份风韵,热烈中更多了一份安详和沉静,母爱使她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光彩。这种光彩我似曾相识,但又有所不同。
年轻时的我们都曾经光彩照人,但是,有些光彩是属于恋爱时节的果实。那种光彩,就像吸收了充足的阳光和养料,滋润地飞扬在枝头的苹果,神采奕奕的。就像小叶当年那样。当然,这是属于我和小叶之间的秘密。
我自认为是很能为朋友保守秘密的,只要有朋友对我说:这件事我只对你说了,不许告诉别人,那我肯定会将事情沉在心里,锁在记忆的小匣子里。有时,时间久了,还会找不到开启的钥匙,成为永久的秘密。但我也遇见过这样的人,对我说出了她的在我看来很严重、不能示人的秘密,我除了感激她的信任,还会惊恐不安,就像守候在一片即将成熟的西瓜地的看瓜人一样,小心地看护着。但是,还在我为此紧张惶恐的时候,这个秘密却已成为满城风雨,而传播者正是那个让我“守瓜田”的人自己。不懂得这种人当初何苦对我神神秘秘的,非要生生做知己状。
我和小叶与一般朋友不同,我们不需要彼此叮咛,就会很自然地达成默契,知道什么事情该说,什么事情该问,什么事情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什么事情彼此担待。
女儿和我在摆弄“玩具娃娃”,小叶便站在我家阳台向外眺望。苗条的小叶因为做了母亲,因为奶酪黄油的营养,身体饱满圆润了许多,但是胖得和谐,凸凹有致。梳了多年的那条又粗又长的大辫子,依然还在身后,从背后望去,小叶的整个身体就像一把曲线分明、优雅神秘的大提琴。
我不知道小叶这么宁静地想什么又在看什么?
自从搬到这座高层住房里,我很少在白天向外眺望,因为没有什么好风景,看到的不过是肮脏的一片狼藉的楼顶。那很少的一片绿地,也被四周高耸的楼群挤压得失去了生动的色泽。关起门来在房子里,我时常感觉自己就像生活在枝头的鸟儿,既不能脚踏实地,离天堂也很远。
女儿最初住在这里时,曾伤心地流着泪说,“我写作业时再也听不到雨水滴落在树叶上的声音了,听不到窗外枝头上麻雀的吱喳声了,也听不到好听的小贩叫卖声了。”
我经常调侃像我一样生活在高层的朋友,说我们其实就是一群“鸟人”。的確,我們整日奔波忙碌,为名所累,为利所累,奋斗的结果不过是一个远离了自然的栖身“鸟巢”。我们还不如鸟儿们,人与人之间空间距离愈来愈近,但是,心里距离却愈来愈遥远,别说出现危险时袖手看热闹而没有路见不平的英雄,就是邻里之间彼此也少有往来。在我们楼下住的一个自称知识分子的鸟人,竟然还会为方寸之地和邻居剑拔弩张,口水不断。
小叶感觉到了我凝视她的目光,缓缓的,她转过身来,慈爱地看着被我们玩累了睡熟的儿子,然后轻轻的似乎不经意地说:我见到他了。
“我见到他了。”这是小叶回国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世界说大很大,说小很小,我就是不久前在互联网上,与一个三十多年失去联系的朋友通上了话的。更何况,那是一个让小叶当年神魂颠倒忘我献身地在一起十年的恋人哦。我相信,凭小叶的韧性和执著,他们是会见面的。我没有问到这个问题,是希望当初因为“他”而漂洋过海,远走他国,饱受生存艰难和精神寂寞的小叶,能彻底摆脱笼罩在小叶心灵的情感阴霾,就像小叶越洋电话里不断对我讲的那样:“相信时间能让我忘记过去。”虽然,一位曾经让我们迷信的伟人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但是,背叛,对饱受情感折磨的小叶是多么的必要哦。
人的思维和观念的变化,有时是瞬间发生的,有时则需要付出一生的努力。就像我的婚姻被小叶这个旁观者判定,我和那个人不断拉大的距离,终究会导致我们要走到尽头,但必须由我自己勇敢地迈出这一步。而我却一直执迷不悟,愚蠢地总是以为对方是个弱者,需要等待对方强大了,清醒地面对现实,自觉地做出分手的了断一样。我也看到了当年小叶无望的爱情,只能是泡沫的中国股市,看似轰轰烈烈,波澜壮阔,最终的结局就是惨痛和悲凉,就是没有结局。但是,人在事中迷,小叶没有能让我尽早迈出那一步,我也无法使小叶尽早走出畸形的情感堡垒。要么人常说,最难战胜的人就是自己。
其实,小叶的轰轰烈烈,波澜壮阔,完全潜藏在了她的内心深处,海平面始终是风平浪静的。我们是这么好的朋友,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她那么多年到底是在为谁痴狂。这一方面因为,我们虽然是好朋友,但我们懂得互相尊重对方,决不会不经朋友允许就走入对方的领地窥视盗取。
朋友之间是这样,夫妻之间更应该是这样,可很多的男人或女人根本不懂这一点,以为那张合法的结婚证,就决定了对方的身体和灵魂,应该在自己面前永远赤条条的,毫无个人空间和个人自由。恋爱疯狂时期,一句“你是我的”让人心尖颤抖的话语,就决定了彼此成为对方私人财产了吗?占有了对方的身体,就以为连同心灵也一并没收了吗?有这样念头的人真是愚不可及。更何况,比海辽阔的是人的内心,要想在心海里探险徜徉,恐怕付出一生也难以到达哥伦布的新大陆。这是夫妻之间值得庆幸的,因为彼此愿意生活在对方心海里。不幸的是,更多的夫妻,不过是把对方当作手中把玩的物件,或是家中放置的摆设,占有着它,却始终放弃它。
我遇见、并一起生活了快二十年的那个人就是愚蠢男女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小叶遇见的那个他是怎样的呢?
我说,我至今不识小叶的那个“他”的庐山真面目,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小叶无法说出有关他更多的信息。因为,他是已婚男子;因为,他有一个令他骄傲值得炫耀的漂亮妻子;因为,他还有等待他飞黄腾达的名利场。这就注定了,他们连合法的那张纸都不可能有,只要他们的关系继续下去,热烈开朗单纯阳光的小叶,只能将情感的光辉隐蔽在黑暗和混沌之中。
我在婚姻问题上,就是个缺少理性凭感觉简单用事的傻瓜。当年,在一片以沉默做反对的气氛中,我没有去想生活可能遭遇的艰难和拮据;没有去想文化的差异可能缺少的共同语言;没有去想社会地位的差别可能造成的心理扭曲;没有去想永远不会有的夫贵妻荣的虚荣。却只为了一点点感觉,因为那个人在篮球场上曾经像一只快速奔跑的黑豹,矫健而敏捷,那种动感的美瞬间触动了我的奇妙的神经,就这么头脑简单地答应嫁给了那个人。
跟我一样傻的小叶到底又为了什么呢?23岁如花似玉的年龄,明明知道这是一场没有结局的恋情,却苦苦地守候了10年。起初,小叶说,我就爱他的霸道,他的不容置疑,他的唯我独尊。每当他对我说我是他的,那时刻,我就激动得浑身颤抖,就想化作水融入他的怀抱,哪怕死一回都愿意。
人类的情感就是这样不可思议,可能会因为生命的柔弱而生怜爱,也可能因为对强权敬畏而生爱情。我说小叶你就不为将来着想吗?你可能不会每天晚上和你热爱的他相拥入眠;你可能不会每天早上触手便感觉温暖的存在有多么的美好;你可能在过马路时不会有自然地伸向你保护你的手;你可能为给自行车充气自己得掂着打气筒吭哧吭哧打气;你可能在遇到挫折时没有坚强的臂膀靠一靠;你还得练就一个好身体,不然生病了没有人照顾,天要塌下来时也不能顶天立地的撑起来。因为这些时候,说你是他的那个人不会出现,或者说不会坦然地及时地出现。
小叶面对我一连串的质问,不以为然地一笑,反问我说,你这么热爱婚姻,那么你的婚姻里有这些温馨浪漫又实际的东西吗?我即刻哑言,我知道,我所说的正是我缺少的。坦然地出现在我面前的那个人,在法律的保护下,可以坦然地浑浑噩噩,无所事事,并且堂而皇之地享用和肆意掠夺我所辛勤创造的果实。
日子就这样沙漏般点点滴滴地滴落着,埋葬着我和小叶们的青春和大好时光。小叶的爱情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再高潮迭起,程式化的庸常琐碎纷至沓来。小叶抗拒庸常的同时,却又渴望着庸常。她常说,她下班时,总先站立楼下迟迟不肯回家,仰望着她家黑暗的窗户,她希望出现奇迹,能有人为她点亮回家的灯火。
在节假日里,我被乏味庸俗折磨着,盼望着上班能借助忙碌调整苦涩的心情。小叶则被孤独淹没着,家中安静的墙皮发出的剥脱声都能把她吓一跳。一个是渴望孤独,一个则要摆脱孤独的两个女人,经常在深夜里抱着电话聊个不停。烦恼和痛苦便又在时空间穿梭往来,无限地蔓延开来。除了倾诉,谁都不能拯救对方。烦恼和痛苦便愈加深重,于是,我们害怕见面,慢慢地连电话都很少打了。
那一年,我随意插活的一棵昙花,竟然在初夏的一天凌晨四点开了花。我没有看到昙花绽放最灿烂的时刻,待我懵懵懂懂从睡梦中醒来,盛开过的花瓣已疲惫地合拢在一起,弯曲着身躯,耷拉着脑袋。让人好生心痛。那一刻,我蓦然觉得这昙花就像我和小叶,小叶无论怎样美丽,怎样光采照人,也只能在黑暗中孤独地默默地瞬间绽放,无人喝彩。而我则被不幸的婚姻很快掏空了青春,过早地沧桑、疲惫、衰败,苦不堪言。
心情沉重地赶去上班,小叶早已守候在我的办公室门口。她说向我告别,她已经办好了去加拿大留学的手续。我惊喜小叶这突然的变故,真心为小叶感到了一份轻松。
她说,你没有说服我,是他用一举一动说服了我。他除了不断地要求我——要求我做事低调不张扬,要求我不能透漏半点有关我们的秘密,要求我该对谁微笑,该对谁冷漠,要求我在他困难时必须守他身边,他苦闷时我要随叫随到,还要求我留着辫子,素面朝天,因为他喜欢……但是在种种要求之外,他从不考虑我的感受,不考虑我们的将来,不关注和他在一起之外的任何我的事,我的生活,我的工作,我所追求的事业。说到底其实他一点都不在乎我,不欣赏我。我只是他苦闷时的一味调节剂,他手中把玩的一个小物件。他竟然将我拥在他怀里时,还能一遍一遍地赞赏着他妻子的才能和魅力。我知道,我坚守的这份情感不属于我,可是,我以为我是属于他的,因为他说我是他的。这些日子,我反复地对着空气中虚无的他追问:我是你的吗?我是你的吗?我是你的吗?!
我说小叶啊,我俩的悲哀就在于,我们将身体交给对方的时候,也将我们独立的自我交了出去,我们把自己都丢失了,我们还自以为我们在恪守做女人的准则。
那一天,两个一无所有的女人哭作一团,一同用泪水洗涤我们依稀尚存的那一点点自尊。
“我见到他了。”现在,小叶在时隔多年后又一次很郑重地对我说,“但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她说:“我是在机场见到他的,我们其实是乘坐同一个航班,从北京回到西安,但是我们彼此都不知晓。出港时,要不是来接他的妻子叫他的名字,我们将擦肩而过,形同陌路。他胖了许多,挺着个肚子,一副志得意满的神气。他没有看到我。我惊诧落地的第一时刻就能见到他的同时,突然感觉,他是一个多么平常的男人啊。”
我在默想当时的情景,这很像一部我看到过的美国电影的场面:因为爱上一个不该爱的女子,曾位居高官的男主人公身败名裂,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流落异国他乡的男主人公,行走在一条光阴侵蚀的石板路上,穿着一双塑料凉鞋,手提着一袋食物,潦倒而落魄,却在片尾时说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画外音:若干年后,我们在机场相遇了。她是一个多么平常的女人哪!
沉思良久的小叶,将那条又长又粗的大辫子拿在手中,抚摸了片刻说:我该剪发了,这条辫子,赘在脑后,背在身上,好重好重啊!
我懂得小叶的这条辫子为谁而留,所以对她剪辫子的决定毫不奇怪。
小叶回到加拿大温哥华两年之后,我和女儿离开了完全属于我的、一点一滴倾注了我所有心血填充起来的“鸟巢”,开始了艰难漫长的离婚旅程。小叶则在大洋彼岸恋爱着。她说,她和吉诺比利的爱情刚刚开始,她一点一点地感受着吉诺比利的好,被一个好男人具体又实在地呵护着、关爱着,真好。她说,她懂得了,爱情就在生活的细节里,就在生活的庸常里,就在每天清晨伸手可触的温暖里,就在不断地发自内心地说“我爱你”之后的热吻里。
小叶还告诉我,很奇怪,她的可爱的儿子的眼睛在变幻着颜色,现在完全变成了一对清澈的蓝眼睛了,就像他的爸爸吉诺比利。我佯装妒忌地说,那你现在不再想我了吗?
有一天,我跟随一位作家朋友参加一个聚会。席间,一个出版社的老总侃侃而谈,任何人谈到的话题,他都要深入评说一番,并且言辞激烈地对与自己相悖的观点进行反驳,始终把自己当成了至高无上的智者,当作话语的中心。他高大的身躯透着一股霸气,令我很不舒服。我一言不发地看着他表演。他肯定看出了我对他的不屑,相互敬酒间,他走到我的面前,虽然他的身材高大,但是前凸的肥胖肚子使得他整个人看起来臃肿累赘。他对我说,我们得好好喝一杯,因为十几年前我就知道你了,
我在回忆是否和他有编稿过程中的文字交道。他说,是一个人经常谈起你,一个我的朋友。我等待他说出他的那个朋友的名字,但是,他明显地在斟酌着该怎么说:“她其实是一个我们共同的朋友,多年前,突然去了加拿大。”
我惊愕地看着他,难道就是这个鸟人,只用轻描淡写的一句“你是我的”,却没有任何承诺地占有了一个青春女子十年的光阴吗?果真就是他吗?我神思恍惚地看着他那双被兴奋和酒精燃烧的眼睛,试图找出答案。他没有继续说下去,但我发现,这个鸟人的眼睛竟然也是褐色的。他又回到他的座位上,恢复了领袖欲膨胀的神情,好像此前并没有发生什么,重新高谈阔论起来。
我仍然一言不发地看着他表演,回味着小叶说过的一句话:这是一个多么平常的男人啊!岂止平常,简直不值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