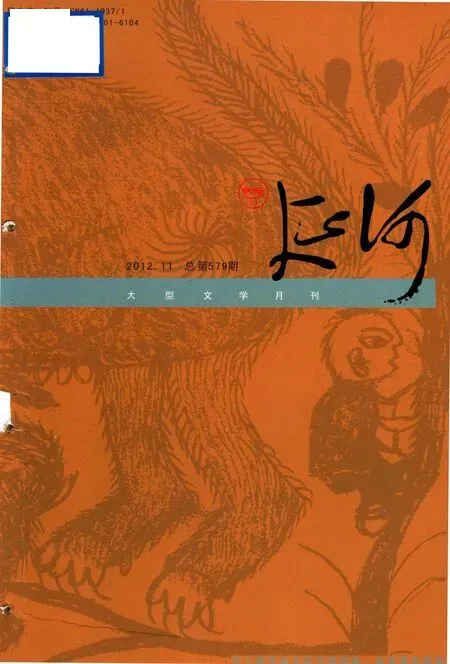追忆我的父亲
王玉平
老 笛
岁月茬苒,不知不觉,父亲去世已经两年多了。两年多来,每当我看到挂在墙上的那管漆色斑剥的老竹笛,便不禁悲从中来,往事如潮水般一齐涌上心头……
(一)
二十四年前,我在公社中学上初二,那时,学校经常组织文艺宣传演出。周围的同学有学拉二胡、板胡的,有学说快板的,而学吹笛的人最多,受环境的影响,我也想要买一根笛子。为此,还专门到供销社去问了笛子的价钱:每根三角。可是,我却没钱买。
那时,我家生活实在艰难。母亲常年有病,不能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哥哥在外地当兵,姐姐高中毕业才开始上工,每天只能挣5个工分;我和弟弟、妹妹上学;七口之家,实际上全靠父亲一人支撑。每年年底结算,都欠生产队的粮钱。每到开学,总为几块钱的学费发愁,记得一次我过生日,午饭在家吃了一碗高粱面搅团,然后父亲给了我八分钱,去街道馆子里吃了一碗素面,便幸福得向同学炫耀。而买笛子我却要向父亲要三角钱,数目太大,我实在没有胆量张口。
但笛子对我的诱惑更大,内心斗争了好几天,一天吃早饭时我吞吞吐吐地向父亲开了口。果然不出所料,父亲“啪”一声将筷子摔在盘子里:“买那东西有啥用处哩?没钱!”“才三角钱。”我小声说,没想到父亲更火了:“三分钱也没有。我一天挣十分工才多钱!”围坐在炕上吃饭的一家人全都默然无声,我愤然放下饭碗,眼里噙着泪水,拿起书包,气冲冲走出了家门。
前两天才下过一场大雪,村外起伏的原野,弯曲的道路上全部覆盖着厚厚的积雪,我满怀委屈,在雪地里茫然徘徊,无意间一回头,看见父亲远远跟在我后边。我装作没看见,更放纵地在雪中乱踢乱踹,故意显出伤心欲绝的样子。我想以此方式向父亲示威,让他知道不给我买笛子的后果有多么严重。但父亲并没有跟过来。
晌午放学回家,走进窑门,我一眼看见一根褐色的笛子放在木柜上,新的,正是供销社卖的那种。两手捧着梦寐以求的笛子,我却觉得惘然若失……
有了自己的笛子,很快我便学会了吹奏一些歌曲,诸如《我是公社小社员》、《大海航行靠航手》等,有时还在全家人面前得意地表演。父亲听了后只是淡淡地笑一笑,什么也不说,这不免让我有些失望。
转眼到了初春,一天下午放学后,我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西斜的春阳照着两旁麦苗返青的田野,也照着极远处淡烟轻笼的山塬。田间,有三三两两捡拾荠菜的人影。一阵微风带着泥土的气息从脸上拂过。我蓦然感到一种从熟睡中苏醒的清新。将到村口,忽然传来一阵笛声。我不觉停下了脚步侧耳聆听,这笛声悠扬宛转,似乎又夹杂着某种忧伤,丝丝缕缕,在村野上空飘荡开来。
半天我才回过神来,急忙往村子里赶。到了家门口,我吃惊地发现笛声竟然是从我家传出来的。推开大门,便看见父亲坐在窑门口的长条凳上,正专注地吹着笛子。从西边黄土崖头斜溜下来的一线夕阳,照在他饱经风霜,皱纹深深的脸上……
这天下午,我知道了父亲是在解放前跟着打醮的(为去世的人做法事)学会吹笛子的,那是一种在那个时代被人看不起的下贱职业,但为了生活,年轻的父亲别无选择。同时,我也知道了他所吹的曲子是《绣荷包》、《苏武牧羊》和《男寡妇》等。
这些曲子后来我跟着父亲都学会了。《绣荷包》、《苏武牧羊》大家都知道。而《男寡妇》,听父亲说,唱的是一个死了婆娘的光棍汉自己抓养一双儿女,艰难度日的凄惶。
对于父亲吹这些曲子时笛声中透出的忧伤,直到后来对我家的历史有了了解之后才逐渐明白。
原来因为家境过于贫穷,父亲一直娶不起妻子。解放后,生活有了大的改善,但父亲已过了而立之年,成家更难。后来,过继了伯父的一个儿子加以抚养。直到父亲四十三岁(1961年),才娶了我的母亲(带着我同母异父的哥哥和姐姐)。那笛声中的忧伤,实在是他心底深处昔日隐痛的流露。
(二)
1980年,我考上了延安大学中文系,这一年,父亲62岁。
临行前,父亲为我绑扎铺盖,把那根笛子也裹在了中间。十七岁的我,还是第一次离家出远门,父亲一直将我送到村口。我坐着手扶拖拉机走了很远,还看见他久久站在那里……
大学生活紧张而又丰富多彩,课余周末,经常有各种各样的文体活动。我没有别的爱好,闲暇时便用笛子吹一两首歌曲自娱,同宿舍的同学无人说好也无人批评。到了元旦,系里组织文艺演出,我大胆报了笛子独奏。或许是自己水平欠佳,吹奏完毕后,台下只是礼貌性地响了几个掌声。但轮到别人用吉他弹唱流行歌曲或用小提琴演奏时,掌声却一浪高过一浪。至此,我才有些明白,除了自己吹笛子水平不高这一原因之外,我的那些生长在黄土高原,听多了秦腔和信天游的同学们,似乎更喜欢西洋乐器演奏出的乐曲。
从此之后,我不再在宿舍里吹笛子,只偶尔于周末晚饭后一个人爬到学校后面的山坡上,坐在松树下静静地吹那些熟悉的曲子。对面是连绵起伏黑魆魆的山,山脚下是汤汤流淌的延河。有时吹着吹着,一轮清冷的月亮就从山顶升起在深蓝的夜空。望着月亮,我便想起家乡,想起父亲,想起父亲对我的叮嘱。于是,我又恢复自信,继续努力于自己的学业。
上大学的几年间,我家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哥哥在部队提干并成了家(原来过继给父亲的我的堂兄1961年已回到了伯父那边),姐姐医学院毕业后参加工作也出嫁了。二是家乡搞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分给各家,温饱已不成问题。而更重要的是,父亲完成了也许是他此生最宏伟的工程——修建新庄基(宅院)。
我家原住的老地方,只有一孔窑洞,两间小厦房,经历了几辈人,早已破败不堪。虽然生产队早就给我家批了新庄基地,但因为生活困难而迟迟没有动工。哥哥姐姐参加工作,给父亲经济上以较大支持,才使他夙愿得偿。
为修建新庄基父亲全力以赴,倾尽心血。除挖掘地基、打筑院墙是花钱雇人以外,三孔窑洞的开掘整修、院落的平填夯筑等大量工作,都是父亲在忙完地里农活以后,一个人起早贪黑、默默完成的。只有在寒暑假时,我和弟弟才给他帮一点极有限的忙。
父亲的右腿早年得过很严重的关节炎,天阴下雨或劳累过度便疼痛难忍。我真的很难设想,他是怎样以年过花甲的高龄,拖着病痛的腿脚去进行那些繁重的劳动的。那三孔高深宽大的窑洞他是怎样一镢头一镢头开挖出来的;挖下来的黄土他又是怎样一架子车一架车运走的;那偌大的院子他又是怎样一锨一锨平整出来的……听父亲说,挖第二孔窑洞时,他从架子上跌下来,在地上躺了很长时间也没有人知道,幸好没有伤筋动骨。说起这件事时,父亲的语气很平淡,而我的心灵却受到强烈的震撼。新庄基实在是父亲用自己的汗血与生命浇筑出来的……
大学四年级第一学期,父亲来信说,新庄基修成,已经搬进去住了。一放寒假,我便带着急切的心情赶回了家。母亲去宁夏给哥哥带孩子已走了一个多月,迎接我的是父亲和弟弟、妹妹。坐在父亲为我烧热的土炕上,看着收拾得朴素洁净的新窑洞,我心里洋溢着阵阵的温暖。
不大功夫,父亲把饭做好端上来,是他自己擀的面条。我这边吃着饭,他挎了老篓(带鋬的大筐)到麦场里去背柴,一边走一边直着脖子咳嗽。看着他蹒跚而去的背景,我嗓子眼像被什么堵住了,一口饭噙在嘴里半晌咽不下去……
除夕这天天气晴好。后晌老早给爷爷奶奶的坟上烧过纸回来,我们便忙开了。我和弟弟、妹妹给大门、三孔窑的门上依次贴上春联。父亲则把那些从集市上买回来的各种神像逐一贴起来:两扇大门贴上门神,大门后贴上土地爷;储存粮食的南窑里,在麦囤上贴上仓谷神,并点起一盏油灯,插上三柱香;给每个窑里的炕厢上贴上炕帖,给院子里的树贴上树帖。看着父亲专注而虔诚的神情,许多复杂的意绪在我心中翻腾。
做完这些事情之后,我和弟弟点燃了一长串鞭炮,村子里各家各户的鞭炮声也不断响起,此起彼应。一会儿,空气中便飘散着火药的幽香。煦暖的阳光洒满洁净的黄土院落,也映照着窑门上鲜红的春联,我的新家弥漫着温暖与祥和的气氛。
不知为什么,父亲忽然想要吹笛子。我赶忙把从学校带回的笛子拿给他。转眼间,清亮悠扬的笛声响了起来。还是那曾经熟悉的曲子,但其中却融合着欢乐;还是那风霜刻蚀的脸膛,但深深的皱纹里却洋溢着喜悦。我和弟弟、妹妹静静地听着。树底下堆积的雪正在无声地消融。
(三)
1984年,我大学毕业了。
大学四年间,我学会了写诗。毕业前夕,在一组题为《给父亲》的诗中,我写下了这样几句:“父亲呵/我是你的/即将调理出的小牛犊……”
但我这头“牛犊”却并没有回到家乡,走向田野,没有去为父亲拉犁耕种。我被分配在渭北一座小城的厂办中学当了一名语文教师。
这座小城号称“飞机城”,这家直属中央的大厂以制造飞机为主。两万多职工来自天南海北,他们的工资待遇、生活水平都非常高,他们的子女大多具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
当了几年班主任,和学生的关系亲密融洽,无话不谈,但却从没有好意思流露过我会吹笛子。直到1987年,我带了新一届学生,并且是文科班。学生们思想活跃、喜爱文学,很多人擅长文艺,师生相互交流更多,无所拘束,如同朋友。迎新年的联欢晚会,学生们准备了很多节目,他们一定要班主任也准备一个。犹豫再三,我带上了笛子。晚会非常热烈,同学们或唱歌或跳舞,还有吉他、电子琴演奏。而出乎意料的是,我的笛子独奏却得到了更为热烈的掌声(我知道那并不是出于礼貌),许多人还对笛子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要求跟我学。这使得原来心存自卑的我受到了很大鼓舞。常常在周末的夜晚,坐在学校空旷的操场上,头顶朗月疏星,周围树影摇曳,我畅开胸怀,尽情地吹奏着笛子,一曲接着一曲。笛声中,我仿佛置身故乡的原野,回到了父亲身边……
第二年夏收忙罢,我将父亲接来,想让他到城里来散散心,开开眼界,也算是我工作后给他尽一点孝心。
刚来的几天,父亲很高兴。每天我上课走后,他都一个人出去转悠,回来就给我讲说他看到听到的自认为新鲜的事。比如城里人穿的都很洋活,和电影里头的人一样;城里的男的女的说话都好听,个个像广播员。最让他惊叹的是,上下班时骑着车子的工人蚂蚁似串,像河一样能淌半个多小时……
可再过了一阵子,父亲的情绪有些低落起来。他提出想要回去,理由是自己头发长了,他在街上寻了好几回,都没有见剃头的,这时我才意识到,远离了田野,远离了村人的父亲实际上很寂寞。为了能让他多住几天,我提议我来给他剃头,没有剃头刀子我也不会剃头,我用剃须刀。
洗好头,父亲顺从地坐在凳子上。手拿剃须刀,对着他濡湿的花白的头发,我满怀感慨: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为父亲剃头。上大学以前,我的头都是由父亲剃的,实际上高中时我就嫌剃的头太土,怕同学们嘲笑,总想用推子理发。可那时家里穷买不起推子,村镇上更没有理发店,为剃头常常要和父亲吵闹一场。上大学后,父亲再也没有要求过为我剃头,谁能想到,今天我竟然要给父亲剃头了。
剃完头,父亲看上去精神了许多,心情也显得愉快。不知怎么,我忽然想起要父亲吹笛子,他犹豫了一下,接过笛子,面对窗口坐好吹了起来。窗外,骄阳斜照,夏日的风穿过窗前枝繁叶茂的绿树,掀动着黄色的窗帘。听着父亲的笛声,我脑海中显现出另一幕情景:
夏夜的麦场,中间是晒了一天后攒起的麦堆,场边是金黄的麦秸垛,另一边是一排高高的杏树,东升的明月把婆娑的树影印在洁净的麦场上。劳累一天的父亲坐在碌碡上抽完一锅旱烟,喝完一壶酽茶,开始吹笛子,我躺在架子车上仰望星空,静静地听着……
正当我随着笛声沉浸在回忆之中时,父亲却停了下来:“吹不了了,人老了,气短得很。”他说。一瞬间,我恍然醒悟:今年,父亲已经七十岁了……
第二天,我带父亲去照像馆为他照了一张像。照片上,他正襟端坐,两手分放在膝盖上,笑得很认真也很实在……
(四)
1995年8月的一天晚上,突然接到长途电话,母亲病危。
当我仓惶奔回老家时,母亲的遗体已经入殓。我们兄弟姐妹围着母亲的灵柩呼天抢地、撕心裂肺地哭嚎,接下来就是浑浑噩噩操办丧事,送母亲入土。连续几天,大家都沉浸在悲伤之中,没有人理会父亲。只依稀记得第一天回来,他两手抱膝,蹲在炕上,低垂着头,嘴里不停地喃喃自语。
母亲的“一七”过完,我和哥哥、姐姐、妹妹都要走了。父亲看上去更加衰老。他拄着拐棍送我们:“你几个走吧,公家的事要紧,屋里有升平(我弟弟)哩……”正说着,他忽然哽咽起来:“我都七十七了,也活不下几天了……”话没说完,他的脸上已是老泪纵横。我的心顿时如针刺一般疼痛,却想不出一句话来安慰父亲,最终还是硬下心走了。长途汽车开向繁华的城市,贫瘠的故乡、年迈的父亲离我越来越远……
茫然和忙碌之中,又是一年过去。1996年7月14日上午,弟弟忽然打来电话,说父亲当天早上殁了。放下电话,我半天回不过神来。对父亲的去世,我已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可怎么也没想到,他会走得这样突然这样匆忙。
回到老家,正是黄昏时分。大门外,大幅白纸写的丧告已经挂起;大门上,白纸黑字的挽联格外刺目。也许才经历过母亲去世的悲伤,跪在父亲的灵前,我没有了捶胸顿足的哀号,只有无声的啜泣和入骨的痛悔。弟弟说昨天父亲还去赶集,在街上跟人说笑呢,今早上去窑里叫他起来吃饭,就发现他已经咽气了……
安葬完父亲,我在父亲生前住的窑里漫无目的地翻捡。这是他抽过的烟锅,石头烟嘴已经磨损变色,黄铜烟锅里结满烟垢;这是他喝过的茶壶,壶盖缺了一块,壶内积满茶锈;这是他枕过的砖头,油腻光滑已变成黑色;这是他铺过的羊毛毡,边缘脱散,中间还有几处破洞……劳累一生辛苦一生的父亲晚年生活竟还是这样俭朴寒碜,我痛悔的泪水流了满脸。但此刻,让我更感深痛的还是父亲晚年的孤寂。哥哥、姐姐、我,还有妹妹先后都离开家乡在外地工作,母亲为我们带孩子也常年在外,家里照顾他生活的只有弟弟两口子。我不能想像,我们不在他身边,尤其是母亲去世的一年间,那一个个漫长的夜晚,父亲一个人在自己的窑里是怎样度过的……
躺在父亲的炕上,我恍惚看到童年时的一幕情景:父亲蹲在炕头抽着烟锅,昏黄的油灯光把他的影子大大地投在墙上。我和弟弟躺在被窝里,听父亲给我们说谜语:“青石板,石板青,青石板上钉银钉。”“一树黄杏,天明落净。”“半个碗,撂过墹,看去近,拾去远。”“十四五岁正当年,二十六七体不全,刚到三十命已完”……
蓦然间,我听到一缕若有若无的笛声从窗外飘过……
父亲去世三周年的祭日,傍晚。
西天,残阳将落,晚霞如火。收割完不久还没有翻耕的麦田如同农民裸露的胸膛;远处的山塬,一片苍黄,偶尔间杂着几抹沉沉的绿色。
坐在父母的坟前,我手持那管漆色斑剥的老竹笛,吹完了《绣荷包》,吹完了《苏轼牧羊》、《男寡妇》,吹完了我会吹的所有曲子。最后,我刨开坟墓上已经丛生杂草的黄土,将笛子埋了进去。
三十六岁的我,第一次明确地意识到,从此,自己将永远不再是孩子。同时我也知道,我欠父亲的实在太多,而且终生无法偿还……
父亲与钱
小时候的记忆中,父亲特别爱钱惜钱,总是把钱看得很紧。
我出生在1963年,三年自然灾害刚结束,我的故乡陕西长武又属偏远山区,土地瘠薄,物质匮乏,人们生活极其贫困,所以从小就很少见也吃不到什么零嘴小吃。偶尔在外面看见有小孩吃果丹皮或水果糖,我馋得流口水,回家跟父亲要几分钱,结果遭到一顿斥骂。等到上学了,常常为要一两毛钱买作业本或笔而惹他生气吊脸,几天后才给我,还要附带一顿节约教育。
但如果能有意外收入,哪怕是一两毛钱,他也喜出望外。记得有一年秋天,下午放学回来,父亲正蹲在地上收拾晒了一院子的柴草,忽然听见他哈哈哈地笑起来,引得一家人都跑去看,只见他手里举着一张两毛钱的纸币兴奋地说:“两毛钱!我在草里头拾了两毛钱!”那种开心与喜悦的神情就像小孩,至今记忆犹新。
父亲在家里中窑的门顶上藏了一个破旧的黑色小木匣,时常看见他神神秘秘地往里面塞什么东西。有一天趁父亲不在时,我和弟弟偷偷搬了凳子把木匣取下来,弄得满手满脸尘灰。打开一看,大失所望,原来里边装的是一些生锈了的麻钱,什么“康熙通宝”“嘉庆通宝”之类,毫无用处,令我和弟弟很扫兴。
爱钱惜钱的父亲总想摆脱贫穷。每年过年,三十初一都舍不得放几个炮的他,到了初五却非常慷慨,要放很多炮,而且放炮的方式也很讲究。先分别从三孔窑洞的最里头开始放,然后在院子里放,再在大门里边放,最后在大门外边放。父亲告诉我们说,这叫“打穷气”,用炮把“穷气”从家里打出去,因为这一天是“五穷”,打走“穷气”,咱家就有钱了。
为什么正月初五是“五穷”,父亲也给我们讲了。当年秦琼秦叔宝在危急关头救了唐王李世民之后,骑着黄膘马飞驰而去。李世民忽然想起仓促之间忘了问救命恩人名讳,于是骑马追赶询问,远远地只听见秦琼的回答中隐约有一个“穷”字,再问时只见秦琼摆手,意思是不必问了,而李世民误以为恩人是姓“穷”名“五”。回去之后,李世民敬立牌位上书“救命恩人穷五之神位”,每日焚香供奉,结果使得秦琼越来越贫穷,最后落魄潞州,以至于当金锏卖黄膘马。再后来,李世民夺得天下,为感念秦琼,便将正月初五定为节日,称为“五穷”。这一天,家家放炮,驱赶贫穷,祈福求财……
尽管父亲年年正月初五都放炮打“穷气”,可我家的贫穷状况却不见改观,父亲还是没钱。那时侯,我家六口人,只有父亲一人在生产队劳动挣工分。父亲辛劳一天挣十分工(一个劳动日),到年底结算时,一个劳动日才值一两毛钱,刨过要付给生产队的口粮钱,每年都要倒欠队里几十块钱。没办法,父亲只有在劳动之余给人下苦挣钱。
那个年代,下苦的门路不多。我印象最深的是到县城去给公社供销社拉货。太阳落山放工回来,父亲和哥哥简单地吃喝一点就拉着架子车出发了。我们公社街道离县城三十里路,中间还要翻一条大沟。去时空车子还好说,回来时一车拉三百多斤货,其重其累可想而知。货拉到供销社卸完回到家里,往往都是后半夜了。有一次,父亲贪心多拉了几十斤,结果负载太重,翻沟爬坡时车到半坡里拉不动了。无奈之下,父亲只好把货先卸下来一部分,由哥哥看守,父亲一箱一箱往坡顶上扛。等折腾到家,鸡都叫了。
一车货三百多斤,来回六十几里乡间土路,再翻一条大沟,最终挣到手的不过三四块钱。
还有就是到四五十里外的甘肃宁县去担菜油回来零卖。一担菜油八十多斤,大概能赚六七块钱。
宁县和我们县之间隔着一条河,没有桥。那一次已经是立了秋的季节,白天天气很热,夜晚却凉意袭人。父亲挑着重担走了几十里路,人累体热,夜晚光脚蹚水过河,两腿被冰凉的河水激渗,回来就得了很严重的关节炎。父亲又舍不得花钱看病,只用一些土方偏方自己贴治,最终留下了后遗症,天阴下雨,膝关节就红肿疼痛,难以行走……
父亲晚年时,我家经济状况终于有了较大改观,但父亲对钱的爱惜依然如故。在外工作的子女偶尔给他一些零花钱,他却舍不得花,一点一点都攒了起来。手里有了几百块闲钱,父亲就有了想法,他想让这些钱变得更多,结果犯了错误。
那年春节我回家,父亲忽然拿出来两摞银元。我很吃惊,问他从哪弄的,父亲惴惴不安地给我讲了来历。原来有一天他在集市上碰到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踅摸着跟他搭话。先夸赞说父亲很有福气,几个儿女都在城里干事挣大钱。然后又说她手里有几十块银元,家里有急事等着用钱,想把银元便宜卖出去,问父亲要不要。开始父亲还犹豫,可老太太说她的银元一个只卖12块,拿到城里一个就能买到七八十块,父亲一听心动了,回家把自己攒的钱拿来,一下就买了20个,过了几天后,父亲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他感到自己可能被骗了。但他又不甘心,因为这些银元他一个一个都细看了,而且使劲用嘴吹了后放在耳朵边听,不像是假的。我问父亲买这些银元干啥用,他有些心虚气短,吞吞吐吐地说:“我想……以后留给你几个……”我才明白父亲的用意,他是想拿这些银元当做将来留给我们兄弟几个的遗产,因为他曾不止一次念叨过,村里谁谁去世时给儿子留了几个金元宝,谁谁去世时给孙子留了两罐子银元……
这些银元我带回去让懂行的朋友鉴定,结果没有一个是真的。随便拿起一个扔到水泥地上,立刻碎为几瓣。等下一次回家,我把鉴定结果告诉父亲,一瞬间,他的目光由希望转为失望,满脸痛悔,叹息连声。
多少年以后,痛悔交加的却是我。我痛悔自己太愚昧,竟然直言告诉父亲银元是假的,让他失望痛心;我痛悔自己太蠢笨,不懂得用善意的谎言欺骗父亲,给他心灵以安慰……
一生爱钱惜钱,为钱下苦为钱挣命的父亲辞别人世至今已经十二年了。十二年里,每次祭祀扫墓,我都尽可能多地给父亲烧些纸钱,希望生前没有享多少福的父亲在另一个世界里能成为有钱人,活得轻松滋润,过得安逸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