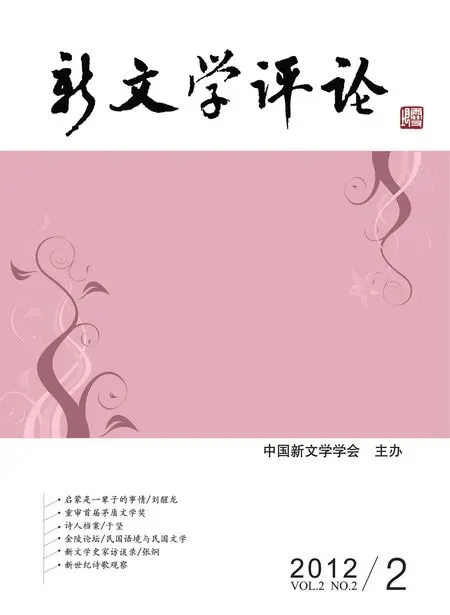新世纪诗歌的传播格局与新诗文化的缺位
◆ 吴投文
新世纪诗歌的传播格局与新诗文化的缺位
◆ 吴投文
尽管新世纪诗歌尚不足以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历史时段,但因处于世纪交替的特殊时期,又因新诗即将迎来它的百年华诞,作为一个文学话题,新世纪诗歌似乎承载着人们的某种特殊感受和期待,在一些研究者那里,也可能包含着文学史定位的意图。不过,对未经充分过滤的新世纪十年诗歌进行文学史定位,显然还为时过早。我想,把一个尚未充分展开的文学时段抽离出来,赋予某种理想化或理念化的建构模式,这其中包含着一种切割历史整体联系的文学史焦虑。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诗歌失去“轰动效应”以来,随着诗歌读者的大量流失,诗歌的边缘化趋势日益加剧。到90年代后期,诗歌边缘化趋势所产生的后果已非常明显,这甚至成为人们质疑新诗合法性的一个主要依据。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经济和文化领域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诗歌的生存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社会文化环境,“在市场与权力相胶合的年代,诗歌越来越扮演着前所未有的奇怪角色”①,诗歌的文化身份被不断稀释和分化,在一种几乎整体性的狂欢追逐中,转化为拥有某种商品属性的文化附属物,这使诗歌沦为时代舞台上一个无足轻重却也炫目亮丽的点缀。因此,在新世纪诗歌表面的繁华之下,诗歌遭遇的困境实际上并未得到缓解。尽管那种认为新世纪诗歌已经边缘化到“消亡”程度的论调耸人耳目,却令人难以置信,而那种认为新世纪诗歌已进入到空前“繁荣”的论调类乎瞎子摸象,同样显得非常可疑。这两种极端的看法表明新世纪诗歌所逐步展开的复杂情形,一方面,诗歌的困境在新的情势下有进一步加剧的可能,另一方面,跨越困境的途径也并非全然没有,而是需要在新世纪复杂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寻找诗歌展开自身丰富性的途径和由此可能诱发的新的前景。这就是大众文化语境下诗歌的基本处境,而要系统地考察新世纪诗歌的基本处境、诗歌的传播格局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观察视角,并可以由此透视新诗文化严重缺位的复杂形态。
新世纪诗歌的传播渠道呈现出多样化的格局,在传统的纸媒之外,最显著的变化是新媒体的深度介入,“如今,诗人和读者都能接触到诗歌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的技术,如计算机、互联网、移动通信设备、摄像机、电视和电台广播,也都能利用词语、形象、声音和实物间无穷的相互作用”②。新媒体的触须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其广泛运用带来新世纪诗歌传播渠道的结构性变化,新世纪诗坛多元共生、众声喧哗的基本态势显然与此直接相关。值得注意的是,新媒体的扩张伴随着工商社会里无止境的利润追逐,其终端追求是利益最大化。新媒体往往把高雅文化的优势部分转化为商业品牌的附属物,对诗歌的利用一般都要经过精心的选择和取舍,突出诗歌中属于“公共文化”的部分,以取得博取眼球的广告化效应,而抑制诗歌中的原创性和先锋性因素,以减少可能带来的广告因素的弱化。新媒体对新世纪诗歌的操控可以说已达到无孔不入的程度,一方面导致诗歌虚假繁荣的征象,一方面造成诗歌不断边缘化的趋势。尽管如此,新媒体以其对现代科技的组合性优势,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催生诗歌创作新格局的形成,以技术手段激发诗人的创作热情,给日益边缘化的诗坛注入某种新的活力。
新世纪网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成为诗歌最主要的创作平台、发表领地和传播空间。互联网语境下的新世纪诗歌出现一系列的新变,不仅影响到诗人的创作情态和读者的阅读方式,乃至彰显出一种新的诗学意义③。网络有利于发表和即时性交流,在技术层面上有着传统媒介无法取代的综合性优势,诗人们轻点鼠标就可以置身于一个虚拟的对话场域中,在网络空间分享一场诗歌的盛宴,尤其是网络的扩张本能很容易形成一个具有凝聚力的诗歌话题,这确实有利于诗人们的交流,可以推动诗人们广泛的协作互动。对大部分诗人来说,网络可能是最重要的诗歌现场,网络诗歌总额之大,远远超出纸媒的承载量,就此而言,网络可谓新世纪诗歌的第一现场。不过,网络诗歌似乎也远远不足以承载人们对新世纪诗歌的预期。在人们的潜意识里,网络诗歌的文化定位模糊,还不足以与纸媒诗歌相提并论,尤其是在经典诗歌的参照下,其文化身份多少显得有些可疑,在主流文化的夹缝中摇摆不定。由网络诗歌引起的错觉往往造成人们对新世纪诗歌评价上的分歧,不管是“繁荣”论者还是“消亡”论者,都难免受到这种错觉的蒙蔽,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新世纪诗歌的尴尬处境。另一方面,人们也注意到,网络正在改变中国诗歌发展的一些基本格局。就我个人的观察来说,这种改变是整体性的,也是建设性的,网络对于诗歌的正面影响要大于负面影响。网络诗歌生态的芜杂和混沌并不可怕,其中包孕着新世纪诗歌综合性生长的态势。特别要提到的是,网络是先锋诗歌竞技的最佳场所,被狭隘的纸媒所隔绝的先锋诗歌往往通过网络被敏锐的读者发现,先锋诗歌往往是先在网络上铺成潮流才被纸媒有选择性地接纳,由此可能形成某种新的诗歌格局。但网络又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具有去遮蔽的作用,一方面又在形成新的遮蔽,其中也包含着一种隐性的权力运作。在网络的包容性后面有着复杂的选择机制,通过分化与选择形成权力运作的分配格局,由此达到网络传播的利益等差效应。对新世纪诗歌来说,网络的分化和选择所带来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如网络炒作所博取的超高点击率往往是网络隐性权力运作的结果,不仅无法达到对网络诗歌精品的有效遴选,而且还会形成坚固的屏蔽效应,使网络诗歌精品被大量的文字垃圾淹没。另外,网络空间广泛流行的浅写作与浅阅读带给诗歌的伤害也值得警惕。显然,要充分有效地利用网络优势为新世纪诗歌服务,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新世纪以来,诗歌纸媒的分化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值得注意。按照一般的说法,诗歌纸媒有官刊和民刊之分,尽管两者之间也不无互渗,但界线分明,艺术定位与选稿原则大都有明显区别。这些年官刊的地位进一步滑落,民刊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可以说,这些年的诗歌热点基本上与官刊无关,要观察真实的诗歌现场,这些官刊最多算是一个补充或“附录”。从这一方面来说,新世纪的诗歌生态有某种恶化的趋势,官刊在读者中的影响急剧降低,有品位的诗歌读者很少去理会这些官刊。对研究者来说,官刊可有可无,绕过这些刊物似乎也并不会降低批评和研究的质量。一些诗人拒绝官刊发表自己的作品,宁愿把作品刊登在民刊上。有时一整本刊物翻下来,找不出一首好诗,全是一些莫名其妙的拼凑之物。这些官刊的最大特点就是平庸,无特点,无个性,自居正统,体制僵化,已经完全失去过去在诗歌界的权威性地位。倒是民刊的活力和无序值得看好。活力表现在限制少,可以自行其是,自己决定办刊的理念,落实有选择性的诗学主张。这看起来无序,也有很多的文字垃圾杂陈其间,但在无序中却孕育着生机和创造力。新的创造最初总是和无序联系在一起,一旦规范,就会落入平庸的陷阱。具体到当下的民刊,杂而多是一种正常生态,但一些民刊也有向官刊靠拢的趋势,用“正规”出版物的“规范”方式运作,想方设法挤进主流诗歌圈。和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创新观念的弱化和道义担当的相对缺失在降低民刊的整体品质。一些民刊的失守和被收编反映出一种“中庸化”的艺术立场在诗坛有重新抬头的趋势,官刊的运作体制僵而不死,仍然在某种权力格局中起着规范的作用,维护官刊摇摇欲坠的正统地位,这也表明诗歌纸媒的畛域之争并未尘埃落定。
新世纪诗歌“繁荣”的另一迹象是诗歌活动的虚热化。诗歌在新世纪之初似乎时来运转,有研究者用“诗,由流落到宠幸”④一语加以概括,倒也显得非常形象。新世纪诗歌一改原来“流落”的破落户形象,在日益加速旋转的时代舞台上成为粉墨登场的“宠儿”,这种变化实际上折射出在新世纪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诗歌处境的诡异之处。由于新世纪以来经济因素的强力驱动,“文化搭台”作为商业和政绩项目得到大力推广,“诗歌热”也随之升温,诗歌的文化装饰功能得到强化,名目繁多的诗歌节、诗歌研讨会、诗歌联谊会、诗歌朗诵会、诗歌排行榜、诗歌评奖等活动于是应运而生,大有遍地开花之势。值得注意的是,“与20年前不同的是,新世纪诗歌活动的大多数主办者不再是国家的文化部门,而是政府、企业、大学、私营老板等”⑤,一些诗人变身为诗歌活动家,穿梭于各种诗歌活动之间,看起来风光无限。在消费时代的成本核算中,诗歌活动的成本相对低廉,诗人是一种近乎免费的劳动力,他们一般只需要廉价的掌声和虚拟的成就感,根本不需要支付像影视明星那样昂贵的出场费,而诗人的出场作为一个文化符号会产生某种特殊效应,这又是明星演唱会无法达到的效果。这些诗歌活动的举办往往以“大而全”的模式顺应流行媒体的技术路线,抽取诗歌文化中的消闲功能或政治教化功能加以无节制地放大,以换取可能达到的商业或政绩目的,还可以形成虚假的学术繁荣征象。这些大张旗鼓的诗歌活动往往与诗歌本身无关,诗歌沦为一个炫目的幌子在招摇,在幌子的后面有一双强有力而无形的手在操控。这些诗歌活动的实质是排除与商业功利和政绩冲动相对立的异己性因素,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把诗歌文化的“纯洁”和“高端”因素转化为凸显实用价值的文化装饰功能,这也是新世纪诗歌真实处境的一个方面。
在新世纪之初由诸多复杂因素构成的文化语境中,传播渠道的通畅实际上并未抑制诗歌进一步边缘化的趋势。诗歌的困境在新的情势下反而在加剧,不过是由原来的整体萧条在繁荣的幌子下转化为隐性化发展的态势,在异乎寻常的“诗歌热”表象下形成诗歌边缘化的诡异局面,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诗人重新回到时代舞台的聚光灯下,但诗人的文化弱势地位依旧,他们被挤压在狭窄的物质空间,难以在精神世界得到真实的呼应。新世纪诗歌因某种契机或现实需要重新回到公众的视野,公众却往往以一种戏谑化的方式进行回应,在狂欢中把诗歌转化为某种泡沫性的精神刺激物或某种生命本能释放的替代性对应物,显然,其中包含着对诗歌艺术精神的深度消解。2006年的“梨花体”、2010年的“羊羔体”成为公共事件,就颇能说明一些问题。两个事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把个体写作的局限性扩大为对现代新诗写作的“妖魔化”,尽管其中也包含着公众对当下诗歌现状的不满和要求艺术提升的声音,但在大量网民混合着娱乐化和低俗化的狂欢式仿写中,也反映出公众对现代新诗惊人的无知和以无知为乐的文化消费心理。在这种现象背后,诗歌写作的严肃性和探索精神被逐出公众的视野,只剩下追求便捷与实用的大众文化市场逻辑。诗歌不便于贩卖,不像流行歌曲、电影、绘画等文艺形式可以产生直接的利润,但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利用,因此,诗歌不具有完全的文化商品属性,只能作为文化市场的补充居于边缘化的位置。当然,实际的原因可能复杂得多,但不管如何,诗歌的公众地位显然在下降,给人造成的错觉,就是诗歌在走向“消亡”。错觉的另一面则是诗歌的“繁荣”,那似乎可以理解为诗歌的装饰性“救急”效应。这种“繁荣”局面表现为局部热闹,整体萧条;内部热闹,外部冷清。还可以换一种说法,新世纪打开的文化市场有时需要一种救急用品,在情急之中恰好可以用诗歌补上。因此,新世纪诗歌的“繁荣”局面说到底是边缘化的另一种形式。然而,这种市场化的选择实质上是对诗人尊严的冒犯,诗人们抵抗诗歌的边缘化是一种正当的权利,也是有操守和创造力的诗人维护诗歌理想的基本动力,不过,在消费主义文化的总体性语境中,他们的这种抵抗可能更多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诗歌边缘化的进程在短期内难以看到遏制的迹象。
新世纪诗歌边缘化的隐性加剧导致一个直接的后果,那就是新诗文化的严重缺位。“新诗的困境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困境。呼唤一种成熟的新诗文化,是我们在回顾新诗近百年的发展历程时无法绕开的一个问题。”⑥新诗文化是中国当代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格局中,是显示民族文化特色和文化自信的高端文化形态,具有凝聚民族文化心理、激发文化创造的功能,关系到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学的健康发展。中国新诗的历史也是新诗文化逐步形成的历史,但就新诗文化积淀的整体情形来看,却包含着诸多的潜在危机,尚未在民族文化心理层面形成广泛的共识。发展到新世纪之初,诗歌边缘化的隐性加剧牵动当代文化内部的结构性调整,诗歌由于其“内在的美学原因”,不能转化为可以取得实际利用价值的“文化品牌”,被作为文化产业的边缘形式对待。在更深层的文化理念上,消费时代的文化选择突出实际的可操作性,需要在实践中落实某种直接的主题性规划,而诗歌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则往往包含着对现实的对抗性诉求,落实在世俗功用层面上,诗歌对消费文化的媚态毫无文化尊严可言,只能导致诗歌文化价值的旁落,而诗歌与消费主义文化的对抗虽能维护诗歌的文化尊严,则必然被排除在高度固化的文化市场逻辑之外。诗歌不能在文化与消费之间转换自如,其自身固有的艺术逻辑形成某种面对消费主义文化的封闭性,造成其游离于新世纪之初文化语境的孤绝处境。事实也是这样,诗歌在文化市场占领的份额微乎其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尽管社会公众乐于对诗歌事件进行围观,而诗歌的实际读者却在大量流失,在这种现象的背后,是文化消费与市场效应捆绑在一起,潜在地规约着人们的阅读取向。由于消费主义文化氛围的全方位渗透,新世纪之初的文化现实注重舞台效应,诗人的角色定位与时代舞台的“中心话语”格格不入,诗歌的文化价值与时代的舞台背景所呈现出来的总体价值选择背道而驰。诗人作为文化精英的悲剧就在这里,在大幕拉开的一刹那,他们惊惶的面孔一闪而过,消失在时代舞台深不可测的幽暗之中。实际的文化语境已经对新诗文化形成一种潜在的压抑机制,这就是新世纪之初新诗文化严重缺位的现实处境。我想,这并不是一个过于悲观的估计,而是新世纪之初由诗歌边缘化的隐性加剧所显露出来的种种迹象。同时,这种种迹象表明,新世纪诗歌的困境必须在文化层面上找到有效的解决途径。
社会公众对诗歌的总体性隔膜是新诗文化缺位的一个重要表现。尽管新世纪的诗歌传播呈现出多样化的格局,新媒体的普及有助于诗歌的文化装饰功能延伸到生活的日常层面,但实际上传播媒介的多样化并没有真正带动诗歌的有效传播,反而具有某种潜在的遮蔽性,使诗歌的传播呈现出不断窄化的趋势,这正是大众文化语境下所形成的文化过滤机制所带来的严重后果。社会公众的文化读物并不是自主选择的结果,而往往是被传播媒介经由某种精心设计的利益方式诱导和代理的结果,社会公众的阅读兴趣被大众文化塑造成一种倾向于浅阅读和浅理解的惯性阅读模式。实际上,在大众文化中包含着诗歌的敌对性因素,诗歌也被大众文化预设为一种敌对势力,诗歌的精英文化身份在大众文化语境下被处心积虑地肢解,诗歌的纯正文学品质受到潜在的排斥,诗歌的精神性内涵和内在深度只有被转化为消闲性的文化附属物,社会公众才会乐于接受,也由此造成其艺术感觉的内在弱化。在一首诗面前,社会公众不管是一脸不屑还是无所适从,实质上都是艺术感觉弱化的表现。诗歌的这种处境显然受制于一种总体性的文化语境,大众文化处于“优先阅读”序列的顶端,在文化市场中占有压倒性的份额,而作为高雅文化和精英文化的诗歌则被挤压在在大众文化的夹缝里,无法得到人们精神世界的内在呼应,在时髦的文化流行品掩盖下,社会公众对诗歌的总体性隔膜凸显为新世纪以来文化生态的一个重要侧面。另一方面,在社会公众的艺术感觉普遍变得麻木的情境下,诗歌却凸显出一种异质的新的感受性,“从人的精神处境出发,发挥诗歌的难以替代的文化批判价值”⑦。就消费主义时代的总体精神趋向而言,诗歌代表一种背离性的精神价值取向,诗歌通过向精神世界的内部生长而获得自由的文化创造空间,实际上在新世纪之初诗歌所激活的文化创造力并没有衰减,不过是在大众文化的挤压下转化为精神世界的一种内在力量而已。这一方面意味着诗人以批判性的姿态面对现实,从骨子里反对大众文化的媚俗姿态,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诗歌的边缘化包含着非常复杂的情形,“当代诗歌从公共日常交谈、高等学校教室、书店和主流媒体中惊人的消失表明,诗歌在人们的心目中正在消失或不再被想起”⑧。诗歌在受众层面的这种大面积消失固然反映出社会公众对诗歌的普遍冷漠,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诗文化缺位的峻急情势,却并不意味着诗歌本身的沦落,诗歌的边缘化在某种意义上转化为一种反向的推助力,使诗人在远离“中心话语”的边缘位置反而能够维护文化使命的纯粹性。这也就是为什么新世纪的诗歌看起来危机重重却又充满内在活力的原因。

注释:
①张清华:《持续狂欢·伦理震荡·中产趣味——对新世纪诗歌状况的一个简略考察》,《文艺争鸣》2007年第6期。
②[英]殷海洁:《中国当代诗歌的媒体化》,《新诗评论》2011年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③参见张德明:《互联网语境中的新世纪诗歌》,《中南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④徐敬亚:《诗,由流落到宠幸——新世纪的“诗歌回家”(之一)》,《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
⑤徐敬亚:《诗,由流落到宠幸——新世纪的“诗歌回家”(之一)》,《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
⑥吴投文:《中国新诗之“新”与新诗文化建设》,《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⑦洪子诚:《诗歌的“边缘化”》,《文艺研究》2007年第5期。
⑧[英]殷海洁:《中国当代诗歌的媒体化》,《新诗评论》2011年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