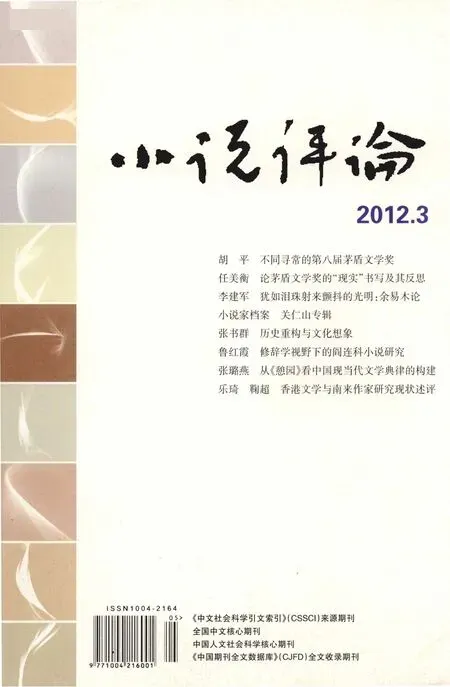从《憩园》看中国现当代文学典律的构建
张璐燕
在一个各式各样“经典”层出不穷的年代,人们以诸如“红色经典”、“鲁迅经典全集”、“朱自清散文经典全集”、“中国中篇小说经典”等名义,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甄选,一方面是势所必然的,另一方面又不禁让人心生疑虑:由于缺乏必要的距离,这些所谓的“经典”真的能经的起岁月的淘洗吗?或者说,如果真的有所谓“现当代文学经典”的话,又是哪些质素的存在,使这些作品区别于中国古典及世界文学史上的其它经典之作,而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呢?
虽然对于《憩园》的评价一直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但是,现在的大多数现当代文学研究者还是倾向于承认,《憩园》至少是包含了一些可以构成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的因素的。因此,通过分析《憩园》文本所包含的经典性因素,或许将有助于我们发现构成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的部分典律之所在。
一
与巴金的其它小说相比,《憩园》的最大特征在其复杂性。这种复杂性首先表现在小说的结构方面。相对于巴金小说经常采用的单线结构,《憩园》的结构非常类似于一出戏剧:《憩园》讲述了“我”、姚国栋、杨梦痴、万昭华、姚小虎、寒儿等人的身世经历和情感体验,故事的主体是“现在的故事”,各个人物“过去的故事”通过回溯来体现,并对“现在的故事”的发展、突变造成直接的影响。再加上瞎眼女人和老车夫的故事这条隐含线索,使《憩园》在较短的篇幅内包含了繁复的内容,“而且故事之间及其各自内部意绪的冲突构成了文本价值取向与情感指向的复杂性,形成了作品的复调品格。”也就是说,由于《憩园》中“各个故事中的多种思绪彼此诘问、相互质疑,”①即使是人物的同一行为,出于不同的价值立场和观察角度,也有着迥乎不同的认识与评价。因此,作者对于人物的价值判断在这里被暂时搁置,《憩园》在情感表达方面因此呈现出一种复杂难明的特质。
比如,在批判杨梦痴腐化堕落、自私自利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他对于家园的深深眷恋、对于美好事物的无限热爱、对于家人的真诚忏悔,都让人不由自主地对他有所宽宥;姚国栋的眼高手低、言不顾行固然让人觉得好笑,但他对朋友的古道热肠、对亲人的深挚之爱,又让人不禁对他的不幸遭遇给予深切同情;万昭华的温柔善良、充满爱心使《憩园》整体上的灰暗色调带上了一抹温暖人心的亮色,但她种种帮助别人的设想却只是停留在口头,对于所处环境的无力摆脱使她成为一只无法真正飞翔的“笼中鸟”;“我”对于社会的冷静观察、对于他人的真诚救助、对于存在意义的痛苦思索,体现出一个启蒙者的可贵品质,可“我”始终只是一个无能为力的旁观者,不管是杨梦痴、姚国栋,还是万昭华、寒儿,“我”的介入对于他们的命运没有产生丝毫的改变……
就像许多论者指出的那样,使《憩园》包含了如此丰富歧异的情感的缘由,是因为巴金本人人到中年、初建家庭,心态变为平和;是因为时代的变迁,过去家族罪恶的制造者如今也成为封建制度的牺牲品;是因为战争的艰苦环境,使巴金进一步体认到人的凡俗本性;是因为“‘我’对写作价值的消解,意味着对五四新文学确立的改良人生、疗救人生的启蒙主义功用的怀疑,一定意义上也是对时代赋予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变革社会责任的疑虑”②。这一切使得《憩园》中的人物更接近生活本身,而不是某种价值观念的载体,《憩园》因此也就成为一出关于“人”的悲剧:“《憩园》真正要哀悼的主要是作为‘人’的杨梦痴、万昭华、姚国栋等因自身存在的人性弱点而导致或将要导致的‘非人’待遇。这是难以避免却又不能不正视的人间悲剧。”③
对于“人”的悲剧的揭示及正视,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不同于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人”的意识的觉醒,使现代中国人不再把人生的希望寄托于外来的拯救上,而必须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必须独自面对“人”的生存困境并做出自己的选择。在这一选择过程中,由于发现社会的黑暗与不公、人性的丑陋与卑劣以及“人”的脆弱和无奈并产生悲剧精神也是在所难免的。在此意义上,“在文学经典的价值维度中,文学精神始终是最重要的一维,而对于‘五四’后的中国文学而言,悲剧精神及其衍生的批判精神构成了其文学精神的某种核心。”④这种现代文学精神使中国现当代作家不能仅仅满足于为读者营造一个远离尘嚣的美丽梦境,而是借助自己的作品书写普通人柴米油盐的琐碎生活和备受煎熬的内心世界,再现他们挣扎求生过程中感受到的希望与幻灭、幸福与失落,现当代文学作品由此也很难拥有简单明晰的价值判定和包治百病的万用良方,而充满了种种必须承受的人生苦痛,表现出一种浓重的悲悯意识。
二
那么,面对“人”存在的苦痛与人生的荒寒,必须自我负责的现代中国人该如何应对?以暴易暴,用自己和他人的牺牲换取未来美好生活的选择是否值得践行,就像巴金早期小说中的主人公那样?
《憩园》中对于杨家长子杨和形象的处理因此变得极富暗示性。与巴金笔下的其他“长子性格”不同,杨和不仅意识到自己身上肩负的家庭责任,更有决心和能力履行这一责任;他不会停在原处、自怨自艾,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亲人走向末路,而是一个有着铁一般手腕的坚决地行动派;他敢于挑战父亲的权威,动用自己的关系逼父亲出去工作,甚至不顾社会舆论将不成器的父亲赶出家门;在家产被父亲全部败光的情况下,他用自己的双手养活了家人,收获了属于自己的爱情,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巴金小说中少有的成功者,一个充满希望的新人。然而,与杨梦痴和寒儿对于憩园的深情依恋不同,他对这个生长于斯、充满祖辈温馨记忆的园子没有丝毫的温情,而以强硬的态度代父亲签字将憩园卖给别人;在杨梦痴已经表示了对于家人的真诚忏悔,也了解到他食不果腹的生活处境之后,杨和依然对父亲拒不接纳,这也是导致杨梦痴最终悲惨死去的一个主要原因,小说对于他心理活动的刻意回避,正反映了巴金对这一人物的复杂态度。“如果说在他身上体现了巴金的毁灭冲动的话,那么这可能不是本我的弑父冲动,而是作者内心的通过毁灭来谋求新生的欲望。这个欲望在巴金40年代之前的作品中有着大量的表现,但却是第一次被作者与无情二字如此彻底地嫁接在了—起。”⑤下意识中,巴金希望塑造一个与以往不同的强有力的人物,以满足他改变现状的强烈内在需求,却又无法接受与这种性格伴生的杨和的冷酷无情,在他身上,反映了巴金对于暴力与正义问题的深入反思,体现了巴金对于知识分子或者说文学价值的重新定位。
需要指出的是,这绝不意味着巴金对于自己前期观念的彻底抛弃。终其一生,巴金的创作中都有一种一以贯之的东西,那就是对于人类和自己民族永难磨灭的“爱”。因为这颗爱人的心,正如巴金的早期散文《我的心》所说的,“这几年来我怀着这颗心走遍了世界,走遍了人心的沙漠,所得到的只是痛苦,痛苦的创痕。”⑥巴金深深地为这无爱的黑暗世界而苦痛,并因此把寻找破除这一黑暗世界的路径作为他人生与创作最重要的目标。只不过在他早期的小说里,巴金寄希望于通过暴力来实现“爱”的目的,到了40年代则“爱”既是巴金追求的目标同时又成为祛除黑暗的手段,从而显示了他文学观念的内在调整。
某种意义上,抗战后期颠沛流离的恶劣环境使人到中年的巴金深刻感受到了自身力量的渺小与人生的无奈,他也因此认识到知识分子的价值主要不在于对于暴力革命的直接参与或倾力讴歌——事实证明这既不是知识分子所擅长的也不是可以毫无疑义地加以履行的——而在于“给人间多添一点温暖,揩干每只流泪的眼睛,让每个人欢笑”⑦,通过文学创作给读者美的享受、爱的熏陶,让他们看到人间的希望、获得前行的力量。
可是必须加以认真考虑的是:巴金对于这种“爱”的解决方式真的是绝对信赖而没有丝毫疑虑吗?相对于小虎之死这一悲剧性结局所显示的某种生活的现实性与必然性,可以在别人的影响下发生根本性转变的瞎眼女人和老车夫故事结尾的虚幻性与偶然性也就显而易见了。极具意味的是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文学作为一种虚构艺术的价值才真正得到凸显:“这个虚构的几经变更的故事展示了如下两个维度的意义:一是在现实中无能为力的“我”用白日梦的方式给虚构世界的痛苦人生一种想像的慰籍与帮助;二是对在怀疑中渐显虚妄的写作价值的重新确认,既然‘我’的写作无法成为疗救病态人生的一剂良药,那么就让它发挥一点减轻病痛的作用,以悲天悯人的态度给无望无助的人们些许心灵的安慰。”⑧文学的作用主要不是立即改变现已存在或即将到来的现实,而是由于寄托了人类对于爱与美的永恒理想,成为感受到存在的荒诞性的现代人的一条精神自救之路,其是否能够产生实际的效果是不必加以过多考虑的。
三
正是从这个角度,如果说所谓“典律”只是一种编选的角度,一种内在的价值选择,当代人不断命名“经典”、由自己选择哪些作品属于“经典”的行为本身,就是对于自我艺术鉴别能力的一种肯定,显示了当代人树立属于自己的文学价值尺度的努力,反映出一种与现代线性思维方式相一致的强烈的自我认同冲动。那么,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典律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应该是与现实生活的密切相关性。换句话说,“古人把‘经’理解为一成不变的思想权威,或超乎凡庸的圣人之所造作,其实经典所以为经典,并不在其玄学的先验权威,而只因为它全面深刻地总结了民族生活的历史经验,反映了民族命运的本质。经典也是发展的、凡俗的,和每一颗关怀民族命运的普通的心灵息息相通。”⑨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与其说是和古典文学经典一样提供某种关于生活问题的权威解释或者答案,不如说是提供一种关于生活可能性的思考,一种现代中国人对于人生价值和道路选择痛苦思考的形象,所谓“文学经典”必须有一种现代精神的融入,与其是“僵尸的乐观”,不如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如布鲁姆指出的,“……对千百万非白种欧洲人来说,莎士比亚代表了他们的伤悲,他们与莎氏用语言所塑造的人物认同。对他们来说,莎氏的普遍性不是历史的而是最基本的,因为他们的生活被他搬上了舞台。在他的人物之中,他们看到和遇到了自身的苦恼和幻想,而不是早期商业化伦敦城所显示出的社会能量。”⑩展现当代中国人的“苦恼和幻想”,批判他们精神上的种种缺陷,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通过对他们生存际遇与艰难选择的再现,促使人们真正思考有关“人”的存在的本真问题,呼唤一种更美好生活的到来,理应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必须具备的一个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如同一些审慎的学者所担忧的那样,过于轻易地将那些没有经过时间沉淀的作品目之为“经典”的举动,正从侧面显示出人们心态的浮躁和内心的极度不自信,长期以来对于他者眼光的过度重视也使我们的文学成为外来理论的演练场,使我们的一些作家和评论家成为西方观念的模仿者与操演者,而失去了属于自己的最根本的东西。其实,民族经典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可能正在于“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是谁和我们所到达的位置”⑪保持与中国特有文化传统和独特审美心理的紧密关联性,使中国现当代文学成为真正属于现代“中国”人的文学,这或许也是我们在构筑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典律时不得不注意的一个问题。
注释:
①②谭杰:《〈憩园〉:启示意图与情感真实的冲突》,《南昌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6期。
③聂国心:《〈憩园〉〈寒夜〉:巴金走向绝望的文学巅峰》,《齐鲁学刊》2009年第2期。
④黄万华:《文学精神与文学经典》,《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1期。
⑤姚新勇:《〈憩园〉:五四启蒙文学的一个转折性象征》,《文学评论》2002年第4期。
⑥⑦孔惠惠等选编:《巴金作品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470、365页。
⑧刘世楚:《〈憩园〉人物谈》,《湖北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1期。
⑨郜元宝:《鲁迅六讲》(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8页。
⑩[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⑪[意]伊塔洛·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