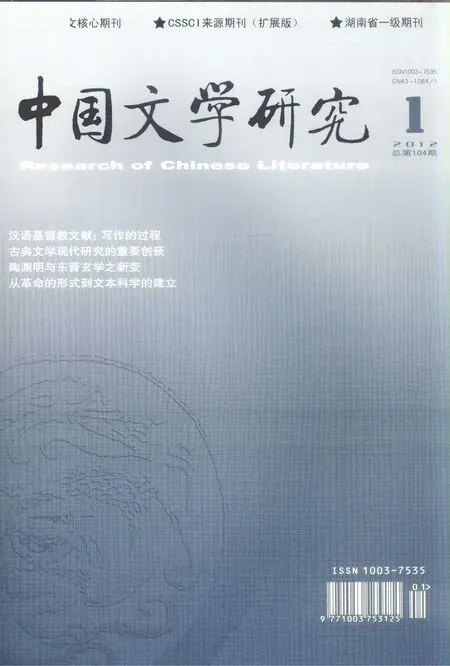赋:作为铺成、排比扩展的空间思维方式:从空间思维重释中国诗学传统赋比兴之一
邓伟龙 尹素娥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图书馆 广西 桂林 541001)
如果要从中国古代诗学中找出一个可以贯穿始终的核心范畴,那么“赋比兴”无疑是值得关注的。可以说自20世纪以来,凡是涉及中国古代文论的学者几乎均对其投以极大热情,值得我们关注的是:首先赋比兴作为中国古典诗论的核心范畴已为越来越为学者所认同,虽然其中有太多的夹缠,但这正说明了问题本身的意义与价值;其次,学者在探讨比兴时已越来越注重其艺术思维的角度〔1〕。然而问题是:在这一核心诗论范畴中,如果赋比兴都为诗歌的表现手法、技巧或创作(包括接受)的艺术思维方式,那么它们在诗歌创作中各自起到什么作用?为什么会存在重比兴而轻赋的现象呢?或许我们可能做不到像福柯那样进行一番知识考古学的研究,但正如启蒙时代所说的一句名言:“懂得了起源就懂得了本质。”那就让我们以历代文论家的阐释为基础,以当代的研究成果为参照,并引入有关时间思维和空间思维的理论成果来探寻其背后可能隐藏的秘密吧。那么什么是时间和空间思维呢?在此不得不将这个看似与本文无关的问题有所交待。
一、时间、空间思维及与文学活动
就学科而言,思维方式的研究多属于心理学的范围并可按不同原则有多种不同分类,此不多述。但是无论怎样分类,按照唯物主义物质决定意识的观点,其实任何思维都是对存在的认识,而存在是物质的存在,物质的存在总是处于运动变化之中,且时间和空间则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2〕,故作为“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和事物之间内在联系的规律性作出概括与间接反映”的“人类思维至少应当具有这样两种基本的反映形式:—是能有效地对事物的‘空间结构特性’,即……空间思维形式;二是能有效地对事物的‘时间顺序特性’即……时间思维形式。”〔3〕也就是说,时间思维和空间思维是人类思维的两种基本方式〔4〕。那么空间和时间思维有何特点呢?为不至于误解,故将学界有关论述俱引如下:
“空间思维……的基本特点就是既要从整体上去把握事物的基本属性即事物在空间的存现形式与性质,又要从整体上去把握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即空间位置及组合次序等结构关系,……反映‘空间结构特性’就是空间思维的最基本特征。……这种‘空间结构特性’不仅是某个事物通过视觉表象的具体体现,也是事物之间内在联系规律性的直观透视。”〔5〕
“时间思维……的基本特点就是从一维线性的时间轴去把握事物运动过程的本质属性,而建立在语言概念基础上的逻辑思维正好最适合这种需求。这是因为,逻辑思维可以通过运用分析、综合、抽象、概括等方法,很方便地对事物的各种属性进行思维加工,从中提炼出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概念’。”〔6〕
并且就时间思维和逻辑思维及与空间思维的关系来说:
“建立在语言符号序列的顺序性和直线性基础上的逻辑思维,尽管其优势只是对一维时间轴上展开的活动事件作出反映,但由于三维空间中的视觉景象也可转化成—维时间轴上的—系列活动事件……也就是说,它既可适用于时间思维的场合,也可适用于空间思维的场合。但就逻辑思维的实质来说,由于它是建立在语言符号序列基础上,具有一维、线性的特点.最适合反映的还是具有顺序性、持续性的运动变化过程……所以,我们并不同意……把它称之为‘抽象思维’或‘抽象逻辑思维’,更不能简称之为‘抽象思维’。而是应当科学地把它称之为‘时间逻辑思维’或‘线性逻辑思维’,其简称则为‘逻辑思维’。”〔7〕
这就是说,逻辑思维其实就是时间思维,同时逻辑思维在空间思维中也存在。这当然不是自相矛盾,因为按照现代学界的观点其实任何思维都有一定的理性、抽象即逻辑性。当然上文所引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譬如其中虽然将时间与空间思维的特点区别开来但又有截然对立之嫌,事实上任何思维同时既有时间的思维又有空间的思维;再者就空间思维的具体情况而言,空间思维不一定只存在于对事物相对静止状态本质属性和规律的反映,在动态过程中也存在并亦可进行空间思维,反之时间思维也是如此,二者只是偏胜而不能偏废。针对于文学的具体情况而言,虽然文学活动(包括创作、欣赏等)也受一般心理规律的影响,但文学活动并不是一般的心理活动,它有着自己的特殊规律。因此我们引述上文的目的在于,如何从心理学的探讨成果中得出符合文学本身的时间和空间思维的观点。
我们认为,文学既然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而人类的任何实践活动都离不开时间与空间这一人类存在的基本条件或存有状态,那么任何文学活动都会对时间与空间这一基本存有状态或条件产生思考和认识,而这些思考和认识的结果反过来又影响文学活动的整个过程。故我们认为:一、文学活动中确实存在时间和空间思维两种基本的思维方式;二、具体而言:所谓时间思维就是指在文学活动中重在运用一维的、线性的、分析的、演绎的、推理的、思辨的、甚至逻辑思维为主的类似时间顺序的思维方式;所谓空间思维就是指在文学活动中重在运用非线性的、整体的、非分析演绎的、多维意向性思维为主的类似空间立体的思维方式。一维与多维,线性与非线性,分析与整体是二者最主要的区别。在具体的思维过程中,二者都以表象或意象为思维的基本单位,但时间思维重在对意象的认识具有抽象性,空间思维却重在意象的审美注重具象性;换言之,时间思维偏重于真假之辩、思、言,空间思维重在融隔之区、感、意;前者是听觉的,后者是视觉的。故相对于时间思维来说如果文学作品所反映的情、景不真实(也指想象的真实)那么艺术价值就不高,而对于空间思维来说则真实与否并不是最重要的,艺术价值的高低系于作品营造的空间或空间感能否让人融入其中还是让人格格不入等等。如果将时间思维与空间思维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可如下所示:
空间思维 时间思维
非线性、多维 、互渗 线性、一维、因果
比喻(主观性)、视觉(可见的)现实(客观性)、听觉(可读的)
图象、意象、散点视 话语、抽象、焦点视
审美、身体、感性 认识、灵魂、理性
直觉、顿悟、直接 归纳、推理、间接
能指、形象、美感 所指、合情、合理
整体、综合、修辞 局部、分析、逻辑
读者、文字、误读 作者、声音、原义
断裂、跳跃、不确定性 连续、确定性
诗歌 小说(散文)
…… ……
不过,以上区分只是出于理解的方便相对而言,并非绝然对立的,正如时间与空间思维之间往往存在交叉、融合与互渗一样。理解了这些,就可以具体来谈赋比兴背后所隐藏的思维秘密了。因为既然赋比兴是中国古代诗歌的表现技巧和艺术思维方式,那么探讨作为技巧和思维方式的赋、比、兴其思维本身又分别有何特征?可以说清楚赋比兴思维本身的特征,也就清楚了使用具有这些特征的技巧和思维方式所创作出来的诗歌的整体风貌了。下面分而述之,本文先说赋(关于比、兴的空间思维方式我们将有专文探讨)。
二、赋比兴及轻赋而重比兴
从赋比兴出现的最初情况来看,应当说赋的地位至少不比比兴低。这无论是在《周礼·春官·大师》中:“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周礼注疏》卷二十三)还是在《毛诗序》中:“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毛诗正义》卷一,)以及后来的解说中(除钟嵘等人外)一般而言赋之位于风后而居于比兴前的位置基本不变的,即使我们现在赋比兴连用时仍将赋置于首位。再者,从赋比兴的发展演变历程来看,赋相对于比兴而言,其基本意义即将赋理解为一种铺排和叙述是夹缠最少也最明晰的。还是让我们回到原典,先来看以下几个对赋的经典解释:
(汉)郑玄:“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周礼》卷二十三,《十三经注疏本》。)
(梁)刘勰:“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文心·诠赋》,人民文学本。)
(唐)孔颖达疏:“赋者,直陈其事,无所避讳”(《毛诗正义》卷一,《十三经注疏本》。)
(宋)朱熹:“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诗集传》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清)李重华:“赋为敷陈其事而直言之,……即随物赋形之义也。”(《贞一斋诗话》,《清诗话》本。)……类似这样的观点还有很多,可见在古人心目中,无论是经学派还是审美派,虽然其表述不尽一致,但把赋作为诗歌的一种铺陈技巧或手法却基本相同的。在此我们先不评论这些观点,还是先让我们看看历代对赋与比兴的看法:
“诗之作,兴,上也;赋,次也;”(〔宋〕杨万里《诚斋集》卷六十七,《四库丛刊》本。)
“赋实而兴虚,比有凭而兴无据,不离字句而神存乎其间,神之在兴者十九,在赋者半之。”(〔明〕彭辂《诗集自序》,《明文授读》卷三十六,味芹堂刻本。)
“比兴是虚句活句,赋是实句。有比兴则实句亦为活句,无比兴则实句变成死句。”(〔清〕吴乔《围炉诗话》卷一,《清诗话续编》本。)
“唐人诗宗《风》《骚》,必兴多。宋诗比兴已少,明人诗皆赋也,便觉板腐少味。”(〔清〕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四》,《通志堂集》卷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作诗最忌敷陈多于比兴……”(〔清〕方南堂《辍锻录》,《清诗话续编》本。)
“作诗者若有赋而无比兴,则诗心凋丧……”(〔清〕潘德舆《养一斋李杜诗话》卷二,《清诗话续编》本。)……
如果追溯得更远一点,早在南北朝时期刘勰、钟嵘等在其《比兴篇》和《诗品·序》中亦可看出其对赋的轻视,此不多述。但到此可以切入我们的问题了:为什么古人对于赋的观点无论是作为诗歌的技巧还是方法,但轻赋而重比兴却几乎众口一词?不要以为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其实正如傅修延所说:“方法毕竟是主体的工具,是主客体相联系的中介。……文学观念的变革有赖于思维方式的变革。恩格斯说方法是对象的类似物,我们想大胆地发挥恩格斯的这一观点:方法不仅是对象的类似物,而且也是主体的类似物。”〔8〕也就是说,文学方法的选择体现一定的文学观念,文学观念的生成却依赖于一定的思维方式。故我们认为作为赋比兴的方法反映着古人的文学观念,而这种文学观念的背后却隐藏着支撑这种观念的思维方式。而作为古人对诗歌表现技巧或方法以及轻赋而重比兴的几乎众口一词的观点,恰恰表明古人对诗歌文学观念的一致性,而这些又体现了其思维方式的根本一致,反过来说也惟其思维方式的根本一致才会有文学方法、观念的基本相同或一致。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呢?
三、赋:作为铺成、排比的扩展空间思维
首先,我们先论述作为诗歌表现方法或技巧的赋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以前学术界多认为古人之所以在赋比兴三者之中轻赋而重比兴,是因为赋注重铺排叙事,而中国古代诗歌的传统在于抒情言志,这当然正确。但即使同是叙事,西方与中国传统又有何区别呢?为了说明清楚,我们先引《伊特利亚》第二卷4第3—47行的诗句和《诗经》中被认为是赋诗或者说是用赋的手法写成的例子:
1、“他穿上新制的细软的衬衣,
套上宽大的披风,于是在端正的脚上
系上一双漂亮的鞋,把镶银的刀
挂在肩上,然后拿起王国的笏
这是他的永远不坏的法宝。”〔9〕
2、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或负其糇。三十维物,尔牲则具。/尔牧来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尔羊来思,衿衿兢兢,不骞不崩。麾之以肱,毕来既升。(《诗经·小雅·无羊》)〔10〕
试比较一下上文所引的例子,很明显如果我们将前者五行“诗”改变一下排列方式,不以分句排列而把它们联成整段文字,那么它与小说或散文几乎是没有任何区别,同时如若把这五行的顺序打乱或颠倒一下,那么其结果会让人不知所云。而《诗经》中的诗句即使不以分行排列仍然是美妙的诗,并且即使将其中的每章顺序打乱重新组合,并不太会影响人们对诗的理解,这是为什么呢?其中的原因肯定很多,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正如今道有信曾说:“西方对人类存在的根本理解,把重点放在时间上。”〔11〕反映在文学中则即使在诗歌中其叙事也重在按因果的、逻辑的、线性的、时间的顺序进行,可以说传统的西方文论更多地是一种时间模式的分析,这不仅体现在其史诗传统中,就连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对古希腊悲剧的分析,所注重的就是作品在时间层面的展开:所谓“悲剧是对于一个完整而具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所谓的‘完整’,是指事之有头、有身、有尾。”〔12〕到黑格尔那里这种时间的展开则更是表现为理念的最后胜利(《美学》第一卷),而后来发展出的叙事学、甚至人物性格和心理分析可以说都是建立在时间模式之上的,同时对时间模式的注重也同其对逻辑的兴趣联系在一起,如在古典的学科中,修辞总是被语法和逻辑的分析所吞没。而中国古代作为诗歌表现技巧、方法的赋并不是或至少不是严格地按照因果的、逻辑的、线性的、时间的顺序进行,赋的主要功能并不重在叙事而重在铺排、敷陈,所谓“赋之言铺”,“赋者,铺也”,“赋者,直陈其事”……也就是说赋就是将诗人的所见所闻所思的内容按其所需而非按其必然的展现出来,其目的不在于线性时间的演绎,而在于生动空间的展出!基于此我们认为:作为诗歌创作方法、技巧的赋其实就是一种空间创造的方法、技巧,而支撑这种技巧和方法的思维方式就是空间思维方式!
是不是这样呢?从上文对时间思维和空间思维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实所谓“赋者,铺也”这一诗歌表现手法就是将所要的描绘对象栩栩如生地一一刻画铺陈出来的空间营构的技巧,是空间的铺排的生动展出!朱光潜先生在论述诗与散文的骈偶起源时认为骈偶化起源于赋,他说:“何以说诗和散文的骈偶化都起源于赋呢?赋侧重横断面的描写,要把空间中纷陈对峙的事物情态都和盘托出,所以最容易走上排偶的道路。”〔13〕这一段话虽然探讨的是骈偶的起源,但“赋侧重横断面的描写”与“把空间中纷陈对峙的事物情态都和盘托出”却表明了赋作为空间展出的突出特点。同时在古人对赋的认识中,无论“铺采摛文,体物写志”,还是“寓言写物,错杂万物,”“匠事布文,以写情也”等都是强调赋之物、事与志、情等之间的多维意向性关系而绝非只是对事、物、景的简单的描绘;再者在心与物的关系上,刘勰云:“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纪昀的评论称:“随物宛转与心徘徊八字,极尽流连之趣,会此,方无死句。”〔14〕请注意随物宛转和与心徘徊,这就是说赋不是一维的、线性的认识与被认识关系,也不是分析演绎的逻辑推理,诗人从受到物色影响、呼唤、感召,到运用语辞文字将物类联系起来,这物类并不是提供分类的认识对象,而是心物交融的审美空间〔15〕。李仲梦说:“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也。”(胡寅《斐然集》卷一八,《四库全书》本)所谓“叙物”,不仅是一个“铺陈其事”的问题,还必须和“言情”结合起来,只有把作者的情感和客观的物象表现得淋漓尽致、维妙维肖才是赋。
如果我们再将作为文体的赋尤其是汉赋纳入我们的讨论范围,那么赋其实就是一种最直观的空间方位叙事艺术!而什么是空间方位叙事呢?李立这样解释:“是指从空间视觉思维出发的叙事艺术”,它“既是描绘外部世界的艺术手段,也是观照外部世界的技术方式。它是以具有叙事性质的空间联结形式而展现的,这种带有叙事性质的空间联结形式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平面或立体的方位联系,而是以叙事主体为中心或基点的前后、左右、上下、天地之间的联通,体现的人与包括天地在内的世界融通与联系。”〔16〕赋作者骋目游心,在“苞括宇宙,综览人物”之时,力图表现出空间的广阔,从而也就使本属时间艺术的赋,带有空间艺术的特征,将时间的延长、移动,化为空间的拓展。而所谓“苞括”、“综览”便是汉赋开展的空间结构;“赋家之心”乃是赋家的以心理空间图式为形式的审美及创作心理。如若避开汉赋的文采工艺特性,可以说,“没有空间世界及其结构,便没有了汉大赋,开展着的空间是汉大赋一切表象形式的统率者。”〔17〕对此邓乔彬先生说:“汉赋这种……与绘画的‘以时观空’极相似,尤与国画的长卷相近。它们都以观赏中的时间的持续绵延,感受到空间的无穷扩展,并使形象唤起的想象得以在广阔的空间驰骋。”〔18〕其实在作为人类成长标志的感性精神中,自然地包含着空间意识、空间感觉的重要内容,这一内容内化形成的感性思维的基本定势就是心理空间图式。而对空间的想象与夸饰是受着以心理空间图式为特征的感性思维定势驱动的。这一图式运动的形式所赋予的对象物的形式便是:并列铺排、横向展开以及外在涂饰。因此,汉大赋铺排、弘富、繁丽的空间世界,都是以空间图式为基本定势的人类感性思维的产物。同时汉大赋虽写特定的现实空间,却综览八方,“苞括宇宙”,对有限的现实空间,进行了无限的艺术夸张,而且汉赋的艺术张力就存在于它的空间结构以及经其组合控制而塑造成为千奇百怪的事态与物态之中,离开这些,要欣赏汉赋不是茫然无措便是误读错解〔19〕。到此可见文体赋的创作是空间图式这一人类感性思维的产物,赋之为文,就是空间思维的结果。如果再联系到现代心理学研究的相关成果,人类的思维包括归纳推理都起源于对空间关系的认识,那么这些论述则无疑是深刻的,因为不仅因果性起源于人类对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的认识,而且一般意义上的时间关系可以还原于空间关系,且归纳推理源于对因果性的认识,因果性起源于时间关系,而时间关系又是空间关系的衍生,因此,归纳推理起源于对空间关的认识〔20〕。
再就具体的汉赋作品来看,在费振刚等校的《全汉赋》〔21〕中,所收作家82人,所录作品297篇,其中完整或相对完整的赋文约161篇。据李立研究,这161篇赋文中,约42篇作品在创作中运用了空间方位叙事方法,涉及作家23人,方位叙事91句,均占各数的四分之一以上。并且汉赋的空间方位叙事主要有左右式,前后式、南北式、东西式、阴阳式、上下式、东西南北式、前后左右式、东南西北式、东南西北上下式十种形式及平面直线型、立体直线型、平面四方型、平面圆型、立体圆型五种空间方位叙事类型;其中平面直线型、平面四方型和立体直线型叙事是最常见的类型,其涉及作家、赋文篇数分别为20与30,9与15,10与13〔22〕。陆机在《文赋》中说:“必所拟之不殊,乃暗合于曩篇。虽杼轴于予怀,怵他人之我先。苟伤廉而愆义,亦虽爱而必捐。”文章最忌雷同,那么这些汉赋作家们如此热衷于这些几相类似的空间方位叙事呢?答案可能会有很多,但我们认为其恐怕与作为文体的赋所使用的本身就是一种空间思维方式和空间营构技巧、方法的赋(铺陈)不无关系,也就是说,文体之赋就是将赋比兴之赋的那种空间铺陈、方位叙事的技巧及空间思维方式一脉相承并发展至极致的结果!
另外,从赋的接受来说,赋绝非线性的、一维的、逻辑分析推理的时间思维可以容纳的,它必须调动读者全部的感官和才智,全心身的投入,流连其中,因此是典型的多维的、非线性的、非逻辑分析推理的空间思维。对于这点王世贞有着精彩的论述:“骚览之,须令人裴回循咀,且感且疑;再反之,沉吟嘘唏;又三復之,涕泪俱下,情事欲绝。赋览之,初如张乐洞庭,褰帷锦官,耳目摇眩;已徐阅之,如文锦千尺,丝理序然;歌乱甫毕,肃然敛容;掩卷之余,彷徨追赏。”〔23〕虽然此处王世贞将骚、赋分而言之,但言骚亦可用之于赋,其所谓“裴回循咀,且感且疑”、“沉吟嘘唏;又三復之”、“耳目摇眩”、“彷徨追赏”都是在说在欣赏骚、赋时那多维互动的非一维、非线性、非逻辑分析推理的空间思维的特征。从上可见,赋其实就是一种铺成、排比、扩展的空间思维方式!
四、作为铺成、排比的扩展空间思维之赋的缺陷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中国古代诗歌强调的是空间建构,但为什么却轻视同是空间思维方式的赋而重比兴呢?我们认为答案还应从赋本身入手。其实从上文的论述中我们多少可以看出:赋虽然是一种具有空间思维的思维方式,也是一种空间建构的技巧、方法,但是它在具体进行空间建构时,却又多多少少受到线性的、逻辑的、理性的思维方式的干扰,也就是说这种空间思维夹杂着更多的时间思维的痕迹。就以赋最典型的空间方位叙事为例,虽然在由上、左、前而下、右、后;经东而西而南而北等等的铺陈、排比中,空间是展开了,但同时主体的思维还是或多或少需要理性的安排、条理的分析甚至逻辑思辩等的参与,这就与古人强调的即目即景、一触即觉、整体直观有相悖之处了。就现有记录关于赋家作赋的具体材料来看,司马相如作《子虚》、《上林》近百日乃就。(《西京杂记》卷上)扬雄作《甘泉》,“为之卒暴思精苦,赋成,遂困倦小卧,梦其五脏出在地,以手收而内(纳)之。及觉,病喘悸,大少气,病一岁。”(《北堂书钞》一百二引桓谭《新论》)张衡作《二京》历十年乃成。(《后汉书》本传)以至以后左思接踵《两都》、《二京》构制《三都》,闭门构思,十年乃成。(《晋书》本传)王芑孙云:“作赋之功,固以淹迟极妙也。选义按部,既待捻髭。招字就班,几经搔首。俯俛有无,怊怅阙失。阙而存之,久乃录焉。所以子建七步之奇,不夸于赋,子云甘泉之奏,独致肠出。”所以他说“赋自不关妙悟”。(《读赋危言·审体》,据何沛雄《赋话六种》增订本,香港三联书店版)很明显这种要作者经年累月,弹思竭虑的创作如果没有理性、逻辑、思辨的思维参与是不可能成功的。
同时,在使用赋进行创作时,物、景、事、象与志、情、意、境、之间往往并非自然而然的切合一起,而是需要人为的努力,所谓“叙物以言情”即如此。在这个过程中,高明者可能会做到浑然一体、水乳交融,但下之者却景是景,物是物,情是情,意是意,二者不能完美的有机融合,也就是说物质的、自然的空间不能与主体的情感、审美的空间合二为一,即使能达到这点,也为中国古代审美标准中的重自然浑成而轻人工雕琢而视为等而下之的。
再者,由于赋多为“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这似乎更符合作为时间性的语言艺术的表现需要,但同时却往往言尽意亦尽而落了古人所谓的“言荃”了。在接受中因而也就少了一种“迂回”(〔法〕弗朗索瓦·于连语),缺了几分含蓄,丧失了耐人寻味的品质,直言之即令人想象驰骋的审美的空间打开不足。
最后,也正是由于赋重在“直书其事,寓言写物”、“铺采摛文,体物写志”,故其结果是赋可能对事物的描绘精细,但却不可能穷尽万事万物,因而是实有余而虚不足,而在中国古代审美思想中,重要的不是实,而是实后面的虚,经由写出的字面的实而进入更广阔的虚,虚实相生空间才会更加开阔,也才是最高的境界,可是赋种空间思维方式在建构空间时却较难达到这点。实多则虚少,这种类似橡皮筋的规律使得赋在诗歌创作中往往难以超越。所以古人说:“正言直述,则易于穷尽,而难于感发。”(〔明〕李东阳语),“赋是实句,……无比兴则实句变成死句。”(〔清〕吴乔语)“有赋而无比兴,即乏生动之致,意味亦不渊永,结构虽工,未足贵也。”(〔清〕冒春荣语)非大言欺世,乃切中赋之弊的。
如果以上推论大致不错,那么就可以为赋的探讨作一个简单的总结了。我们认为赋既是一种空间建构的技巧或方法,又是一种空间思维的方式,赋的运用就是一个空间的展开,它和比兴一样,一起为建构富有空间感的诗歌艺术服务。但这种方式仍或多或少并较明显地需要线性的、分析的、思辩的甚至逻辑的时间思维参与,这较之比兴更甚,同时其本身仍具有时间思维的痕迹,因而古人既将其作为诗歌创作的重要方法,又对其于比兴而言视之以轻且越到后来越是如此也就理所当然了,而其背后所隐藏的秘密则是时间与空间思维的方式。
〔1〕关于这一个世纪来“比兴”研究的学术观点可参看李健.比兴思维研究——对中国古代一种思维方式的美学考察〔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17.
〔2〕李秀林等.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3〕、〔5〕、〔6〕、〔7〕何克抗.创造性思维理论——DC 模型的建构与论证〔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3、20-21、21、22.
〔4〕参见周报林、刘啸霆.论时间思维和空间思维〔J〕.学术交流,1990(5).
〔8〕傅修延,黄颇.文学批评思维学〔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2-3.
〔9〕转引自莱辛著、朱光潜译.拉奥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86.
〔10〕(清)阮元校注.十三经注疏〔C〕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438.
〔11〕(日)今道有信.东西方哲学美学比较〔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179.
〔12〕亚里斯多德.诗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25.
〔13〕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M〕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185.
〔14〕(梁)刘勰著,(清)黄树琳注,纪昀评.文心雕龙注〔M〕.台北:世界书局,1980.162.
〔15〕可参见宇文所安著,王柏华、陶庆梅译.中国文论与评论〔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290;黄冠闵.神与物游——论《文心雕龙》中的想象中介问题〔J〕.台湾:《汉学研究》,2005(1):165-192.等
〔16〕、〔22〕李立.论汉赋与汉画空间方位叙事艺术〔J〕,文艺研究,2008(2).
〔17〕、〔19〕杨九诠.论汉大赋的空间世界〔J〕.文学遗产,1997(1).
〔18〕邓乔彬.汉赋的美学特征〔EB/OL〕.http://tieba.baidu.com/f?kz=107601389.
〔20〕参见蒋柯、熊哲宏.从因果性到空间关系〔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7);颜青山.认识发生的空间维度——兼评皮亚杰学说的心理学地位〔J〕.武陵学刊,1996(4).等。
〔21〕费振刚、胡双宝、宗明华辑校.全汉赋〔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23〕王世贞.艺苑厄言〔A〕.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C〕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962-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