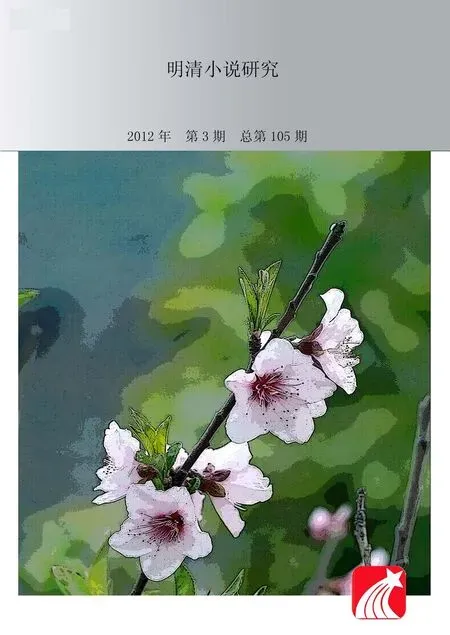明清剑侠小说文化观剖析
··
明清两代,剑侠小说创作十分流行。文言小说数量众多,编辑选本风行一时,出现了在文学史上较有影响的《剑侠传》、《续剑侠传》等文言小说集。白话小说创作也是成绩斐然,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长篇小说类型,具有比较明显的文体特征和文化印迹。尤其在文化观念上,其独特而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更能突出地体现这一类型小说的“异度空间”。鉴于学术界对此研究领域的欠缺,本文拟从修行观、生命观、宇宙观和情爱观四个方面予以论述,试图对明清剑侠小说的文化观进行一次较为系统而全面的考察,剖析其独特的“基本文化架构”,以便读者能够较为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这一文学品类①。
一、道侠一体的修行观

剑虽是神物,未经仙家“炼”过,仍不合用,须剑侠施以法力才有神通。《童之杰》中女剑侠对童之杰的宝剑这样评价:“此道家荡魔剑也,非吾辈所用者,故须人力,始克奏功。若吾剑之飞腾变化,则行之无阻矣。”②可见它与剑侠所炼之剑有别。剑侠所用之剑经过法力煅造,能搓剑成丸,大小随意,且具有驱魔意识。《仙侠五花剑》中公孙大娘的五花神剑——芙蓉青剑、葵花黄剑、榴花赤剑、藓花黑剑和桃花白剑,是她“在丹房采日精、月魄、电火、霜花并雷霆正气而成,其质非钢非铁,乃是落花之液酿成。每花只取乍落的第一瓣,故得先天第一肃杀之气,和以铅汞,计凡千炼始成。剑质可以吹毛使断,濡血无痕,削铁如泥,砸石成粉”③。五花神剑由于经过剑侠公孙大娘的冶炼,可以飞行变化,具备极大神通,其中芙蓉青剑尤其了得。剧贼燕子飞得了此剑,为非作歹,众剑仙居然无奈他何。为了制服此贼,公孙大娘又炼成霜锷丸,花了361天时间,“这剑丸乃取百花上所受之霜,积而为液,和以铅汞,锻炼而成”。百花经霜而凋,以霜锷丸破五花剑,实有天然相克之理④。霜锷剑丸炼成后,众剑仙终于将燕子飞铲除。郑官应《续剑侠传》中收录明代钱希言文言小说《青丘子》,较详细地描述了剑侠“炼剑”的过程:
室中有药鼎,高数尺,周遭封固,紫焰光腾,照耀林壑,第教生以守炉看光,添縮薪炭,不得擅离妄视而已。每昼则有玉女持稠膏一筒,投鼎中,搅和之,鼎中声类霹雳。夜半则有青童复持稠膏,依前沃入,其声漰湱如旧。此室之中,玉女二人,青童二人,更番直应,日以为常。生偶问及鼎中何物,皆笑而不对。先生已具知之,愠怒诟责,便欲驱逐出门,众相跪请,乃止,后遂不敢发问。久之,丹鼎成矣。出其金液,计可六百余斤,分而为二,又折至七八斤而止。移至大磐石上,捣之,昼作夜息,渐渐而薄,因成铁片。择甲午、丙午诸日,铸成六剑,悬于绝壁之下,以飞瀑溅激其上,日月之光华烛之。历经旬朔,剑质始柔。此六剑各有名目,先生举一畀生,令童子开启脑后臂间藏之,亦无所苦。⑤
青丘子隐居深山炼剑,有专备炼剑的净室、药鼎,有青童玉女守炉看火,金液出炉后,又在大磐石上昼夜锤捣,并以飞瀑溅激,以日月光华照耀,方才炼成宝剑。这类详尽的“炼剑”描写无疑是道教冶炼金石制作丹药过程的形象叙述。
上述炼剑属于“外炼”,更具有宗教想象力的是“内炼”——“以气炼剑”。《女仙外史》第8回九天玄女教唐赛儿“以气炼剑”:
(玄女娘娘)就把剑来,如屈竹枝一般,哗哗剥剥粉碎若瓜子,都吞在口内,咽下丹田。瞑目坐有半日,只见玄女娘娘微微张口一呼,一道青气约丈有七八尺,盘旋空中如虬龙攫挐之状。飞舞一回,将气一吸,翕然归于掌上,是一青色弹子,付与赛儿道:“此剑也,你再吞入丹田炼它九日,就能出没变化。”又传以炼剑之法……赛儿将青丸吞下,按秘传之诀,以神火锻炼五日,觉在腹中盘曲旋绕,或伸或缩,也就张口一呼,见青炁飞向空中,长有七丈余,不觉大骇。遂忙忙吸入,再加锻炼,只觉腹内动掣有力,不能容受,只得仍然呼出。在空中旋舞片刻,再吸入时,越不能容。赛儿知道必有差错,乃静候玄女驾临。⑥
九天玄女的“以气炼剑”法是道教“服气术”与内丹术的夸张表述。“服气”是道教中以气息吐纳为主的炼养方法,其理论基础是道教生命元气论。道教把“气”作为生命赖以维持的根源之一。道教经典《太平经》宣扬“气本论”,《老子想尔注》中有关于聚气成形的修仙大法,《云笈七签》综论“行气”、“调息”、“吐纳”的“诸家气法”,认为:“人与物类,皆秉一元之气而得生成,生成长养,最尊最贵者,莫过于人之气也。”⑦内丹修炼是以人体为鼎器,以精气神为药物,在意念的操作下掌握阴阳和合的火候,根据“逆而返还”的道理,使周身气息从“有”归“无”,达到“五气朝元”的境界。鼎器、药物、火候是内丹修炼的三大要素,唐赛尔就是因为没能掌握火候,炼剑过程便出现了差错。
“以气炼剑”的情节虽是小说作者的艺术夸张,但有道教理论为依托。《真龙虎九仙经》中在“炼精华为剑,巡游四天下,能报恩与冤,是名为烈士”四句经文下有唐代著名道士罗公远、叶静能的注文。罗公注曰:“第七气侠,唯学定息气,便将精华炼剑,剑成如气,仗而往来,号曰气剑也。”叶公注曰:“侠剑者,先收精华,后起心火,肺为风鞴,肝木为炭,脾为黄泥,肾为日月精罡也。肾为水脾,土为泥模,身为炉,一息气中,为法息成剑之气也。”⑧经文及罗、叶两人的注,可以看作是对“以气炼剑”的宗教理论阐述。
除了炼剑之外,剑侠在修行中还特别重视服食丹药,以此作为修行的重要辅助手段。中国传统观念一直认为食用药物可以除病消灾、延年益寿。《列仙传》就大量记载了凡人因服食天然药物,不饥不寒,身轻如飞,返老还童,长生不死。道教对这种服食观念加以继承、吸收,使之理论化,形成了效乾法坤、颠倒五行的金丹修行理论。东晋道士葛洪在《抱朴子内篇·金丹》中说:“余考览养性之书,鸠集久视之方,曾所披涉篇卷以千记矣,莫不皆以还丹金液为大要者焉。然则此二事,盖仙道之极也。服此而不仙,则古来无仙矣。”⑨葛洪还对这种“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的金丹养生术进行了理论探讨。受此影响,小说中的剑侠往往在修行中借丹药改变气质,增进功力。《淞隐漫录·姚云纤》写姚云纤学剑:“尼启甲得红白丸各一,令斋戒沐浴,然后吞之。十日后,自觉身轻捷如猿猱,力能举重物。每晨于庭中舞双剑,人但见万道寒光,绝不睹其身;空中有鹰隼过,飞剑掷之,无不下堕。”⑩《仙侠五花剑》中白素云是一个娇怯怯的女子,学不得剑术,红线便给她吃了一粒金丹,使其易筋换骨,气质大变。《绿野仙踪》冷于冰向徒弟介绍丹药在修行中的作用:
丹药乃天地至精之气所萃结,非人世宝物可比,不产于山,定产于海。既系珍品,自有龙蛇等类相守,更兼妖魔外道,凡通知人性者,皆欲得此一物食之,为修炼捷径,较采日精月华,其功效倍速。仙家到内丹胎成时,而必取自于外丹者,盖非此不能绝阴气,归纯阳也。
小说第93回又详细介绍各种仙丹在修行中的作用。此类服食仙丹与修行相济,增进功力,速成剑术的描写,是剑侠小说常见的情节。
除了服食与炼剑,剑侠的修行还包括行侠人间,干预社会,这是为了“外积功德”。《程元玉店肆代偿钱 十一娘云冈纵谭侠》中剑侠韦十一娘说:“世间有做守令官,虐使小民,贪其贿又害其命的;世间有做上司官,张大威权,专好谄奉,反害正直的;世间有做将帅,只剥军饷,不勤武事,败坏封疆的;世间有做宰相,树植心腹,专害异己,使贤奸倒置的;世间有做试官,私通关节,贿赂徇私,黑白混淆,使不才侥幸,才士屈抑的。此皆吾术所必诛者也。”《绿野仙踪》火龙真人收冷于冰为弟子,特意叮嘱:“凡有益于民生社稷者,可量力行为,以立功德。”并借冷于冰之口称:“修行一道,全要广积阴功,不专靠宁神炼气。”第45回更明确指出:“玄门一途,总以渡脱仙才为功德第一……其次莫如救济众生,斩妖除逆。”小说中的剑侠总是把扶正祛邪、解救生灵作为修行的必要功课,自觉地担当起“替天行道救苍生”的重任。《墨余录·河海客》中总宪公子依仗权势,强抢民女,欺压百姓。剑侠河海客身居海外,特意赶来为民除害,他对总宪公子说:“余本越人,幼学剑于太华山,术既成, 即遨游海内,专理人间不平事。今闻汝父子恶稔已极,特来除之。”《剪灯余话·青城舞剑录》中真无本、文固虚两位剑侠,隐居深山修道,但仍关心国事,时常出山诛杀恶人,亦仙亦侠,所谓“英雄回首即神仙”。剑侠修行,既要内炼为本,又需外积功德,内外兼修,才能功德圆满。
服食与炼剑是内炼气质,替天行道、干预社会是外修功德,不论是“内炼”还是“外修”,剑侠的修行都与道教密切相关。内炼气质采用的各种手段,如服食丹药,行气导引,吐纳调息,以及内丹修炼的“和合阴阳”、养心炼神等都是道教的炼养方技,而外修功德也与道教的“救世济物”的修道信仰相通。道教宣称:“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乐人之吉,悯人之苦,赒人之急,救人之穷,手不伤生,口不劝祸,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主张“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祸,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功也”。甚至认为“人欲地仙,当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由此可见,剑侠的替天行道与道教的救世济物实是同质异构。
就修行理念、修行实践而言,道与侠是融为一体的。道教贵生重气,修心养命,形神俱炼,追求永恒,为此创造了多姿多彩的炼养方技。剑侠修炼“剑术”虽是意欲掌握救世济民之术,但最终目的还是通过修炼超越生命,成为与世长存的剑仙。除了修行目的与道教一致外,剑侠修行的手段也完全照搬道教炼养方技,剑侠修行的过程就是修道成仙的过程,仙侠走在同一条路上。
二、超越自然的生命观
在世界万事万物中,生命是最神秘、最重要的客观存在。从本质上看,生命涵盖了“形”与“神”两个方面,探讨“形”与“神”的关系就是剑侠小说生命观的首要问题。“形”指的是生命的形体样态,包括躯体的外在形状和铸成躯体的诸多器官、血液、筋脉等;“神”指的是躯体内部的指挥系统。“形”是物质性的客观存在,而“神”则是精神活动;“形”与“神”相互依存、相互作用。《荀子·天论》云:“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臧焉。”这种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使躯体具有意识,生命得以维持。
按照大自然的规律,个体生命有一个从诞生趋向消亡的过程,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小说中剑侠修炼剑术的目的是超越生死,迈向永恒。《绿野仙踪》的冷于冰在经历了仕途失败和师友病亡之后,对现世人生产生了幻灭感,“觉得人生世上,驱名逐利,毫无趣味”。第5回他对众人说:“我如今四大皆空,看眼前的夫妻儿女,无非是水月镜花,就是金珠田产,也都是电光泡影。总活到百岁,也脱不过死之一字。苦海汪洋,回头是岸。”于是弃家访道,立志成仙,最终在火龙真人的指导下成就仙业。《亦复如是·何配耀》中道人用剑术除去何配耀附身恶魔,并“索纸七张,每张上各画一圈,其大者可径尺,依次叠小,至如一粒粟。曰:‘先以大圈粘壁上,终日兀对,令心不出圈外,七日内心气可足。若功力不懈,七圈皆用,效当自知。’何如法行之,至四十九日,心地忽然明澈,飘然而去,不知所终”。修炼“剑术”可以超凡入圣,得道成仙,有限的生命个体通过勤学苦修,坚持不懈,可以超越自然,长生久视,这是剑侠小说对生命形态的一种诠释,反映了明清剑侠小说超越自然的生命观。
在明清剑侠小说中,剑侠的成仙得道大都是形神一致的,即以肉体凡胎修成神仙。但也有形神分离的。《七剑十三侠》里草上飞焦大鹏在赵王庄阵亡,剑侠傀儡生在他阵亡之时,将他的灵魂度回山去炼魂七日,炼成仙道。之所以如此,书中写道:“但因余七妖术厉害,凡胎肉骨,都不能进去破他,须要脱了凡胎,方能前进。”焦大鹏脱了凡胎后,跟随玄贞子炼成剑术,“他本是无影无形的,因傀儡生把他魂灵炼过,要现形便与凡人无二”,因此不怕天罗地网、迷魂妖法,立下奇功。焦大鹏的成道过程是“形”“神”分离,兵解成仙。对此,小说有一番解释:
你道怎的为兵解成仙?仙家有一派流传,要度脱凡人成仙,必要此人死于刀兵,可脱凡胎,这就名为兵解。并非是旁门左道,不过是个外功。与玄贞子内功一道,略有分别。内功是凡胎肉骨,亦可飞升;外功必须脱了凡胎,方能成功。二者虽有内外之分,并无高低之别。
小说将弃尸成道与肉身成道都视为玄门正宗,没有高低差别,只是修道方法不同而已。在小说中,“兵解”又称“尸解”,有诸多描写,如《遁窟谰言·飞剑将军》中剑侠吴思演死于刀兵,“吴之亲丁来收其尸,纳之棺中,载至苏州乡间唤人舁于冢上,举之觉甚轻,启而视之,已无所有,惟留常日所用一剑而已”。《淞隐漫录·廖剑仙》中剑侠廖蘅仙“将没时,晨起见白猿至,叹曰:‘我其死乎?’即服衣冠,危坐堂中,近瞩之,则已体冰气绝。及殓,有双剑出自鼻中,直入霄汉而杳。人以为尸解云”。《淞隐漫录·许玉林匕首》中剑侠许玉林与妻子双双死于匕首,亲友为其办丧事,“及举槥入土,轻若无物,异而启视之,并空棺也。人咸以为生与女皆剑侠者流,游戏人间,借尸解仙去”。《徐笠云》一篇对尸解的描述更为形象、具体。小说中一幼妇与僧通奸,并与之合谋杀死丈夫,事发后,按律当斩。“弃市之日,妇与僧神色扬扬自若,首虽陨地,身犹僵立不仆,腔中绝无滴血;群见有小人二自腔出,仿佛僧与妇状,冉冉上升。生亦目睹,忿然曰:‘岂有修成剑术而为此坏法乱纪之事乎!’掷剑向空,二小人随剑俱堕,身首异处,倏忽入地而没,旋即尸仆血流”。幼妇与僧炼魔入道,企图借兵解飞升,却被徐笠云以剑术阻止。篇中幼妇与和尚的“神”被描绘成小人般的形体,脱离肉身,冉冉升空,这类无形的“神”凝聚成为有形的婴儿的描写,对后世剑侠小说影响极大。
明清剑侠小说对生命形态的描述有着浓郁的宗教文化色彩。生命中的“形”与“神”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各种宗教高度关注并反复阐述的问题。道教认为,生命以“道”为始基,因道化气,以“气”为生。《长生胎元神用经》云:“炁结为形,形是受炁之本宗,炁是形之根元”,“神以炁为母,母即以神为子,子因呼吸之炁而成形,故为母也。形炁既立,而后有神,神聚为子也”。“炁”同“气”,在道教经典中常常出现。生命中的“形”与“神”都是因“气”而生,成为生命存在的不可或缺的两种要素。对于两者的相辅相成,《西升经·神生章》这样阐述:“盖神去于形谓之死,而形非道不生,形资神以生故也。有生必先无离形,而形全者神全,神资形以成故也。形神之相须,犹有无之相为利用而不可偏废。惟形神俱妙,与道合真。”所以道教主张形神俱炼,性命双修,超越生死,肉身成仙。
佛教也关注生命中的“形”与“神”。佛教认为,世间的一切事物,包括各种物质现象、精神活动,都是因缘和合而生,都在迁流转变之中,所有的一切都是变化无常,没有常住不变、永恒静止的事物。佛教称为“诸行无常”。既然世间的一切都是变化无常的,那么就不存在能独立自生、永恒不变的精神主宰,这就是“诸法无我”。佛教所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但佛教在否定“我”(精神主宰,或曰灵魂)的存在的同时,又肯定众生“业力”的存在。“业力”是人们一生思维和行动的总和,是众生生死流转的动力。人的生命消亡了,但其“业力”不会消亡,而且还会引起相应的果报,决定着轮回转生者的命运。这就是佛教宣扬的因果报应、六道轮回。“业力”既然不会随着生命的结束而消失,并有一定的支配意志,从本质上说与灵魂就没有差别。
道教与佛教对形神关系的认识有所不同,南北朝时期著名的道士陶弘景在《答朝士访仙佛两法体相书》中这样论述:
凡质象所结,不过形神。形神合时,则是人是物;形神若离,则是灵是鬼。其非离非合,佛法所摄;亦离亦合,仙道所依……假令为仙者,以药石炼其形,以精灵莹其神,以和气濯其质,以善德解其缠。众法共通,无碍无滞,欲合则乘云驾龙,欲离则尸解化质。不离不合,则或存或亡。于是各随所业,修道进学,渐阶无穷,教功令满,亦毕竟寂灭矣。
依据上文,对于形神,佛教是“非离非合”:人在轮回之中,精神与肉体必定结合,故曰“非离”;但佛教追求的解脱之道,是要超越轮回,摆脱肉体对精神的束缚,故曰“非合”。道教不同,它追求的是个体的长生不死,企图维持形体的永存,必须形神兼备,举形升虚,所谓“欲合则乘云驾龙”。但是修炼到一定程度,修道者就可以超越凡人的生存方式,精神可以自由地离开肉体,飞升上界,所谓“欲离则尸解化质”。“亦离亦合”的状态,是指修道者可以对“形”“神”自我控制,自由分离,自由重合,从而达到冲破生存困境、超越生命极限的理想境地。
明清剑侠小说的生命观虽有佛教的元素,但其主要内容还是反映出道教的生命哲学。尤其在《徐笠云》一篇中,幼妇与和尚离形尸解后,真神化作小人冉冉飞升,十分形象地描绘出道教生命演化理想。老子《道德经》云:“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受老子思想的启发,道教采用逆向复归的理论指导修炼实践。道教第三十九代天师张嗣成解释说:“吾身妙于婴儿,天地妙于无极,道体妙于大朴。”道教将人生修炼目标比作婴儿,并与天地、道体相提并论。对这种逆向复归的终极目标,道教典籍提出了修炼程序:“万物含三,三归二,二归一。知此道者,怡神守形,养形炼精,积精化气,炼气合神,炼神返虚,金丹乃成,只在先天地之一物耳。”“万物含三”指万物都包含精、气、神。道教认为,人来到世上,先天禀赋的精气神会逐步分离,慢慢死亡,所以必须将三者炼为一体,永不分离。“三归二”指炼精化气,“二归一”是炼气化神,直至炼神返虚。进入这个层面,精气神凝结而成的元婴之体就可以出现了。剑侠小说对生命演化进程的形象描述是荒诞的,但其致力于冲破生命有限的努力,则具有人类对生命超越的终极关怀的普遍意义。
三、仙凡混容的宇宙观
明清剑侠小说营造的世界,可以说是一个较为复杂的平面世界。说它是平面世界,是因为剑侠的修炼、替天行道以及仙魔斗法等都是在同一个世界里展开;说它较为复杂,是因为在这同一层面里,还存在着相对的仙凡之别,如层次的高低、距离的远近等。
在这个层面里,仙和凡是混容杂处在一起的。剑仙往往以平凡困苦的姿态,甚至是邋遢的面容出现于尘世。《狯园·青丘子》中剑侠青丘子,隐于武当山修道,其弟子王生上山寻师,“至则室庐如故,扃户无人”,一日,“忽于荆南道上见先生溷迹丐者之中”。《池北偶谈·女侠》中女剑侠隐身于偏僻的尼庵中,经常骑着黑驴行走于道上。《旷园杂志·瞽女琵琶》中女剑侠装扮成盲女,“挟琵琶漫游遍宇内”。《耳食录·王黄胡子》中某剑侠栖身于豪族公宅,与众人吃饭时常坐末位,神态癃惫,衣冠了鸟。《耳食录·何生》中女剑侠“雄服游戏人间”,衣冠褴褛,“以贫自晦,遂不为人识”。《聊斋志异·侠女》篇中侠女与其母亲在市井中租住一陋室,母女俩靠针线活艰难度日。《李汧公穷邸遇侠客》中的剑侠隐身市井,行踪诡秘,衣着随便,“也不做甚生理,每日出去吃得烂醉方归”。剑侠游戏尘世的目的是考察人心,赏善伐恶,度化有缘,积累功德。他们必须与凡人打成一片,置身于凡人的世界,如此,方能识透人心,分别善恶,了解世情,辨别真伪,真正做到替天行道。
剑侠虽然与凡人混杂在同一世界,但他们总是巧妙伪装,不以真面目示人,一旦身份暴露,他们就飘然远去,脱离凡人的视线,不知所终。剑侠隐身修道之处虽然与普通人处于同一层面,但却有高低、险峻与平易之别,不是向道心切、毅力坚定的有缘人,是无法找到剑侠的存身住所的。《狯园·青丘子》中的王生,“好寻名山,博采方术,有高蹈遐举之想”,所以只身踏入深山,寻觅仙迹。他“践丹危,履翠险,或下或高,且数十里。隐映若有洞门在断崖绝涧中,水流花开,风气似春”,终于寻到神仙处所。经其祖王重阳的指点,他又坐船入楚,抵达江陵,寻至武当山下,“负囊独上,缘磴跻攀”,几经周折,方能得拜剑侠青丘子为师。《程元玉店肆代偿钱 十一娘云冈纵谭侠》中程元玉跟随剑侠韦十一娘师徒前往其修道处云冈山顶,“过了两个岗子,前见一山陡绝,四周并无联属,高峰插手云外……(三人)攀萝附木,一路走上。到了陡绝处,韦与青霞共来扶掖,数步一歇。程元玉气喘当不得,他两个就如平地一般。程元玉抬头看高处,恰似在云雾里,及到得高处,云雾又在下面了。约莫有十数里,方得石磴。磴有百来级,级尽方是平地”。韦十一娘师徒炼剑的山崖,十分陡峭,“下临绝壑,窅不可测。试一俯,神魂飞荡,毛发森竖,满身生起寒栗子来”。《夜雨秋灯录·郁线云》中女剑仙长公主选择林木幽深的都梁山上修行,《剪灯余话·青城舞剑录》中真无本、文固虚两位剑侠在远离尘世的青城山中炼剑。《淞滨琐话·粉城公主》篇中,女剑侠粉城公主住地桃花奴,须飘洋过海,再翻越十余座山岭方能到达。
剑侠修行为何一定要选择高山峻岭、绝壁危崖呢?这是因为高山危崖人迹罕至,杜绝喧嚣,浩瀚深邃,气象万千,参天的古树,飞泻的山泉,幽深的洞穴,奇异的丛岩,其声色光影闪动着生命的灵性,高耸险峻更汇集了天地日月精华。《抱朴子·明本》称:中世以来,求仙访道者皆飘然绝迹幽隐,“山林之中,非有道也,而为道者必入山林,诚欲远彼腥膻,而即此清净也”。于是,远离红尘而又孕育着无限生机意趣的大自然就成了剑侠修炼剑术、打通天界与人间的中转站。
剑侠入深山修炼,除了脱尘离俗、亲近自然之外,在深层意义上,还与中国上古社会普遍流传的入山寻仙、上山升天的思维认识有关。《淮南子》、《拾遗记》等书对此有较为具体的描述:
昆仑之邱,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
《淮南子·坠形训》
昆仑山有昆陵之地,其高出日月之上。山有九层,每层相去万里。有云色,从下望之,如城阙之像。四面有风,群仙常驾龙乘鹤游戏其间。
《拾遗记》
在古人的思维模式中,山与天是最为接近的,登山而上便可入天界,甚至可成神仙。这种山天相通的思维模式的产生,“盖因高山云雾缭绕,山天相接,似隐似现,极易令人产生飘然于天国仙境的联想与幻想之故”。
剑侠的修行处所尽管偏僻遥远、陡峭险峻,普通人或遭逢意外,乱走误撞(如《粉城公主》中的任生),或一心向道,坚定寻找(如《青丘子》中的王生),或经人指点,相随前往(如《剑侠》中寻找失金的官吏),或主人相邀,扶助随行(如《韦十一娘》中的程元玉),总能步入剑侠的生活领地。这是因为剑侠与凡人的生活空间处在同一个层面,两者虽然有地势高低、难易之不同,环境喧闹与寂静的差别,却处在同一片天地间。
在明清剑侠小说里,没有天庭和地狱的描写,所有的故事都在凡人的世界里展开。《何生》篇,写剑侠了奴姊妹本是天界紫兰宫的捧剑使者,因舞剑误伤守宫之鹤,“故谪堕人间,使主游侠之事”。谪堕期满,两女重返天庭,与何生从此“殆无相见之期矣”。这篇小说提及天庭,但并没展开描写。小说中,剑侠是在天界中犯有过错的神仙降谪人间,一旦期满便返回天庭,不再干预尘事,与凡人也不能再有往来。天界和人世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至于地狱的描述,在明清剑侠小说中更是难觅踪迹了。
明清剑侠小说中天庭和地狱的缺失,表明剑侠的活动天地是一个单层面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仙凡之间虽有距离和高低的阻隔,但彼此有较多的交往与沟通,剑侠甚至易容变貌混迹于凡人社会。这种单层面空间的营构,使得剑侠的活动范围被局限在尘世中,其命运和活动内容都与芸芸众生紧密关联,因此格外关注这个世间的动乱和灾难,自觉地承担起替天行道、诛恶降魔的责任。这种单层面空间的设置,使得剑侠小说与神魔小说之间有了相对清晰的分野。
四、自相矛盾的情爱观
爱情,是人类最美好的情感,也是文学作品中历久弥新的题材,但在古代剑侠小说中却举步维艰。唐宋时期的剑侠小说几乎没有男女情感内容的描写,偶尔涉及,也是或凭借神术,成全别人的爱情;或言及婚姻,却无爱情可言;或借婚姻为掩护,事成之后弃之如敝屣,勇于“断爱”,毫不留情,基本上没有爱情火花的闪烁。之所以如此,一是出于宗教的因素,所谓“恩爱害道,譬如毒药”。二是源自叙事策略。即用凡人的视角来描述剑侠,刻意不触及其生活方式,尤其是情感世界,以增加剑侠的神秘性。
至清代,这种“侠不言情”的创作格局被打破,剑侠摆脱了“无情”的生活状态,开始在爱情世界里漫游。以剑结缘是清代文言剑侠小说的言情模式。在具体演述时分成两种套路:一是雌雄双剑配姻缘。《许玉林匕首》中许琳和妻子皆有奇遇,各得到一把匕首,两刀长短一样,许琳的刀文凸而显出,铭阳文,其妻之刀文凹而深入,铭阴文,两人因此结为夫妻。《虞初广志·李凉州》篇叙李凉州得遇奇人,获赠宝剑,此剑“出世五百年,尚未得偶”,后入滇中,遇一戎装女郎,家中也有一把宝剑,两剑“一雌一雄,毫发俱肖,合之吻合无间”,两人遂成佳偶。二是男女比剑成连理。《遁窟谰言·老僧》中卫文庄“体魄瑰伟,丰神清拔”,精通剑术,闻西安有奇女子仇慕娘比武招亲,欣然前往。比武场上,两情相悦,结为伉俪。《淞隐漫录·女侠》篇叙剑侠潘叔明性情豪迈,精通剑术,匹马裹粮,游走四方,在山东道上遇绿林豪杰,潘叔明与女剑侠程楞仙飞剑相斗,各自倾心,英雄美女,喜结良缘。《淞隐漫录·倩云》中秦雨衫夜入盗窟遭遇倩云,比剑后拜倩云为师,终至鸾凤和鸣。在男女比剑的叙述中,女子的剑术总是高于男子,对爱情的态度也较男方主动,这种柔弱与刚强的对比描写,很好地衬托了女侠的飒爽英姿、似水柔情。
以剑结缘是剑侠之间的言情模式,而剑侠与平常人之间的相爱更注重人的品性、才情。《何生》与《广寒宫扫花女》中的女侠原是仙女下凡,男服装扮游戏人间,衣衫褴褛,无人相顾,而何生与郑生却送钱送物,关怀体贴,从而使仙女顿生眷恋之情,不但在危急关头出手解围,而且主动示爱。正如《广寒宫扫花女》中女侠所言:“余雄服游戏尘寰,物色奇士,殊无知我者。君乃与我金,赠我衣。侠之所在,即情之所钟也。”《淞隐漫录·姚云纤》写女剑侠姚云纤与孙公子谈论诗词曲赋、地理风情及音乐,且联诗斗酒,赏花看月,相见恨晚。《虞初广志·柳珊》中女剑侠柳珊,从小父母双亡,卖身抚署,抚军欲将她嫁给幕僚李生,李生因未有母命不从,抚军以势相压,李生直面顶撞。柳珊见李生据理力争,很有骨气,怦然心动,在李生遭劫难时尽歼盗匪,并委身下嫁。《淞滨琐话·剑气珠光传》描写侠女白如虹与才子随照乘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白如虹随父出门经商,随生誓不他娶,照料白母,寻访如虹,如虹也绝不别嫁,等待随生。两人久经磨难,爱心始终如一,终于苦尽甘来,别后重逢,成就姻缘。在此类言情模式中,剑侠多为女性,喜欢女扮男装,男方都是普通人,有才情,有骨气,有侠心,最终赢得侠女的爱情。
清代剑侠小说第一次为读者营造了剑侠的情爱大厦,她给原本过于虚幻、神秘的剑侠世界增添了生机和诗意,尤其是女剑侠的情爱追求和情感流露,更是如同美妙动人的乐曲,在读者心中产生强烈的震颤。女侠温文尔雅,仪态万方,豪爽不失妩媚,主动伴以矜持,爱意缠绵而又英姿飒爽,真可谓:红衣剑胆芳魂在,柔情侠骨动人心。
如果我们整体审视清代剑侠小说有关情爱内容的话,那么就会发现这一时期小说的创作者对待爱情的态度是矛盾的,并不全是赞美,也有贬低、排斥。《廖剑仙》叙廖蘅仙跟随一程姓老翁学习“剑术”,道术将成时,有一美女前来扰乱清修,“廖心几动,急自遏制,念此淫娃坏我大道,盍不杀却?忽觉鼻中奇痒,一道白光突出,美人已杳。启目视之,座下死一九尾狐”。老翁对廖蘅仙不为情惑的行为赞不绝口:“子不犯色戒,真侠士也。再修三百年,可成剑仙。”《浇愁集·侠女登仙》中女剑侠张青奴对冯生说:“实告君,我剑仙张青奴也。向从妙手空空儿学技,见玉面郎君美,偶动凡念,师怒,责罚尘世立功德三十万。”这两篇小说都将“情爱”视为修道的障碍。
有些作品试图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徐笠云》篇,徐笠云与剑仙吕端之女互相爱慕,而此女“惟因剑术已成,将登仙籍,不愿再履尘世”,就换吕端的侄女莼香前来与徐笠云“以了前缘”,这是用偷梁换柱的方法来化解“情”与“道”的对立。而《淞隐漫录·剑仙聂碧云》中的聂碧云“虽与士人为伉俪,而食宿自别,察之,似绝无所染者,群疑为非常人”。小说描述的是一种纯粹的精神恋爱,试图以“灵”“肉”分离的办法来调和“情”与“道”的内在冲突。此种柏拉图式的恋爱方式为民国年间的小说家承袭,创出所谓有名无实、违反人性的 “合籍双修”的剑侠夫妻模式。
情欲与修道相冲突观念由来已久。在明清剑侠小说中,“情欲”常被用来作为考验修道者是否心诚的手段。明胡汝嘉《韦十一娘传》中,韦十一娘拜赵道姑学艺,师诫:不得饮酒、淫欲。半夜,“有男子逾垣而入,貌绝美 ”,以武力逼其犯淫戒,韦十一娘说:“死即死耳,吾志不可夺也。”男子收剑而笑道:“可以知子之心矣。”原来男子是道姑变化,来考察韦十一娘是否心诚志坚。情欲与修道的水火不容,源自中国人传统观念中对元阳的迷信,认为守住元阳,保护真阴,勤修炼养,就能得道飞升;而泄了元阳,只能历经劫难,转世重修。所以,在剑侠小说中童男童女在修道时总是事半功倍。既然情爱是修道的障碍,剑侠的生存状态就只能是无情。另一方面,剑侠对情欲的排斥,还根源于“万恶淫为首”的封建礼教道德观。在中国古代社会,男女关系要符合礼,“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责任重大,且始终与道德密切相关。至于男女相悦的“情”则被视为放纵的表现,与“礼”是不相容的,因此情欲必须克制,甚至灭绝。于是,在剑侠小说中,正直的剑侠不仅不犯色戒,而且对淫荡之徒总是深恶痛绝,必欲剿灭而后快。
除了上述修行观、生命观、宇宙观和情爱观四个方面以外,明清剑侠小说还有着浓厚的宿命意识,在价值观念上,表现出以仁为本,善恶分明,重视伦理等道德倾向,以致在“剑术”描写中也有着正邪之分。总的来说,明清剑侠小说的文化观是丰富多彩的,体现出多元化的格局,它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元素,而道教文化起着主导作用。在具体的文本表述中,这些文化形态通过小说描写的人物和情节生动形象地呈现出来,从而彰显了这一文学品类独特的艺术魅力。
注:
① 剑侠小说是武侠小说重要的分支,“剑术”与侠义构成其基本的叙事内容,二者缺一不可。此类小说的产生,有其独特的文化渊源,艺术表现上,也有其鲜明的个性特征。关于剑侠小说的界定范围与演变趋势,请参阅拙文《古代小说中剑侠形象的历史与文化渊源》(《文学遗产》2009年第3期)、《明清长篇剑侠小说的演变及文化特征》(《文学遗产》2010年第3期)。
②[清]长白浩歌子《萤窗异草》三编卷2,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89页。
③④ [清]海上剑痴《仙侠五花剑》(与《宋太祖三下南唐》合刊),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182、322页。
⑥[清]吕熊《女仙外史》,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84页。
⑦《道藏》第22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第383页。
⑧《道藏》第4册,第3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