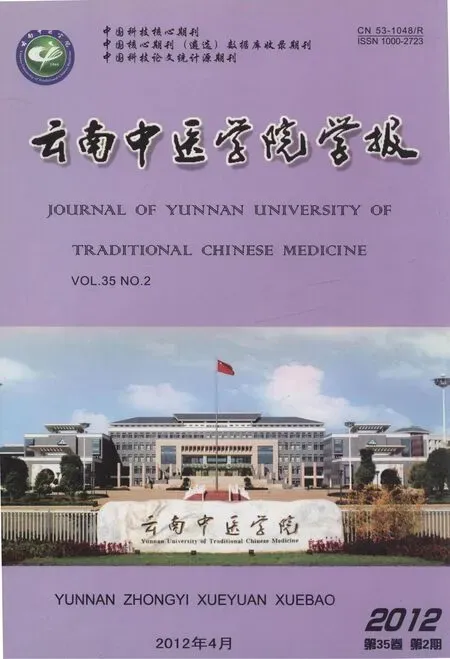骨质疏松症与抑郁症关系的中西医研究进展*
张学娅,张 颖,许东云,罗珊珊
(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云南昆明 650032)
骨质疏松症 (osteoporosis,OP)是一种常见的老年性慢性疾病,其发病率已经紧随糖尿病、老年痴呆,跃居老年疾病第三位。2008年10月20日在北京发布的《骨质疏松症防治中国白皮书》指出,我国至少有6944万人患有OP,约占总人口7%。全球对OP都给予了普遍关注和重视,而每年的10月20日是“世界骨质疏松日”。因此,关注和研究OP具有重要研究意义。而抑郁症 (depression)则被称为“蓝色隐忧”,“心灵感冒”。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在大城市的高强度脑力劳动者在高压力高竞争的环境下迅速成为此病的高发人群。在过去,OP和抑郁症被认为是两种不相关的两个系统疾病。但随着传统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的现代医学模式转变,近年来研究发现:OP与抑郁症具有密切的关联性[1,2];抑郁症在 OP 中普遍存在已经成为共识[2]。OP与抑郁症密切关联性的提出体现了现代医学从“治病”到“治病人”的科学转变。因此,提出OP与抑郁症的关联性研究,具有重要科学研究价值。基于此,现就OP与抑郁症的相关性研究做出综述,为今后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前期基础工作。
1 国外研究现状与发展动态分析
OP与抑郁症的相关性研究最早始于国外。1994年Schweiger等最早进行骨密度与抑郁症关联性的研究,他们发现抑郁症组的骨密度比对照组平均低15%[3]。此后,二者的关联性越来越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例如,1999年Coelho等发现,OP患者中抑郁症状更明显[4];2007年Altindag等在绝经期后抑郁症妇女中进行骨密度测定,研究发现抑郁患者中常出现骨密度降低[5];2009年Cizza等人明确提出:将抑郁症作为OP的高危因素[6]。近年来,涌现出更多的国外文献报道OP与抑郁症密切相关,在此不再一一枚举[7-10]。截至2011 年5 月15 日,以 “osteoporosis depression”为关键词在 PUBMED上检索,可检索到660篇相关文章。目前已经确定抑郁是OP的一个危险因素,抑郁症在OP中普遍存在已经成为共识[2]。
在这些文献中,尽管强调OP与抑郁症的紧密关联性,但目前尚缺乏有效的前瞻性的研究来确认两者的的因果关系。研究表明,二者之间可能存在三种关系[9]。一是抑郁症直接导致OP,OP是抑郁的一个不良后果。最具代表性的是2006年YirmiyaR等在美国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上的报道[11]。他们利用药物让老鼠产生类似人类抑郁的行为,结果这些老鼠出现了骨质流失;而后又让老鼠服用抗抑郁药物,结果发现,老鼠的骨密度随之增加,行为也更加活跃。二是抑郁症诱导的行为异常,如焦虑,饮食睡眠习惯改变等,可间接导致OP。三是OP可导致抑郁症。研究发现:OP患者很多感到悲伤、沮丧、气馁和抑郁,这些抑郁的情绪可能来源于OP对躯体的影响[12]。而这些研究报道主要集中于临床观察,目前尚缺乏有效的实验研究来证明。
在这些国外文献关于OP与抑郁症相关性机制的研究中,中枢神经系统被认为扮演了重要角色[13]。目前OP与抑郁症相关性的机理研究,多数围绕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机制展开研究,其中下丘脑-垂体-肾上腺 (hypothalamus-pituitary-adrenal,HPA)轴及其相关受体是OP与抑郁症相关性的研究重点。围绕着HPA轴,开展了下丘脑分泌的神经递质、垂体肾上腺等分泌的激素、细胞因子介导的调节环路等一系列研究。例如:抑郁情绪会激发交感神经系统释放去甲肾上腺素,损伤成骨细胞[11];抑郁情绪通过释放5-HT诱导OP[7]等。这些研究表明,OP和抑郁症可能是两个互为因果的慢性常见疾病,二者经由以HPA轴为中心的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构建以脑-骨骼为靶点的复杂网络。
值得提出的是,2010年,Bab等人在Current Osteoporosis Reports中明确提出“脑—骨骼交感信号(brain-to-bone sympathetic signaling)”概念[7]。在此,OP和抑郁症的密切相关性,共同搭建出脑—骨骼轴网络。“OP和抑郁症构建脑—骨骼轴网络”是现代医学发展前沿领域的最新学说,为OP和抑郁症相关性研究提供了最新现代医学理论支持。心身同治的普及将促进医学界的发展,相信不久的将来,必然有更多研究在OP与抑郁之间开展[3]。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二者研究的重点仍将围绕中枢神经系统开展。
2 国内研究现状与进展分析
中医学古籍没有OP病名记载,但有与OP表现相似的记载,与“骨痿”、 “骨痹”、 “腰痛”、 “骨枯”、“骨极”等病名接近。中医学古籍也没有抑郁症病名记载,但“郁症”、“脏燥”等病名记载与抑郁症接近。我们知道,中医学最基本的哲学思想是“天人合一”,即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同时人和自然、社会具有统一性。其中,“肝肾同源”是重要的中医理论之一。“肝肾同源”又称“乙癸同源”,它体现了中医学整体观,体现了人和自然社会的统一性。“肝肾同源”哲学思想渊源于《易经》,医学基础根源于《内经》,临床实践丰富于汉唐金元时期,理论体系正式形成于明代李中梓的《医宗必读》[14]。所谓“肝肾同源”,它揭示了同属于下焦的肝肾两脏生理、病理上存在着相互滋生、相互影响的密切关系。在五行,肝性属“木”、肾性属“水”,以“水能生木”之自然现象取类比象,提出“肾水之精以养肝木”的理论,此即所谓肝肾“母子相生”。肾藏精,肝藏血,肝肾精血互生,精血关系是“肝肾同源”的基础。此外,肝肾经络相交通并共同隶属于奇经,诚如如《内经》云“肾足少阴之脉……其直者,从肾上贯肝。”故曰:“肝肾同源”。具体来说,它揭示了肝肾两脏在生理、病理上相互滋生、相互影响的密切关系。相比较于国外,国内研究体现了中医整体观理论指导下中药方剂治疗OP与抑郁症的特点,即在“肝肾同源”理论指导下来认识二者关系,从而指导治疗。
中医学对OP的认识,是禀赋不足、情志不调等各种内外诱因,导致五脏功能失调,其根本在于肾虚,与肝相关。《内径·素问》云:“肾主骨髓,髓生肝。”在五行,肝性属“木”、肾性属“水”,以“水能生木”之自然现象取类比象,则“肾水之精以养肝木”。肾主骨藏精,肝主筋藏血,精血互化,故曰:“肝肾同源”。肾精不足,脑海骨髓空虚,则骨质脆弱;精血不足,肝不藏血,则血不养筋,肝失疏泄。《素问·上古天真论》云:“七八,肝气衰,筋不能动……,形体皆极。”指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出现“肝气衰”,而后“形体皆极”。中医学理论认为:肝主筋,主藏血,主疏泄。其在体合筋,连接骨节,故又为“罴及之本”。肝脏与肢体运动紧密相连。肝脏气血衰少,血不荣筋,则动作迟缓,行则掉振鼓栗,不能久行久立,从而发为骨痿。因此,OP的发生,从中医学来说,与肝郁肾虚密切相关。而中医学对抑郁症的认识,是以情志内伤为主要因素,肝气郁结、肾气不足为其重要病机。因肝为风木之脏,主司情志,是一身气机之枢纽,故所谓“郁症未有不伤肝者也”。而肾为肝之母,肾阳不足,不能鼓动肝气升发,疏泄失司,而致气机郁结,加重情志抑郁,诱发诸症更加显著。《黄帝内经》指出“阳主动”,肾阳为一身阳气之根,动力之源,而抑郁症以抑制、淡漠等功能低下、“不动”的表现为主。肾阳不足,不能振奋精神,则记忆减退、认知迟钝、感觉异常等。因此,抑郁症的发生,从中医学来说,同样与肝郁肾虚密切相关。由此可以看出,OP和抑郁症都与“肝肾同源”的理论相关。中医学“肝肾同源”的经典理论对OP与抑郁症的认识,为OP和抑郁症相关性研究提供了中医学基础理论支持。
尽管中医学对OP和抑郁症相关性认识早于国外,相关的基础理论研究报道也数目繁多,不甚枚举。但同时从“肝郁肾虚”途径研究中药方剂治疗OP与抑郁症的报道,在公开发表刊物检索到的报道甚少。在动物实验中,国内研究报道补肾法对OP大鼠有治疗作用[15,16]。结合现代科学技术路线,证明其机制是通过下丘脑分泌激素介导的细胞因子通路[15]。通过补肾治疗OP的代表药方主要有二仙汤[17]、枸杞子与桑寄生[18]等。相比较补肾法治疗OP,益肝法治疗OP的动物实验研究鲜有报道。同样,在国内动物实验研究报道中,有大量文章提示补肝法对抑郁症大鼠具有治疗作用[19],益肾用治抑郁症的研究则相对较少。而同时从“肝郁肾虚”途径认识OP和抑郁症相关性,研究中药方剂治疗OP与抑郁症的报道,则更少。因此,从“肝肾同源”理论开展OP与抑郁症的相关性研究,可能开辟新的研究途径。
3 小结
OP与抑郁症密切关联性的提出,体现了现代医学从“治病”到“治病人”的科学转变,具有重要科学研究价值。而近年来二者的相关研究,多数围绕与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相关的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展开。尤其是最新“脑—骨骼交感信号”的提出,为OP和抑郁症的密切相关性搭建出脑—骨骼轴网络学说。“OP和抑郁症构建脑—骨骼轴网络”是OP和抑郁症相关性研究在现代医学发展前沿领域的最新学说;同时中医学“肝肾同源”的经典理论为OP和抑郁症相关性研究提供了中医学基础理论支持。现代医学对OP和抑郁症的密切相关性认识与中医学“肝肾同源”理论是不谋而合的。OP与抑郁症密切关联性的提出,为今后进一步探索OP与抑郁症相关性的分子机制,为从整体抗OP及抑郁症的药物治疗,提供了研究新思路和方法。
[1]许超,肖鲁伟,童培建,等.骨质疏松症与抑郁症关系的研究进展[J].中国骨质疏松杂志,2009,15(9):693-696.
[2]赵刚,蔡定芳.抑郁和骨质疏松症[J].国外医学精神病学分册,2002,29(2):104-107.
[3]何伟涛,许超,史晓林.骨质疏松症与抑郁症关系的研究进展[J].2009年浙江省骨质疏松与骨矿盐疾病学术年会暨《骨质疏松症诊治进展》专题研讨会论文汇编,2009年.
[4] Coelho R,Silva C,Maia A,et al.Bone mineral density and depression:a community study in women[J].J Psychosom Res,1999,46(1):29 -35.
[5] Altindag O,Altindag A,Asoglu M,et al.Relation of cortisol levels and bone mineral density among premenopausal women with major depression[J].Int J Clin Pract,2007,61(3):416-420.
[6] Cizza G,Primma S,Csako G..Depression as a risk factor for osteoporosis[J].Trends Endocrinol Metab,2009,20(8):367-373.
[7] Bab I,Yirmiya R.Depression,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and Osteoporosis[J].Curr Osteoporosis Rep,2010,8(4):185 -191.
[8] Bab IA,Yirmiya R.Depression and bone mass[J].Ann N Ycad Sci,2010,1192:170 -175.
[9] Kumano H.Osteoporosis and stress[J].Clin Calcium,2005,15(9):1544-1547.
[10] Gold DT,Solimeo S.Osteoporosis and stress:a historical perspective[J].Curr Osteoporosis Rep,2006,4(4):134-139.
[11] Yirmiya R,Goshen I,Bajayo A,et al.Depression induces bone loss through stimulation of the 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J].PNAS,2006,103(45):16876-16881.
[12]周勇军.独活寄生汤加减治疗原发性骨质疏松症40例疗效观察[J].中医药导报,2009,15(5):37-38.
[13] He JY,Jiang LS,Dai LY.The roles of the 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 in osteoporotic diseases:A review of experimental and clinical studies[J].Ageing Res Rev,2011,Jan 22.
[14]刘琰,严灿,吴丽丽.“肝肾同源”与情志调控机制的理论探讨[J].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2009,23(3):43-45.
[15]孙鑫,郑洪新,燕燕,等.补肾与健脾方对骨质疏松症大鼠干预作用及下丘脑PKC蛋白表达的影响[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0,16(5):387-389.
[16]刘玲萍,李捷,孙平,等.补肾壮骨中药对糖皮质激素诱发骨质疏松大鼠的干预作用[J].中药材,2010,33(4):593-595.
[17] Hua Nian,Lu - Ping Qin,Qiao - Yan Zhang,et al.Antiosteoporotic activity of Er-Xian Decoction,a traditional Chinese herbal formula,in ovariectomized rats[J].JEthnopharmacol,2006,108:96 -102.
[18]董佳梓,鞠大宏,贾朝娟,等.桑寄生、枸杞子、桑椹对去卵巢大鼠骨质疏松症的治疗作用及其机理探讨[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0,16(6):483-486.
[19]阎玥,王桐生,谢鸣,等.肝郁脾虚证模型大鼠HPA轴中枢相关受体的表达及疏肝健脾方药的干预作用[J].上海中医药杂志,2010,44(2):58-60.
——紫 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