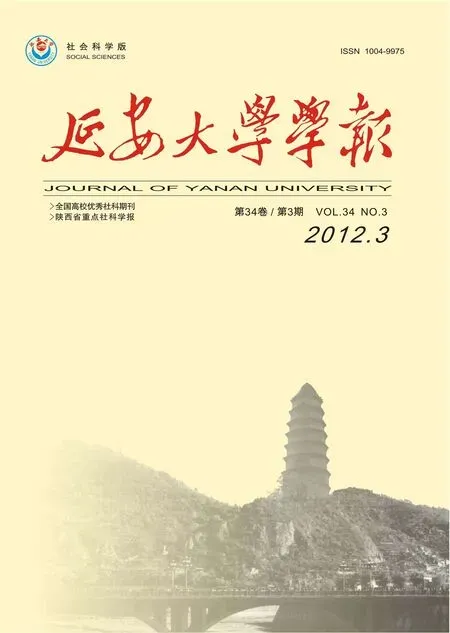“鲁迅”在延安
田 刚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新文化的“旗手”,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被确立之后,其作品遂在以延安为中心的共产党控制区内迅速传播并弘扬开来。对此,当时的《新华日报》曾于1941年1月7日和8日以连载形式发表过一篇署名“惊秋”的长篇报道《陕甘宁X区新文化运动的现状》,其中特辟一节“鲁迅在延安”。该文称:“鲁迅,这一个愈久愈光辉的名字,它永远存在觉醒了的中国人民大众的心理。最尊重鲁迅的,是最澈底为中华民族、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为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斗争的延安。‘鲁迅的方向,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鲁迅的旗帜,即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旗帜’(洛甫)因此,研究鲁迅,学习鲁迅,继承鲁迅的事业前进,成为努力于中华民族新文化工作者底一个基本的任务。在延安,鲁迅的品格,被称为每一个革命青年尤其是文化工作者的修养的模范,鲁迅的语言,被引作政治报告中最确切的补充例证,鲁迅对新文化运动的见解,被作为研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基本道循,金字红色书面的《鲁迅全集》,成为青年们最羡慕的读物”[1]。可以说,鲁迅已经成了延安文化生活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延安新文化的象征。
“鲁迅”在延安的深入人心,是与其作品在延安及各解放区的广泛传播分不开的。当时延安所在的陕甘宁边区在经济上是中国最贫困的欠发达地区,文化条件自然不能与上海、重庆、武汉、西安等大城市相比,但这并不妨碍这里文化的繁盛及人们对精神生活的强烈渴求,相反延安却成了抗战时期文艺最为活跃的文化中心之一。而鲁迅及其作品在延安及各解放区的传播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的。其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种方式:
一、鲁迅作品在延安的编辑、出版和改编
首先是“鲁迅全集”在延安及各解放区的传播。1938年6月15日,《鲁迅全集》初版的“普及本”在上海出版,由“鲁迅纪念委员会”(主席蔡元培、副主席宋庆龄)编纂,鲁迅全集出版社出版。全集共20卷,1—10卷系鲁迅著作,12—20卷系鲁迅译著。8月1日,《鲁迅全集》又以“复社”名义出版的甲、乙两种精制的纪念本——每部书上均特别标明为“非卖品”,且各有顺序编号,都只印了二百部。6月25日,生活书店连续在汉口《新华日报》预约《鲁迅全集》,称全集是“出版界空前巨业!新中国伟大火炬!”全书六十种计五百万字,分订二十巨册,硬皮布脊。蔡元培序,许寿裳撰年谱。全书定价二十五元。早在5月,周恩来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预订了我国第一部20卷本的《鲁迅全集》精、平装本各十套(后来送到延安时实际上各为八套)。该书6—8月出版后,购回给了延安鲁迅图书馆和鲁艺图书馆各两套,其中送给毛泽东的《鲁迅全集》为精装本第58号。现在保存的那张著名的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伏案写作的照片上,这套紫红漆皮封面、黑色漆皮烫金书脊、二十册的精装本的《鲁迅全集》即清晰可见。作家杜鹏程在抗战胜利前一年,有一次到毛泽东的办公室,就见到他的书柜中摆着二十卷的《鲁迅全集》,其中有一本在桌子上摊开放着,看来足有一寸多厚。当时,杜鹏程不好意思去翻阅,但是匆匆一瞥,也使他心情异常激动,直到后来,当时的很多细节,还清楚记得[2]。另外,由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上海鲁迅全集出版社于1941年10月初版的1—30册《鲁迅三十年集》,鲁艺图书馆也收藏了一套。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大连光华书店于1946年又一次陆续大量翻印了《鲁迅三十年集》和《鲁迅全集》,使得这两套《鲁迅全集》在各解放区得到进一步广泛的传播。
其次是各种“鲁迅选集”在延安及各解放区的编辑、出版和传播。从1940年到1949年,延安及各个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干部群众热烈争购鲁迅作品,党和政府的文化教育机关,也多方设法翻印和编选鲁迅译著。除了大连光华书店翻印的《鲁迅全集》对《三十年集》等大型图书以外,还有很多单行本、选编本以及译作翻印本。据初步统计,这些“鲁迅选集”大致有如下10种:
1.《鲁迅论文选集》。张闻天委托刘雪苇编选,1940年10月由延安解放社出版。该“选集”以“编年”方式共选鲁迅在各个时期重点作品79篇,卷首由张闻天写成《关于编辑<鲁迅论文选集>的几点声明》作为“序言”,最后以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作为“附录”,选目精当,注释简要。《编选声明》特地阐述了印刷此书的目的和意义,说明解放区人民是把鲁迅著译当作精神食粮来看待的。特别是编者运用毛泽东思想来评价鲁迅及其著作,指出鲁迅是“近代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现代中国青年,从鲁迅先生的作品中可以得到很多有益的宝贵的东西”。
2.《鲁迅小说选集》。1941年,刘雪苇又受命于张闻天编成《鲁迅小说选集》,并于同年亦由延安解放社出版。该“小说选”同样以“编年”方式选辑鲁迅《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中的主要作品17篇,基本囊括了鲁迅小说的重要作品。“选集”卷首以《关于编辑<鲁迅小说选集>的几点声明》作为“序言”,最后的“附录(一)”收录鲁迅有关自己小说的文章五篇:即《<呐喊>自序》、《<自选集>自序》、《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阿 Q正传的成因》、《<出关 >的“关”》等,“附录”(二)收录了鲁迅写的《自传》,介绍鲁迅的生平事迹。《鲁迅小说选集》出版后,延安《解放日报》1941年10月19日《文艺》附刊发表了当时洛甫同志的秘书许大远(即须旅)所写的长文《鲁迅的小说》,副题是“介绍《鲁迅小说选集》并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
《鲁迅论文选集》和《鲁迅小说选集》由解放社出版以后,各个抗日根据地很快都加以翻印。计有:一九四一年十月新华日报华北分馆版,一九四二年华北书店版,一九四六年四月张家口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版。除此而外,各个地区,甚至各个县城也都翻印出版。尽管这些书籍土纸印刷,纸捻装订,颜色很不一律,而且有些在仓促行军之中辗转携带,在暗淡如豆的灯光之下摩挲研读;大部残破不全,但是人民群众还是对它善加保护,多方流布,使它在培养群众的革命思想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3.《故乡》。1941年7月由华北书店出版发行,收录有鲁迅的《故乡》、《风波》和《孔乙己》三篇小说。由于物质条件困难,它使用彩色宣传纸油墨印刷的,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较早出版的一本鲁迅著作。
4.《阿Q正传》。1943年7月由华北书店出版发行。这本册子,是著名鲁迅研究家徐懋庸对《阿Q正传》研究的注释本。注释声明中说:徐懋庸对《阿Q正传》的注释是从1941年开始的,“前年冬,抗大的一个同志,曾提议道:“把你对这些作品的意见,写出来发表罢’,于是我开始想到注释的办法……”。所以,徐懋庸注释的《阿Q正传》,对当时学习和研究鲁迅著作的青年同志起了很好的开导作用。10月21日延安新华书店登出新书《阿Q正传》等广告。
5.《一件小事》。1944年8月由延安印工合作社出版发行,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选编的。该“选集”收录鲁迅小说五篇:《阿Q正传》、《一件小事》、《故乡》、《祝福》、《孔乙已》。五篇小说,正文前有导语,文后有注释。书的正文前有“总政宣传部1944年8月1日”写的《编辑缘起》,书末有写于1944年7月1日的《编后记》。《编辑缘起》阐述了总政宣传部编印“文艺读物选丛”的目的,是为了供给部队中一些文化精神食粮,使战士和干部“在紧张的战斗与生产和整训中,能得到一些生活上的调剂”。编选的标准“不是从单纯的艺术水平的观点出发”,而是“针对着我们部队中的干部文化水平不高,社会知识与经验不够广阔,想用这些作品来提高我们的文化水平,帮助我们了解中国社会的各个侧面,中国社会各阶层的面貌、感情、思想和行动,使一些拙象的社会阶级概念形象化。”1947年东北解放区翻印此书时,改书名为《鲁迅小说选》。
除了编辑、出版鲁迅的“全集”和“选集”,鲁迅作品还以其他传播形式在延安及各解放区出现。这其中包括:
1.鲁迅作品的戏剧改编。最早把鲁迅作品《阿Q正传》进行改编并搬上舞台的是陕北苏区时期。1937年3月7日,苏区人民抗日剧社成立。这年夏天,廖承志、赵品三、朱光、杨醉乡、董芳梅联合公演了《阿Q正传》一剧。廖承志扮演王胡,赵品三扮演阿Q,杨醉乡、董芳梅扮演尼姑。演出相当成功,毛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不时地鼓掌。时在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夫人观看了《阿Q正传》的演出,她称:“演出组成功的剧目之一,是鲁迅的名小说《阿Q》。剧本是由上海的许幸之改编的,改编得确实很好。逗人发笑的农村无产阶级阿Q这个角色,是由剧社社长赵品三扮演的。自这个剧演出以后,凡他所到之处,人们就风趣地打个喷嚏:‘AhQu—oo!’(啊—啼呜!)向他问好。同他一起演出的,是剧社的儿童演员,扮演了悲剧中一个面孔严峻的卓别林式的小人物,引起了一场狂笑,几乎能把屋顶吵塌”[3]。1938年10月19日,鲁迅艺术学院为纪念鲁迅,演出活报剧《鲁迅之死》,钟敬之编导。1941年1月1日,延安各界热烈庆祝新年,医科大学又演出了话剧《阿Q正传》。
2.以鲁迅为主题的展览会。1940年4月,为纪念中国新兴木刻的栽培者鲁迅,鲁艺曾举行延安首次木刻展览会,共展出二百幅作品。后来又应延安鲁迅研究会之请,画家张仃绘制了鲁迅大画像,雕塑家王朝闻塑造了鲁迅的浮雕像,这两件美术作品,至今仍是现代美术的名作之一。1941年1月2日,为纪念鲁迅逝世四周年而筹备的展览会在延安文化俱乐部开幕。茅盾得知后,特意把自己珍存的一份鲁迅手迹交给展览会展出。这就是l935年为苏联国际文学社所写的《答苏联国际文学社问》(一封信)。这份手稿在茅盾离开延安时,交留方纪代为保管。这次展览分四部分:鲁迅著作;鲁迅在国外;鲁迅书信照片;鲁迅先生死后。展品二百余件。参观人冒雨络绎不绝,两天来达六百余人。
3.以鲁迅作品作为政治宣传品。1942年4月,《整风文献》作为整风必读文件由延安解放社发行并印刷(随后曾多次重印,发行量巨大),内收以“鲁迅论创作要怎样才会好”的鲁迅《答北斗杂志问》一文。1942年5月20日,《解放日报》重新发表鲁迅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并加编者的话。6月16日,为整风学习,“鲁艺”印出列宁的《论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和鲁迅的《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两篇著作,作为研究参考资料,以推动延安文艺界整风运动。7月31日,《晋察冀日报》重新发表鲁迅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并加“编者按”。编者按指出:“其中对于左翼作家和知识分子的针砭,对于文艺战线的任务,都是说得很正确的,至今完全有用。”9月2日,晋察冀边区文化界整顿文风委员会编印的《整风参考资料》出版。该“资料”选载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鲁迅《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高尔基《和青年作者的谈话》及别林斯基、杜勃洛留勃夫、瞿秋白的文章。1944年5月,周扬编选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由延安解放社出版。该书是为了更好地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编辑的,其中选辑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高尔基、鲁迅及毛泽东同志的有关文艺理论和意见。其中鲁迅的意见引用最多,颇引人注目。
二、延安的鲁迅纪念活动
在延安,对于鲁迅最隆重的纪念就是以“鲁迅”来命名有关的机构和学校。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还在陕北山区苦苦转战的中共中央及中央苏区政府,立即发出发出由张闻天起草的《为追悼鲁迅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致许广平女士的唁电》、《为追悼与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电》这三份文件,指出:为了永远纪念鲁迅先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还决定在全苏区内:(一)下半旗致哀,并在各地方和红军部队中举行追悼大会;(二)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基金十万元;(三)改苏维埃中央图书馆为鲁迅图书馆;(四)在中央政府所在地设立鲁迅纪念碑;(五)收集鲁迅遗著,翻印鲁迅著作;(六)募集鲁迅号飞机基金。同时,中共中央及苏维埃政府还向主政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提出如下要求:(一)鲁迅先生遗体举行国葬,并付国史馆立传;(二)改浙江省绍兴县为鲁迅县;(三)改北平大学为鲁迅大学;(四)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奖励革命文学;(五)设立鲁迅研究院,收集鲁迅遗著,出版鲁迅全集;(六)在上海、北平、南京、广州、杭州建立鲁迅铜象;(七)鲁迅家属与先烈家属同样待遇;(八)废止鲁迅先生生前贵党贵政府所颁布的一切禁止言论出版自由之法令。表扬鲁迅先生正所以表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4]。随后,陕北苏区即成立了“鲁迅青年学校”、“鲁迅剧社”等机构。1937年党中央迁驻延安后,又相继成立了鲁迅图书馆、鲁迅师范学校、鲁迅小学、鲁迅艺术学院、鲁迅研究会、鲁迅研究基金会等以“鲁迅”命名的机关和学校。1940年7月25日,晋察冀边区还设立的“鲁迅文艺奖金”,以鼓励创作,开展边区文艺运动。
除了以“鲁迅”命名的学校和机构以固定的形态彰显出“鲁迅”在陕甘宁边区的独特价值和意义之外,还有的就是规模更为宏大的鲁迅纪念活动。这些纪念活动大多是在鲁迅诞辰或逝世纪念日举行,其浓厚的文化和政治仪式的色彩是不言自明的。而通过这些纪念活动,使得鲁迅的形象在延安及各解放区更加深入人心。
中共中央最早对鲁迅的纪念,是1936年在陕北保安举行的鲁迅逝世追悼会。1936年10月30日,在中央苏区所在地陕北保安举行了鲁迅追悼大会。据《红色中华》10月28日报道:“自鲁迅先生逝世消息传来后,党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少共中央局三机关发起盛大之追悼鲁迅筹备会,该会负责人选已决定,正在筹备收集鲁迅先生的译著及其他作品,并将在志丹市于本月卅日召开各机关部队群众团体之盛大的追悼会”。据当时曾参加了这次追悼大会的朱正明回忆:“那天,红军和各部工作人员以及红军大学学员都出席参加,人数总在一二千之间,毛泽东并亲自出席发表了演说,对于这位革命的青年导师,苏维埃政府给予了沉痛的追悼及崇高的哀思。那时天气很冷,全体参加者已经在寒风中坐立了二三小时”[5]。但是,由于国民党的封锁,这次保安追悼鲁迅的大会在当时和后来都鲜有人知,以致于各种有关悼念鲁迅的文献资料不仅没有记载下大会的具体情形,而且毛泽东在鲁迅追悼大会上的讲演内容也没有保留下来。
1937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一周年,刚刚成立不久的陕北公学在延安举行了纪念大会。应时为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的邀请,毛泽东参加了纪念大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据说当时参会的人并不太多,毛泽东在演讲时没有稿子,但其讲话的内容却被在座的陕北公学第一期学员汪大漠详细地记录了下来。后来汪大漠把稿子寄给了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胡风随即将该演讲定名为《论鲁迅》,以“毛泽东演讲,大汉笔录”的署名发表《七月》1938年3月第10期上。就这样,毛泽东的这篇著名演讲被保存了下来。但其实,“大汉”应为“大漠”,肯定是因为“大汉”的“漢”的繁体字在形体上近似“大漠”的“漠”,遂造成了上述的误读。
1938年的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活动更是具有特殊意义。这一日,正是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之际。扩大会全体致电许广平女士,表示哀悼和慰问。《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致许广平女士电》称:“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中全会开会中,适逢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日,扩大会全体追念先生对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与对文学运动伟大的贡献,深切表示敬意。当此民族危急之际,尤深哀悼,除全体静默追悼外,特电慰问”[6]。也是在这一日,武汉和延安都举行了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武汉纪念会是以“文协”和“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的名义召开的。但“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秦博古两同志本来很忙,因为纪念鲁迅先生而特意赶来”[7]。而延安的纪念会在规模和形式上更是盛况空前。《新华日报》(重庆版)1938年11月23日以《延安纪念鲁迅逝世二周年》(敏英)为题,报道了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主持召开延安纪念鲁迅逝世二周年大会的盛况:
“大会是由边区文化界救亡会主持的,一个并不甚么大——府衙门,能容纳四五千人的会场的正面,张挂满了各团体学校或个人送来的花圈挽联,挽歌等。看去极其庄严隆重。……大会主席团——毛泽东、陈绍禹……等中国领袖,和周扬、沙可夫、沙汀、柯仲平、丁玲、徐懋庸等十三人——在全体到会会员的鼓掌声中一致通过了。大会即由柯仲平同志宣布开会并报告开会的意义,继由周扬讲演,随后丁玲、徐懋庸、沙可夫等同志都相继讲演。最后,丁玲同志提议在‘延安文艺界抗战联合会’内成立一个‘鲁迅研究学会’;延安各大图书馆都要买一部《鲁迅全集》。大会就在一个响亮的雄壮的‘同意’和纪念口号声中闭幕了”。
如果说,在此之前延安的鲁迅纪念活动在规模上还只是局部的或者说是还不具备浓厚的“仪式”意义的话,那么,从1940年鲁迅逝世纪念日开始,其规模和形式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是因为:第一,鲁迅已被中共领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树为中国现代新文化的“旗手”,“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纪念鲁迅,其突出的文化政治色彩和鲜明的象征和“仪式”意义是不言自明的;第二,在1940年1月举行的陕甘宁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洛甫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抗战八年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的报告,提出了组织新文化运动大师鲁迅先生的研究会或研究院等的建议。1941年1月15日,由艾思奇、萧军、周文组成干事会的延安鲁迅研究会正式成立。从此,延安的鲁迅纪念活动开始有了稳定的发起者和组织者。
1940年8月3日(农历),是鲁迅先生诞生六十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新华日报》特别发表社论《我们怎样来纪念鲁迅先生?》,指出要继承鲁迅“创作的光荣传统和他一生所抱的为民族、为人民和为求进步而斗争的精神”;“要学习他坚强不妥协和坚持抗战到底的精神”;“要加强进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同日,《新华日报》还以《行都文化界纪念鲁迅六十诞辰》报道了重庆文化界纪念鲁迅六十周年诞辰大会的实况。郭沫若、田汉、张西曼、葛一虹、沈钧儒等到会并讲话,一致强调“学习鲁迅不屈不挠的精神”。8月15日,《大众文艺》》1卷5期推出“纪念鲁迅六十生辰”专栏,刊出周文的《鲁迅先生和‘左联’》、茅盾的《为了纪念鲁迅的六十生辰》、丁玲的《‘开会’之于鲁迅》、胡蛮的《鲁迅在生活着》等纪念文章。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四周年的忌日。这一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悼念青年的导师鲁迅先生》,指出“我们今天来纪念鲁迅,不是要把他当作过去来回忆,而是要把他当作现今革命战阵面前的旗帜去追求”。在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月刊第二卷第三期(10月25日)刊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纪念鲁迅逝世四周年》的社论,开始完全按照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思路来评价鲁迅。而于10月19日在延安举行的鲁迅先生逝世四周年纪念大会更是盛况空前。这一天,“全延安的文化人,文化工作者,青年学生,工厂工人及广大‘为奴隶们争取自由解放’而韧战多年的老革命战士们”,共三千余人参加了纪念大会。当时的记者是这样描述大会的盛况的:
“虽然会前仅是一纸的通知,但以鲁迅先生生前在革命业绩上的伟大号召力量,使一个能容一千余人的会场,感到了过分的狭小,一排排的座位上,早已被先到会的人紧紧的集拢得没有一点空隙,作为两边的人行路上,也被人塞得无法通行。会场四周的窗棂外边面,重叠的人群在竞相扶肩翘首的向会场内瞩望,而会场的大门口,黑压压人群仍象潮水似的向里涌进”[8]。
纪念会上,吴玉章、萧军、周扬、冯文彬、萧三、张庚、艾思奇以及延安工人代表朱宝庭等分别在会上讲了话。最后丁玲讲话,提出今后纪念鲁迅先生的具体措施:一、成立鲁迅研究委员会,分组研究其遗著;二、发动边区各地成立鲁迅研究委员会并与之取得联系;三、延安各机关学校成立鲁迅研究小组;四、建立鲁迅材料室;五、雕塑鲁迅遗像;六、加强鲁迅基金委员会工作,募捐文学奖金;七、电询鲁迅家属,探询其经济状况,并予设法救济。
1941年10月19日的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大会是由新成立的“鲁迅研究会”具体筹办的。大会在延安中央大礼堂隆重举行,参加者有作家、诗人、戏剧家、美艺家、音乐家……及各界代表达千余人。会前成立了“鲁迅纪念筹备委员会”,并由筹委会散出“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特刊”与“鲁迅语录”多种,人民争相传阅着。开会后由“鲁迅纪念筹备委员会”报告筹备经过,接着选举主席团,向鲁迅遗像致敬,并唱鲁迅纪念歌。继由主席萧军作报告,总结过去工作,提到成立“鲁迅研究会”,出版《鲁迅研究丛刊》第一辑、《阿Q论集》与《鲁迅论文选集》、《鲁迅小说选集》,创作鲁迅画像和制成鲁迅石膏像;并举办“鲁迅纪念展览会”。会上通过继续出版《鲁迅论文选集》和慰问鲁迅先生家属信的提案。晚上有文艺节目。于此同时,重庆“文协”等八团体在抗建堂举行鲁迅逝世五周年纪念晚会。晋察冀边区文化界举行鲁迅逝世五周年纪念大会。山东《大众日报》和《新山东报》出版纪念鲁迅专号。一一五师的“文艺习作会”举行鲁迅纪念会,并讨论文学的民族形式问题,同时在《战士报》刊出纪念鲁迅专号。
1942年的鲁迅纪念大会是在延安整风运动的政治大背景下召开的。这一年的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会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轰轰烈烈的延安整风运动由此而启动。5月2日、16日、23日,为解决延安文坛的冲突和混乱景象,党中央以当时的中宣部长凯丰的名义召开了三次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界的整风运动由此也开始全面铺展开来。10月18日下午,延安各界举行纪念鲁迅逝世六周年大会。中央大礼堂外面贴着鲁迅遗言:“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由于事实的教训,明白了唯有新兴的无产阶级,才有将来”。会议主席团由丁玲、周扬、萧三、塞克等组成。丁玲讲完开会意义后,吴玉章以思想革命家,社会革命家、文学革命家、文字革命家四点作为正确估价鲁迅先生的致词。他说:“鲁迅先生是中国文化界的旗帜,我们要完成鲁迅先生的一切事业。”徐特立说:“鲁迅先生始终是站在革命政党的立场上,他从来没有背离它。鲁迅先生看重革命行礼实际工作,因此鲁迅先生是真正理论和实际联系的。”萧三说:“一个革命文学家一定要无产阶级化,在这一点上鲁迅先生是做到的。鲁迅先生从来没有个人英雄主义,他非常谦逊地说自己是大众中的一个,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他的爱和恨是敌我分明的,他爱大众,恨大众的敌人因此鲁迅先生是没有歪风的完人。”
但10月18日的鲁迅纪念大会却是在混乱的争议中不欢而散的。据萧军夫人王德芬在《我与萧军风雨50年》一书中回忆:
1942年10月19日(按:根据《萧军日记》应为18日)下午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召开的“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六周年大会”上,萧军是主席团成员之一,也是“鲁迅研究会”总干事,正坐在台上。该他发言了,他又从大衣口袋里把“备忘录”掏了出来当众念了一遍。台上主席团的五位党员作家丁玲、周扬、刘白羽、柯仲平、李伯钊和两位非党作家艾青、陈学昭,为了表示“党性”,一个接一个地站了出来和萧军展开大辩论。……(最后),刘白羽说:“今天谁也不要走!”意思是必须辩论它个“水落石出”。萧军说:“对,谁走谁是孱头!”丁玲、周扬、柯仲平各人都有个人的议论,萧军一个人“舌战群儒”,在人多势众强大压力下,他理直气壮毫不气馁,口若悬河,越辩越激动毫不示弱,你有来言我有去语,从下午八点一直到午夜两点钟,辩论了六个多小时还没有收场,台下一千六百多群众无一人退席,都要看个结果,气氛十分激烈紧张。我和艾青的夫人韦嫈站在台上从大幕后面的幕缝看到台上台下情况,忧心忡忡,非常着急。忽见大会主席吴玉章老先生站了起来,他见双方僵持不下,劝解说:“萧军同志是我们共产党的好朋友,我们一定有什么方式方法不对头的地方,才使得萧军同志发这么大火。我们应当以团结为重,自己先检讨检讨”。萧军一听气消了不少,站起来说:“吴老的话还让人心平气和,这样吧,我先检讨检讨吧,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的错行不行?那百分之一呢?你们也想一想是不是都对呢?”这时丁玲忽然站起来不顾吴老的调解和开导,不冷静地说:“这一点最重要,我们一点也没错,百分之百都是你的错,我们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你这个朋友等于九牛一毛,有没有你萧军这个朋友没关系”。萧军一听气又来了,他说:“我百分之九十九的错都揽过来了,你们一点错都不承认,尽管你们的朋友遍天下。我这根毛啊也别附在你这牛身上。我到延安来没带别的,就是一颗脑袋,一角五分钱就解决了(一角五分钱可以买一颗子弹),怎么都行,从今天起,咱们就拉——蛋——倒!”萧军用右手重重地顿了三下,怒气冲冲走到幕后招呼我“走!”下台而去,大会不欢而散,群众议论纷纷[9]。
这里萧军在大会上所念的“备忘录”,是萧军所写的一篇短文《纪念鲁迅——检查自己》。写这篇文章的起因是:六月初,萧军接到通知要他到中央研究院去参加批评王实味大会。会后他对会上一边倒的批判方式发了几句牢骚,不料被走在旁边的一位女同志听到了,回到“文抗”她就向党组织汇报了。过了几天,中央研究院派来了四个代表:有金灿然、王天铎、郭小川、郭靖,拿着一份八大团体一百零八人签名的“抗议书”来找萧军。代表们走了以后,萧军越想越生气,立刻连夜写了一份“备忘录”,把那天去中央研究院参加批判王实味大会所见所闻经过,连同本人的意见详尽地写成书面材料准备上呈中共中央毛主席。
没想到,这篇“备忘录”却在鲁迅逝世纪念大会上引起如此轩然大波,而且还影响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层。10月19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纪念鲁迅先生》,指出:“鲁迅先生的伟大,不仅在他是一个中国近代的最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体大的革命家、民族解放的战士、中国共产党的良友与战斗的同志。”同时还特别强调:“只有与先进的阶级一起,只有自愿的遵守它的‘命令’,只有与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恶劣残余及反革命的托派活动作坚决的斗争,才配得上作为‘鲁门弟子’,才配得上作一个先进的文学家,作家”。同一日的《解放日报》上,还登有祭文《鲁迅先生逝世六周年祭》以及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和《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的片断,以表明鲁迅的党性原则和战斗精神。《解放日报》的社论,显然是针对萧军而来。
1943年10月19日的鲁迅逝世七周年纪念日真是“别有一番滋味”。这一天,在延安并没有举行任何纪念鲁迅的活动。而同一日的《解放日报》以近三个版面的篇幅,全文发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同时在题后文前加“按语”。该“按语”称:“今天是鲁迅先生逝世七周年纪念,我们特发表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二年五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纪念这位中国文化革命的最伟大的最英勇的旗手。”“讲话”以如此的方式隆重出台,这其中颇具有一种象征的意味:从此开始,延安大型的鲁迅纪念活动不再举行,代之而起的乃是以“讲话”为精神核心一种新的文学体制和文学规范。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由此而拉开序幕。
三、鲁迅研究成为延安的“显学”
延安是当时鲁迅研究的重镇。早在1937年5月,在延安即由“文协”主持召开了两次会员座谈会,讨论由上海左翼文艺运动引起的“两个口号”的论争问题。到会七、八十人,丁玲任主席。根据丁玲建议,由原来从上海来的文艺理论组的负责人李殷森(朱正明)会前阅读了一些资料,作了长时间准备,在会议一开始,就作了关于联合战线下的文艺运动的报告。据他后来在一九三七年秋天回上海后写的《陕北文艺运动的建立》中,说他的报告的内容为:第一部分是联合战线论;第二部分检讨这两个口号的论争;最后是联合战线下文艺运动的目标和任务。文章中记录了他当时的观点:“显然的‘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更适合于进行和建立战线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这个口号是太狭窄了。即以它的名字一项而论,标榜‘大众文学’,那末非大众的分子就已经都被关在门外,丢到联合战线之外去了。民族统一战线不仅是要‘大众’的联合,而且是要联合非‘大众’的资产阶级、地主以及甚至军阀等等。如果政治上的联合战线或整个的联合战线的阵营是这样的广泛,而文艺界的联合战线却是如此的狭窄,那末这个联合战线是不可能建立的。所以‘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这一口号在目前确是不适合的。”他还在文章中介绍了中央局宣传部长吴亮平做的结论:“最后,由中央局宣传部长吴亮平做了结论。他说对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论争,我们同毛主席与洛甫、博古等也作过一番讨论,认为在当前,‘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更适合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作为一种前进的文艺集团的标帜是可以的,但用它来作为组织全国文艺界的联合战线的口号,在性质上是太狭窄了。”这篇文章也简要地谈到座谈会上“吴奚如和白丁两人是赞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的,因为它的革命性质比较明显。”根据参加这次座谈会的一位同志回忆,当时他曾就“两个口号”的讨论等问题,问过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笑着回答:“两个口号都是对的。不过,一个有立场,一个没有立场。”
自从鲁迅被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被确立为新文化的“旗手”,“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以后,鲁迅研究遂成为延安的“显学”之一。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吴玉章、谢觉哉等都是铁杆的“鲁迅迷”,床头或案头常年都放着鲁迅的著作,而且对鲁迅都有精深的见解和研究。而鲁迅的弟子、战友和专家如丁玲、萧军、周文、欧阳山、草明、高长虹、范文澜、艾思奇、陈伯达、胡乔木、周扬、徐懋庸、周立波、何其芳、舒群、罗烽、力群、胡蛮、江丰、雪苇、张仃、须旅、何干之、欧阳凡海等更是遍布延安各个机构,至于说鲁迅的崇拜者和忠实读者,更是不计其数了。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1941年1月15日,延安成立了鲁迅研究会。“鲁迅研究会”选出艾思奇、萧军、周文三人组成干事会,同时又成立了由艾思奇、萧军、周文、周扬、陈伯达、范文澜、丁玲,萧三、胡蛮、张仲实等十人组成的编委会。鲁迅研究会成立后,召开了多次例行的工作会议,制定了详细的研究纲领和研究的步骤,从而在传播和宣传鲁迅方面发挥了核心的组织作用。继延安鲁迅研究会成立之后,1941年2月5日,晋察冀边区拟成立鲁迅研究会。《晋察冀日报》报道:沙可夫、远千里、田间、孙犁、周而复、张春桥、周巍峙等已组织鲁迅研究会筹委会,鲁迅研究会即将成立。抗日战争结束后,在延安的鲁迅研究会的主要成员大多移师张家口。1946年7月14日,张家口鲁迅学会成立。7月14日张家口鲁迅学会成立。学会选出常务委员五人:萧军为常务,何干之出版,欧阳凡海研究,其余的为邓拓、沙可夫。这三大鲁迅研究会,除了主持或参与上述的鲁迅纪念或宣传工作外,还在鲁迅研究和普及方面做出了卓有实效的工作。这些工作包括:
1.编辑出版了三辑的鲁迅研究丛刊。延安鲁迅研究会成立时,即制定了详细的研究纲领和研究步骤。“研究纲领”中拟从六个方面对鲁迅及其作品进行全面的研究并大致落实了具体的研究人员:A、思想研究:艾思奇、陈伯达、雪苇;B、行传研究:萧军;C、创作研究:丁玲、周文、舒群、周扬、立波;D、翻译方面;E、学术研究:范文澜、江烽、胡蛮;F、鲁迅作品在国外的研究。而在1941年在延安出版两辑《鲁迅研究丛刊》即是上述各领域研究的论文结集。《鲁迅研究丛刊》第一辑分思想、创作、行传、学术四个专栏,收录九篇鲁迅研究专题论文,同时还附录了三篇有关延安鲁迅研究会活动的报道。《鲁迅研究丛刊》第二辑收录文章五篇,分别为:《论鲁迅》(毛泽东)、《论鲁迅的杂感》(瞿秋白)、《回忆鲁迅先生》(萧红)、《铸剑》(萧军)、《采薇》(萧军)。但遗憾的是,第二辑《鲁迅研究丛刊》虽然已经排好并打出了纸型,却因当时经济和印刷条件太差而未能得以付印。同时,延安鲁迅研究会为纪念鲁迅逝世五周年,于1941年5月27日在《解放日报》发出《敬征关于讨论阿Q文献》的“启事”。8月,《阿Q论集》编辑成书,收有钱杏邨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青见的《阿Q时代没有死》、茅盾的《阿Q相》、徐懋庸的《关于阿Q》、锦轩的《阿Q的后事如何》、鲁迅的《阿Q正传的成因》、朱彦的《阿Q与鲁迅》、张天翼的《阿Q论》、立波的《论阿Q》等论文共20余万字[10]。但遗憾的是,《阿Q论集》在延安时,本来印刷厂说好与《鲁迅研究丛刊》第1辑同时出版,但最终没能印成。据说纸型已经打好,萧军曾经催问过几次,却没有得到回答。1945年大批干部陆续离开延安前往东北、华北,萧军希望吧《阿Q论集》的纸型带出来,也没有回答[11]。另外,张家口鲁迅研究会编辑的《鲁迅学刊》在于1946年8月5日在《晋察冀日报》副刊版上创刊。它是张家口市鲁迅学会的会刊,萧军主编,只出版了4期,最后因《晋察冀日报》撤出张家口市而停刊。《鲁迅学刊》是最后一个在《晋察冀日报》上创办的副刊,在它短短4期里,关于鲁迅作品和学术思想的评论文章,使读者更多地了解了这位左翼文艺旗手的坚韧的战斗精神和不懈的革命斗志。以上各级鲁迅研究的刊物,均有鲁迅的学生萧军编辑。
2.撰写了高质量的鲁迅研究的论文和著作。延安时期的鲁迅研究成果,除了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等的鲁迅论之外,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论文或著作还有:艾思奇的《鲁迅先生早期对于哲学的贡献》,周扬的《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现实主义者的路——纪念鲁迅逝世二周年》、《精神界之战士——论鲁迅初期的思想和文学观,为纪念他诞生六十周年而作》,正义的《鲁迅语言理论的初步研究》,茅盾的《关于<呐喊>与<彷徨>》,立波的《谈阿Q》,萧军的《<铸剑>篇一解——鲁迅先生历史小说之一》、《<铸剑>篇底史料又一出处》,张仃的《鲁迅先生作品中的绘画色彩》,何其芳的《两种不同的道路——略谈鲁迅和周作人的思想发展上的分歧点》,何干之的《鲁迅思想研究》(张家口新华书店1946年5月版)等。这些论文或专著代表当时鲁迅研究比较高的水平,至今仍有着比较大的影响。另外,在延安至少还有三次比较集中探讨鲁迅及其作品的学术讨论:一次是六届六中全会之后由陈伯达、艾思奇、周扬等发起的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一次是延安整风时期关于“鲁迅杂文时代”的讨论,一次是1942年默涵和力群在《解放日报》上关于“祥林嫂的死”的讨论,这三次围绕着鲁迅作品的大讨论,对于深入研究鲁迅及其作品产生了相当大的助力。
3.以多种形式进行鲁迅及其作品的普及工作。让鲁迅及其作品深入到大众之中,也是鲁迅研究会的重要工作之一。举办讲座,是普及鲁迅的主要方式。1940年12月25日,边区文协文艺顾问委员会为使文艺小组及其他团体的文艺习作者,有系统地了解文艺理论,特约延安作家每两周在文化俱乐部报告一次。这其中,茅盾报告了《中国文学运动史》、周文报告了《阿Q正传》。1942年5月7日,陕甘宁边区米脂的文艺运动,已逐渐活跃起来。雷加在米脂中学作了《<阿Q正传>漫谈》的报告。1946年8月26日,全国文协张家口分会、鲁迅学会等为帮助广大爱好文艺青年自修,联合举办暑假文艺讲谈会,每周二次。萧军讲如何从事业余文艺工作,欧阳凡海讲中国新文艺发展史略;何干之讲文艺的使命和现代中国几位革命文艺作家介绍(鲁迅、郭沫若、茅盾);沙可夫讲马克思主义文学观;周巍峙讲农村文艺运动的几点经验;唐伯弢讲关于改革平剧的几个问题,邓拓讲文化普及运动的几个问题(详见《解放日报》报道)。编写鲁迅及其作品的通俗读本来宣传鲁迅,也是普及鲁迅的重要方式之一。在这方面,作家孙犁和徐懋庸花费了更多的心血。1941年9月,孙犁编写的《鲁迅的故事》出版。该书由沙可夫作序,作为“青年儿童文艺丛书”由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出版发行。另外,孙犁还编有《少年鲁迅读本》共十四课,连载于边区《教育阵地》[12]。1942年12月24日晋察冀边区文协准备于近期由孙犁编写《少年鲁迅读本》。后该书于1946年6月由晋察冀边区张家口教育阵地社出版。徐懋庸也是鲁迅的着力宣传者之一。1943年,他对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和《理水》进行的通俗的注释,其中力图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新精神来诠释鲁迅作品,这两本书分别于1947年7月和9月由华北书店出版。
鲁迅及其作品在延安及各解放区的广泛宣传和传播,使得鲁迅的形象和思想日益深入人心。鲁迅在延安不仅是中国现代新文化的象征,更是人们的人生指针和精神偶像。在如此的历史情势下,一股由“鲁迅”而引发的文艺思潮在延安文坛悄然涌动。
[1]惊秋.陕甘宁边区新文化运动的现状[N].新华日报(重庆),1941-01-07.
[2]读鲁迅先生书——并怀念雪峰[M]//杜鹏程文集:第3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78.
[3]海伦·斯诺.卓有成效的延安舞台[N].安危,译.陕西戏剧,1984(3).
[4]共产党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为追悼鲁迅致国民党中央南京政府电[N].红色中华,1936-10-28.
[5]L.Insun.西北特区特写·陕北的戏剧运动[J].正明,译.今日中国(英文版),1939(8).
[6]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致许广平女士电[N].解放,1938-10-31.
[7]欲明,密林.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昨日下午在青年会举行[N].新华日报(武汉),1938-10-20.
[8]郁文.鲁迅先生逝世四周年纪念大会志[N].新中华报,1940-11-07.
[9]王德芬.我和萧军风雨50年[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1):117-118.
[10]征集《阿 Q论》文献[N].文艺月报,1941-05-01.
[11]萧军.鲁迅研究丛刊·新版前记[J].学术丛刊.哈尔滨:鲁迅文化出版社,1947.
[12]张学新.晋察冀文艺大事记[J].新文学史料,198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