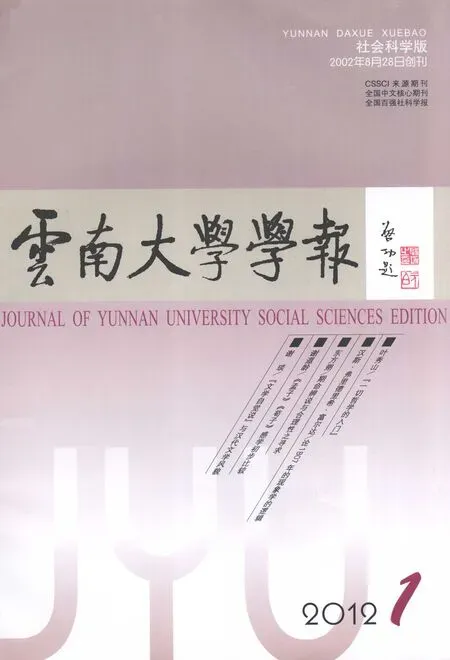论1807年的现象学的逻辑
汉斯·弗里德里希·富尔达著,舒远招译
[1.University of Heidelberg,Heidelberg Germany;2.湖南师范大学,长沙410081]
论1807年的现象学的逻辑
汉斯·弗里德里希·富尔达1著,舒远招2译
[1.University of Heidelberg,Heidelberg Germany;2.湖南师范大学,长沙410081]
黑格尔;现象学;逻辑
在研究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内容时,应该同时研究其体系学的形式。1807年的现象学是建立在诸逻辑基本环节的某种序列的基础上的,而这种序列与黑格尔当时的逻辑学构想是相一致的,并且在现象学内具有一种统一的功能。要弄清这些基本规定之进程,有着诸多困难。在现象学的布局中的修改并没有走到损害现象学之逻辑根基的地步。本文第一章表明,从一开始,黑格尔就提出了这一要求:在非实在的意识的方式与逻辑的环节之间要有一种严格的对应。第二章讨论这些逻辑的环节作为什么进入意识的经验当中,以及它们如何组织意识的经验。第三章具体说明这些逻辑的基本环节的序列及其同意识的诸阶段的对应。文章最后还把一种有关现象学的方法和有关耶拿逻辑学的发展的见解,提出来进行了讨论。
近几十年来,对黑格尔现象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这部著作的形而上学的、人类学的、社会的和历史的观念。这些观念,曾经是丰富而具体的、有助于我们的时代意识达到自我理解的内容。与之相比,现象学的形式,它的体系学与方法,则似乎激发不了人们的兴趣。尽管当今有一半的世界哲学在谈论辩证法,而且在谈论时知道对黑格尔的影响史负有义务,但是却几乎没有这样的工作:即通过尽可能准确地分析黑格尔的思想形式,而在辩证法的意识中估测与黑格尔的距离。尽管黑格尔辩证法的形成史使人感到惊讶:在思辨的观念论者中,最早满足于将康德实践哲学的成果和原则转化为时代批判之实践的那个人,却恰好是黑格尔,是他忽然构造了哲学史所了解的最为抽象的、似乎离生活最为遥远的学科——思辨逻辑学;尽管黑格尔当年是从当今实际应用的辩证法相信离它们并不遥远的那些动机出发的,然而,关于黑格尔的思辨,它的这种片面的理论的性质,通常总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概念辩证法在实践理念中所具有的那个根源,却很少得到研究。最后,尽管黑格尔的现象学是将存在于时代中的要求传达给他的时代之教育,并且同时在时代要求和教育面前为思辨知识做出系统辩护的最为详尽的尝试,它却几乎没有作为这样的尝试而得到认真探讨。新黑格尔主义复兴的辩证法所带有的学院式的苍白无力,和另一方面即现代逻辑学和科学理论的说服力,似乎禁止了这一点:在同黑格尔的直接论辩中使辩证法成为一个问题。
假定情况这样,即这种禁止事实上是无限有效的,尽管如此,我们哲学思维 (Philosophieren)的历史性理解的幅度和强度,却依然要求在进一步追问现象学的内容时,依据其体系学的统一来研究现象学。以下的阐述,就带有这个目的。当然,在表明思辨逻辑学在怎样的形态中,并且以怎样的方式进入现象学的时候,仅仅是满足该目的的诸多必要条件之一。以下阐述并不想揭示:现象学必须整合哪些不同的思想动机。以下阐释也无意解释现象学或意识的经验科学的这一普遍的思想:一门科学的思辨的观念,该科学是在意识的要素中进行的,并且因此也是自然的知识可以通达的,但是其根据、地基和“以太”(Äther)却已经构成了纯粹的知识。以下阐释假定了对于现象学的观念、对于现象学与随后出现的逻辑学的关系的规定事先已有所了解,并且试图说明:这个1807年没有阐述的逻辑学—构想,在已经阐述的现象学的范围之内,是如何出现的,以及对显现着的知识的描述,如何构成了一个系统的整体。如果在现象学中存在着这样一个整体,那么,人们可以把上述问题纳入一段黑格尔引文—— “这个作为自在的东西 (das Ansich)的内容,这个首先还是一种内在的东西、不是作为精神、而首先只是精神的实体的目的”,现象学应该产生出这种实体的自为存在——之中吗?[1]
对进入这个方向的一种解释尝试形成障碍的是这样一个信条:人们根本不可能谈论现象学的某种统一地贯通着的体系学。现象学之作为著作整体 (Werk-Gangzes),只能历史性地加以把握,自黑林 (Haering)对现象学的形成史做了研究以来,口号就是如此。这种见解的根源,原本已经存在于黑格尔学派之中,该学派面对1807年的这本书时总是显得尴尬。但是,首先是对现象学进行划分的尝试的大量出现——在这期间至少有七种此类尝试①对此请参阅作者:《进入黑格尔逻辑科学的一个导言问题》(Das Problem einer Einleitung in Hegels Wissenschaft der Logik)。法兰克福/美因茨1965,57及后面各页,124及后面各页。——和对于这部著作的文本出处的历史性的—语文学研究,有助于这种见解达到对于自身的意识。在这期间,珀格勒 (Pöggeler)令人信服地阐明了现象学不可能以黑林和霍夫麦斯特 (Hoffmeister)所指明的方式实现出来。然而,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现象学的阐释并不是完全按计划进行的,这种证据是如此地有力,以致于即使珀格勒也首先须依照这部著作的命运 (das Werkschicksal)来进行解释。如果黑格尔本人确实承认过现象学的编排遭到了那种他在出版和印刷过程中曾经抱怨过的“不幸的混乱”,[3](P161)如果一位与黑格尔有相同地位的作者都指证了自己,那么,想使人相信他的著作具有贯通的统一,就显得毫无指望了。但是,黑格尔在其面前自陈有失的语文学分析的法庭,并不是必须在此作出裁决的唯一的主审机关。一种著作史的诠释,理应在编排和构想之间作出区别,并且把对构想的解释放在首位;因为有关某部著作之构造的不和谐性的任何一种论断,都已经预先假定了有关该著作的观念——这种观念必须以适当的方式获得——的一种事先决断(Vorentscheidung)。在黑格尔对“他在其中使精神自我运动的西班牙式的方法的靴子”所做的自信的表态[3](P332)与我们试穿这双靴子的尝试之间,有一种鲜明的对照。有鉴于此,宣称我们拥有这样一种关于现象学的观念,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可疑的了。如果黑格尔语文学不应当陷入那条出自于康德的解释、作为拼凑工作理论 (patch work theories)而为人所熟知的歧途的话,则首先就应该揭示现象学的逻辑根基,并且审查:由黑格尔所指明的这种划分的复多性 (Pluralität),是否并未由此并没有证明是必要的和得到辩护的。如此一来,这部著作之统一性的界限,才可以得到规定。
倘若凭借对现象学所包含的逻辑的追问,现象学的划分理应得到更好的理解,那么,构成现象学之基础的逻辑诸环节 (Momente),就必须作为逻辑的环节被探明;被奠基者 (das Fundierte,指现象学——译者注)把这些环节(指逻辑环节——译者注)歪曲得面目全非的原因,必须被揭示出来,而且还必须表明:这些环节之联系的隐蔽性,并没有给“现象学的概念基础在编写期间就被撕碎了”这一假定提供辩护。着眼于这个纲领,我想提出在以下阐释中应该得到证实的诸论点。我要断言的是:
1.1807年的现象学,建立在逻辑基本环节的某种序列之上,而这种序列与黑格尔当时的逻辑学—构想相一致,并且在现象学之内具有一种统一的功能。
2.要弄清这些基本规定之进程,有着诸多困难,这些困难首先根源于现象学的观念。然而,这些困难也部分地根源于思辨逻辑学在大约1805年所处的状态,部分原因,或许还在于现象学在其中得以实现的那些环境。
3.在现象学的布局中的修改——倘若黑格尔在排印期间还做了这类修改的话——并没有走到损害现象学之逻辑根基的地步,——也许在仅有的一点上例外,但这一点还需要研究。
为了使论证具有条理性,我并不想对每个论点逐一展开讨论。对这些论点的论证,穿插在以独立主题为中心的三章当中。第一章应该表明,从一开始,黑格尔就提出了这一要求:在非实在的意识的方式与逻辑的环节之间要有一种严格的对应。第二章讨论,这些逻辑的环节作为什么进入意识的经验当中,以及它们如何组织意识的经验。接着,第三章必须说明,这些逻辑的基本环节的序列及其同意识的诸阶段的对应。凭借这种方式,将使这一点成为可能:除了涉及现象学之建筑术的上述论点,还要把一种有关现象学的方法和有关耶拿逻辑学的发展的见解,提出来进行讨论。
一
A.一般而言,科学的任何一个抽象环节,都有一个显现着的精神形态与之对应,黑格尔本人在现象学的末尾说出了这一点。然而,“科学”这个称号——这种对应被归于该称号——使得许多作者,甚至还有珀格勒,[3]从这个段落[1](P562)和与之相似的段落[1](P33,74)中,得出了这种意见:这个体系的任何一个部分,都应该有一种现象学的形态与之对应。于是,这种归入(Zuordnung)就显得是很不准确和有漏洞的。只是,文本关联清楚地表明:黑格尔必定意指了现象学的诸形态 (Phänomenologie-Gestalten)要归入逻辑的诸环节。因为在这句被援引的引文中所谈到的“科学”,在那里本身是作为哲学体系学的环节出现的:作为这样的环节,科学在哲学体系学中本身即是内容,与具有其他内容即一方面是意识、另一方面是自然和历史的其他环节并列。也就是说,它涉及到在第二部耶拿实在哲学的结尾处被指出的同样的体系划分。[4](P272)逻辑的东西在其中本身就是 “科学”,只要它在 “其生命的以太”[1](P562)中展开精神的定在和运动。与此相应,现象学的序言也表明:首先在意识的要素中形成的精神的诸环节,在现象学结束之后会在知识的要素中运动,而且这种运动就是它们的“在简单性的形式中”的运动,就是“逻辑学或思辨哲学”。[1](P32)最后,在被断定的对应关系中明确说到了科学的“抽象”环节,说到了科学的“纯粹”形态,纯粹概念及其运动。所以,人们必须毫无疑问地认定:这种对应,不应该关系到整个体系的划分,而只应该关系到逻辑的主要环节。
这些被引用的文本段落,形成于现象学的撰写即将收尾之际。考虑到黑格尔的构想可能发生了改变,所以,它们仅仅就整部著作而言才允许被使用,倘若它们应该与现象学的开端就整体的进程所说的那些话相一致的话。情况实际上就是这样。因为在导论的末尾处[1](P74)黑格尔曾承诺:意识的经验必须在自身中把握“精神之真理的整个王国”,也就是说,真理的这些环节在这种特有的规定性中并不自我呈现为抽象的、纯粹的环节,而是呈现为意识的诸形态。这些环节,被称为该整体的环节。即使在这里,这些环节在其在现象学之外的组织中也是抽象的和纯粹的。确认这种逻辑的东西可以理解为精神的真理,这就够了。对此,下面的事实已经提供了一个证据:按照序言的这些被引用的段落,[1](P33)这些环节应该是精神的环节,逻辑学在知识的要素中把这些环节的运动组织为整体;不过,在第二部耶拿实在哲学的末尾,[4](P272)这门科学的在时间上更早的布局,也使先行于自然哲学的、亦即与逻辑学具有同等意义的“思辨哲学”,[1](P33)终结于精神关于自身的知识。同样,在第一部耶拿形而上学中,逻辑的与形而上学的认识的循环,是在“绝对精神”[5](P172)中才得以终止的。如果人们必须假定黑格尔在开始撰写现象学之前,就已经想要知道把原本二分为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体系学科做成统一的逻辑学或思辨哲学的整体,就像珀格勒令人信服地阐明的那样,[6]那么,人们也就必须假定:这门学科把它的内容的诸环节界定为精神的诸环节。然而,黑格尔说得更加清楚,他不仅一般地说到精神,而且说到精神的真理的王国。这个表达,如果不是意指精神在那个它自己就是“它的生命的以太”的地方所达到的自我适应 (Selbstadäpuation),又该意指什么呢?
最后,这种被断定的对应的意义,并不仅仅可以从黑格尔的直接表述中得知,它的必然性也可以从显现着的知识 (das erscheinende Wissen,这个词在贺麟、王玖兴先生的《精神现象学》中译本中被译为“显现为现象的知识”——译者注)的科学这个思想中推导出来。因为显现着的知识是这门科学 (指现象学——译者注)的对象,同时是这门科学的媒介,因而显现着的知识应该在这门科学中变成这样一种媒介,在此媒介中,它的本质以简单的方式是自为的。现在,它的本质的这种简单的自为存在只是一种确定的东西,并且仅当它同样是它的诸规定性——这些规定性给予它内容——的一种完备运动的结果,就像是这种运动的初始 (Erstes)和没有运动的宁静一样时,才是这种自为存在。于是,仅当它在这种定在的生成中——在显现着的知识的科学中——就已经是它的诸环节的完整运动时,它才能作为这样的媒介具有定在 (Dasein)。反过来说,也仅当显现着的知识面向它的内在的东西之整个显现范围时,它才可能是“自我完成的怀疑主义”;因为惟有如此,精神才适合于——在纯粹知识中——审查何谓真理。[1](P67)因为这个 “内在的东西”就是精神自身,正如精神隐藏在意识的要素中一样,于是,它的环节就必须在这种意识中完整地出现,由此,不仅意识能够纯化为精神,而且精神才可能是意识的真理。
B.意识诸形态和逻辑诸环节的这种对应,不论是在现象学的开端还是结尾处都被断定,但这并不一定表明:在开端和结尾处的两次断言,意味着某种完全相同的、或至少是某种休戚相关的东西。人们可以把这一点当作一种在开始时并未包含在内的修改来看待:在结尾处,精神作为这种对应的主体呈现出来;而在开端处,对应的主体却是意识,在意识的经验中,逻辑的诸环节应该对应于意识的诸形态。
恰好是着眼于必须作为经验——这种经验是意识做成的——主体来理解的东西的这种变化 (Metamorphose),这种转变,在导论的末尾就已经显示为不可避免的。这种“意识对于自身所做成的经验,按照经验的概念,是完全能够把这个东西 (指经验的概念——译者注)的整个系统,或者精神之真理的整个王国,包容在自身当中的”。[1](P74)在这个句子①当然,这个句子在语法上不可能得到明确的解决,因为人们既可以把“这个东西的整个系统”(das ganze System desselben)理解为经验概念的整个系统,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意识的整个系统。中,如果这个决定性的“或者”渐渐演变为拉丁语sive的含义,就像通常在黑格尔那里一样,那么就必须假定:他把经验概念的整个系统,也就是经验的简单统一——这种统一是自行发展的——的系统,与逻辑的王国设定为相当的。由此,意识的经验在此或许就已经经由经验的概念,而回溯到了意识的经验运动的一个主体,该主体把经验“包容在自身当中”,而且是有别于意识的一个他者。鉴于黑格尔措辞的简洁,人们还难以断定这种解释是否过于武断。但是,即使是对逻辑诸环节如何自我呈现的方式,也做出了双重刻画,也就是说,现在明确的是:它们的自我呈现,就像它们也是为意识的那样,——亦即如果人们认为逻辑诸环节以及意识,每一个首先都是自为的,此外,它们也是为 (für)意识的。但是,黑格尔接着再度更精确地说到,逻辑诸环节的自我呈现,就像意识出现在意识与逻辑诸环节的关系中那样——亦即在这种关系中,这种关系把意识作为这样的意识来构成,而且并没有首先达到意识的概念。由此,意识清楚地依据它与精神的关系并作为精神的关系被提及。接着,导论最后的句子把在描述过程中的这种关系的扬弃,宣布为最必需的东西。
对现象学方法所做的整个“先行提醒”(vorläfige Erinnerung,黑格尔对现象学方法的这种“先行提醒”是在导论中作出的,读者可参阅中译本[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上卷]第 57 ~59 页)的上下文,[1](P70~75)也体现了这种风格。在引入意识概念(Bewuβtseinsbegriff)——这种引入没有把意识作为精神的关系凸显出来——时明确提到:意识的本真的规定究竟是什么,在这里同我们毫不相干。接着,借助于对意识所作出的这些规定,这一点被指明了:对意识而言,一种作为尺度和对象的自在 (Ansich),倘若它仅仅是对于知识而言的,其差别是如何存在于这些规定中的,以及这些规定是如何使意识应该实施的一种审查运动成为可能的:这种审查运动就是意识的经验。在承认了这种运动——只要在其中产生出新的对象——包含了我们附加的一个赋予该进展以必然性的环节之后,借助于对精神之真理的提示,这个意识概念才被超出。从这种区别及其扬弃出发,接着还可以阐明这种呈现出来的意识运动的双重含义及其目标。
作为一种精神运动的意识之经验的构想,不可能是在撰写现象学的过程中才形成的,这一点,如果还需要一个证据来支持的话,那么,该证据在第一部耶拿精神哲学中就已经可以找到了:在那里,意识也被回溯至伦理的绝对总体性,回溯至一个民族的精神,在这个民族精神中,先行的级次 (Potenzen)自此开始都变成理想的;[4](P235)在那里,这种回溯也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我们以此来认识精神的组织的方面,[4](P200)另一方面,是意识如何把反思——它依照这另一个方面曾经是我们的反思——设定在自身之中的方面。[4](P203)
那么,从所有这些东西中会得出什么结论?至少可以说:如果人们想要就现象学这部著作的命运作出猜测的话,人们当然 (eo ipso)不可以把在现象学进程中所做出的对于其基本概念的重新诠释,当作构想之转变的一种索引,而只能当作这个构想的必要环节,而该环节的效力范围必须是已经可以通观的,否则,这种重新诠释对于文本理解所产生的不清晰性,就总是会多于对这些不清晰性的排除。
二
在上一章中只是阐明,黑格尔断言:意识的这些个别形态对应于处在稳定次序中的逻辑的诸主要环节;但是,上一章并未像黑格尔可能确信的那样,阐明这种对应是可能的,而且在现象学的不同阶段上统一地实现出来了。倘若这种确信得不到辩护,则下面的立论就总是缺乏根基的:这些逻辑环节在现象学中拥有一种确定的功能,它们的秩序必定是隐蔽的,甚至在表面上必定被弄乱了。所以,现在必须表明,那种逻辑学在纯粹思维中作为“确定的概念”来处理的东西,[1](P562)是如何把现象学也组织成一个整体的,在这里,这种纯粹的规定性并无必要被“我们”、抑或被我们所考察的意识设想成逻辑学的确定的概念,并拿来用于论证。
如果人们——正如它在这种关联中可能显得是必要的那样——想要探究现象学的程序中那些终究构成了该程序之独特的、与思辨逻辑学相对的特殊的逻辑性,那么,就会出现可能让人害怕的问题。思辨的辩证法——它现在是“现象学的”或纯粹概念的——说到底真有一种能够讲得清的意义吗?对于这个问题,在此当然不能作出确切的回答。不过,即使人们在历史地忠实于某种在历史上有强大影响的思想时,假定了思辨的概念辩证法的讨论价值,下面这种做法也是富有意义的:把辩证法的探讨拓展至精神现象学,并追问现象学的方法以怎样确切的方式预期地参与到了纯粹概念的思辨认识,而并非就已经是这样一种认识了。如果沉湎于对现象学的这个从现象学上来阐明的内容的直接理解,不了解现象学的认识与思辨概念的上述被断定的关系,并依据一种照常形成的“事情—直观” (Sach-Anschauung)来审查现象学的个别教本的明见性 (Evidenz),这不是更好一些吗?增补这种解释模型——顺便说一句,这种解释模型在许多情形中都证明了它的多产性——的需要,除了体现在待解释者(指黑格尔本人——译者注)的独特要求中,还体现在这个事实中:今天,辩证法的讨论并不像经常指向历史性地自我理解的情境分析的一种合理媒介那样,常常指向一个在自身中封闭的纯粹概念的体系了。只要这种意图归根到底与黑格尔还有一种关系——该意图向黑格尔显示了一种无场所的普遍的思辨—逻辑的东西的观念的无意义性,就必定会进行有关现象学的辩证法结构的探讨;因为对黑格尔来说,现象学是这样一个地方,在这里,历史情境的出口,同进入纯粹概念辩证法之“神秘主义”(Mystik)情境的入口相遇。因此,如果人们打算对现象学做一种富有成效的解释,那么,“现象学是如何做成的”这个问题,就可能不是多余的。当然,为了使这种解释更加富有成效,还必须要求这种解释并不放弃黑格尔对一种纯粹概念辩证法的要求,而且并不妨碍沉湎于黑格尔式的所谓概念“运动”。正如黑格尔本人在运用概念阐释的方法构造他的“体系”之前,曾寻找对他而言是确定的东西的真理一样,一种针对现象学之方法的提问,也必须在现象学的结构中寻找一种真理,它并不必然地是自我思维着的概念的那种真理,但也许依然允许有一种合理的理解。
我的目的只在于确立上面的立论,为了这个有限的、并不指向现象学辩证法的一种普遍讨论的目的,这种要求 (指在解释“现象学是如何做成的”时,又不放弃黑格尔对纯粹概念辩证法的要求这个要求——译者注)也许必须由此而得到满足:人们把黑格尔对现象学方法的事先和事后的说明,同在个别章节中事实上实施的程序进行对照。不必审查或假定现象学证明在细节上的严格性,也不要复制高度分化了的现象学观念,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在技术上把握现象学的构造程序,并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这种程序作出评判。当然,这种判断在思辨的概念性 (Begrifflichkeit)的普遍思想及其连贯性 (Kohärenz)——这种连贯性的可能性是人们必须预先假定的——中,会找到自己的界限;它也会在黑格尔的下述要求中找到自己的界限:在系统地组织起来的概念中,能够接纳 (einholen)首先是事实上出现着的现象学思想。同黑格尔的这个要求相比,以下阐释仅仅是对于现象学方法形态的“外在反思”。不过,相对于某种黑格尔化的构造,以下阐释具有这样一个优点:不必复制和论证思辨的证明过程。
A.如果与表面现象相反,这一点应该是真的,即科学的每一抽象环节一般地都有一个显现着的精神的形态与之对应,那么,这种对应的意义就必须是可以说明的,而且,有关这种对应的断言是必须可以确证的。如果放弃这种意义的一种思辨的构造,则这只不过意味着:那些由于黑格尔的逻辑学而为人所熟知的基本环节,在其未变更的次序中,总是可以在现象学的确定的体系位置中重新找到,而且,从对于现象学之方法的说明中,可以为必须被视为“位置”(Stelle)的东西找到标准。可以表明:逻辑序列的诸环节,会在对显现着的知识的描述的哪些位置上、并且以怎样的方式进入意识的经验,以及它们如何在经验中达到连续性。在此必须预设:这些呈现为形态的环节,并不把这些形态作为对应于它们 (指逻辑诸环节——译者注)的东西,仅仅展示给那种根据思辨—逻辑的阐释来把握的知识。由于现象学本身的确是一种先行于逻辑把握的认识的展开,因而这种预设很可能是有效的,——完全不用提及关于这种认识的那些说明,在这些说明中,那种对应被断定了。如果这种假定是有效的,则可以推论:这种对应,并不只是借助于意识在其各个阶段上的发展了的整体而变成可以理解的;因为一种不是思辨地展开的思维,当然恰好理解不了这个当下整体的逻辑性。于是,这种对应必须借助于对显现着的知识的描述的个别特征而给出。支持这一点的还有:对经验的这些说明,就像对于逻辑学和现象学方法之区别的最终提示一样,都使这种对应集中于确定的点。
如果人们承认,这种对应可以借助于对显现着的知识的描述的规定好了的个别结构要素而看出来,那么,这一点就显得是可能的:这种对应并不存在于唯一的关系中,而是存在于逻辑环节与当下整体的不同方面的多重关系之中。情况甚至很可能就是这样。因为正如已经表明的那样,逻辑的诸环节,以及它们的简单本质,即概念,[1](P562)其自我呈现是具有歧义性的:这些环节,作为自我呈现着的东西,就像作为意识、作为意识的诸形态一样,同样是在意识中的,或者是为意识的;此外,与自我呈现的概念的关系还表明:逻辑诸环节还呈现在认识中,即呈现在对显现着的知识的描述中。于是,这些环节以三种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1.在意识中,这就是说,正如它们是为意识的;2.在意识的当下形态——它们作为自我呈现的东西是这种形态——的要素中;3.在认识——我们是这种认识——的要素中。这种对应,应该跟哪种呈现方式有关呢?
显然,如果这种对应仅仅跟最后一种呈现方式有关,这是不够的,因为这些环节的自我呈现,的确应该使意识的自我审查成为可能。但是,这也是不可能的:这种对应此外还仅仅与这些环节作为意识诸形态所是的东西有关。虽然人们必须承认存在这样一种对应,因为根据文本,当意识出现在它与这些环节的关系中时,这些环节确实应该是形态。但是同时,它们应该是为意识的;而且,如果自我审查的意识这个思想——自我完成的怀疑主义的理念——应该得到满足的话,则逻辑诸环节无论如何还必须在其为意识的存在中,构成一个连续的序列;是的,对方法的先行说明 (见《精神现象学》导论——译者注)甚至使人期待:这种序列是最重要的东西。但是,这个序列是如何实现的呢?对我们的认识来说,什么东西在意识当中,这确实是从构成当下意识形态之原则的东西出发来界定的。这种东西就在当下的意识形态那里,而当下的意识形态不是简单之物,而是一种感性的和概念的、普遍的和从属于精神之具体的历史性生命的多种规定的混合。意识形态之作为意识形态,并不具有逻辑进展中的某个环节的性质;而且它的独特的纯粹概念的基础,是纯粹科学的一个后来的阶段:理论自我之作为意识向绝对精神的发展。①在耶拿形而上学中就是这样,它大致对应于在纽伦堡逻辑学中从理论理念之向绝对理念的进展。于是问题是:逻辑诸环节的整个运动,如何才能被整合进这个进展之中 (抑或整合进意识的这个进展之中,正如它在精神中自在自为地自我规定那样),如果该进展被描述为诸形态的序列的话?也就是说,如何能够以双重的方式——这些形态本身包含这种对应,和在这些形态中为意识的东西包含这种对应——被整合进这个进展之中?
对形态序列本身而言,这个问题是不难回答的。形态,这个在黑格尔自然哲学中引进的概念,是关系的一种总体性,[5](P265)在此总体性中,两个方面处在独立性 (自我等同的存在)的规定性之中,[4](P22)因而无论如何不是什么简单之物。因此,对应不可能跟形态的实在性(Realität)有关。但是,对应也不应该仅仅跟形态中的某个个别的方面有关,因为逻辑诸环节是诸形态。对应只能面向形态的原则,而这个原则,同时是在所知和知识的规定中形态之现实化的普遍要素。但是现在,由于这个原则在现象学中始终是作为结果——在此结果中,先行形态的辩证运动对我们而言结束了——而获得的,有鉴于此,形态序列本身与逻辑连续性的对应便得到了保证。
但是,为意识的东西情况如何?逻辑的序列何以在意识中有其对应?凭借这个问题,在形态范围内的一个部分或环节被寻求了;这个部分的条件是:它拥有必需的简单性,以便能够作为一种符合逻辑形式的东西得到考虑。但是同时,它必须是形态的原则在其意识中是如何为意识的方式。现在,对黑格尔来说,通过意识概念,事实上确保了意识的某种形态能够满足这些条件;因为在与生命——在生命中,对个别生命体而言,它的普遍之物,即它赖以生存的内在的生命过程,并未变成一个自为的生存者[5](P165)——的区别中,意识作为自我(Ich)是简单的类,这个类自为地作为这种简单之物而实存。[1](P138)如果这个简单之物一般地对于自我有效,那么,正如我们在现象学中所考察的那样,就无论如何有某种类似的简单之物,对于作为意识的自我和对于意识有效。即使人们没有从意识和真知识的这个简单之物出发,思辨地复制现象学的概念,人们也可以由此看出:在意识当中,什么东西必须符合于逻辑的形式。因为形态的原则,同时是自然意识试图依此达到真知识的当下的类型和方式。通过总是构成对象和知识的东西 (这个“东西”指意识——译者注)的发展,形态便达到了一系列具体的规定,就像在其原则的范围内被设定的那样。但是,这些规定的要素,及其共同持存的媒介,保留了那种简单的、作为先行运动之结果而获得的统一。[1](P91)自然的意识常常把自己和它的对象冒充为某种东西,在这种被冒充的东西的范围内,这种统一,又重新作为自然意识的对象性内容和它的知识的基本规定而找到了自己,即作为那种在意识看来就其内容而言是真实者 (das Wahre)的东西,和作为知识必须借以测量自己是否符合对象的相应的方式而重新找到了自己。或者从精神 (自我审查的意识是在同这种精神的关联中出现的)出发来看:精神作为纯粹的内在之物,作为本质(这个本质,作为在其真理中自知着的精神是向意识隐藏起来的),便是实体。这个实体在现象学中得到考察,就像它是意识的对象那样。[1](P32)此时,实体在其中便是在意识中的这种形式,就是“自在的直接性” (Unmittelbarkeit des Ansich)。[1](P558)但是,因为意识也跟那个意识将之同自己区别开来的东西[1](P70)有关,且因为意识就像在它寻求真理的过程中自我审查那样得到考察,因而对意识而言,这个自在 (Ansich)便同时作为一种知识的方式——意识将之认作正确的方式——而在场。当精神在意识的要素中铺设自己的环节时,对立便应当归于这些环节。[1](P32)因此,对应的环节一旦落入意识当中,它在多种多样的、通常总是更为具体的确定的意识内容那里,就是抽象的性状,着眼于该抽象性状,诸内容便是“自在”、“真实者”或“本质”,且同时是相关的知识形式,这种形式应该保证内容作为更真实的东西被意识到。
这个结果,通过黑格尔对于方法的说明而得到了证实。在对方法的先行提醒之后,开始了经验运动,这场运动将精神之真理的整个王国包容在自身当中,并因而应该跟精神的运动很好地同步 (phasengleich),总是跟对于意识而言是自在的或真的东西同步;它继续通向一种新的自在,对于意识而言,这个新的自在是通过意识的从进入自身的反思向一个新的、源自我们的对象的颠倒 (Umkehrung)而实现的。黑格尔对逻辑学的和现象学的描述所做出的事后区分,则指明了这一点:“在精神现象学中,任何一个环节都是知识和真理的区别”,他并且凭借期间显露出来的精神概念的手段,接着描述了如上被称作经验的那个运动:该环节作为从意识或表象进入自我意识以及颠倒过来的来回往复的运动出现。也就是说,如果人们考虑到,我们所考察的意识,事实上是把自己变成对象的精神的意识,那么,人们也就可以把这个运动描写为从意识或表象向精神的自我意识走来 (Herübergehen),这个运动把真理和知识对于意识而言的区别,溶解在一种无对象的、怀疑的非知识 (Nichtwissen)的知识当中,并且将一种把两个有区别的方面统一于自身的规定变成为我们可以理解的,然而该规定本身并未变为对象性的。反之,这个作为结果而达到的环节,则从自我意识向意识走去,如果我们将自我意识与意识的具体规定联系起来,并且由此展开精神的一个新的意识阶段的话。对于这种被考察的、在其自然的含义上的意识而言,这就意味着:当我们把它从自我怀疑的反思——它事先终止于这种反思——转向、即“反转”到一个新对象上时,它便获得了一个新的对象。
B.但是现在,凭借一种既在意识 (该意识同时要求一种确定的、认知着的行为方式)的要素、又在意识的自在 (Ansich)那儿的双重对应的基本思想,把个别的诸对应揭示出来、并由此发掘逻辑根基的可能性,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保证。对应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为了使对应变得明朗,就必须阐明在把握它的时候造成误导的那些困难。即使人们不想重构那种过程——在其中逻辑的诸环节变为自然意识的形式,人们至少必须认识那些占有被标记位置的概念的形式结构。这些概念的标记 (Bezeichnung),通常意指表象的诸形式和概念的具体化,意识将这些东西算作是自己的内容,尽管意识根本没有现实地在被提到的概念结构中思考自己的真理。意识的思维只是表面上拥有自己的概念的具体化,就像意识本身并未把自己作为自己的概念来理解一样——意识自为地确实就是自己的概念。[1](P69)然而,因为意识同时运用了更抽象的、适合于自己的结构的概念,所以,借助于个别章节的文本,通常并不难以发现有效的对应。这样,在其最初形态中的自然意识,就可能使自己的真理在与感性形式和反思形式的混合中呈现出来 (vorstellig),——意识确实同时把存在 (das Sein)冒充为真理。意识辩证法的成果被称为普遍之物。但是,意识仅仅涉及到一种感性的普遍之物[1](P100)这个提示,以及更为清楚地,这个普遍之物的结构,就已经表明意识只能符合于逻辑的无限性。在现象学的更进一步的进程中,意识在其中自我理解或我们在其中描述意识的那些规定,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依据对应的形式而使自己变得透彻。
不过更困难的,是防止通过概念而实现的不同运动阶段的不平等和干扰的误导。由于逻辑诸环节的自我呈现并不是简单的,这种自我呈现也就不可能是那种在此呈现中和在显现着的知识中由这些环节所引起的运动;而且,这个多样的运动的哪个环节在什么时候前进,这不是按照一个外在的模型而得出的,而是由这些环节的当下的关联得出的。这样,对我们而言,也就是在认识当中,一种被考察的形态还从未界定过的规定,经常就“已经现成存在了”;因为对我们而言,在对先行运动的考察中,除运动的那种最终结果以外,也形成了运动在两个方面——知识的方面和对象的方面——的统一,这种统一之作为这样的统一,如果不是在结果中变成了先行自在 (Ansich)的为—意识—存在 (Für-es-sein)的话,是不允许算作新形态的原则的。例如,对我们而言,在阐释自我意识概念的末尾,在自我意识的双重化中,如果人们为了双重化而加入这种存在于欲望的经验之中的统一的话,则“精神的概念就已经”存在了,尽管这种统一首先从属于理性的自我意识的现实化形态。[1](P140)
甚至形态本身也并不必然处在跟要素——在此要素中形态的内容具有定在——同样的逻辑阶段。因为一种形态具有哪种规定性,并不是仅仅从简单的原则——对我们而言,此原则导致了诸概念的先行的、没有成效的运用——中,而是由该原则如何规定意识的对立而得出的。[1](P32)例如,如果意识促使它的真实者 (das Wahre)不再是不同于它本身的一个他物,因为对象变成了生命,则形态就是自我意识,而它的原则和要素仍然首先是有生命的定在。[1](P263,284,125)
最后,对那种对意识而言是真实者的东西的进一步规定,还如此之久地远远落在其他各种运动的后面,就像诸结果“只能设定在对象性的含义中”[1](P103)似的。如果意识——像在导论的末尾所提示的那样——应该达到一个点,在那里,现象 (精神的真理,就像这种真理是为意识的那样,因而是意识的当下的自在)变得跟本质 (形态的内在规定,精神之真理的当下环节作为这样的形态出现)一样,那么,在一种形态的规定性的范围内,意识当然必须补上为了它的自在 (Ansich)的发展而丢失了的、走过了的阶段。由此一来,现象学直至精神——在精神中达到了这种平衡——的划分,便可以得到解释;同样,也可以解释在精神那里所发生的描述程序的转变。
C.于是,正确地分析起来,现象学的阐释便可以作为诸概念的一个考虑周详的和成体系的运动构造 (Bewegungsgefüge)而得到证实,这些概念对诸形态本身和意识的经验加以组织。但是现在,就被断定的逻辑诸环节与有关真实者的诸见解的对应的连续性而言,个别的、相互重叠的诸概念运动的多样性和阶段推移,以及一个阶段的诸初始规定在诸现实——这些现实不再属于初始规定的逻辑范围——中的展开,是一个难以洞察的问题。那个总是出现的、作为自在而变成为意识的环节,来自于完全不同于逻辑运动的一个概念系列,该概念系列为意识本身奠定基础,而且,按其纯粹的意义,该环节确实必须可以整合到这个概念系列之中;也许,这个总是出现的环节也可能来自于一种完全不同于此前描述的运动,因为描述的方法改变了;而且,该环节恰好处在这个系列之中,这一点首先也并不在于形态展开的节奏中;因为就现象学的一部分而言,这些形态的原则已经有了其他更高的对应;而且在原则向形态的展开过程中,出现了最为不同的规定,在这些规定中,归根到底失去了原则的现实化。在这里,这个在逻辑的东西的进展中正确的环节,应该如何作为意识的自在而产生出来?这个当下的自在,不是从逻辑进展的一个事先设计的模型,简单地纳进了现象学的进展吗?
如果人们考虑到,这个成问题的环节,从属于对显现着的知识的描述的那种关联——被考察的意识本身必须在这种关联中活动,那么,这个问题就更加复杂了。这个环节应该是审查的尺度。也就是说,意识必须能够明智地和为了自我理解而同这个环节打交道,而且意识必须对此有一种至少是内在的明见性:这个相关的环节作为自己的现在的自在 (Ansich)而从属于自己。这一点,对我们而言何以会得到保障?在此,不是形成了一种两难处境吗?或者,一种对应于该逻辑环节的自在,只能通过放弃科学的现象学阐释——当我们以此外在地整理大量的形态时——而提供出来,但是以此方式,至少可以正确地对待在寻求自己的真理的怀疑的意识。或者,形态的序列在理解着的认识中得到组织,而怀疑的意识对此不可能有所参与,因为怀疑的意识并不认为那个明智的环节是它的自在,或者不认为它是自己借以能够进入科学的正确的东西。
被寻找的,是一个普遍的原则,该原则保证了意识的这个自在 (Ansich)在随着第一个阶段而来的每一个阶段上,都由此而具有它的同所属逻辑环节的对应,即由于意识的这个自在也:
a)按照它在理解着的认识中的位置而对应于它的形态的原则;
b)然而仍是一种可以被意识容纳和运用的规定,这种规定
c)必须容纳内在的、为意识的明见性,——按照我们在其中理解这个自在的诸概念。
黑格尔试图由此而满足这些条件:他始终使这个新的自在,不外乎是这样一种方式,在此方式中,意识试图借助于自己的新内容,一并把握意识形态之原则的运动。由此,正如在对方法的先行提醒中所预告的那样,那种对意识而言在之前的形态中变成了单纯为意识的自在 (Für-es-Ansich)的东西——变成了知识的落空的、进入结果之内容的运动——,变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内容的新的自在。这样,例如知觉的自在,便是知觉之对象的自我等同 (Sichselbstgleichheit)。但是这种形式,是变得简单的、我们借助于感性确定性的结果而认识到的运动:于是,也就是逻辑学理解为相互对立的一种颠倒的结果的那种东西。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撇开意识内容和意识对立的规定性,并且仅仅关注于这种运动形式,那么,这种形式也就能够被我们用来阐释一种与逻辑环节相对应的自在,而且这种阐释确实同时是从形态之原则中获得的,尽管形态原则作为意识内容的组成部分,可以把其他逻辑范围的规定包括在自身当中。
但是同时,一个这样的自在,由于它的抽象的简单性而可以容纳在明智的意识当中,而且可以与在形态的要素中被设定的内容——作为明智的意识的对象和知识——相比较。对意识而言,经验的运动不外乎是遵照认知行动的一种确定的格言 (Devise)对这个自在的结构与其他意识内容所做的这类比较,以及不外乎是这样一种尝试:通过对内容上的规定做出替换 (Vertauschen),而产生出这个自在的结构在内容上的可运用性 (Applizierbarkeit),直到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再被替换为止,因为互换是完备的了。由于开始时被设定的内容以及形式的差别,只要这种自在在概念的形式中运动,只要这种意识内容作为本身回复到知识的运动的统一而被意识到,这种尝试便必定终结于矛盾之中。但是,甚至在这个自在变成为意识的自在之前,我们就已经能够把意识的经验,作为这样一种被掩盖的、以及被让渡的 (entäuβert)逻辑经验来理解了,因为知识的运动,在自在的内容方面,不外乎就是这种概念的运动。
这样,对意识而言,说到底也存在着这种内在的明见性,由于这种明见性,意识将新形态的自在,作为这样一种自在加以承认。因为这个新的自在,向来都恰好是意识本身此前曾作为知识之统一的运动。
如果我们还成功地在现象学的章节序列中查明逻辑的诸基本环节——这些逻辑基本环节的系列标志着现象学形成时期黑格尔的逻辑学,那么,下述假定便可以得到辩护了:黑格尔不仅把一种确定的意义同“逻辑诸环节与现象学诸阶段有一种对应”这一断言联系了起来,而且相信在自己著作的阐释中也认真地实现了这种意义。当然,就现象学的方法来看,大多数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解决。此外,还应该附带地表明:在个别章节的开端对这些形态的阐述,还绝不可能遵循跟思辨逻辑学一样的程序,尽管——或者毋宁说因为——这种阐述仅仅“对我们而言”才是可以理解的。与之相反,这种阐述如何具有积极的性质,按照哪些标准来实施,以及这种阐述——尽管它也只是处在思辨逻辑学之可能性的前提下——是否可以被视为可能的,这都是悬而未决的。同样尚未得到探讨的是:这个所谓的可以为意识所理解的经验辩证法的否定过程,具有怎样的必然性?此外,只要逻辑的环节出现于知识的形式中,就有必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它上面。然而,这个谦逊的证明 (黑格尔借助于这个证明的技巧使经验运动同逻辑进展相一致),就已经允许得出一些推论,这些推论对于问题视野和有关辩证法的一种普遍讨论的任务是富有意义的。
1.看起来似乎是:在现象学中,对逻辑的东西的讨论,并不只是、甚至于首先并未涉及到这个问题:对诸形态的科学的阐述——这是我们的附加 (Zutat)——是如何进行和如何得到辩护的。关于这种阐述,人们可以尝试把意识与自己本身进行一种怀疑的沟通这个思想,从逻辑的体系学中孤立开来,但是由此,经验辩证法同逻辑的东西的内在关联并未消失。
2.经验辩证法同逻辑的这种关联,似乎比形态阐述同逻辑的东西所具有的关联更加密切,这种形态阐述不仅用知识及其真理的形式上的差异进行操作,而且必须分离地发展出未曾想到的意识内容。恰好是在我们对显现着的知识的描述最为彻底地放弃理解着的认识的地方,纯粹概念的内在连续性显得最为清楚,而与此同时,按照形态阐述这另外一个方面,由于概念的混淆,这种连续性变得暗淡了。在对显现着的知识的描述中,逻辑的东西越是远离关于自身的知识,它自为地就越是内在的东西;在我们——理解着的认识者——只是旁观的地方,概念也许活动得更加纯粹,尽管我们旁观的对象并不是逻辑的东西本身或它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意识。
3.黑格尔的意图是:不是把意识在其中自我理解的诸结构从外面宣判给意识,而是从对意识的理解出发来阐释出这些结构。人们可以有很好的动机,来怀疑黑格尔式的纯粹概念的目的观念 (Zweckidee)是否允许这样一种程序。但是,在把握 (意识诸结构)的时候,人们将回避不了对于逻辑环节——在黑格尔式的描述程序中含有这个环节——的一种严肃的讨论。为思辨的诸概念——实践意识和每一种有限的意识的定向是在这些思辨概念中自我规划的——作出辩护 (既是一种面对自身的辩护,又是一种面对意识在其中自我理解的方式的辩护)的问题,并不独立于完满中介——在此中介中,逻辑的和绝对的观念应该被带至毫无缝隙的统一——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的问题。——下一章将会提供支持这一见解的一个发展史的证据。
三
应该表明,对显现着的知识的描述具有哪些可能性,使得逻辑诸环节的连续序列出现在意识当中。现在,为了对这一普泛的考察作出补充,还必须对从属于现象学的逻辑学的诸主要环节和意识诸形态的相应的诸规定作出证明。同时,还需要探讨黑格尔的逻辑构想在1804和1807年之间是否有过变化这个问题。所以,一种有关黑格尔的逻辑体系学在这些年间有所发展的假设,便构成了以下论述的起点。
如果人们把 1802/03——或 1804 年①根据基默尔 (H.Kimmerle)以及其他人根据一份字母形式的统计学对耶拿手稿的写作日期所做出的鉴定;参阅《黑格尔—研究》第4卷 (在准备之中)。——的耶拿逻辑学和形而上学与现象学末尾和前言中关于逻辑学所发表的见解进行比较,就会看出:在这期间,黑格尔必须首先在致力于消除他提供给我们的第一种思辨哲学形态的两个基本缺陷:其一,他必须使方法成为对逻辑学的内容而言是如此内在的东西,以至于关于这个内容可以说,它在它自己那里而并不只是在我们的反思中有着自己的运动。与此具有同等意义的,则是这样一个任务:不仅在诸概念对立在其中得到扬弃的总体中给予诸概念对立一种持存,而且使诸概念对立的通过绝对者 (durch Absolute)的扬弃与出自绝对者的起源 (Hervorgehen)相等同。其二,也即作为刚才提及的这一点的条件,是必须消除学科的这种二分:一是以否定为主的辩证逻辑学,二是太少否定的、紧跟着这种逻辑而来的形而上学。根据珀格勒的推测,[6](P305)这一步,在第一部耶拿实在哲学那里,就已经迈出了。——如果为我们所获得的耶拿逻辑学和形而上学,应该是在1804年即在第一部耶拿实在哲学之后才形成的,那么,下面的考虑就与第一部耶拿实在哲学无关了。因为无论第一部耶拿实在哲学跟逻辑学和形而上学在时间上可能有怎样的关系,以及两者之间可能有怎样的实际关联,这两门先行于自然哲学的学科 (指上述辩证逻辑学与形而上学——译者注)之统一为逻辑学或思辨哲学,并不需要立即导致一种完全内在的方法。
这种统一必定会导致哪些结果?在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连接部分,在有关对称 (Proportion)的学说——在其中论述了定义、划分和证明——中,黑格尔使逻辑内容的运动反思自己本身。由此得到的结果是:这个整体的方法,但尤其是形而上学的方法,始终处于从属地位(unterbestimmt),而并未把内容充分置于自己的主导之下。于是,有必要在较晚的地方、并且作为更加差异化的结构,推导出该整体的程序,并产生出一种从确定概念的逻辑学向客体性 (Objektivität)的形而上学的新过渡。现在,对称的诸结构必须在先前的主体性(Subjektivität)的形而上学的关联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有关理论自我 (Ich)的学说正好与此相适合,它由此同时被更好地形式化,而且接近于在纽伦堡逻辑学中构成认识理念的东西。但是,因为认识在这里不再像先前那样能够纷纷避开绝对的原理 (这些原理在它们与他物的关系中保持漠然、不变,即包含较晚的反思结构),而且因为为了思辨认识的方法必须同时发展出一种新的、更加整合的结构,因此,使认识自身对存在于自身之中的这种结构进行反思,即对自我/理解着的概念的自我进行反思,便必定显得是最容易想到的事情。于是,这种方法由此便始终还要面对实践自我的形而上学的内容,这个实践自我,不论是在耶拿实在哲学中,还是在现象学中,都构成了伦理精神的基础。与之相反,先前的形而上学的开端——同一性和与同一性相对的诸概念的根据——便必须容纳进关系逻辑学之中,这个关系逻辑的开端,反正迫切地需要一种修正。
这种改变了的、在上述观点下实现出来的逻辑学构想,在黑格尔那里事实上可以得到证明。在1805/06年第二部耶拿实在哲学的末尾,思辨哲学的内容序列用这些词语得到了说明:“绝对的存在 (Sein),自身别物 (das sich Andres,生成为关系),生命和认识;知晓的 (wissendes)知识,精神,精神关于自身的知识。”[4](P272)
现象学末尾和前言所说的逻辑学是否由此已经得到了说明,这首先依赖于这个问题:可以把知晓的知识理解为什么?如果知晓的知识又被理解为逻辑进展的形式,那么,在现象学的末尾所说的逻辑学,就完全可以同在以上被援引的系列中谈及的逻辑学区别开来。因为现象学的末尾说到了一种自我运动着的逻辑内容。因而必须假定,方法已经被挪到了逻辑学的末尾。也就是说,内容方面的运动,首先不再只是我们理解地认识着的反思的一种必然性,而同时是存在的必然性。[1](P562)自我 (Ich)的形式上的自我等同 (Sichselbstgleichheit)必须挪到后面的位置,并且代替自我,在思维的关系与生命之间,要给予绝对的概念或生命的简单本质[1](P125)一种更加独立的地位,就像上面所引用的系列似乎要做的那样。
现在,如果人们在上述观点下,根据文本的逻辑内容来阅读现象学的文本,则最引人注目的便是:这个逻辑内容,就既不可能跟上面所引用的逻辑的东西的系列有关,也不可能跟明确地被修正的逻辑的东西的系列有关。因为作为诸要素——诸形态在这些要素中具有自己的内容——而出现的是:
I.未规定的定在 (Dasein),在此未规定的定在中这个自我 (Ich dieser)和这个存在着的东西 (das Diese seiende)存在,但是它们的实在性自我证实为否定性。
II.一般的事物性 (Dingheit)或者纯粹的本质,在此本质中,物质和事物共同持存,但是在此纯粹本质之内,尚不能使物质和事物的为他存在 (ihr Sein-für-anderes)和自为存在(Fürsichsein)区分开来。
III.实体与它的显现着的偶性的关系。
IV.有生命的定在。
V.认识着的定在。
VI.精神。
VII.精神的自我意识。
VIII.纯粹概念。
这里所缺乏的,是在第二种假定之后和生命之前有待出现的简单概念。在第三阶段之内,只有规定的概念——对应于它在诸关系的逻辑学中的位置——作为从属于知性的第二阶段的东西而出现。另一方面,纯粹概念处于整个系列的终点。
与之相反,如果人们审视对意识而言是自在的东西的系列,那么,人们在理性中就通向了必须同一种简单的、先行于生命和认识的概念逻辑学的构想相符合的规定:种—属关系在范畴中的简单统一,就像这种统一是直接的那样。因为这个自在 (Ansich)的方式的系列是:
I.存在。
II.自我等同。
III.简单的内在之物,这个内在之物还属于反思的逻辑 (Reflexiongslogik),知性出于上述理由而停留在反思逻辑的阶段上。
IV.关系,①在其论述精神现象学的编排的论文中,珀格勒采纳了有关逻辑环节和精神形态的对应问题 (参阅本卷52及后面各页),这个问题,我在我的书(《在黑格尔的逻辑科学中的一个导论问题》,法兰克福1965,94及后面各页,140及后面各页)中和在此处发表的、1964年在罗要蒙特[Royaumont]阐明的论文中提了出来。他没有忽略这一点:我首次解答这个问题的尝试,遭受着跟1808/09纽伦堡逻辑学的范畴的片面的和保持着某种公式化的关系之苦,在这里,对现象学本身所内含的结构和先行于现象学的逻辑学的发展史的结构的更确切的考察,理应取代纽伦堡逻辑学的位置。然而,在我看来,在关系到现象学的思辨结构时,珀格勒的诘难——这些诘难主要针对由我所断言的逻辑环节与自我意识的诸形态的对应——表现出了一种类似的不清晰性,正如他对现象学迄今为止所做的研究所带有的不清晰性一样。珀格勒搁置了去追问借以能够在逻辑形式和意识形态首先富有意义地谈论一种“对应”的标准。所以,在他看来这是有失体统的:我在这项工作中还声称,对自我意识而言是真实者的那个东西的逻辑的根基,构成了诸关系的逻辑。现象学——珀格勒如此说——在有关颠倒的世界的知性章节的末尾立即进展到生命,与之相反,纽伦堡的意识学说恰好修正了这个要点,并且相应地允许逻辑学走上这条经由力而达到关系范畴的道路。但是,在1808/09年的意识学说的§17中,仅仅是一个诡辩取代了“这个要点”的位置——这个不是区别之物的区别之物,还应该使关于意识跟它的对象的区别失效!——而且,在这个时候,这一点也没有保留下来:海德堡百科全书和对于百科全书§423的附注,重新包含了作为向自我意识的过渡规定 (Übergangsbestimmung)的生命概念。因而它很少支持这一点:在这里显示了逻辑学构想的一种如此原则性的改变或者在著作方面一种如此深远的摇摆,就像珀格勒对一条“笛卡尔主义—康德主义的”道路和一条“亚里士多德主义的”道路的区别理应使人预料的那样。珀格勒的第二个论证是,关系诸范畴不可能紧接着现象和超感性的世界出现,因为意识凭借对立而将它们甩在了后面,这个论证,导致了意识形态之原则和要素方面的逻辑根基,与那种当下的、对于意识而言是真实者的基础的规定的一种混杂,这种对于意识而言是真实者的东西,还作为把握这个真实者的方式而对应于这个真实者。我在上面则试图表明:人们必须把两者区别开来,如果人们想要把一种有秩序的意义与现象学有一种逻辑根基的断言联系起来,并且希望由此而实现一种在我的书中未经中介地同时并存的结构考察 (94及后一页,140及后面各页)的关联的话。具体来说是:
A.独立者 (Selbständiger)的关系。
B.思维的关系,确定的概念、判断和推理。
V.统觉的统一,具体来说是:
A.作为这样的统一,即在直接的矛盾中,把一种双重化的东西、绝对对立的东西断定为本质:统觉的统一和同样的事物。
B.生命的结构;因为现在自我意识在自身(Selbst)和存在 (Sein)之统一的要素中重复了自己的运动,以至于对自我意识来说,在它之中曾经是形态之原则的东西就是自在:自我意识本身就是目的。
C.认识,正如施密茨与耶拿逻辑学相应的对称章节所做的比较所表明的那样。②施密茨 (HSchmitz):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在他的“耶拿逻辑学”中的准备》 (Die Vorbereitung von Hegels,,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in seiner,,Jenenser Logik”)。载 《哲学研究杂志》(Zeitschrift f.philosophische Forschung),14(1960),16及后面各页;参阅22及后面各页。于是,在这里为这种引人注目的结构的同一性给出了解释。
VI.精神。
VII.精神的自我意识。
VIII.纯粹概念。
撇开那些被提到的意见分歧,这个双重模型证明了在现象学过程中逻辑学构想的一种连续性,这种连续性是在讨论这部著作的命运时不应该被忽略的。该双重模型表明:这些通过罗马数字所标记的阶段,是由逻辑的诸基本环节所规定的,如果这些环节是诸原则,同时是意识的诸形态的诸要素的话。更确切地看,该双重模型还表明:不仅是这种划分,而且在这上面对意识所做的设定,也通过作为意识原则而出现的这些基本环节而实现出来了;而且,该双重模型还为此给出了一个理由:这些形态媒介 (Gestaltmedien)从自我意识起还必须再度划分开来,以便在这种对意识而言像是真的东西的方式之内,取得这种在自我意识中预期的意识的统一。这一点发生在精神之中——在公开出版的现象学中,按照一种重复的预期而出现在紧接着有生命的定在的要素中。关于精神,这种模型最终表明:意识必须作为意识形态而达到在导论中所预告的那个地点;它必须破除自己的这种假相,就好像是跟陌生的即仅仅为意识的东西和作为一个他物而存在的东西纠缠在一起似的,或者与此具有同等意义的是:在这个地点,现象必须变得跟本质相同;因为现在,意识在要素本身——意识的知识的内容和意识本身存在于这些要素中——那儿遇到了它的自在,这个自在,就是为了它的意识的意识自身;不过,意识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成为一种还不真实的存在,并不得不用凭借自己的内容而做出它的自在的有差别的经验,直至它的自在以及它的要素是纯粹的概念。仅仅从现在起,对这个自在的描述才不再必须遵循包藏在对意识的描述中的逻辑,而是必须敞开精神以及精神关于自身的知识的未重叠的逻辑结构。
因此,人们必须在更高程度上承认现象学的被公开的形态有一种系统的统一,就像在发展史的考察中迄今为止所揭示的那样。但是此外,如果人们再考虑到黑格尔论述现象学的更早的残篇,并且更确切地考察上述两个被提及的逻辑系列的区别之点,那么,就会显示出新的不协调性。这些不协调性还更明确地支持这一点:在进行现象学的研究工作时,黑格尔的逻辑学构想在这个被提及之点上做了修改。不仅打印在“文献”中的残篇,[7](P353)而且耶拿实在哲学的残篇IV[4](P259)都表明:先行于伦理精神之开端的,是一种成果,在此成果中,达到了主体性在其与自身的关系中的纯粹的自我适应。出自文献的页张把这个成果称作“纯粹思维的纯粹思维”,并且就这种思维而断言,它是自在的或自我等同的实体,而且同样地是意识。从这个结果中走出来的诸形态,具有绝对知识的名称,并且是由此而实现出来的:意识和自在之间的区别重新出现。于是,在这里,导论的末尾说到的现象和本质之间的平衡,也许同时是一种更高逻辑次序的重大转折,是一个交叉范围的结尾和开端,就像在最终的编排中出现的那样。有许多证据都支持这一点:这个结束着的范围,是从自我意识开始的生命和认识的范围,它在纯粹思维的纯粹思维中首先达到了自我意识的完成了的实现。于是,自我意识的运动,也许就并不在不幸的意识那儿即告终止。按照现象学的最高划分,它也许原本被划分为A.意识,B.自我意识,C.绝对知识,而且这个绝对知识又再度分为A.精神,B.宗教,和C.科学。被提到的第二部残篇即具有这个标题,该残篇包括了现象学的最后一章,并且由此也包括了对于先行章节的一份概观。与那份文献的残篇完全一致,第二残篇构造了从自我 (Ich)/自身的自我 (Ich des Selbst)向精神的过渡,这个自我,是它的自为存在与其自身的简单性和等同性,并因此是自在存在;该残篇并且说:自我的这种趋向于精神的运动,从属于自我意识——该残篇将观察的理性归属于这种自我意识。现在,这个明显的、至少是在现象学撰写期间的编排上的改变与上面援引的、与公开出版的现象学的实际进展有所偏离的逻辑系列的一致,使得这一点很有可能,即逻辑学的修改和现象学编排的修改,这两者是同时进行的。因此,这接近于推测:一直到至少是1805年夏天,黑格尔对此都在犹豫:在同一个步骤中推导逻辑的理念和绝对理念,纯粹思辨的东西的运动形式和它的绝对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或许做得不错,尽管对我们来说,要凭借完全调解的批评去做这件事并不容易。
[1]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M].霍夫麦斯特 (v.J.Hoffmeister)编.汉堡,1952.
[2]珀格勒 (O.Pöggeler).对精神现象学的诠释 (Zur Deutung der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J].黑格尔—研究,(1961),1.
[3]黑格尔往来书信 (Briefe von und an Hegel) (第1卷)[M].霍夫麦斯特编.汉堡,1952.
[4]黑格尔.耶拿实在哲学 (Jenenser Realphilosophie)II[M].霍夫麦斯特编.莱比锡,1931.
[5]黑格尔.耶拿逻辑学、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M].拉松(v.G.Lasson)编.莱比锡,1923.
[6]珀格勒.黑格尔的耶拿体系构想 (Hegels Jenaer Systemkonzeption)[A].哲学年鉴 (Philosophisches Jahrbuch)[M].
[7]黑格尔发展文献 (Dokumente zu Hegels Entwicklung)[M].霍夫麦斯特 (v.J.Hoffmeister)编.斯图加特,1936.
B516.35
A
1671-7511(2012)01-0015-14
2011-03-12
汉斯·弗里德里希·富尔达 (Hans Fridrich Fulda),男,海德堡大学哲学教授;舒远招,男,哲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 本文译自:Hegel-Studien,herausgegeben von Friedhelm Nicolin und Otto Pöggeler,Beiheft3.S.75-101.H.Bouvier u.Co.Verlag,Bonn 1966,Printed in Germany.Druck:Georg Hartmann KG,Bonn.本文的全部脚注都是根据原文翻译的,《精神现象学》等著作的引文页码都是德文版的页码。译者的少量注释添加在正文中间。本文把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简称为“现象学”,这一“现象学”与胡塞尔的现象学无关。
■责任编辑/卢云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