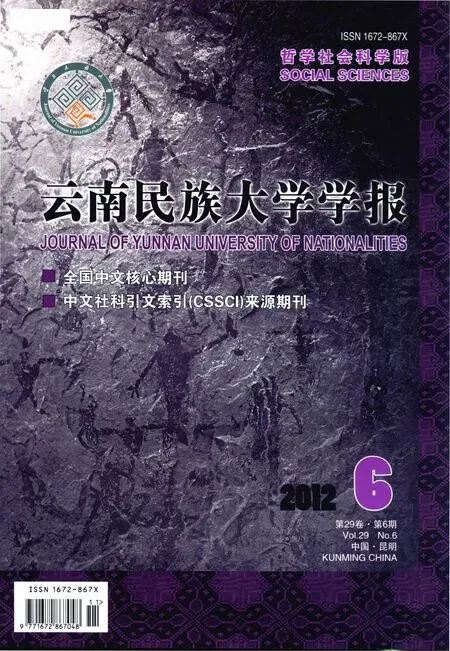清末民初对西双版纳的开发
杨筑慧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100081)
西双版纳地处我国云南省极边之遥,历史上又为烟瘴之地,人们往往视为畏途,故在元代之前,汉文史籍中鲜有对该地的明确记载。从元代至清代,虽然中央王朝在这里设置了土司制度,但其势力并未深入该地,当地的傣族人依然按照原有的民间政治制度管理这一方土地,这种情况直到清朝末年才稍有改变。
一、开发背景
从近代对西双版纳的开发来看,其背景主要与普洱茶的产销和西方殖民者的入侵有密切关系。
普洱茶在西双版纳的种植历史悠久,主要以六大茶山为著。民间曾有“武候遗种”之传说,当地一些民族甚而称诸葛亮为“茶祖”加以供奉。[1](P3)可见早在公元三世纪时,以茶叶为纽带,西双版纳即与内地有联系。唐宋时期,随着吐蕃对茶叶需求量的逐渐增多,茶马古道成为西双版纳与内地、藏区联系的重要纽带。清代檀萃在其《滇海虞衡志·志草木第十一·普茶》中说:“普洱,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普洱古属银生府,则西番之用普茶,已自唐时。”最早记载普洱茶种植的是《蛮书》卷七:“茶出银生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清代是普洱茶销售的重要时期,乾隆年间即因普洱茶质优而被列为“贡茶”。清阮福《普洱茶记》云:“每年备贡者,五斤重团茶,三斤重团茶,一斤重团茶,一两五钱重团茶,又瓶盛芽茶、蕊茶,厘盛茶膏,共八色。”清王朝还在思茅、勐海、易武等地设置官茶局、钱糖茶务军功司等机构,统制茶叶产销和税收。18~19世纪(清雍正末期至光绪初年)的140多年间,普洱茶的销售处于其鼎盛时代,最高年产茶八九万担,一般年份也有五六万担,每年有千余藏族商人前来购茶,茶叶销售甚至到了印度、缅甸、暹罗、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南亚和东南亚国家,每年运茶的马匹不下5万。[2](P225)对此情景,檀萃在《滇海虞衡志》一书中说:普洱茶“出普洱所属六茶山,一曰攸乐,二曰革登,三曰倚邦,四曰莽枝,五曰蛮耑,六曰慢撒。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粮矣。”《新纂云南通志·物产考》载:“普洱茶之名,在华茶中占特殊位置,远非安徽、闽、浙可比。……普茶之可贵,在于采纂雨前,茶素量多,鞣酸量少,回味苦凉,无收涩性,芳香清芬自然,不假熏作,是为他茶所不及耳。普茶每年出产甚多,除本省销用者外,为出口货之大宗。”鉴于普洱茶销售之盛,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即以民办官助之方式,在思茅至茶山 (倚邦、易武)的崎岖山路间,修筑了一条约300华里的茶马道,道宽约1.67米,全用石块铺砌,使茶叶的转运更为畅通。茶叶销售的兴旺又带动了沿路客栈、酒店、食馆、商铺的发展。但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后,由于朝廷不断增加茶捐,加上土官的盘剥,导致茶山人民不断起来反抗,茶叶销售遭到打击。清光绪年间,茶山疾病流行,茶农或死或逃,茶量下降,加之中法战争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所致茶价过低,至宣统年间(1909~1911年),年产仅13000担,茶叶贸易大大衰落,茶庄大部分破产,茶区一派萧条之景,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民国时期。其时,由于战祸、国外交通受阻、国内交通不便、国民党残兵扰乱等原因,西双版纳的茶叶产销急剧衰败,茶农生活凄苦。到1949年,全区茶园残存面积仅31400亩,产量仅6992担,降到了历史最低点。[2]
普洱茶的销售在有清一代及民国初年虽然起起落落,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双版纳地区的开发,尤其是城镇的兴建、商业贸易的发展。
如果说普洱茶的产销所带来的利润是吸引人们前往西双版纳,并在有意与无意间开发了当地的话,西方殖民者的入侵则是引起人们关注边疆的重要原因,并直接促进了政府对这一地区的开发。
新中国成立以前,西双版纳在一定意义上基本由当地土民首领所管辖,即便是元明清三朝在其地设置了土司,中央王朝所实行的仍是“以夷治夷”的间接管理,其势力均未深入西双版纳腹地。但基于对中央王朝和国家的认同,以土司制度为纽带,西双版纳的傣族土司一直视其地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并以纳贡、征调等方式,保持与中央王朝的联系,这种关系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中央王朝才将当地的行政设置作了一些改变。
历史上的西双版纳辖地要比现在广阔得多,据史书载,南宋时期的景陇金殿国辖地“东至老挝,南至景海(泰国清莱),西至南孔(即缅甸境之萨尔温江),北至元江”。[3](P97)元代辖地据《天下郡国利病书》载:“其地东至落恐蛮(今老挝北部),南(应为“西”)至波勒蛮(今缅甸景栋一带),西(应为“南”)至八百媳妇(今泰国北部),北至元江府(包括今普洱、宁洱等地),西北通孟连。”明代,由于与老挝结亲,以及缅甸东吁莽应龙的入侵,部分领地或作为陪嫁送给老挝,或被划归缅甸、老挝,大片领土丧失。[3](P97)清初,西双版纳辖地大致与明末同,虽土司嫁女将一些地方作为陪嫁划出,但大多仍属现中国版图内,如景谷、孟连等。雍正七年(1729年),清朝在十二版纳实行部分改土归流,分车里宣慰使司所辖江内(澜沧江以东)六版纳(思茅、普藤、更小董、勐乌、六大茶山、橄榄坝)置普洱府,隶云南省。其余江外(澜沧江以西)六版纳仍归车里宣慰使司管辖。
西双版纳地处中老、中缅边境地区,历史上边地人民相互往来密切,有的在血缘上还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当地土司也与今老挝、缅甸等地的一些泰人上层有姻亲关系。民国典籍称,“沿边居云南正南方之极边,东南界法越,西南界英缅,西北界澜沧县,北界思茅景谷,东北界宁洱、墨江、元江。东南西三方面,均为英法属地毗连,曲折长至千四百里,东西相距千里,南北相距七百余里,而积十余万方里。有三万八千余百户,计二十万人口,每方里平均不及两人。”[4](P84)1840年鸦片战争后,云南成为英、法殖民者觊觎之地。从1873年到1883年,法国殖民者在不断入侵越南的同时,也将其魔爪伸入中国。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则是法国殖民侵略者处心积虑发动的侵略战争,这场战争遭到了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但中国人民在中法战争的胜利却以腐败的清政府与法国签署不平等条约而成了“不败而败”。1885年6月9日,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巴特纳在天津签署了《越南条款》,承认了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而且还允许法国在云南、广西两省通商、减税和准备设立领事馆等。由此,为法国侵入云南、广西打开了大门。1895年,日本帝国主义通过侵华的中日甲午战争签订了《马关条约》,割占了我国台湾省和辽东半岛。法国以其在强迫日本归还中国辽东半岛中有“功”,公然提出要将西双版纳十二版纳之一的勐乌、乌得作为“补偿”,腐朽、卖国的清政府竟然答应了法国无耻的要求。其时,勐乌、乌得辖地约3000平方公里,132个村寨,6873户,50862人。[3](P364)除勐乌、乌得外,清政府还将磨丁、磨别、磨杏3盐井割让给法国的殖民地——老挝。
对于云南西南边地,在外敌入侵前,并没有受到非常重视,“自光绪十一年英人占据缅甸后,中国对于沿边,以国防关系,始加以重视。”[4](P83)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边疆危机加深,许多仁人志士深感忧虑,纷纷提出各种治策,如民国时期,不少人建议在普思沿边地区修建公路、设建置、开办教育等,视之为治边的重要举措。缪尔纬在《开发普思沿边计划》中指出,设县治是“时势之需要”,也是改进“沿边当务之急也”。[5](P60)对于沿边开发的重要性,李文林从边疆的视角谈到:“沿边之东与法属安南接壤,其南与英属缅甸相连,国防界线,曲折至千四百里之长。江内之江城、六顺、镇墟三县,与法越界,江外之车、五、佛三县,与英缅界。越南地势,似大头而湾长,以眉公河(澜沧江)为界,河之南岸,上为缅甸,界线颇短,下为暹罗,界线甚长。越南北部甚宽,东自广西镇南关起,西至江城县止。越南由沿边江城入
境,至宁洱,思茅,墨江,等处均不下数百里之遥,沿边全境地势,东方南方成钝角,江城镇越为东部钝角,深入于法越地界,东南西三界俱为越土。五福佛海两县地势,成为南部之钝角,深入于英缅地界,东南西三界俱为缅域。缅甸地势,似一斜长三角形,东界越南暹罗,西界印度,正北地方甚宽,较越南北部与我国相连之防线尤长,东自车江起,西至前藏止,边界至今尚多属未定。由车里起至澜沧县南界之南版江止,为已定界。澜沧县之西界上至耿马之上邦恩地方皆属未定界,又由此以至龙陵之尖高山,为已定界,腾冲西部全属未定界。统观云南西南界务,严重复杂,令人望洋兴叹,若中央政府再不从速由划界之根本工作入手,则英人之野心决非止于得片马与江心坡而已。后患无穷,望早防之!”[4](P128~129)他同时还说到了美国教会的入侵为“沿边病入膏肓之隐忧奇祸”。正是基于这样的忧患意识,民国时期的一些仁人志士们提出了种种治边之策。
二、开发的主要措施
西双版纳由于偏处西南边地一隅,加上瘴疠流行和交通状况十分不便,在清末以前与内地交流十分少,汉地移民亦屈指可数。如1951年中央访问团二分团调查,景洪汉族仅有250人,仅占景洪总人口的1.8%[6](P1)。长期以来,西双版纳的少数民族聚居多以单一民族为主的村寨为基本空间,族群内部及族群间的互动则以集市贸易的方式进行。五天一次的集市,人们主要交换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山野货物,以及汉人带来的铁器、针线等,基本目的也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日常生活、生产所需,是一种有限的交换方式,那种以赚取剩余价值为主要目的的交换并不普遍。故而,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极难形成大的市镇,也不会激起人们更多的物质欲望。当然,此种生活方式在外来者看来显得较为“蛮荒”,加之近代以来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从而激发当时一些有志之士保疆卫土的爱国热忱,也促使了当时的中央政府对边地的开发活动。
综观清末民初的西南边地开发措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学校教育的开办或普及、交通的改善、治所的设置、移民垦殖等。如熊光琦在其《开发澜沧江全部与巩固西南国防之两步计划》中谈到:“……滇省由西北以迄东南,数千里边防线内,地广人稀蕴藏至富,又尽人皆知,其有拓殖之价值与必要。是以云南省政府于废道后,复有第一第二两殖边督办之设,意即在谋边事之改进,与边地之开拓也。澜沧已划入第二殖边区,光琦奉令于去冬来官斯土,到任以后,周谘博访,切实考虑,既审知其在地理军事交通经济文化上皆占有重要形胜,足为全国西南锁錀屏蔽,故认为与普通殖边区情形稍别,是宜特别筹计设法,缩短其进化过程,使全部皆得以充分进展。当切就地方现实状况详密规画,拟具革新具体方案,计分两步。第一步,甲,定期建设县治于猛朗 (澜沧县城);乙,修筑直通缅甸与邻县五干路;丙,就边夷实用上施以特种教育;丁,先行开垦猛朗荒地;戊,确定土司地位,变通自治办法。第二步有四,甲,收服未归化野卡;乙,抚绥半归化之驯卡罗黑;丙,变通现行官制,实行分区垦殖;丁,统一地方财政,减轻边民负担。”[7](P15~16)熊光琦还就第二步计划作了详细说明。在文中,他就澜沧的瘴气如何消除谈到:“若论烟瘴,澜沧全县,无处无瘴,远客初来,无人不病,医药两缺,死亡之多,尤属当然。但认真研究,所谓瘴者,天然气候,仅占十之二三,而人事则当占十之七八,盖皆于卫生毫不讲求也。猛朗地方,初设县治何以不闻有瘴,殆兵燹以后,因积尸腐坏,发而成疫。今经数十余年,城社邱墟,毒蛇螫虫,遨游其间,腐草败叶,充塞盈野,兼以河流从未疏通,四山积水挟同各种腐化生物,复滋生种种病菌,到处洋溢奔流而下,饮其水者又安能不病且死?果设治确定,则当选行焚山刈木,芟除蔓草,疏滹河流沟渠,积极开垦荒地,并严格讲求卫生,设备医药,两年以后,人烟既多,瘴毒自除。”[7](P18~19)他的思想,一定程度也代表了当时仁人志士们对西南边地的认识。
1、办教育
教育是民国时期开发西双版纳地区的一项重要举措,当时的官员和学者们多有谈及。如缪尔纬认为,五福县 (后改为南峤)沿边民族复杂,语言不通,文字歧异,办理教育,应循序渐进,因地制宜,“当停科举兴学校时,为鼓励入学起见,对于学生,除发给书籍外,并伙食制服,亦由公家供给,盖人民难与虑始,事当创办,虽縻费亦难避免也。沿边人民不知学校为何物,入学为何事,召集生徒,难于拉夫,欲令其向学,势不能不优其待遇,而经费有限,焉得人人而济之,故欲扩充学校,经济上实有所不能。且边民语言习惯,均为内地不同,不通土语,教授即无所施,此项师资,决非普通师范生所能胜任,求其既谙教法,并通土语者,非优给薪水,决不能得。经费与师资,两受限制,在办学者既已感受困难,而招收学生,又复不易。即令强迫入校,教师对生徒,不惟不能引起其好学之心,并言语之间,亦多隔阂,则旋进旋退,或作或辍,入学数年,毫无效果、此种学校,其何以取得社会之信仰,事当创始,即启人民之轻视,欲其进行无碍,其可得乎?故与其扩充校数,实际无补,不如多筹经费,精选教师。其于学生,亦择其优秀,厚给奖资,使既入学者,有所观感,未入学者,亦见而生羡。庶几办一学校,有一学校之益,收一学生有一学生之用。”[5](P77)
李文林《到普思沿边去》“二十二”“教育”篇中也谈到:“……沿边 (指江外)教育,设治二十余年,尚无何项成绩。”[4](P119)这里的教育即以汉语言文字为主要工具的现代学校教育,在西双版纳地区大致起于柯树勋时期。他鉴于当时西双版纳地区主要通行“缅文”(即傣泐文)而使政令、文告难以通晓的情形,于民国元年 (1912年)在车里设学堂一所,收聪颖子弟三四十人入校诵习汉字,并拟在经费充裕之时,在西双版纳各勐都设立学堂,以普及教育。但直到李文林到车里之时,所见并非学堂,而是“文武圣庙”,即柯氏之祠堂。柯氏执政版纳至民国十五年,却在“百中难找一二识汉字者”。[4](P120)此外,时版纳还有九龙江 (即车里)宣慰司所在地有学校一所,美国教会办的学校一所 (民国二十一年创办,为四年制初小,民国三十一年停办),五福 (后改为南峤)有两所,佛海有一所,共六校八班,多为民国十六年(1927年)以来所办,其中以佛海办学尚可。可见当时版纳的现代学校教育尚处于萌芽时期。
从民国二十年到三十年 (1931~1941年),西双版纳的学校教育得到了初步发展。民国二十年(1931年),镇越县府督促每乡设初小一校,当年,曼秀、麻黑、曼撒、曼腊、曼乃各设一校,每校一班。同年,车里县设县立第一、第二初级小学。民国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 (1932~1934年),车里县新设县立初级小学8所。民国二十五年 (1936年)后,车里、佛海、南峤、宁江、镇越、六顺等省立小学相继设立,各地区还设立一些短期小学。民国三十年 (1941年),象明区新设曼拱小学、蛮砖小学。佛海、南峤、宁江到民国三十年 (1941年)时共有16所小学。[8](P9)1942年,由于日本侵略军的空袭,以及物价上涨、村民逃散等原因,车里、佛海、南峤等地的学校均被迫停办。尽管抗战后胜利后又陆续恢复,但随之而来的内战,时局动荡,学校教育又在1949年时纷纷停办。
从上述可以看到,西双版纳在民国初年的学校教育虽然有一定的发展,但办学状况极不稳定,而且均为初级小学,没有高级中学,同时,办学质量也不尽人意。除了经费困难、师资短缺、时局动荡、书籍文具缺乏等原因外,当地人对学校教育也不重视。如姚荷生在《水摆夷风土记》中所言:“紧接着县政府是关岳廟兼柯氏的生祠,房屋已经破旧,现在稍加修饰,改作省立车里小学的校舍。这座小学当然也是一种装饰门面的东西。因为经费本来很少,而到这千里外的瘴区来做校长的,多少总想捞几文。如此怎能请到好教员呢?而且夷人有他们自己的教育制度,每个男孩子到了七八岁就送到廟里做小和尚,在那里接受着他们需要的教育。当然他们不愿把子弟送进小学,浪费宝贵的时光学习汉文。此外,夷人对于教育有一个特殊的观念,他们叫学生为小兵,认为现在上学,是为了将来给征兵的。而当兵打仗是他们最害怕的事,自然更不肯让子弟进学校了,给政府迫得没有办法时,宁愿出钱和谷子请汉人的小孩子代读,或是把女孩子送去,读了一二年,家长就来要求停学,理由是女儿已大,应该回家谈恋爱了。我们到车里的那一天,正值小学行毕业礼,全校学生在操场里排队,一半以上都是摆夷小姑娘。学校这样办下去,对于开化边民,不但没有帮助,反使他们深得这是一种负担,而引起反感来呢。”[9](P70)1951年4月,中央访问团二分团在镇越调查时曾记载道:“傣族聚居于勐腊、勐捧及勐菕三区的平坝,伪政府于民国二十一、二年间,曾办了一所小学,设一班,强迫头人送子弟入学,许多人不愿去,只好请人代读,每月给十元半开。现在勐捧区筹委刀昇平、勐腊刀龙总叭,都是当时头人雇来读书,后来当了头人的。民国二十二、三年,伪县长李文新在勐腊、尚勇、曼得、勐捧、勐满、勐菕和臼龙等地设立国民学校,都任用伪参谋团的人员为教员,他们多会说傣话,但是作风很坏,有的还暗中进行特务活动,给当地兄弟民族同胞留下很坏的印象。由于解放前国民党政府办教育留下的恶果,以致影响到解放后办学校也是困难重重。目前只有勐捧设初级小学一所,学生40名,教员仅有一人,叫鄷启荣,原籍思茅,经商亏本后流落于此。”[10](P34)
2、修筑道路
交通也是当时对西双版纳开发的重要项目之一。如前所述,西双版纳地处祖国极边,新中国成立前,与内地交往不甚密切,此概由交通不便所致。李拂一在《车里》第五章“交通”中说:“车里——十二版纳地居热带,气候温暖,原野肥沃,有广大无垠之森林,无穷尽之矿藏,至于粮食牲畜,满仓盈野,取之不尽。人民性好和平,爱自由,能互助。惜于交通一道,因循苟且,极不讲求,道途梗阻,荆枳满地,顺至社会文明无由增进,天然财富,莫由开发。民国初,我政府将车里各土司地,分区设治,改置流官,。当局者亦曾注意及此,每年挨户捐收折工银元四角,除建官署而外,即用之于道路交通之整理。顾此项折工,一再提用于军事需要,不能专注力于道路建设事业。以故十二版纳之道路交通,仍无相当基础。”[11]时从车里至思茅需9日之路程。清道光二十五年 (1845年),曾修筑过思茅至易武的石砌驿道,官员、商贾采办采购贡茶,均行此道。不独如此,西双版纳的樟脑、紫梗、木棉以及内地的物质也多以马帮运送的方式行走在该驿道上。但当时西双版纳与境外缅甸、泰国的交通却较与内地为发展。据1951年的一项调查,当时车佛南的“茶叶销路向来是经过境外市场,销往西藏、南洋。占百分之八十五的紧茶,似乎全部经过缅甸、印度再转入西藏。占百分之十五的圆茶经缅甸、泰国,以仰光、曼谷两地为集散地,销南洋、香港,北至土耳其。”[12](P9)有鉴于此,柯树勋曾于民国二年正月与各勐规定章程十二条第三项中以“折工”之法筹款修路,“旧规各勐百姓,均要派夫做工送担,现值创关伊始,一切营建工程,用夫很多。兹定每年每户,只派工两天,又恐人民农忙时耽误耕作,或因路途迟延,往返食费受累,故再酌定,每工一天,准折银二角,一年二工,每户折银四角。随门户捐上纳,缴解总局,由本局长另招工程队代做。……”[13](P127)柯树勋以此法修复了已废的思茅至景洪九龙江大道。缪尔纬在《开发普思沿边计划》中认为,“云南在中国,交通事业,最为落后,普思沿边,又最落后,……”。在他看来,交通不便影响了普思沿边的开发,土地的垦殖,也给外敌的经济入侵埋下伏笔。因而,修路是的一项重要工程,并提出了具体的措施,“修筑土路,胥用民力,路线测勘后,即可以各县同时工作,惟桥梁涵洞,须用工匠,如同时并举,非惟财力不逮,即工匠亦不敷分配,故工程之先后,不能不先为规划,沿边地界,至打洛止,打洛江外,为英属景栋,其道路已可以通行汽车,一入吾境,则荆棘塞途,几于无路可寻,岂地势限之耶?亦缘人力未至耳。土人迷信最深,兴作土功,即可利用其祈福心理,谓修桥筑路,功德最大,得福愈多,彼既有所希冀,工作自愈努力,此为余所曾经试验者也。”[5](P65~66)缪氏认为,当地土人有修桥筑路积功德的观念,可利用此来修筑道路。事实上,在西双版纳傣族地区的车里宣慰司议事庭内,设有监督官召龙纳允专管道路修筑,人们常随农事节令对道路进行整修和维护。按习惯,居住在坝区的傣族人多在每年傣历开门节前 (公历11月底左右)全村出动整修田间及通往寨外的道路,以便于秋收及探亲访友,至次年栽种结束后就不再修路。除此以外,还有祈福积功德、修桥铺路为孩子保平安、以及惩罚犯人修路等方式,故当时西双版纳各勐、各村寨间均有道路相通,但多为一些土路,并不能通行汽车。缪氏之主张,契合了当地的习俗,并以此法修筑了五福至佛海的汽车道。除此法外,缪氏还提出了延用“折工”和发行公债以筹款修筑道路的措施,前者尚有基础,但后者在其任内亦未见实施。
可见,尽管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政府对西双版纳地区的道路建设给予了一定的重视,但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西双版纳仍无一条通往内地的汽车道。
3、移民实边
移民实边屯垦自秦汉以来就被中原王朝视为开疆拓土的重要举措,不过,有清一代,并没有在西双版纳地区进行过系统或持续的移民实边。民国时期,云南地方政府在西南边疆地区积极推行“存土置流”的政策,在保留土司制度的同时,逐步建立了一套自成体系的流官政权,并在景洪修建官署,开设商店,招来商人到车里、勐海、易武经商。为配合流官建政,还采取了鼓励向边疆移民的政策,并有计划地向边疆一些地区移民。如云南地方政府在普思沿边 (西双版纳)、腾龙沿边 (德宏)推行移民殖边活动,逐步以设治局和县取代土司在边地的行政统治权,汉族移民于是进一步渗透到这些地区。1913年,普思沿边行政总局长柯树勋在《治边十二条陈》中提出“召垦”政策,吸引了云南本省及广西、贵州等地汉族纷纷进入西双版纳等地开垦土地、经商、做工。民国时期由于民政户籍部门及田赋税收户籍本残缺不全,有的统计资料并不十分准确,但从中我们仍可看到西双版纳人口变动的基本状况。据统计,1913年,西双版纳所属车里、佛海、勐遮、勐笼、镇越、易武、普文、关房八个行政区估计有3万户,12.2万人,其中居住坝区的傣族约8万人,山区少数民族约2.2万人,汉族居民约500人。民国十八年 (1929年),云南地方政府鉴于沿边地区连接越南、老挝、缅甸,涉外事务繁多,国防关系重要,故在宁洱设立了云南省第二殖边督办公署,辖双江、澜沧、车里、五福、佛海、镇越、宁洱、思茅、六顺、普文、江城等县,滇西南沿边地区汉族人口由是日益增加,大量汉官、商人、教师、手工业者、军队陆续进入西双版纳,使当地人口结构也相应起了变化。据1935年云南省民政厅《云南省户口总调查报告书》的统计,当时车里 (7559户,41159人)、佛海 (5513户,22314人)、南峤 (7166户,25108人)、镇越 (5150户,17604人)、六顺(6634户,31238人)5个县共计 32022户,137423人,其中汉族约有1000人。又据1946年国民政府云南省民政厅统计,时西双版纳傣族有73916人,其中车里 (景洪)23000人、镇越 (勐腊)11899人,南峤 (勐海县勐遮)15000人、佛海 (勐海)12881人、宁江 (勐海勐阿)4800人、六顺 (景洪景勒)2874人、思茅 (景洪普文、象明等)2255人、江城 (江城整董)1227人。[13](P67)至1949年,西双版纳人口增加到20万人,其中坝区傣族10.5万人,山区少数民族约8万人,汉族为5000人,没有形成大的汉族人定居点,且多居于城镇,从事商业贸易。[14](P139~140)同时,囿于西双版纳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移民实边在当时效果并不佳,诚如缪尔纬所言:“云南之西南,沃野千里,半属荒原,垦殖之声,早已甚嚣且尘上,余之到澜沧五福,亦抱垦殖主义者也。招募垦民,经多少周折,仅得百数人。乃未逾年而死者过半,其未死者,亦兔死狐悲,皇皇求去。余虽不以此灰心,惟因交通不便,垦民病死,即无从补充,且粮食价低,垦荒者亦无甚兴趣。故余认为从事垦殖,必先由交通着手,盖供求不相应,则物价之低昂,虽蓍龟不能卜,巧厝不能算也。生计学唯一之危险,为生产过多,现在虽然沿边田土,已垦者不过十分之三,所出粮食,已经供过于求,无从销售,谷贱则病农,农既病矣,谁复肯投资开垦,与之同病?此在交通不便地方,自然之趋势也。既已修筑汽车路,则往来之人,日渐加多,粮食实为最急之需要,且运输既便,则他处之仰给于此,亦正不少,需用既切,招垦自易,所谓垦殖事业,可以求次弟举行矣。”[5](P70)由此可见,移民实边的开发之举,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在西双版纳地区也未达到应有的效果。
4、设治
尽管清雍正七年 (1729年)清政府曾分车里宣慰使司所辖江内 (澜沧江以东)六版纳 (思茅、普藤、更小董、勐乌、六大茶山、橄榄坝)置普洱府,隶云南省,但却并未真正对今西双版纳腹地进行过实质性的统治。因此,设治成为民国初年许多文人志士和地方官员治理西双版纳的主要政策之一。在他们看来,治所设置,一是有一个稳定的地方管理机构,二是可召来外域民众,垦荒拓土,三是可促使城镇发展,四是治理瘴疬,消除危害一方的疾病。故而,柯树勋时代即在车里建立了治所,设置了衙门,作为管理西双版纳地方的中心。而从西双版纳城镇发展史来看,其兴起即与茶叶的贸易、治所的设置密切联系在一起。如景洪城,历史上曾是西双版纳宣慰司署的所在地,民国时的“普思沿边行政总局”公署也设于景洪城,并有商贸小街,称为景德街。与此同时,行政总局还制定了景洪城建设规划之策。据《普思沿边志略》记载,柯树勋为大兴土木,营建城坦、衙门,城外建壕沟 (护城河),还置汉文学堂、卫生机构,架桥筑路,开放市场,建立邮讯等公共设施规划,并亲自测绘制图旧城布局方案。从其图来看,布局功能明确,设有南门、西门,庙祠,房屋、道路及公共设施,集中于澜沧江西南北方向发展,街道为“井”字形道路网络,东西走向布局道路十条,其名为土星、木星、火星、金星、宣化、水星、太阳道;南北走向九条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纬路)。县城十字路中心名为中山路和中正路相交,有滨江、环城路围绕,东西为道,南北为路,规划较为严整。但其任上且直到新中国成立前也未能实现。不过,姚荷生对其评价道:“柯氏统治车里十余年,虽然没有伟大的建树,但也有不可磨灭的功绩。第一他对夷人恩威并用,土司们敬之畏之,像神明一样,不敢轻启兵端,人民才有了喘息的机会。同时,逐渐消除汉夷的界限,汉人移来者日多,为将来十二版纳汉化立一基础。其次是把云南的货币介绍进来,将车里圈入了中国的经济系统。于是车里和内地贸易才逐渐兴盛,而本地特有的富源出产也因此发达起来。”[9](P79)又如勐腊城,1913年,国民政府设普思沿边行政总局第五行政区分局于勐腊,领勐腊土把总及勐捧、勐伴、勐仑、被过4个土便委。民国十六年 (1927年),设置镇越县时,勐腊曾为镇越县的辖区之一。镇越之名,是建县时因其地居极边,界连法越 (法属越南),故定名“镇越”,寓镇守越边之意。
综上所述,西双版纳在唐代已为南诏地方政权所辖,宋代史书中即有与中原王朝往来的记载;元代中央王朝在此设立政治制度,进行间接统治,明代及清代仍延用该法。清末以来,随着茶叶销售的兴旺和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入侵,中央王朝及地方政府开始在西双版纳设立与内地一统的行政管理制度,欲对西双版纳进行直接管理。与此同时,为加强这种管理,还在当地进行教育、设治、改善交通、移民垦殖等活动,使西双版纳地区与内地的交往逐渐增多,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其社会发展状况。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清末民国初年的这种开发,由于中央政府重视程度不够,似有“隔鞋搔痒”之感,同时由于战乱等原因,直到新中国成立前,西双版纳无论在政治制度还是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依然延续着千百年来的状况,从而也使边疆的稳定受到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从现有的行政版图看,我国有2.2万余公里的陆地边境线,与14个国家接壤,陆地边疆线大多远离中心地区,又多居住着少数民族,其文化水平、经济发展、基础设施远较内地滞后,而与国外多个民族的亲缘关系,又使他们的国家认同感时常出现摇摆状态。在当前非传统安全因素占主导地位的情形下,如何管理和建设边疆成为国家稳定、边疆安全、社会和谐建构的重要因素。就此而言,对近现代以来我国边疆问题的研究无疑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1]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缉委员会.基诺族普米族社会历史综合调查[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
[2]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志 (中册)[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3]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志 (上册),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4]李文林.到普思沿边去 (上篇“普思沿边之实况”)[C].云南边地问题研究 (下卷)[M].昆明:云南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出,1923.
[5]缪尔纬.开发普思沿边计划[C].云南边地问题研究(下卷)[M].昆明:云南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出,1923.
[6]刘杰整理.车里县情况,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傣族社会历史调查 (西双版纳之一)[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3.
[7]熊光琦.开发澜沧江全部与巩固西南国防之两步计划[C].云南边地问题研究 (下卷)[M].昆明:云南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出,1923.
[8]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志 (下册)[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9]姚荷生.水摆夷风土记 (第二部“十二版纳见闻录”)[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
[10]高文英.镇越县情况,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傣族社会历史调查 (西双版纳之一)[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3.
[11]李拂一.车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1.
[12]佚名.车佛南茶叶产销简况[C].《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组.傣族社会历史调查 (西双版纳之十)[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7.
[13]宋恩常.西双版纳历代设治[C].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西双版纳傣族社会综合调查(一)[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3.
[14]西双版纳国地经济考察报告[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